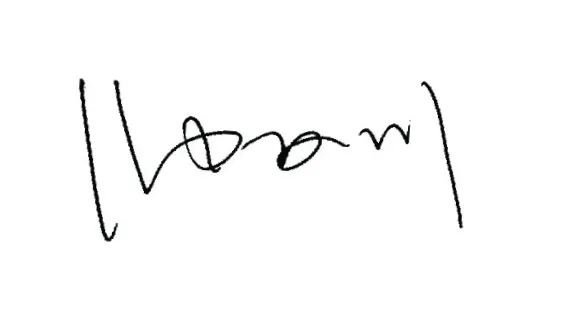“文革”的烙印
“文革”的烙印
我能记事以来最深刻的一段回忆,是3岁时,我躺在床头玩,嘴里念叨着两个领袖的名字:毛泽东,朱德。那是睡前受大人们闲谈的影响。年幼的我把这两个名字当无意识的发音练习,反复在嘴里念叨,最后简略成:毛朱、朱毛,毛朱、朱毛,忍不住联想到乡下孩子常见的毛猪和猪毛,噗嗤一声笑起来。被惊到的父亲一下走到床头,按住我的嘴,警告我说不许瞎念。
父亲没有解释理由,但自此之后,受到惊吓的我再也没念叨过这两个词。
那是1976年的夏天,“文革”在当年10月即宣告结束。这是这场运动对一个孩子所留下的具体而微的影响。
我们是一个八口之家。上有劫后余生的老奶奶,下有五个孩子,父母作为承上启下的家庭支柱,各自背着家庭成分的原罪。父亲是右派兼反革命劳改释放犯,母亲是地主子女。双料“政治贱民“的标签,自然成为家庭孤立于周边社区环境的最大特征。
“文革”中最常见的政治场景是批斗会,父亲自然是批斗台上的常客,不仅如此,被批斗前作为苦力还要负责搭批斗台,批斗完还得和其他一起被批斗的政治贱民拆台,此谓“三台”。如何化解一个父亲在孩子眼里被当众批斗的屈辱和尴尬?他的文人习惯是赋诗自嘲,诸如“人生三台寻常事,休将白发唱黄鸡”之类。
我母亲则极力约束五个孩子,不跟别家孩子发生任何冲突,甚至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她竭力在复杂多变的政治运动中小心翼翼地维系一个家庭的平安。细心的主妇甚至能从过年时我们拜年挣回来的糖果里,判断出各家各户对我们这个家庭亲疏远近的关系调整。
在我四个哥哥姐姐眼里,治保主任与生产队长都是极威风的大官,可以决定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甚至生死存亡。
到了1980年代之后,再回忆起“文革”以及之前的社教四清等,我母亲习惯用一个词来总结那段时光,叫“受打击时”。这个短语用的是和受难者身份很相宜的被动语态,甚至找不到主语,自然就无所谓怨怼与仇恨。老人家也确实语调平和,听不出有多大的哀怨。
这是“文革”对一个家庭的影响,连抱怨都会避免具体的指向,恐惧的记忆早已经融入血液。
想起2013年秋天,父亲撰写的回忆录出版,在长沙开一个读书座谈会。座谈会前一天的半夜,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明天这个会是否要紧,公安局会不会来捉人。
又想起2012年秋天,我在港大新闻传媒研究中心盘桓,父亲也过来小住了几天。钱钢老师请我们父子吃饭,说我俩性格相似,文风也类似,开玩笑说千万不要“满门忠烈”。
编完本期封面,我发了一条微博感叹政治歧视下的家庭环境对下一代人的性格影响。回想起来,虽然不能说乡亲邻居们都是坏人,但在“受打击时”,我们这个大家庭毫无疑问是孤立的,被打量的。清高、洁身自好与小心谨慎、凡事退让这些处世风格就成为父母安身立命的烙印,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五姐弟的集体性格。
这是“文革”对几代人的影响。我希望,能在我和我的女儿这一代之间,彻底斩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