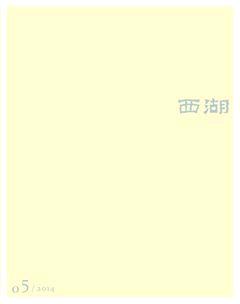随之悲欢的观者和过客(创作谈)
午非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所医学校内,所以有去解剖教室看死人的经历。
孩童的好奇心特别重,特别是对这种非常规事物,更是执着到痴迷。当然,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无法消除的恐惧。这种恐惧,至今无法说清,也许就是关乎命运,及其冥冥中难以挽回的消散。
这种恐惧,在未来的成长中,会被各种类似的事物代偿,却难以消解。尽管,我们随着经历和年龄的增长,不断把自己的人生变得从容,不断淡化理想、爱情及各种黑色的、无法言说的东西,但我知道,那种恐惧依然藏在指尖骨缝,伺机而动。
所以,在我的人生中,我一直都是个小心翼翼的观者。
也许正因如此,我才会成为一个痴迷写故事的人。我理解,这是我对人生恐惧的一种代偿。
可是这真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如果想写得好一点,再好一点。
邵燕祥先生说,置身于母语的长河里,我们有如这源远流长的河水和夹带而下的泥沙。作为被这洪流挟裹的渺小的泥沙,我时常有无力感和退缩心。所以我一直都不勤奋。在北京生活,生存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为了满足自己工作半年发呆半年的习惯和时常出远门旅行的喜好。忘了哪里看过一句话:不要以战术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平庸。可能这算是我平凡人生中一点点不甘平庸的战略。但是大多时候,我只感到自己是两头不靠。
所以,将近六年,六年,我不再写小说。
避此不谈,说说关于行走的意义。在独自游历的那些乡村,城市,栈桥,集市,在陌生的喧嚣和寂静中,在我自己的生活之外,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自己寻找的是什么。直到有一天,在一处飘满落叶的寺庙前,孤独的还乡之心与泪水一起奔流。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行走,只是为了安置我悲伤的出离心。
终有一天,我终将像回家一样,回归自己的心灵,重新去面对所有的记忆和伤痕。其实,这也是写作于我的态势。
或者说,不经过这六年的沉淀和蜕变,我难以回归真正的写作之路。
因为除了真诚和些许天赋,决定你写出什么的,还有对生活真实而深入的感触,对生命冷静而理性的领悟。虽然我还远远不够,但希望是在不断靠近。
在靠近所谓真理的过程中,可能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表达式。舍伍德·安德森在《小城畸人》中写道:起初,这个世界还很年轻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思想,但没有真理这种东西。真理是人自己创造的,每个真理都是众多模糊思想的混合物。世界上到处都是真理,真理都很美丽。 然后,人出现了。每个人出现时都抓着一个真理,有些特别强壮的甚至抓着一打。真理让人变成畸人。
所以,真理有时会被歧义成标准。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和悲悯心,可能我们就是在用标准自省和度人。一位演员说,他是用上帝之心看着自己的角色——如果写作者也能够做到这样的透彻和明晰,这样的出离和慈悲,也许,我们就能离人性的真相更近一点。
当不可避免地走过自传体写作的阶段后,我们终将站到自身之外,用局外人的姿态,去进行理性的创作。这时,你才能真正去研究人物关系与灵魂密码,而不是局限于自己与世人的纠葛。这种姿态或方法,正是我所追求的,努力的,信仰的写作的意义。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能够谈到的,我想谈的,也只有一部《水族》。
在这篇小说里,我用观者的内心,写了一个过客。所以这个过客,应该藏着观者之心。
加缪在《局外人》中有一句话:我们希望不再有罪,也不想对纯洁作努力,我们既无力作恶亦无力为善。——这正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人生状态。
我无意在这样的篇幅和略显荒诞的故事中做道德评判或真理诠释,可能客观呈现才是首要的。我只希望,他们每个人都是有呼吸的。他们是“别人”,却是承载着写作者内心的“别人”,他们的灵魂密码将由作者解读,作者需要了解他们,同时保持清醒的距离。而我并不想将他们与社会剥离,恰恰相反我极力帮助他们融合进去,所以,他们看似是生活的过客,实则为悲欢的世相。只是我不能确定,他们最终会怎样。这是一个将由我和读者一起解答的问题。在这里,不应有任何内心的闪避,我的故事,会默默浮现在我所创造的世界中,而起决定因素的,却始终是这个世界本来的面目。
其实说来说去,我们写的还是人,人性。
故事,不过是人物的血肉和衣表。
也许这正是小说如此让我着迷的原因,因为我们穷尽一生,都在想方设法看清自己,看清别人。
特别喜欢一句佛教语:随喜。“弱性蒙心,随喜赞悦。”这实在好过“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太多太多。其实这个世界再多的悲欢,在佛家看来都是能够合掌言喜的。1909年,林纾先生为日本文学巨匠德富芦花的小说《不如归》作序:“小说之足以动人者,无若男女之情,所以悲欢者,观者亦几随之悲欢。”尽管我不觉得我写的只是男女之情,但还是希望,我是一个随之悲欢的观者,而读它的你不仅仅是随之悲欢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