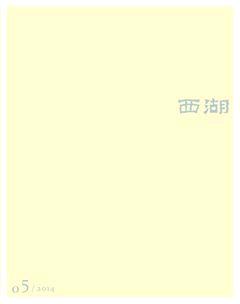汉字动物园:狮?虎
朱孟仪
狮
譬如“般若(bō rě)”,中国式的“智慧”两字既然不能涵盖佛家对宇宙全部秘密的观照,只好自谦(毋宁说是自卑)地将梵语的发音照搬过来,而且还委屈了“般若”两字的读音(读如bān ruò才算“不委屈”)。由于这份文化心理上的自卑(也可能是文化包容的自谦),佛教乘虚而入,经过敬佛—灭佛—敬佛,自卑与自尊交替呈现、三起三落的反复较量,最终与儒、道两家达成和解。握手言欢的结果是,佛家同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对“来世”宏伟愿景的勾画,弥补了儒、道“入世”与“出世”的不足,为中国人现世的进退攻守、三世的因果轮回提供了心理指导。自从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中枢神经以来,大凡意译上捉襟见肘之时(尤其是在翻译梵文时),一般都采取音译的变通。“狮子”就是其中一例。
说来也巧,东汉时期,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土,狮子也大模大样地步入我国。面对这位殊有异相的神兽,中国人一时手足无措,竟然找不到满意的汉字加以标识;情急之下,“师( )”就做了它最初的名称——这也是上古典籍中不见“狮”之踪迹的原因。据说,直到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在太学博士顾野王编撰的《玉篇·犬部》中,才出现了“狮”字。大约是为了区别于“天地君师亲”的“师”,为它加了犬旁归于犬部,以标示狮子虽有佛缘毕竟是兽的类属——此前,《说文解字·虎部》中只有“师”字:“虓,兢,虎鸣也,一曰师子,从虎,九声。”《尔雅· 释兽》中也没有“狮子”,只提到“狻麂,似靛猫,食虎豹”。虽然晋人郭璞在《尔雅注》中固执地认为,狻麂“即师子也,出西域”,但没有更多文献证据——狮子的确来得有些迟。
所以,狮子虽号称百兽之长,但在汉字系统中,地位却很低。有关龙虎的成语俗语比比皆是,而关于“狮子”仅有“河东狮吼”、“狮子大开口”等可怜的几条。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龙、虎既然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有着理不清的瓜葛,在语言中表现出来当然就非常出色;而狮子是外来的动物,又与佛教相关,它既不像龙那样见首不见尾弥散于无限想象的空间,也不像虎那样虎虎生威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因此,狮子在语言中出头露面的就很少。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虽说狮子不见于中国上古典籍,“遣词造句”(更别说造字了)的能力表现一般,但因沾了佛光,狮子初来乍到就以“老师”的面目傲然地出现在华夏文化语境中,这是动物中唯一被中国人认可的“老师”。这位经印度或西域中转、来自西方的神兽,大约真的自以为是全体动物的老师了,尤其是一头叫斯芬克斯的哲学狮子,曾经不厌其烦地盘问每一个过路人:“有一种动物,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这是什么东西?”老实说,这种关系到人的属性的屈原式“天问”(或高庚式的大哉问),只有长胡子的狮子才想得出。不像独霸山林的老虎从不装模作样——“山大王”摆出的理由一般都很直白: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正因为此,“哲学家”狮子在近现代中国遂成为思想启蒙的动物喻体,寄托着中国人的殷切期望。
比如,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曾把他在江西创办的“幼师”称作“幼狮”(我国第一所公立幼儿师范学校,成立于1940年)。在“幼师”与“幼狮”之间,陈先生有意识地建立了个“超级链接”,却无意间消解了“师子”初来中国时因找不到合适汉字来标识它的尴尬。据说,陈鹤琴当年设计了一只可爱的小狮子形象作为幼师的校徽,还成立了“醒狮团”,要求每个学生立志成为一只睡醒的狮子。每当学校集会,大家都齐唱《醒狮歌》:“醒呀!醒呀!醒!大家一起醒。醒呀!醒呀!醒!唤起中国魂。”陈的上虞同乡、作家谷斯范回忆说:“陈校长常常谈起拿破仑的名言:‘东方有个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撼世界。鼓励同学们要有狮子的搏斗精神,改造环境,服务社会,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陈校长所说的“狮子”,经历了自东汉以降漫长的沉睡期以后,突然吼声大作,铆足了劲闯进近代中国人的视野。
1900年,清末教育家、诗人丘逢甲曾赋诗一首:“神州莽莽将陆沉,诸天应下金仙哭。谓佛不灵佛傥灵,睡狮一吼狞而醒。”
1903年,“诗界革命”先驱黄遵宪写道:“散作枪炮声,能无惊睡狮?睡狮果惊起,牙爪将何为?”同年,“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革命军》中叹道:“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也有“猛狮睡,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的句子。这一年的3月29日,高燮发表了《醒狮歌》:“斯时狮睡睡正熟,锯牙不露阖其目。……呜呼!岂有巨物庞然称兽王,含羞忍辱气不扬。”
1904年初,蒋观云也写了一首《醒狮歌》,发表在梁启超担任主编的《新民丛报》上,歌曰:“狮兮,狮兮/尔前程兮万里,尔后福兮穰穰/吾不惜敝万舌、茧千指/为汝一歌而再歌兮/愿见尔之一日复为威名扬志气兮/慰余百年之望眼/消百结之愁肠。”
1904年烟雨4月,由革命团体上海作新社出版的《教育必用学生歌》,其中收录《醒狮歌》两篇、《醒国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
1905年,《醒狮》杂志在东京创刊。
1906年5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连载陈天华的未竟遗著《狮子吼》,时人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
抗战期间,著名高僧巨赞法师在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宣扬抗战救亡,在佛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
从上世纪初开始,仿佛禅师忽作狮子吼,一声棒喝,令意障神迷的中国知识界菩提自现、立登般若,狮子一时成为顿悟者普遍乐于接受的象征性符号。也因此,拿破仑关于中国睡狮的名言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然而,“常识”常常是思维的盲区。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国人不用自己的动物形象(比如龙虎凤麟等)来描述民族复兴,说明中国人缺乏自我号召的力量,似乎只有诸如拿破仑和长一张狮子脸的马克思等受尊敬的西方人的观点,才是靠谱的。另一位名叫费约翰的美国学者认为,拿破仑的预言完全是中国人的杜撰。费约翰说,一些英法学者曾经彻底翻检过与拿破仑相关的原始资料,发现“无论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一手资料,都没有记载拿破仑曾经说过这句话”。如果说醒狮的“棒喝”令人警醒的话,那么美国人的这一通“棒喝”却将中国人一棒子砸晕,为此学术界不得不另寻“睡狮”的发明人。直到有人站出来说“睡狮”的形象是梁启超于1899 年提出来的,才让中国人稍许安慰。一位日本学者前些年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上的文章证实了这一点(《石川祯浩:晚清“睡狮”形象探源》)。而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自由书·动物谈》中,把“睡狮”的专利权推让给了曾纪泽。费约翰也建议将“唤醒中国论”的发明权,归还给曾国藩的长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自此,狮子由文化心理领域进入学术争鸣的前沿。从考据上看,也许费约翰的话是对的。但是,梁启超在“睡狮”形象的推广和传播中,无疑起到了统领作用。
或许,正因为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无可匹敌的语言魅力和学界公认的号召力,使得意欲唤醒睡狮、甚至要以醒狮作为未来的国旗、国歌形象的观点,逐渐成为清末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理念。撇开梁启超的传播,假如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狮子绵延起伏的意象连缀起来,不难发现在动物中,狮子赢得普遍好感的原因是这样的:
一、在西方漫画中,清廷那条腾飞的黄龙被描述为拖着“猪尾巴(pigtail)”的劣兽,已是昏聩的象征;近代精英对这条东鳞西爪的可怜虫,早已深恶痛绝。闻一多在《龙凤》一文中认为,如果非要给这个民族选定一个象征性图腾的话,“那就还是狮子罢,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罢,如果它不再太贪睡的话”。
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东鳞西爪的龙既然是封建帝王的专属,离百姓太远(龙过于专断);虎产于中国,离中国人又太近(容易露丑);而狮子虽是凶兽,却不产于中国,对中国人没有切身的威胁——中国人不曾有一例被狮子吃掉的记录。狮子以真理为上,是勇猛的象征,兼有佛光的笼罩,是护法护身的瑞祥之物。
三、德谟克里特说:动物中只有狮子是睁着眼出生的,所以狮子才如此勇猛,一生下来就证明了自己的高贵。勇猛而高贵的狮子又与“筛子”同音,符合中国“精英教育观”,从八股取士到国考取士,天朝一贯坚持“筛”选法遴选英才(“筛”是“师”参与造字的少数案例之一);况且,狮子是群居动物,奉行集体主义的原则,不像老虎独来独往,无组织没纪律,难于驾驭。至于凤凰麒麟羔羊骆驼之类,又太清高孤傲、仁慈柔弱,尤其是麟凤不食人间烟火、缺乏群众基础,不足以领导国人集体抗辱。
四、在鲁迅看来,骆驼的头酷似羊头,驯服的羊只会率领羊群赴死;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精神三变”里认为,骆驼与狮子的差别在于:骆驼必须听从他人的指导、接受他人的命令,说的是“你要我如何!”;而狮子则是自己做决定、对自己负责,说的是“我要如何!”,“为了获得自身自由和神圣的说‘不的权利……为了这一切,弟兄们,必须成为狮子”。
总之,“借他人之酒杯,浇我心中之块垒”是中国人一贯的智慧——狮子可以不产于中国,但可以在中国得到虚化、神化、理想化、符号化,以至于能够以“他者”的身份代中国人说话,成为中国文化的新载体。这是一头理念的狮子,一头代表中国力量的新狮子,而且这一形象符号暗含了传统文化中狮吼的号召性。于是,睡狮——醒狮——狮吼,作为同一主体的三种状态,用来指称同一主体——中华民族。
佛教用语中早就有“狮吼”一说。据说,狮子吼则百兽惊。在印度,狮吼意指“如来正声”,比喻真理的威严。但是在中国古代,狮子及其与生俱来的伟大声响并不招人待见。大文豪苏东坡曾以“狮吼”一词调侃惧内的好友陈慥:“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个说法,后来被南宋文学家洪迈写进《容斋随笔》,用来比喻悍妇,这一比喻一直沿用至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份文化自信,自夏商周三代经汉唐宋明延至清朝中叶,还是信心满当当的。他们以世界中心自居,号称“中国”,唯我独尊,视一切“他者”为番夷,如此骄傲了数千年之久。然而,数千年既没有换种也没有换地的农业文明毕竟敌不过强大的工业文明;当西方开启的近、现代化风潮席卷全球时,船坚炮利下令人痛心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近代史,给中国人添了一份堵,一份痛。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经历了最初的东西方文化冲撞、文明冲突,在文化反省中,中国近代知识界试图走出迷茫,他们放眼西洋、东洋,在空间坐标上树立学习的榜样,却在时间坐标上竭尽所能地指责、否定传统文化。直到1918年底,从欧洲考察回国的梁启超,了解到西方社会的问题和弊端,主张光大传统文化;梁启超们在经历了自满、自足到失落、回归的曲折心理过程之后,通过审视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及“西洋文化”优劣,终于在空间和时间的双向“他者”坐标下,对中国现实和未来有了独立的判断。可是,这样的声音,已经被“新文化运动”精英集体浮躁的喧嚣声所掩盖。
在狮子的崇拜热潮中,我的本家朱执信先生说:“一个国对一个国,一个人对一个人,要互助,要相爱;不要侵略,不要使人怕;要做人,不要做狮子。既然从苔藓起进化成一个人,便有人的知识,有两不相侵两不相畏的坦途。在这个时代,还要说我是狮子,那就同变老虎去吃亲哥的公牛哀一样。好说,也是梦还没有醒。”朱执信不是狮子,但他发出的声音似乎比狮吼更令人警醒。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写道:“假如狮子能言,我们无法听懂。”智慧的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民族文化的自足与自觉。所以,当美国学者亨廷顿以“文明冲突论”来解释“冷战”后世界走向时,费孝通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形象地阐明了东方式的文化观。亨廷顿讲冲突,代表的是西方以力服人的文化观;费孝通讲和合,乐观中透着中国文化的自信。有了这份自信,我们或许从此不再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也不会妄自尊大、盲目排外。
虎
有没有见到老虎而不必心生畏惧的情况呢?当然有。比如,如果你看见的是一只失了虎威的虎,锁在虎牢关的虎,圈在动物园里的虎,不仅不必畏惧,甚至可以无动于衷。因为,这是一只与数百万年进化史无关,与原始生态场景、巫术占卜、图腾崇拜无关的虎。它们褪去了神秘魔幻的纹理,不过是野生动物园里的一个活标本,远不如一只鲜活的猫可爱;它们“被选择”做了猴子的邻居,却还不如猴子能赚来更多的甜点、香蕉和看客。
好在当代作家张抗抗为当下的老虎补充了丰富的历史背景与鲜活的人文内涵,于是老虎立刻生动起来、威风起来、肃穆起来。她说:
老虎之美,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震慑性,看一眼就会被俘获、被征服。那一刻我会忘记它原本是一头凶猛的野兽……它雄健优美的体态与斑斓鲜艳的毛色、独处的尊严与高傲的神态、端庄的品相与丰富的个性,历经了大自然500万年雨雪风霜的锤炼,才孕育演化而成,并如同雄奇的雪峰和美丽的冰川那般不可再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老虎这种动物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一定负有神圣的使命——向人类展示大型野生动物的雄浑之美、无敌的力量之美。在我们有幸远眺它的那些时刻,它通常只是旁若无人地静卧或是目空一切地踱步,即便它什么也不说不做,仅仅只是一种壮硕伟岸的存在,那也已经足够。
坦率地说,这是我读过的作家中写虎写得最饱满的一段文字。文笔细腻且张力十足的张抗抗,毫不吝啬地将美丽而富有尊严的词奉献给了她热爱的老虎,以至于其他写虎的文字都面临“词穷”的囧态。当然,作家“远眺”或“看一眼”的“这”一只,不见得是景阳冈吊睛白额的“那”一只——在没有性命之虞(注意,“虞”字中有“虎”出没)的情境下,作家与武松的区别在于,作家可以“忘记它原本是头凶猛的野兽”,只管从容铺纸研墨,将溢美之词悉数呈现,而不必像武松那样手提哨棒,靠大碗喝酒来壮胆。因为,如今能进入我们视线的老虎,不过是动物园里的大猫,不可能是作家白桦当真看到的“那一只”(白桦在《一瞥》中说“我只见过一只老虎”),并不代表老虎家族在武松时代的真相。不擅辞令的人看到的老虎不过是动物之一,擅长辞令的人看到的老虎却又很难是山野中的老虎;既擅辞令又见过真的老虎,这种情况就非常稀缺了,所以白桦说:
动物园里的老虎能算是老虎吗?不是它们被关在笼子里,就是我们被关在汽车里。我和它们之间隔着钢铁栅栏或是玻璃,隔着戒备,隔着误解,敌视着。那些虎的皮毛失去了锦缎般的光泽,像枯黄的干草。眼睛失去了光芒,充满倦怠和怯懦。体态猥琐,步履犹疑,它们哪里是真正意义上的老虎呢?它们比猫还要卑微。(白桦:《一瞥》,摘自《与生灵共舞》。)
从造字本义上看,所有动物中,恰恰唯老虎最令古人恐惧,这种恐惧甚至沉淀为列维·布留尔所说的人类的“集体表象”,潜入先民的意识底层,不时制造恐怖梦境。在殷墟出土的中国最古老的书写体系里,“虎”( )的模样让我们瞬间联想到嘴上长有獠牙、身上绘有花纹、张着血盆大口的猛兽。晚期甲骨文“ ”和早期的金文“ ”,虽略去兽身上的纹理,但形象依然阴森可怖。接近隶楷形制的石鼓文“ ”,兽头( )的下面冒出了一个人( )字形——这种半人( )半兽( )的构成模式(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吉萨高地的狮身人面兽),表明体格巨大的猫科动物掌控有对人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是狩猎时期“人”的最大威胁。
在我国古代神话版图上,虎正巧是主司西天的神,象征肃杀、寒冷与萧条。作家徐来在《想象中的动物》一书中说到:“传说虎只在立秋这个节气才会发出真正的虎啸,也只有在虎啸发出之后,寒季才能降临世间。”虎啸催生了恐惧,恐惧挟持了崇拜,原始先民(尤其是山民)由此对虎不得不奉若神明,并模拟其形态、仿效其吼声,创造了声色俱厉的“虎”字(最有益的模拟是华佗创制的“五禽戏”)。汉字中凡由“虎”构成的字,大多与虎的形态、啸叫和特征有关。例如,“虞舜”的虞字,从“虍”的名号背后隐约透露着远古图腾崇拜的遗迹。古文字学家叶玉森认为:“虞乃掌田猎之官,狩猎时披虎首以震慑群兽。”浙江绍兴有上虞古地名,郦道元《水经注》的引文中说:“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乐,故曰上虞。”由此可知,虞还有祭祀娱神唯恐不周的意思。再如,“呼號(号)”的“號”,则由号与虎两字会意而成,表示猛虎的咆哮,令人不寒而栗,大有秋风扫落叶之势。
孔子仿佛聆听过虎的咆哮,甚或在周游列国的半道上遇见过老虎。因此,《论语》中三次提到的虎均指现实中的虎,而不是城市动物园中的虎。《礼记·檀弓下》感喟的“苛政猛于虎”,表明了虎害和虎患的严重性。春秋时期,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老百姓不堪重负,举家逃到深山老林,宁可生活在有猛虎威胁的环境中,也不愿生活在暴政之下——残酷压榨人民的政策,原来比老虎还要凶恶暴虐。同时代的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曾两次提到虎。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人称老聃。彝族学者刘尧汉认为“老聃”是彝语“虎头”的意思,“老子取此名,可能表示他自己是虎年或虎日这个祥年吉日所生”;据说,同为楚人的屈原也以生于寅月寅日而自豪。有专家考证说,“李耳”就是黑虎、雌虎,老子的哲学中也有“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的辩证法思想。虎的威力甚至影响到了天庭,反映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古人之所以称二十八宿为“四象”,乃因东南西北各有七宿,每七宿联系起来很像一种动物。东方七宿连起来就像一条腾飞的龙;因东方属木,木为青色,于是古人称东方七宿为“青龙”。西方七宿连起来像一只跨步向前的猛虎;因西方属金,金为白色,古人故称西方七宿为“白虎”。“四象”作为四方的代名词,在先秦《礼记》中已有记载:“行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
《说文》:“虐,残也。从虍爪人,虎足反爪人也。”文字学者认为,虎的暴力、肃杀意象存留在“虐”字中。甲骨文虐( )是一个会意字,右边是一个虎形,左边是一个人字,两字形会意,表示虎抓人欲噬的意思。小篆的虐字,在虎口之下,有十分清晰的虎爪和一个爬行的小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风俗通义·祀典》说:“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虐字源于老虎用大口利齿残害生灵。因此,虐的本义为残暴、侵害,如“虐杀”、“虐待”、“暴虐”、“虐政”等词中皆包含有此意。上古时代,商代的最后一个统治者纣是鱼肉人民的暴君,遂有“助纣为虐”的成语。
许慎试图对“虎”的暴虐倾向做出解释。五经博士认为,在汉代,人们把虎称为“山兽之君”,意思是说,所有隐居在山林的哺乳动物都得对虎山呼“万岁”,将肉体奉献给它。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动物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在老虎面前俯首称臣,是因为老虎的暴君形象并不像龙那样恍恍惚惚若隐若现、见首不见尾,而是照实(倘用“明目张胆”一词,则显然是对老虎的蔑视)在额头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汉字——“王”。当然,虎额上的“王”,不过是老虎“王道”的外在标签,而真正起威慑作用的据说是神秘的“虎威”。古人所说的“虎威”,不是指虎的威严或威风,而是指虎身上的一块骨头。直到隋唐之际,民间还认为这是一块神奇的骨头。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有相关记述:“虎威如乙字,长一寸,在胁两旁皮内,尾端亦有之。”小说《儿女英雄传》第31回对“虎威”做了通俗的解释:“大凡是个虎,胸前便有一块骨头,形如乙字,叫做虎威,佩在身上,专能避一切邪物。”虎威既然如此神奇,老虎也因此从恐怖分子转身,化为传统文化特别看重的能消灾避害的符号,这些观念遗存于民间戴虎头帽、穿虎头鞋、枕虎形枕的习俗中。
古书上说:“毛虫三百六十而麟为之长。”意思是说麒麟曾管理360种兽类,是一切陆生哺乳动物的君主。儒家主张施仁政,而麒麟恰恰是仁兽,所以虎的君主地位有僭越麒麟的嫌疑,这让儒家很不乐意。儒道双修的东晋学者郭璞尝试调和这一矛盾,在注释《山海经》时,他认为麒麟的性格过于仁慈柔弱,无法有效管理弱肉强食的兽性世界。天帝获悉人间的纷争后,果断赋予了虎许多神性与特权,以平息这场诉讼。譬如,让虎成为唯一懂卦象的动物,它们画地做卦,卜算理想的猎食方向,一算一个准。徐来在《想象中的动物》中提到了周文王的这位动物粉丝。他还说,虎会趁夜色出巡,左眼化为灯盏,右眼搜索领地。如果猎人射出一箭惊扰了虎王,那光芒就会掉在地上。第二天去原地挖掘三五尺,就可以看到被称为“琥珀”的白色石头。
然而,老虎作为“山兽之君”的威风和地位,不久就被“龙”所取代。东北师大汪玢玲在《中国虎文化研究》一文中为此愤愤不平地说,与“龙文化”处于中华民族文化核心地位相比,“虎文化”的应有地位长期被忽视。1988年在河南“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蚌塑龙虎图形,被称为“天下第一龙虎”。虎在墓主人之左,龙在右,表明在原始氏族晚期的信仰中,龙虎文化同时存在,且虎的地位高于龙,虎崇拜曾盛行一时。在那个人神混杂尚未祛魅的蛮荒时代,原始人还没来得及把自己跟动物区分开来,他们以为人的生死均拜老虎所赐——在古代各民族神话传说中,老虎经常被视为开天辟地之神、人类繁衍生息之祖——“天开子(鼠),地辟丑(牛),人生寅(虎)。”彝族史诗《梅葛》说,天地日月、风雨雷电的生成,无不化生于虎。因此,他们对老虎顶礼膜拜,以求得到宽恕,这就形成了崇拜虎的原始宗教。
由于早熟的中国出乎老虎意料提前进入农耕社会,中国的神话格局随之发生嬗变。因为虎图腾取材于原生动物,是狩猎时期的图腾;而“龙”能兴云布雨,正是农业社会所必需的“偶像”。因此,漫长的农业文明扶正了龙的尊长地位。相反,与狩猎文化相关的虎,在封建文化语境下只能为臣,不可为君,这种局面统御中国长达数千年。数千年来,屈尊第二位的老虎也曾几度向龙挑战,于是华夏大地龙争虎斗、血沃千里。然而,偌大个中国,龙椅只有一张,不是虎踞就是龙盘。所以,坐龙椅的永远是龙,坐虎皮椅的非匪即寇。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一头卷发的狮子也跨进中国大门,成为虎的另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形成龙虎狮三足鼎立的超稳定的三角形结构。由于佛祖释迦牟尼被喻为“人中狮子”,因此狮子作为佛的化身,在佛教中享有着崇高的地位。相传,狮子还是文殊菩萨的坐骑,这让狮子更加春风得意,充满神秘色彩。狮子在佛教中的地位,直接影响到中国人对狮子的态度。狮子外貌威严,天生异相,毛发纷披,吼一声檐上瓦片儿就得纷纷落地。据说中国官员见状后赶紧拥戴新的“兽王”,把老虎头上的王冠撸下来给它戴上,还不惜动用文人编排出“狮子吃老虎”的神话。以下是相关神话的摘抄:
北魏《洛阳伽蓝记》说:“虎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唐朝虞世南作《狮子赋》称其为“拉虎吞貔,裂犀分象”,宋人罗愿在《尔雅翼》中说:“其为物最猛,虎豹犹畏之。”《本草纲目》说得更有点离奇:“狮子出西域诸国,目光如电,声吼如雳,……虽死后,虎豹不敢食其肉,蝇不敢集其尾。”明代夏言《狮子诗》称:“怒慑熊罴威凛凛,雄驱虎豹气英英。”孔尚任也跟着起哄,在《桃花扇》第27出中用了“狮威胜虎”的喻词。
虽说上述所引文献并非正史,不足取信,但古人对狮子猛于虎的认识,看来是真实不虚的。到了现代,在狮子与老虎谁厉害的问题上,形成意见相左的两派:西方人认为狮子勇猛,东方人认为老虎威风,双方一时争执不下。其中比较公允的评价是:狮子是战略家,老虎是战术家。战略家吃饱了就睡,养精蓄锐,世称“睡狮”;战术家刻苦练功,除了攀援上树这种有失身份的逃生本领缺失以外(没学成上树,并非猫狡猾,实为虎傲慢),虎谙熟各式摸爬滚打的技巧,还会游泳,有不耻下问向猫学艺的儒家风度。西方人认为狮子具有国际眼光、普世情怀,他们从西向东一路征战,甚至通过白令陆桥进入美洲腹地,行走的区域遍布全球;东方人认为老虎有乡土意识、本位观念,虽然它们也曾由东向西迁徙,但始终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害得欧洲人在翻译中国典籍时遇到“老虎”一词,只好用“狮子”替代。老实说,撇开东西方的不同见解,如果硬逼着狮子和老虎在中国决一死战的话,那么打群架,老虎肯定斗不过狮子,因为狮子是群居动物,有团队意识;一对一单挑,狮子又不是老虎的对手,因为老虎占主场之利,生活在东亚已有数百万年历史,又善独处,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擅长在非洲广袤草原上大兵团作战的狮子,常常会水土不服。双方沙盘演练持续了许多年以后,最终打成平局:老虎高卧中堂,占据了官衙;狮子扼守门户,做了门童——世上两种最大、最凶猛的猫科动物在中国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他们认为“你好我好哥俩好”才是真的好,甚至有一只多情的狮子在与母老虎多年的相处中令她暗结珠胎,喜诞天下无敌的杂交兽二代,名曰“狮虎兽”。还有一部分狮子,看不惯贾府丑陋勾当,厌倦了官场争斗,不务正业地爱上了文艺:他们抖擞精神,披散一肩长发(真把自己当艺术家了),终生与绣球、彩带、戏狮人、威风锣鼓打交道。至于老虎,依然稳坐白虎堂,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怒目圆睁,时刻准备吃人。
元末明初小说家施耐庵看不惯老虎这副德行,认为时刻准备被吃的人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于是,他从民间收罗了一批龙虎山上释放出来的恶魔,托意为民代言,即所谓“替天行道”。其中,有误闯“白虎堂”的老虎的近亲豹子头林冲,以及其他四位与林冲比肩的“五虎上将”和一干人马共计108人。施氏笔走龙蛇,听任各种“老虎”出没于《水浒传》的章回间:武松打虎,扣人心弦;李逵杀虎,动人心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啸聚水泊不满“苛政”的好汉们,基本上都是些不服软或被逼、铤而走险的极端分子。梁山水陆头领除了“五虎将”、“八骠骑”被冠以“虎威”头牌以外,还有不少二把刀的好汉、其绰号中也带“虎”字,如“插翅虎”、“锦毛虎”、“矮脚虎”、“跳涧虎”、“花项虎”、“中箭虎”、“笑面虎”、“青眼虎”等。然而,虽说兵多将广,施氏毕竟是辞官的一介文人,他挑战虎威的理想也不过是想弄张虎皮椅坐坐,心中压根不敢觊觎龙椅,这一点他不如笔下的杀虎者黑旋风。
学者们认为,国人对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敬畏、崇拜、模仿利用,到规避、捕杀,再到珍惜、保护的漫长演变过程。所以,崇拜风习一过,一时间打虎成为时尚。民间的打虎、射虎、猎虎在今天虽属违法,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却反映了人类保护自己免受虎害的自救心理。因此,老虎虽然威武暴虐,但民间也不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猛人。暴虐的“老虎”奈何不得“人多势众”,终于威风扫地、老态龙钟地退缩到人类划定的保护区颐养天年、供人瞻仰去了。因此,白桦在《一瞥》中十分感慨地说:“没有自由的生存环境,任何生物都会失去自己,被迫异化为另外的东西。在那一瞥之后,我再也没看见过老虎了。但,这已经足够了!任何时候我都可以用那千金一瞥,去鉴定物体的真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