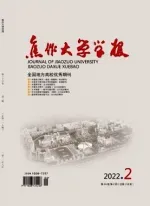徽州区域的社会文化解读——以古村落为中心
张立志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00)
徽州古村落是徽州社会文化的物质呈现,是徽州区域的社会文化遗存。作为徽州区域社会文化的载体,徽州古村落承载着历史时期社会世俗文化等内容,是徽州区域文化的见证和诠释,诸如村落的设计以及布局等理念,体现了徽州村落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历史性,是对徽州社会文化进行研究的重要内容。
1. 宗族文化
徽州古村落一般以血缘关系而凝结,形成“聚族而居,不杂他姓”状态,显示出徽州区域较为发达的宗族文化意象。而宗祠则是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并具有精神上的凝聚力和神圣性。与一般的民居相比,宗祠营造往往气势宏伟且醒目突出,并按照左宗右族的传统礼制格局进行布局。若宗族举行重大活动,宗族成员依宗祠而“日夕居止,拜起坐立,凶吉燕集”,宗祠显然成为徽州区域居民生活及宗族文化的重要纽带。众多宗祠遍布徽州古村落,成为徽州区域村落社会文化的典型特征,反映出徽州区域浓厚的宗族文化底蕴。
宗祠作为全体宗族成员的认同归属和维系家族的情感寄托,具有非常特殊的精神价值象征意义。在社会文化的表现方面,村落建筑则均以宗祠为中心,宗祠高出民居,又较之气魄,体现出庄严肃穆之感。以徽州村落西递为例,“村落空间组织按血缘以祠堂为中心进行布局,全村按血缘关系分为九个支系”[1],显然村落中需突出宗祠的中心位置,并且村落中有总祠并有各个支系的分祠,其中总祠敬爱堂规模宏大,位于村落的中心。西递敬爱堂,“报本之礼,祠祀为大,为之寝庙以安之,立之祏主以依之,陈之笾豆以奉之,佐之钟鼓以飨之,登降拜跪,罔敢不虔,春雨秋霸,无有惑怠,一世营之,百世守之。”[2]说明徽州区域社会中徽州人对祖先的宗祠祭祀非常敬重,宗族成员间认同感也具备坚实基础。“一世营之,百世守之”,勾勒出徽州古村落对村落宗族文化的世代推崇,足显徽州宗族文化悠久历史。清代徽州人著作《橙阳散志》亦描述:“聚族而居,一姓相传,历数百载,衍千万丁,祠宇、坟茔世守勿替。”不难理解徽州人以村落血缘关系为基础并形成稳定的社会文化载体,宗祠凝聚整个宗族,宗族祭祀增加了宗族的稳定性,致使村落内部宗法体系相当稳固。在宗族文化中,宗祠能够增强宗族成员沟通,孕育共同的文化价值,并发挥整合调适的社会文化认同功能。
徽州宗族的繁荣植根于徽州区域社会。宗族体系的维护和延续则构成了徽州区域社会的文化发展要素。宗族文化在社会文化的塑造上产生显著的作用力,成为徽州区域村落文化的主导。除了传统的村落宗祠营造外,宗族的组织严密、宗族运行和管理有序,如徽州宗族围绕宗族姓氏进行的族谱修撰也是徽州村落宗族文化的反映。目前存世家谱中,徽州家谱数量甚多。徐学林据 《中国家谱联合目录》统计徽州六邑家谱数达778种781部,木刻本 415部,占存世总数的 53.4%。由此可见徽州区域家谱之盛,相当程度上对徽州区域社会起到了稳固影响,发挥出宗族成员间组织认同功能,更体现出徽州社会文化对传统的延续。另外,徽州区域村落的祖先奉祀、族田分配、宗族活动等均含有丰富的宗族文化元素,显示出宗族文化在徽州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宗族文化对徽州区域村落的渗透,支撑着稳定的社会结构的运行,保证了社会文化的有序发展。
2. 风水文化
“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3]。 徽州社会中世俗风水文化思想非常浓厚,徽州人在村落的选址和建筑布局以及村居水口等方面都往往会考虑风水元素。徽州的古村落中蕴含了浓厚的风水思想,正是在风水文化的影响下,徽州社会与自然协调相处,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古村落风格。
2.1 藏风得水的村落选址
《葬经》:“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4]说明藏风得水是村落选址的重要要求。徽州古村落往往会把村址和布局设置成依山傍水,并“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的格局。以徽州的典型村落宏村为例,其东有东溪、东山;西有西溪、石鼓山;南向良田;北有黄山余脉;中间平坦。宏村显然四面为山川所环绕,构成了“藏风”之势。除风之外,水的作用也同样得到重视。环绕的水往往作为龙脉所在,形成水流环绕的流动气势,凝聚风水气息。由于“水积如山脉之住,水流如山脉之动。水流动则气脉分,水环流则气脉凝聚”[5],所以,村落形成龙虎围抱、水流环绕的“生气凝聚”格局是理想中的风水模式,通常四周山形构成“藏风”,而一水环流则达到聚气的效果。南宋德佑丙子年(1276年)的洪水暴雨致使宏村西溪水改道,两溪汇合一流,宏村形成了背山面水之势。明初永乐年间,徽州人又三次邀请地师踏勘地形,绘制山川地势图,对村落进行整体规划,其中将村子中心的天然井窟疏浚扩大,开挖成半月形的池塘—月沼,以存蓄“内阳水”。万历年间,又将村南百亩良田掘成南湖。故“爰踵疏月沼旧规,抉田百亩,凿深数丈,周围四旁,砌石立岸,名曰南湖”,形成了以雷岗山为牛头,以村中水流为牛肠,以月沼为牛胃,以南湖为牛肚及以民居建筑为牛身的牛形村落体系,宏村的背山面水格局逐步完善,构成了徽州村落选址的典型风水格局。另外,《西递胡氏任派宗谱》载“任派五氏祖经西递铺,见其多山拱秀,水势西流,爰偕堪家入西川境,遍观形势,有虎阜前蹲,罗峰拱秀,天马拥泉之胜,犀牛望之奇”,可见西递风水以“藏风聚气”为宗旨,同样形成了背山面水之势。纵观徽州村落形状,西递呈舟形,宏村呈牛形,呈坎呈八卦形等,许多村落营造均按照风水文化理念来设计。以西递、宏村等为代表的徽州古村落依托风水原理而规划,成为体现风水文化的理想环境模式。
2.2 聚气生财设计
房屋坐向也是徽州区域社会文化的重要体现。徽州人房屋的建造比较重视民居住宅的吉利,尤其体现在房屋门的朝向上。因门通出入,是风水学最讲究的“气”口,大门的朝向具有特殊意义,故徽州历来便有“宁为人立千坟,不为人安一门”之说。住宅大多是“坐西朝东”或者“坐南朝北”,而门很少往南开的,显然受风水“五行相宅法”的影响。《图宅术》曰:“商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因为商属金,南方属火,火克金,门朝正南,属“相克脉”,故徽州区域大多数民居都非常注重门的风水,极少有坐北朝南的,可见风水文化对徽州民居的影响之深。另外,徽州民居院内多置天井,并有“天井乃一宅之要,财禄攸关”[6]之意。《相宅经纂》曰:“凡地宅内厅外厅,皆以天井为明堂,财路之所……房前天井固寄太狭至黑,亦忌太阔散气,宜聚合内栋之水,必从外栋天井而出,不然八字分流,谓之无神。 ”[7]从中可以看出,天井仍是出于风水需要,其以“聚财”为目的。“天井能使屋前脊的雨水不流向屋外,而是顺水纳入天井之中,以示财不外流”,从而呈现“四水归堂”之景,寓意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文化理念,此寓意表征出在徽州社会的村落文化中徽州人对财富观念的侧面阐释。
2.3 水口文化心理
水口则指水流的出入口或其近旁,在村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味。“入山寻水口,……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奉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财用之不竭。”[8]因而水口在徽州社会文化中的气、财等方面的象征意义非常突出。水口往往隐喻整个村庄风水的咽喉,决定着一个村子的兴亡盛衰。“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宜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处。”[8]所以,在村落的规划中非常重视水口的布置。通常入水口需要水流顺畅,寓意财富以及气的聚合和源源不断,出水口则要锁住水口,不可让财源流失。“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徽州村落一般会在水流上建造桥、塘等物以示“锁”住水口,甚至栽种花草树木等以显示对财富的挽留,彰显出徽州区域朴素而深厚的社会人文思想。水口的营造,使得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相得益彰,形成徽州区域的社会文化外在表现形式。
3. 民居文化
徽州区域社会文化不仅在村落的选址以及外在的规划等宏观布局中得以彰显,其内在布局及装饰则往往更为细致。民居文化是村落社会文化的记忆,民居文化的精彩纷呈则表现出徽州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而居民住宅的外形布局构造、装饰理念,以及住宅内部物品的装饰、细微陈设甚至艺术雕刻等方面均有特殊的含义,传达着深厚的人文内涵和精神。
3.1 吉利文化
徽州人在传统世俗文化的塑造中往往阐发其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徽派建筑中马头墙最为典型。其先,马头墙的建造是由于徽州房屋密度大,出于对防火需要而将各家的房屋进行隔开形成“马头墙”的风格,并且马头墙错落有致,呈现层层叠叠之状,级数各异,多的甚至达到五级,俗有“五岳朝天”之寓意。在远处看去,村落建筑犹如马头齐头并进,给人以吉祥美好之感。徽州民居中还有很多门罩装饰,且多呈现元宝形,体现着徽州人以讨吉利的财富观念意味。住宅内部布局也非常考究。一般的村落主体多为三合院类型,分为左右厢房、中间厅堂,厅堂多悬挂福、禄、寿三星中堂,以象征吉祥如意。除了村落民居的陈设,在建筑雕刻上吉祥理念表现亦较为突出。如宏村的承志堂在“宴官图”两边的匾额上雕刻有元宝与 “金钩钓鱼图”[9]。鱼表示年年有余,元宝则象征招财进宝、财源广进之涵义。还有“和合二仙”的民间神仙,一人持荷(和),另一人捧圆盒(合),象征和谐和好之意。这些都反映出徽州人平安和吉祥的幸福愿望,展现出徽州民众对幸福和美满生活的热爱。
3.2 贾而好儒文化
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徽民寄命于商”[10],徽商成为明清历史时期的著名商人群体。徽州区域素来儒学文化兴盛,故徽州贾而好儒的文化特征明显。重商崇儒的社会文化在徽州村落建筑上也得到很好诠释。
徽州宏村的承志堂是保存于世的大型民居,其主人汪定贵于经商富足后曾捐了个“五品同知”的官衔,在厅堂中“增设了一道具有官家威严的中门。中门又称仪门,原为官署而设,一般只有在重大喜庆日子或达官贵人光临时才打开西门以示欢迎……仪门的两个侧门上都别出心裁地雕上了一个‘商’字形图案”[11],可见徽州人在儒家文化和程朱理学影响下,崇尚商业但更推崇仕途。徽商经商致富而崇儒入仕并不少见。据汪道昆《太函集》记载:“今乃所不足者,非刀布者也,二子能受儒矣,幸毕君志而归儒。”反映了徽州人崇商重儒的心情,并且“重儒”甚于“重贾”,故读书入仕仍为徽人心中的最高理想。在民居中也能看到徽州人贾而好儒的影子。如徽州民居的山墙上常砌有朝天放置的很多不规则的方形官印形状的装饰物,又称为官斗印,充分体现出徽州人对仕途的追求心理。徽商的重商崇儒心理不仅在建筑上可以窥见一二,而且民居内部陈设也充分表明徽商崇儒贵仕的文化观念。另外,楹联、书法、绘画、雕刻等装饰同样展现出徽州民居的儒雅和读书入仕情怀。以徽州民居中常见的楹联为例,大多数徽州的民居厅堂中会悬挂许多诗书楹联,很多楹联其内容都表现出徽州人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及向往。如楹联“孝悌传家根本,读书经世文章”、“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和“绵世泽莫如积德,振家风还是读书”,可见徽州人重儒学礼教,将读书视为做人的道理与人生信条。“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徽州人对儒和商的崇幕,从这些民居文化中均得以体现和反映,故徽州古民居村落为我们提供了窥视徽州社会文化的窗口。
徽州古村落是徽州区域居民生活的社会载体,古徽州的村落结构、村落生活及文化和社会秩序较为全面地表征出徽州区域的社会文化。正是借助徽州古村落这一物化的载体,其社会文化呈现出丰富的内涵。
[1]陆林,凌善金,焦华富.徽州村落[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64.
[2]潭渡黄氏族谱(卷六).
[3]赵吉士.寄园寄所寄[M].合肥:黄山书社,2008.
[4]古今图书集成·葬书[Z].北京:中华书局,1985:25.
[5]蒋平阶.水龙经(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75.
[6]吴才鼎.阳宅撮要(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1.
[7]何晓昕.风水探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112,45.
[8]叶九升.地理大成山法全书[M].台北:台湾武陵出版社,2001.
[9]余治维.桃花源里人家[M].合肥:黄山书社,2006:74.
[10]休宁县志(卷七)[Z].康熙二十九年刊本.
[11]舒育玲.天人合一的理想境地:宏村[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