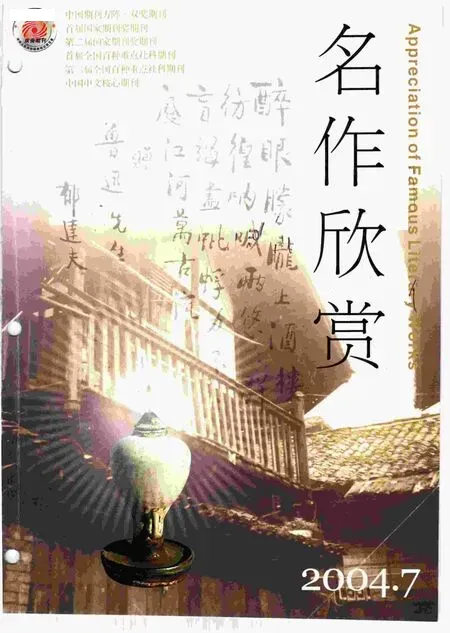对神话文本的现象学还原
——以《愚公移山》为例
上海 杨澄宇
语文讲堂
对神话文本的现象学还原
——以《愚公移山》为例
上海 杨澄宇
《愚公移山》这篇课文是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课文。它出现在目前各个版本的教科书中,而且从1912年入选由蒋维乔、庄俞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五册》起,其改编白话版与文言原版就是各个版本的小学或初中教科书的常备课文。其寓意看似简单明了:体现了一种知难而上,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①但是,细究之下,却又复杂疑惑:或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或与时代的意义相悖而产生争议。这不仅体现在教科书在录用此文时,在其后的“练习系统”中对此所作的脚注;而且,体现在课堂实践中,教师对其阐释的充分开放与争议性,以及语文研究者对之的评论上。
其实,这种争议性体现了语文课程场域中的参与者们,包括教师、学生、研究者、家长等对于偏离单一思维模式的不适应与自适应过程:一种经典的条条框框被打破而带来的不安全感,以及在这种不安全感基础上试图重新构建阅读范式的努力。同时,多元与开放的解读方式也可能造成混乱,而这种混乱很大程度是来源于授课教师 “堂吉诃德”式的尝试,恰如王荣生教授所言:“我觉得郭老师们所张扬的‘解构’,其含义可能仅仅是借此名义来表明自己的一种姿态。”②这种“解构”的姿势——知识,因为充满了教师的个人情怀,缺乏学理上的支持,对于学生或许是一种解放,但也可能是一种更大的伤害。于此,就需要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足以洞察先在的成见是如何附加到语文场域之中的,另一方面又具有学理上的依据。
现象学还原:对神话的观念回溯
现象学还原恰是这样一种方法,而采用这种方法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承认:在传授与学习课文时,有一些成见已经提前处在我们的脑海中,当学生自认为是通过阅读而体验到文本的精神,其实只是印证了某些成见,而这就造成了思维与创造力的僵化。所谓“现象学还原”,即排除掉一切与直观体验本身的构成活动无关的存在预设的方法。具体而言,如何“还原”?正如黑尔德(Klaus Held)所言,它无非就是“悬置”的彻底普遍化。③通过悬置,世界成为现象,与自然科学相反,这一方法不关注现象存在的“什么”,而是对意识的意向显现方式,它的“怎么”。当我们明了现象是“怎么”成为现在的现象时,就能够“回到事物本身”。“悬置”,就是一个加“括号”的过程,将所有成见(当然,在胡塞尔那里,特别指涉自然科学的方法)放进“括号”中。这是一种“看”的方式,关于此,胡塞尔曾经说过:“合理化和科学地判断事物就意味着朝向事物本身,或从语言和意见返回事物本身,在其自身所与性中探索事物并摆脱一切不符合事物的偏见。”④
在本文中,“回到事物本身”即回到《愚公移山》文本本身,在引介到国内的教育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中,最为看重的一点是当事人的“体验”。⑤但是,在本文中,不多作这方面的阐述。笔者认为,对于文本的“还原”,是学生或教师“体验”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本质直观”,才能通过自由想象,把自己从实际知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⑥
“回到文本本身”的现象学还原,第一步需要做的是对于文本在观念中形成的溯源,只有明晰了“愚公移山”所附加上的、先于我们阅读而存在的种种观念,才能打破教师与学生对于课文的某些成见和简单化思维。
一般而言,在教学实践中,老师们会认为《愚公移山》是一则寓言故事,或者说是具有神话色彩的寓言故事。其实,这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在理解文本的时候,寓言故事与神话有着比较大的区别。《辞源》上“寓言”的定义为: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而神话,至少在问世之初,被认为是真实的。如果要给“神话”下一个定义,笔者采用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思给出的论断:神话是关于世界和人怎样产生并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神圣的叙事性解释。⑦
与神话相比,寓言显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真实性与神圣性,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相通之处。首先,神话可以慢慢转换为一种寓言故事,在中国,则常常与道家方士的仙话相结合,成为一种神话的变种。按照袁柯先生的观点,神话受仙话浸染,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山海经》中就有大量的例证。⑧这种仙话,在漫长的历史流传中,其真实性有可能一直未被质疑,或未被普通民众所怀疑,而成为了社会的底层知识。而在这一过程中,神话自然会伴随着某些寓言性,可以被解读、提炼出一些生活经验,甚至产生文学、美学的共鸣。最显著的例子莫如“嫦娥奔月”的故事。其次,寓言也可以成为一种神话,享有非事实,却是事理上的真实与神圣性。当故事拥有了解释世界的能力的同时,它就享有了这两种特质。而寓言,显然具有这样的潜力。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此三者,都是达到宇宙“道理”的手段。
《愚公移山》取自《列子·汤问》,具体成书年代不详,大部分学者认为成书于魏晋。《列子·汤问》这一章与全书的主旨看似没有太多关系,多神话故事。譬如“愚公移山”这个故事之后就是接着“夸父追日”的故事,而“愚公移山”中奉天帝之命移调两座大山的“夸娥氏二子”,“娥”与“父”声音相近,袁柯先生认同茅盾先生的观点:“夸娥氏”即是“夸父氏”的两个儿子。⑨
从以上的角度看,“愚公移山”的故事最初可以看作神话:它讲述与交代了王屋、太行二山的来历,这就是远古人类对于周遭世界的一种自洽的解释。
而从神话到寓言,是神话力量消解的自然结果。恰如神话学家埃里克·达代尔所言:“当神话失去力量时,象征就萎缩为寓言或形式主义……神话意象,在其地位虚弱而仅剩形式的价值后,就成了世俗化活动的主题或谚俗。”⑩而“愚公移山”这则故事在《列子》中的出现,可能已经包含了某种“形式主义”的彰显。郭初阳老师在传授这门课的时候让学生反思“老人崇拜”⑪,其实,愚公固然是老人,持反对意见的智叟也同样是老人,谈不上“老人崇拜”。倒是对于“愚公”与“智叟”的命名反映了《列子》其与老庄一脉的特点,即在“愚”与“智慧”上的辩证性。这从“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上就可以看出来。
寓言是为了说明某个道理,这个道理,一定是属于特定时代的,而这有可能与神话本身的真实性发生矛盾。这里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即如果这个寓言是讲给孩子们听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时候,是否需要某种程度的修改?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爱弥儿》卷二中说,不要和孩子们讲寓言,因为寓言的世界是成人的反映,会污染了孩子纯洁的心灵。这虽是小说家语,但也说明了寓言是需要修改与重写的。在1935年叶圣陶先生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中有《愚公》这篇课文,就对此进行了改写。⑫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改写的课文略去了原文的最后一段,即:“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知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这一句话完全没有在改写版中出现,原因恐怕在于,编者认为,天帝出手解决问题的结局会影响孩子们对于整篇课文寓言的把握,即需要传递给他们的寓意:无畏困难,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之精神。
但是,“降格”的寓言故事同样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神话,秘密正在于“降格”的“形式”上,它足以在新的语境下获得新的“神性”。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看来,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政治就是一种现代神话。言说方式材料包罗万象,包括狭义的语言、照片、绘画、广告、仪式、物品等,它们一开始不管多么千差万别,一旦被神话利用,都归结为纯粹的意指(符号)功能:神话在它们身上只看到了同样的原材料,它们的同一性在于它们都简化为单一的语言状态。⑬
神话当中有两种符号学系统,其中一个分拆开来与另一个发生关联:一种是语言系统,即抽象的整体语言,巴特称之为作为对象(工具、素材)的群体语言,因为神话正是掌握了群体语言才得以构筑自身系统。另一种系统是神话本身,被称为释言之言。符号学家反思释言之言之际,不再需要考虑作为对象(工具、素材)的群体语言的构成问题,也无须考虑语言学模式的细节问题,他只需要了解整体项或整体符号就可以了,只要这整体项与神话相适合、相融合。按照罗兰·巴特的理论,神话是一种作为劫掠的语言出现的,因为它既是意义,又是形式,最后是形式劫掠了意义。
“愚公移山”的精神广为人知,还是来源于特定历史时期对“寓意”的阐释强化:一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忍辱负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精神。⑭而这,后来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如果我们按照罗兰·巴特的解释,可以演化出下图:

“愚公移山”的神话
“降格”的“寓言”,在一种特定的言说体系中又重新“升格”为“神话”。在这个新的“神话”中,“人民”一方面代替了“天帝”的位置,从而解决了结局中“愚公”“自强自立”寓意的尴尬,另一方面,也成了与“愚公”相对的存在者,简言之,“愚公”代表了这一广泛存在者。值得注意的是,享有天然“神性”的并没有从“天帝”让渡到“人民”,而是赋予了整个“神话”,即重新阐释的“愚公精神”。
现象学还原:对神话文本的洞见
既然了解了“神话——寓言——神话”这样的阐释之链,那么就完成了现象学还原的第一步,接下来,教师们就应当“斩断”与“加括号”这样的意义循环,还原回最开始的神话,“看一看”《愚公移山》所要表达的最初本质。这种“看一看”即是还原的第二步,通过这一步,就为达到胡塞尔所言的“生活世界”打下基础,而现象学还原就是为了达到这一世界。所谓“生活世界”,即“原初的活生生的意义形成”⑮,“我们之中和我们的历史生活之中的一种精神结构”⑯,“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⑰。在“生活世界”中,其存在是由“先验主体”“构建”的,是“纯粹的主观领域”。⑱可以发现,完成第一步现象学还原的原初的“神话世界”也具有其类似的“主观”特性。
上演“愚公移山”神话的世界的特征是怎样的呢?神话时代的开始是“万物有灵论”,即自然神,如山神、水神等充满整个世界的年代,这也充分反映在人类的“图腾崇拜”或“图腾禁忌”上。而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加强,开始按照自我的样式来想象神灵,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理性化认识的成熟,女性祖先从生命神话中分离出来并被尊为生育女神,男性英雄开始成为“人格”神。按照埃里克·达代尔的看法,从社会层面来说,这种变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打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讲究生命崇拜和生命保护的神话与强调力量、数量与主宰的权利观念之间的平衡;热忱与威严之间的平衡;母系女性与政治男性因素之间的平衡。⑲
如果按照西方神话理论,《愚公移山》发生的故事,大概是处于从自然神到人格神的这一阶段。譬如,既有山神——操蛇之神,亦有人格化的天帝。但是,可以发现,相比于西方神话中性格张扬而多变的神祇,中国神话的天帝则基本是仁慈的,甚至到了软弱的地步。这一点在“愚公移山”中也得到体现。另外,这种自然神,如山神、水神、土地神,在中国神话故事中一直都被赋予鲜活的存在,并没有消亡,反而被寄予人格神的特征。
刘云杉教授在研究了教科书的童话世界后,也曾举过“愚公移山”的例子,并总结出了古代农耕社会的几个特征,其中有“封闭的空间观”与“绵延的时间观”。⑳先说“时间观”,神话中的时间观有别于“物理世界”,它是绵延的。在移山过程中,虽然“寒暑易节,始一反焉”,但时间依然是悠远绵长的。如果说测量的观念是一切理性的核心,那么,愚公的理性,恰在于采用了一种“生命延续绵延不绝”的测量方式。即用“日常体验的时间绵延可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来抗拒了“个体生命时间的不可逆”。这一点在下面还要详细阐释。
而关于“封闭”的空间性,“愚公移山”中恰恰表达了对于“封闭”空间的不满,“惩北山之塞,出入之迂也”。那么理想中的空间应当是什么样的?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中提出殷周人心目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深层空间意识,即以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㉑,人居于中央,四周是环绕而对应的。这也体现在文本中的种种地理位置的对称上: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豫南;渤海之尾——隐土之北;朔东——雍南;冀南——汉阴。而愚公处于北山,自然无法忍受这种偏居、闭塞的环境。
在这里,我们已经隐约“看到”“愚公移山”神话中所反映出来有别于西方神话的世界观念的区别,而这,正是现象学还原第二步需要还原出的“观念”。
在神话和神话意象中,蕴含着人类内心波动的外在印象、面对世界遭遇的情绪反应、对“外在”冲击的接纳感受,以及与万物融为一体的自在感觉。㉒所以,在神话中,常常能观察到一些简单而深刻的对立统一,而这,正象征着人类始祖在自我意识觉醒时刻,在自我想象的空间、时间内,对于外部环境的自我适应与解释过程。在《愚公移山》这个神话故事里,可以看到这种“人——世界”的对立与融合:
愚公——愚公妻。这种对立,体现了神话中女性力量的衰弱。如上所说,女性已经退居到“生育女神”的地位,她的人格本身,被大大削弱了。所以愚公妻是短视而现实的,这种神话印象,一直贯穿到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但她却是善意的,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且焉置土石?”得到的回答却是:“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解决这种对立的方法非常简单,因为中国神话中,无论古今,都会证明女人是见识短浅的。
愚公——智叟。这种对立表现在两者的“命名”上,而这恰体现了老庄学说对于“智慧”的理解,即“大智若愚”。只有大智若愚,才能对世界有本质的把握,而这种把握,是愚公对于生命的认识与实践。
在“愚公移山”神话中,可以发现强烈的男性荷尔蒙气息,愚公的子孙是孔武而莽撞的。这种男性特征具有强烈的宗族气息,这特别表现在愚公家族的“孤独”上,他的权威几乎没有遇到其他“家族”的挑战,因为其他家族都是“衰败”的:“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而“宗族”,恰是“愚公”对抗王屋、太行的最大的“武器”。
刘云杉教授认为,愚公的故事是典型的玛·米德的“后象征社会”特征:孩子是长者身体与精神的延续,是土地与传统的继承人,也是长者未竟之业的实践者。㉓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愚公移山”背后的观念,但更重要的,有别于西方传统的观念却没有道出,而这一至关重要的“前”观念,反应在下面一组对立与解决中:
愚公——操蛇之神。王屋、太行二山背后的“主角”其实是“操蛇之神”。愚公面对不可战胜的两座大山,给出的方法是:“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用“生命的延续”来对抗死亡,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部分,这特别体现在《列子》这本书的思想中,老子祈求长生、庄子混同生死,《列子》则认为应当直面生死,不求任何虚幻。子嗣的长存就是对付虚幻的办法,葛兆光先生认为,对于祖先的重视和对于子嗣的关注,是传统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子孙的血脉在流动,就有一种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在扩展,生命的意义在扩展,扩展成整个宇宙。中国人把生物复制式的延续和文化传承式的延续合二为一,只有民族的血脉和文化的血脉相一致,才能作为“认同”的基础。㉔从某方面讲,我们至今仍能认同“愚公移山”精神,是因为我们都是“愚公”的后代。当然,这又衍生出了一个新的“神话”,需要我们还原掉。
如果我们在这里仅仅还原出中国古代传统的“血亲”观念,那还是不够的。因为愚公对抗的是操蛇之神,操蛇之神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操蛇之神不仅仅是山神,更是“永生”的代表。奥秘在于“蛇”上,在汉族的神话传说里,“蛇”因为有“蜕皮”的功能,所以是“永生”的,而“人”原本是享有这一能力的,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蛇”篡取了这项能力。
既然“愚公”可以通过子孙延续的功能达到“永生”的效果,难怪操蛇之神“惧其不已,告之于帝”。这个对立的解决方法自然过渡到下面一个对立:
愚公——天帝。严格来说,这不是一个对立,因为天帝用了怜悯与帮助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化解了自己的危机:一是愚公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因为只有天帝才能安排地形地貌;二则是默认了愚公子嗣延续的价值。他为什么能怜悯、容忍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与“愚公”是同源的。在这则神话中,天帝即为“帝”,而早在商朝,商朝祖先之“帝”就拥有了某种神性。“商王朝将高祖远公的宗庙群置于邑中的偏西,似辨出血统亲疏远近的观念……高祖远公,明显具有与土地相结合的神性……如此的神位配置,已具备后世‘左祖右社’的雏形。”㉕赵林教授认为:“左祖右社”意味着自然神灵与人鬼世界的二元对立,但商人又以帝来称呼先王之神主,这又将二元的对立转为二元的统一,事实上,学者亦察知“两者间的分界不是很清,神性有交互现象。”㉖
在祖先崇拜的同时,殷人具有鸟崇拜,“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毛传》);“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鸟”的“神性”让渡给“人类”的同时,其“神性”也降低了,其与“人类”也血脉相连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山海经》中,亦有“操蛇之神”,其状为人与鸟的混杂:“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山海经·海外北经第八》)而《山海经》中对于夸父的描写为:“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山海经·大荒北经第十七》)由此可见,“操蛇之神”与“夸娥二子”具有比帝低一等的神性,而帝的神性本身也和人类的血缘有着不解之缘。
故此,我们可以还原出这样一个观念:愚公所凭借的不是他的精神,而是其血缘传承。而正因为这种血脉传承的“神性”,帝也不得不动容,派“半神”将山脉对称地移开,将“北山”愚公放回到他诉求的“正中”的位置,并且其“永生”的存在也得到了承认。这一刻,“愚公”这一“存在者”,变成了神的“存在”。
现象学还原:课堂上的本质直观
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完成了现象学还原的第二步,即将其本来的、先在的观念还原了出来。从某个方面而言,现象学的还原是一种“防御”的方法,而非“建构”的方法,即排除掉一切与直观体验本身的构成活动无关的存在预设的方法。㉗本文仅仅是根据其现象学还原的精神,分析了在《愚公移山》中需要“加括号”的地方,而如何将其运用到课堂实践中,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而这种课堂实践,其实是一种寻找使学生达到“先验的我”的过程。这就产生了胡塞尔所谓的主体性悖论:构成世界的主体把握自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问题在于,我们——世界的一部分,怎么竟然构成了“整个”世界,即构成为它的意向性产物?答案在于我们需要搁置,还原先在的“经验”,而运用切身的“体验”,这就是胡塞尔在兹念兹的“本质直观”。
是否我们的课堂就应当呈现出一种让学生“体验”的状态呢?也不尽然,因为没有之前的还原,学生所谓的“体验”其实已经被先在的“经验”所劫持,教师们需要从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扫除课本文本中,以及学生头脑中这些附加上的“经验”,让“课堂向四面八方打开”。如何或有无必要将还原过程教给学生,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美国教育学家布鲁纳认为,任何学科以一定的知识的正当形式,都能有效地教给处于任何发展时期的任何儿童。㉘布鲁纳的意思是任何学科知识的“观念”都可以让孩子领会到。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先在知识的“观念”也可以用适当的方式让孩子领会,并明了其“先在”性,解除其“神话”性。
胡塞尔给出了“自由想象”的办法:
这样,我们自由地、任意地创造变项,这些变项中的每一个以及整个变化过程本身就都以“随意”的主观体验的方式出现。然后会表明,在这种连续形象的多样性中贯穿着一个统一……这种形式在随意的变更活动中呈现出自身是一个绝对同一的内涵,一个不变的、是所有变量得以一致的某物,一个一般本质。㉙
我们假设老师在传授这门课的时候,已经让学生领会了先于神话文本的“神话”性,至少自己明晰了文本中种种先在的观念;并打算不将此神话降格到“寓言”——只做传授寓意的工作;而是准备将其还原到现有的“生活世界”,让学生体验到“愚公”的存在,并拥有成为或不想成为其的权力。那么,老师们就自觉运用了现象学的方法,带领孩子在做一件事情:在两个“生活世界”中穿行——从远古的神话世界到此时此刻的世界。恰如德国哲学家齐美尔所言:“生活,就是多多地生活。”这种多样性、开放性,结合现象学还原的“纯粹性”,构成了语文课程场域的应有生态环境。
在语文课堂实践中,现在很多老师的做法是在一堂课的开始,先将课文的主旨、学习的目标书写在黑板上,如果这门课是一堂特定语言知识的传授课,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是在讲授一篇课文之前,则笔者以为,恰是在给学生制造成见,其结果是不仅无法回到文本本身,而且可能是用新的成见来掩饰过往的观念累积。
如何在自己的课堂中回到文本本身,并生成这样的“自由想象”?笔者认为,就《愚公移山》这堂课而言,“课本剧”这一种形式——让学生放弃现在的生活世界,甚至是某种程度地放弃自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个远古的神话生活之中,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生命的抛射与投入,这种生命来源于远古的“愚公”,是对于“自我”的“遗忘”与“重生”:“每当一个主体——无论是一个个体或是一整个时代——已准备好将要把自己遗忘以便把自己化身为和奉献于另外的主体的话,则它其实已在一崭新的和更深邃的意义里发现了它自己。”㉚而这,也将避免现象学还原后突出的“先验主体”的自大与狂妄。
我们可以将课堂看作一个广义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学生、教师时刻处在生成状态中,这个广义文本实践的过程,其实可以是回到课本文本本身的一种尝试,是一场寻求“本质直观”的演出,是一段“归乡”的旅途。当然,除了“课本剧”,老师们在课堂实践中,可以有很多种选择,而“多种选择”本身也是现象学方法排除设定观念的应有之义。笔者就此提出自己的两点看法:
第一,就课堂的“空间”而言,应当是“向四面八方打开”的。只有开放的课堂,才有可能实现学生的“自由想象”,只有在“自由想象”中,学生才能达到对语文的深切感受。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并非无事可做,相反,他必须帮孩子打破思维空间的闭塞,让孩子在碰壁之后还能悠游前行。而在这个空间中,老师们最应当避免的就是各种空间的定势,恰如“神话”中的封闭、中正的空间观,是不适宜带到课堂中的。而现象学方法中的“边缘域”意识,值得老师们借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有体验意识被堵在绝境之上,才能开辟出新的领域。
第二,就课堂的“时间”而言,应当是“绵延往复”的。当然,这种“绵延”观与“神话”中的时间观不同,它不是反复,而是不断生成:未来非是由过去决定,而是拒绝任何先在的特定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甚至是由未来所决定。恰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所提倡的“时间——绵延”观念,课堂不是一个死寂的,哪怕包括了多么先进的多媒体的“材料——物质”世界,而是应当作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进化——变化”的世界展示在“在场”的学生与老师面前。“在场”是一种类似于剧院演出的时空感,它是可以还原的,但每一次还原,都会直指“边缘域”,使得每一次回到“文本”本身都是新鲜的。
当然,“在场”意味着更多的“不在场”,如“功利”的“社会生活”。这就需要语文老师,能有一种大勇气与技巧去将它屏蔽在外,面对汹涌的应试大潮,借用佛教中的一句话,应如“香象渡河,截流而过”。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也应当有这样的自信:当孩子们在纯粹的语文世界中徜徉后,当他们明晰了种种先在观念的束缚后,甚至当他们也开始运用还原的方法时,这个世界已经和原来的不同了。而如果当他们需要应付那些功利的语文观念时,做得绝不会比别人差,也更加得心应手。因为语文生活,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元与复杂。
①戈致中:《〈愚公移山〉介评》,洪宗礼、柳士慎、倪文锦:《母语教材研究》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
②⑪王荣生:《听王荣生教授评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第145页。
③Klaus Held,“Einleitung” zu Edmund Husserl. Ausgew hlte, Texte I: Die phaenomenologiche Methode, Stuttgart 1986, S.20.
④〔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5页。
⑤朱光明、陈向明:《理解教育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外国教育研究》2006年第11期。
⑥Edmund Husserl,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Husserliana I, The Hague 1950, S.104.
⑦〔美〕阿兰·邓迪思:《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⑧⑨袁柯:《中国神话传说:从盘古到秦始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8页,第150页。
⑩⑲㉒〔法〕埃里克·达代尔:《神话》,《狄俄金乃斯》1954年第7期。
⑫叶圣陶、丰子恺:《开明国语课本》上下册,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27页。
⑬〔法〕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⑭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⑮⑰〔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第58页。
⑯⑱〔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吕祥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第138页。
⑳㉓刘云杉:《教科书中的童话世界——一个社会学视角的解读》,《教育研究与实验》,2000年第5期。
㉑㉔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第24页。
㉕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1—824页。
㉖赵林:《殷契释亲——论商代的亲属称谓及亲属组织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㉗张祥龙:《胡塞尔的意义学说及其方法论含义》,《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㉘〔美〕布鲁纳:《教育过程》,《布鲁纳教育论著选》,邵瑞珍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㉙〔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㉚〔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作 者:杨澄宇,青年学者,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生。
编 辑:赵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