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
——兼探虎方之地望*
(中国 台湾)郭静云
(台湾中正大学 历史系,台湾)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
——兼探虎方之地望*
(中国 台湾)郭静云
(台湾中正大学 历史系,台湾)
崇拜老虎的传统源自古代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中。华南拜虎传统的分布范围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野猪和虎的崇拜曾互相结合,后来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山岭拜虎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殷周时期在长江中游之江南地区以湖南、江西为主要分布范围,存在着一个拜虎的古国网络体系,其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为“虎方”。
华南拜虎;江南青铜时代;高庙;后石家河;虎方
前 言
过去,我们时常习惯在讨论虎的概念时,将其视为象征“西方”的神兽(白虎形象),但将老虎作为西方象征的概念,其形成时间很晚,往往不足以代表上古文明崇拜神虎之多元性意义。笔者研究老虎形象来源之后得出推论:古人崇拜老虎之文化发祥地可能有三个:江汉上游西岭、长江中游江南山脉、东北山脉。这三个地区原本皆各自有独特的虎崇拜传统,但由于族群交流和文化传播,而在历史上发生混合、互补及演化的现象。其中最古老的拜虎传统,是源自蜿蜒逶迤的江南山脉。本文拟从零散的考古资料,以及出土和传世文献资料,试图复原江南地区这个拜虎大文明的形貌。
一 从虎形的礼器讨论江南地区崇拜神虎的信仰要点
在长江中游江南山脉中,过去也有老虎出没(属华南虎,学名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在古代,华南虎的生活范围从南岭到湘鄂西的山岭、北至秦岭东南的山林,与另一拜虎传统区域江汉上游西岭交界。华南类型的虎形礼器如石家河玉器虎头(图1:1-3)*荆州博物馆编着,《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页50-95,图78-63。、凌家滩双首虎玉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页59—60,图57—59。;新干大洋洲墓所出的青铜器,如扁圆龙足虎鼎、伏鸟双尾虎(图2)、虎首戈*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合编,《长江中游靑铜王国:江西新淦出土靑铜艺术》,香港:两木出版社,1994年,图版6—9;38;40。等;三星堆和安徽阜南县朱寨镇遗址发现的铜尊亦属华南虎类型(图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页35-36。。这些礼器,都揭示了江南先民对虎的崇敬,这应是源自于他们生活中接触华南虎的经验而产生的信仰。

图1 图2
1-3.石家河兽面饰;4—6、凌家滩8号墓双头虎形玉璜; 1.新干大洋洲墓出土扁圆龙足虎鼎(标本14);2.新干大洋洲墓出土伏鸟双尾虎
笔者推论:江南文明中对神虎的崇拜,源自武陵山脉、雪峰山脉、罗霄山脉和南岭脚下的先民,且在中国境内属于发源最早的拜虎传统,其发展到达江南平原地区,影响长江中游大文明的信仰。凌家滩、石家河已属十分成熟的文明,都曾出现虎头的礼器,这使得笔者推测:江南岭北地区崇拜虎形象的传统,可能拥有比石家河、凌家滩更早的来源。但若从现有的早期文化遗物来看,目前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线索还是十分零散且不够明确。
在新石器早期的文化中,湖南省的西南区——洪江高庙祭祀场所遗址内,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兽骨,这代表着此处应居住着山岭附近的上古猎人族群,而他们在此丘陵台地上曾举行过祭祀活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刚、像开旺,《湖南黔阳县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4期,页4-23;贺刚,《高庙遗址的发掘与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5年第2期,页113-124+图版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页9-15+99-100。。在高庙遗址下层出土的兽骨中,较为突显的是野猪和老虎的骨头*笔者感谢湖南考古研究所提供相关资料,详细考古报告待刊。。高庙下层祭祀坑中发现过完整的猪头骨,以及几具男性头骨与鹿角、野猪下颚骨合葬。高庙遗址下层两次发掘的成果,年代测试在距今7200至6700年间(未经树轮校正的数据),陶器的器形与澧阳平原同期但略早的胡家屋场遗址接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刚、向开旺,《湖南黔阳县高庙遗址发掘简报》,页4-2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页9-15+99-100。。近十几年内,湖南中、南部的丘陵和山地亦发现数处高庙文化遗址,如桂阳千家坪、长沙南托大塘、辰溪征溪口和松溪口贝丘遗址,后者的年代测试在距今6500至6000年间(未校正的数据)*千家坪遗址数据尚未公布,感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资料。其它参:长沙市博物馆、黄冈正、王立华,《长沙南托大塘遗址发掘报告》,《湖南考古集刊》第8集,2009年,页17—2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征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6期,页17-2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6期,页4-16。,都应属于新石器早期狩猎、渔猎族群的聚落和祭祀场地。

图3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龙虎尊的刻纹

图4
1.高庙遗址白陶簋;2.高庙遗址白陶罐高领刻纹;3.高庙遗址白陶钵刻纹;4.松溪口遗址出土的白陶豆;5.松溪口遗址出土的白陶罐口部;6.松溪口遗址出土的白陶盘上双猛兽刻纹
湖南中南部地貌是错综复杂的山地、丘陵与河谷地区,在本地新石器中期白陶和红陶上,明显可以看到山水形状的刻纹(图4:4、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页10-11,图九:5、十:5。,表现出本地先民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与理解。在桂阳千家坪遗址的刻纹陶上,这类“风景”图甚多,包涵了山水及树木的图案。自然条件和文化遗物,都显示了狩猎族群的活动情况。在松溪口遗址所发现、具有神秘意义的白陶礼器上,可见类似猛兽的造型,如白陶盘外壁的图案,则像是一双猛兽对立,而从口中拉出一条线的样子,由于这件礼器有所残缺,因此线的形状并不清楚,但在其上一层可见有一行山岭,而下层刻纹的意义尚不明朗(图4: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页11,图十:1。。不过,在这件陶器上的一双猛兽,相当近似于猛虎的造型。*这些遗址中发现了许多蚌壳,因此,松溪口遗址简报的执笔者猜测:蚌壳的摆置或许是具有规律的,并怀疑可能类似于西水坡遗址那样,以蚌壳组成猛虎的造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页6,图五),但其它参与具体发掘的人员却认为,简报上的图样过于牵强,该数据恐怕并不可靠。
同时,在高庙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含有神秘意义的白陶礼器上,最容易辨识且常见的刻纹图案主要有两种:鸟头图和獠牙图(图4:1-3),此外,还有许多难以辨识的抽象的、几何性的刻纹。而这些礼器上的獠牙图形状,在观察自然界的形状后可得知,最近似于野猪的獠牙。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推论:高庙猎民曾有崇拜野猪的信仰,而埋葬猪头的祭祀坑与獠牙图则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这种獠牙的象征图,在长江流域青铜时代早期礼器上依然颇为常见。在良渚的神圣造型上,有一个极少有人注意的共通特点:在神人像的腿间有两对獠牙,这与高庙礼器上的獠牙图相当雷同。学者们已屡次讨论关于高庙白陶器上的八角星图案,与长江下游常见八角星图案的相似程度*贺刚、陈利文,《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页51-60+92。,显然,古代长江乃是一个精神文化的传播通道,促使了象征獠牙形象的信仰,以及良渚的天神造型信仰互相链接起来,并形成由多元文化要素构成的大神形貌。(有关良渚崇拜对象之形象分析,以及相关信仰的内容,因超出了这次研究的主题,笔者拟另文讨论。)
在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国文明亦出土了带獠牙的神人面像礼器。循着石家河文化的影响势力而逐渐扩展,使得这种造型从长江上游到山东都历历可见,如很多学者认为:日照龙山遗址出土玉圭的刻纹来源,与石家河有关,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带神面纹玉圭,也是渊源自石家河文明的礼器之一*荆州博物馆编着,《石家河文化玉器》,页19;王劲《石家河文化玉器与江汉文明》,何介钧主编,《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曁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邓淑萍,《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六)──饰有弦纹的玉器》,《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一卷第十期,1994年,页82-91;林巳奈夫(日)着、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7年,页232-243;杜金鹏,《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浅说》,《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页51-59。。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源自石家河的獠牙玉人面像(图5),在商周墓也曾出土过,同时,考古学者在殷商时期的吴城文化遗址中,亦发现了同类的獠牙人面像,这显示该传统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很高。

图5
1.晋侯墓出土的玉獠牙神面像;2.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玉獠牙神面像;3.芝加哥艺术学院收藏的玉獠牙神面像;4—5.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玉獠牙神面像

图6
1.湘潭县出土殷商时期铜豕尊的线图;2.新淦遗址出土伏鸟双尾铜虎的线图
不过,如果我们将从高庙以降所传之獠牙图,都视为对野猪崇拜的脉络,那么将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何在同一时期中,却不见大量神豕形的礼器出土?长江流域新石器中期的河姆渡文化,礼器中确有蕴含神性意义的家猪造型、以及小型家猪陶制品出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54,图三三:7;页67,图四一:1。,但在明显曾有崇拜野猪痕迹的地区范围内,却均以湖南山区和丘陵地区为主。到了青铜时代早期,石家河祭坛遗址出土的众多小型陶制动物中,虽也有家猪造型*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着,《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页217,图一六六;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着,《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195,图一五八等。,但野猪造型的礼器迄今仅发现一件,即湖南湘潭县出土的大约殷商时期的铜豕尊*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据笔者自摄照片。。此外,只有时代更晚的极少数几件文物,如山西曲沃出土的西周早期晋仲卫父盉上的野猪造型,其器身形状、纹饰与铜豕尊的野猪形象雷同,但是尺寸很小,并非整个独立的铜尊,而仅有盉盖上的盖耳属于野猪造型,盉身则有两层双凤饕餮纹*山西省博物馆收藏,据笔者自摄照片。。晋国高层贵族墓里出土的两周礼器中,很多都带有南方风格,该铜盉以及晋侯113号墓出土的猪尊,皆应与湘潭县的豕尊具有传承关系。
换言之,江南山丘自上古以来便系先民狩猎活动之区,从此地区的发掘成果来看,自新石器早期便已有崇拜野猪的习俗。不过我们亦可以发现,江南山丘同时也是自上古以来崇拜猛虎族群的活动地区。笔者经过不同礼器的相互对照,注意到两件时代相同的礼器,其构图基本上相同:即江西新干出土的属吴城文化的伏鸟双尾虎,以及湘潭县出土的铜豕尊,两者之间相似性极高。这两件礼器身上皆有夔纹、背盖上伏鸟、两耳竖立、四肢粗壮、尾下垂,且獠牙外露(图6)。
在长江、两湖地区,老虎形的礼器出现数量颇多,造型风格都十分接近,如大约在殷商时期的江西地区所见青铜礼器;湖南发现的虎食人卣、虎纹铜钺、四虎铜镈等。上海博物馆也收藏了形状相似的四虎铜镈。曾在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太保方鼎,似乎也具有南方礼器的风格;时代相近方鼎的双虎器耳的形状亦相近*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5》,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西周1》,图七。线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布伦戴奇藏品(B60B954)(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荆州江北农场出土的西周早期虎尊,也保留了商时代江南虎形器的特点:长开口、獠牙外露而立,但这种虎尊形状属于进一步混合折衷风格造型,把獠牙猛虎的脚做成了马蹄的形状。
湘潭县出土豕尊的造型,相当符合该地区虎形器的文化传统脉络。据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推论:古代对野猪的崇拜和对老虎的崇拜,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互相结合在一起;在礼器的传承演化中,老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对野猪的崇拜。但是,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此种现象呢?
笔者推论:不再崇拜野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猪的驯化使得人们对野猪之类肉食来源依赖度下降,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野猪作为必须狩猎、搏斗的对象,以及其所有的恐怖敌兽形象消退了。同时,老虎作为山林主宰的形象则更加地被突显出来。到了新石器晚期,山区猎民基本上也脱离了游猎的生活方式,到处可见将驯养动物作为获取肉食主要来源的策略,而狩猎则相对地次要化了。我们从两湖山丘地带遗址的情况可知,这里的人群已基本上开始定居,从事驯养、渔猎和制造石器的活动。新石器晚期很多山丘遗址亦出现专业化生产,成为石器制作坊,与平原居民进行交易。其时虽然他们的狩猎活动依然不少,但对生计的重要性却逐步退化,这一类活动本身反而强化了统治者获得权威性的“掌握”领土、资源、权力之意,猎获主要用在大的祭祀典礼、或是具有政权意义的活动里,较少作为日常的食物。
至于老虎的形象,对当时出去狩猎的人们而言,老虎并非因肉食来源为狩猎对象,其中潜藏更多意义,老虎本身是崇高万能的狩猎者,同时也是猎人们在山林地带间的竞争对手和威胁对象;老虎还是在古人从事狩猎、接触自然界时,所认识的最强猛兽,因此而神化了它。也因为这个缘故,江南山地的猎兵崇拜老虎并追求学习,获得它的崇高力量,以超越老虎而确认自己的崇高权威。并且,崇拜老虎的信仰还具有一种关键意义:老虎是森林主宰、山地之王,能够与老虎合为一体的人,即是崇高的巫师,自己便能够成为自然界的神王,在山顶上、也就是最高的境界上,掌握崇高生命的权力。
上述时代与观念的变化,演变到后来,使得对野猪的崇拜往往次于对老虎的崇拜,也因此,獠牙的造型逐步开始被理解为“虎口”。(今日所谓之“犬齿”,在传统中常通称为“虎牙”。)从诸多礼器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出,在山地猎民的心目中,虎口的形象更近似于某些农耕先民所强调的“龙嘴”*关于“龙嘴”在上古文明的象征意义,参看郭静云:《由礼器纹饰、神话记载及文字论夏商双嘴龙神信仰》,《汉学研究》第二十五卷,第二期,2007,页1-40;郭静云:《夏商神龙佑王的信仰以及圣王神子观念》,《殷都学刊》2008年1期,页1-11;郭静云:《“大禾方鼎”寻钥──兼论殷商巫觋的身分》,《艺术史研究》第13辑,2011年,页75-112;郭静云:《殷商自然天神的崇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520-548等。,成为了一种概念性的神化通道。
石家河文化晚期出土的部份神面像中的獠牙,已不太像野猪獠牙,其露出的牙齿比起过去更加接近虎口的形状。可见当时的野猪崇拜应已失去了其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对老虎的崇拜更加兴盛。从高庙兽骨和松溪口白陶刻纹来看,这种转换应该在高庙文化就已经发生了。在此之后,石家河文化晚期阶段(或所谓的“后石家河”阶段)突然出现了很多玉器,其中老虎和獠牙面像的造型图特别多。以笔者浅见,这或许可以视为:作为山地族群的高庙文化后裔中的某支,从山地而下至江汉平原,并可能取得了统治者的身份。过了几百年后,在三星堆和吴城文化的礼器上,我们依然可见到这种獠牙面像,除了前文所提的玉面像外,吴城文化铜面像的牙齿形状亦如此(图7:3)*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合编,《长江中游靑铜王国:江西新淦出土靑铜艺术》,香港:两木出版社,1994年,图20。
吴城文化新干大洋洲墓中,出土了殷商时期的獠牙铜钺。大体上说,中原最常见的铜钺造型是龙张开口、或双龙、双虎饕餮的构图(图7:1—2),以表达用钺斩首时,饕餮吞噬人牲,接受神杀祭礼,而将祭牲送回天上之意。但新干出土的铜钺却仅露齿咧嘴,并无饕餮的结构(图7:4)*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合编,《长江中游靑铜王国:江西新淦出土靑铜艺术》,图52。。依笔者浅见,新干铜钺的獠牙即是虎口,尤其是其牙齿形状与新干出土铜虎的牙齿相同,在吴城文化信仰中,此“虎口”便象征了虎神吞噬人牲的信仰。

图7
1.郑州市人民公园出土的殷商时期的铜钺;2.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钺;3.新干大洋洲墓出土的青铜面像;4.新干大洋洲墓出土獠牙铜钺

图8
1.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虎食人卣的刻纹;2.安徽阜南龙虎尊的虎食人刻纹;3.三星堆龙虎尊的虎食人刻纹;4—5、西北美洲原住民虎食人的萨满雕刻;6.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巴塔克人的短剑象牙柄端的虎食人雕刻
在战国、汉代的文献中,“虎口”譬喻极危险的境遇,如《战国策·齐策三》曰:“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史记·叔孙通传》载:“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589;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页1085。但对崇拜神虎的古人而言,被神兽吞食的人经过此一神秘过程,便可获得它的神力及保护。李学勤先生推断:“吞食象征自我与具有神性的动物的合一。……虎食人或龙食人意味着人与神性的龙、虎的合一,这不失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43。此说法无疑是准确的。中国青铜文明对夔龙饕餮或对神虎的崇拜,都是以龙口或虎口的吞食——神化功能为信仰核心。
大约在殷商时代,南方文明对虎神崇拜的造型刻画,已很明显地描绘出虎神吞噬人类的核心信仰传统。湖南宁乡出土的两件虎食人卣,其上的神虎造型也是做露出虎牙、啃咬人头之状,安徽阜南县朱寨镇和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造型,其蕴含之意也相同(图8:1—3)。本信仰的范围包含西南之雪峰、武陵、大巴山脉,又跨到湘赣之罗霄山脉和湘粤桂五岭山脉。依笔者浅见,这或许都属于传承自江南山岭一带对老虎的崇拜信仰,并同时将虎神的形貌与平原地带龙形饕餮的形象连接起来。老虎吞噬人头的图案亦可在弗瑞尔艺廊收藏的玉长刀上见到,该玉刀被视为相当于石家河时期的遗物,但可惜没有发掘资料,因此我们不清楚它的断代和出处,不过,其刻纹技术与风格,确实是符合石家河及龙山时代的。*林巳奈夫(日)着、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页234。
在南方礼器中,饕餮形的“二虎共首”或夔纹虎神,都表现出正在吞噬人,或咬断人头的形象。一直以来,学界对于虎食人构图的象征意义讨论不辍,张光直先生认为:人头放在猛兽嘴里,并不等于被吃;猛兽只是抱人,而这人的身份可能是巫师,猛兽抱着他嘘气放风,可帮助巫师通天。*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年,页333;令参施劲松,《论带虎食人母题的商周青铜器》,《考古》,1998年第3期,页56-63;卢昉,《论商代及西周“人虎母题”青铜器的内涵及流变》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等。但这种观点恐不符合古人对猛兽的认识,如果人头在老虎的牙齿之间,岂能有不被咬杀的可能性?但这种咬杀在当时信仰观念中,带有进入永生境界的神秘入口的意味。
福莱瑟先生(Douglas Fraser)将虎食人卣联系到西北美洲原住民(阿留申人(aleut)或爱斯基摩人(eskimos))的萨满雕刻(图8:4、5),以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Sumatera)巴塔克(Batak)人的短剑象牙柄端的雕刻(图8:6)*Douglas Fraser. " Early Chinese artistic influences in Melanesia?"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a symposium arrang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August 21-25, 1967, edited by Noel Barnard in collaboration with Douglas Fraser. New York: 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1972, v. III, pp. 631-654, ills.14-16.。被神兽吞食的人经过此神秘过程,便可获得它的神力及保护。从礼器的结构来看,美洲和印度尼西亚的偶像,有可能便是源自江南的巫觋文化。
甲骨金文中,除了从“虎”、“虍”的地名和难以考证的族名之外,还有从“虎”、“虍”的社会团体和政权结构,其涵盖属性也颇为多元:既有殷商王族族团的虎族,亦有殷商侯国的虎侯,又有虎名或从“虍”名的殷周境外的国家。笔者依然以为,族名或国名与老虎有关系,表达该族群或社会对自己的认识,并涉及崇拜习俗和精神文化。了解这些族群的发祥地和国家的地望,有助于理解对老虎信仰多元的发祥地和内在意义。因此下文拟进一步讨论,商代时期虎名的社会团体和政权结构之地。
欲讨论殷商文明对老虎的观念,除了礼器之外,甲骨文也是了解老虎在文化中意义的重要材料。殷商的甲骨文,虽然大部分代表着殷商王族的活动纪录,但从甲骨卜辞所提及有关老虎的叙述中,应该还是可以看出其文化多元的面貌。
在甲骨文中,“虎”字的出现率偏高。虽然很多卜辞是残缺或意义不明的,但基本上却依然可以被归为两大类:狩猎或向老虎猛兽等神兽咒祷,以借其神力;以及“虎”字被用作地名、族名和国名的记录。殷商时期有几个以虎为名的国家,与殷商处于敌对或联盟的关系。其中之一便是虎方,在所有殷商时期以虎为名的国家中,它的历史最为悠久,且所在的位置无一不是在南方。因此下文拟从虎方的地望问题,加以思考江南崇拜老虎族群的历史。
二 虎方之地望考
虎方的记录最早出现在武丁晚期的卜辞里,即与殷商虎族和虎侯的记录年代相近,但是虎方是商王国边疆之外的另一国家,提及虎方的卜辞如下:
……虎方?十一月。《合集》6667
笔者不认为,“途”字宜读为“除”*郭静云,《由商周文字论“道”的本义》,《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页203-226。,所以卜辞的意思是:十一月王令望乘暨行到虎方。这应该是军事旅行,占卜了军事的胜败,并祈求祖先支持保佑、卜问可否出兵。
有关虎方地望问题,学界一致认为其位于殷商边疆以南,但具体的看法却有分歧。其中,丁山、岛邦男、钟柏生先生认为这是淮南地区的古国,或是周代所谓的淮夷之国*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台北:大通书局,1971年,页150;岛邦男着、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804;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页223。;孙亚冰和林欢先生则认为:“虎方在今汉水以北,安陆、京山以南的地区。”*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商代史·卷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436。彭明瀚先生认为:“虎方的地望定在长江以南、南岭以北、鄱阳湖——赣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东……吴城文化和费家河类型商文化便是虎方的考古学文化。”*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101—108。而吴志刚先生则更确定地将之连接到吴城文化:“虎形象作为装饰艺术母题是吴城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除显然有某种特殊含义的伏鸟双尾虎外,新干大洋洲出土有虎形象的鼎达13件之多。吴城也出土过8件卧虎耳圆腹鼎。这在其它考古文化中都是少有的现象。能在重要礼器‘鼎’上广泛饰虎,显然虎的形象对吴城文化的族群有特殊意义。”*吴志刚,《吴城文化族属源流考辩》,《四川文物》2011年第1期,页50―58。
甲骨文中的虎方记载仅见于武丁时代《合集》6667卜骨上。不过,北宋重和戊戌岁时在湖北安州孝感县曾出土了西周早期中方鼎,在其铭文上亦有提到虎方,其文言曰:
隹(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或(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王世民主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后引简称《集成》)器号2751,藏处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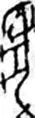

孙亚冰和林欢先生认为,既然中方鼎出土在孝感,那么虎方的位置应离孝感不远,或在随州羊子山附近,不可能到湘江、赣江之远*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页434―437。。但这种理论较为薄弱,因在孝感出土铭文上的记录,未必就只能诉说距离出土地点范围很窄的情况,甲骨金文显示:殷周时期战争实际发生的距离未必那么近。因此,当时掌握汉北地区的周室贵族,可能有意图往外扩展自己的影响或掌握一些江南资源,亦有可能当时的商周政权需面对南方势力往北扩展,故而不得不采取某些防守措施。铭文说“伐反”的用词,可能代表当时的汉北地区正是南北势力的战线区,南方政权往北扩展势力,而周伐反,要固定、加强自己势力的南疆。
从空间的关系来看,从汉北地区到洞庭湖和鄱阳地区的距离相同、路途便利,因此彭明瀚先生所提出的范围,符合中方鼎的出土情况。在武丁晚期,商的领土范围应该最宽,以笔者浅见可能以汉江为西南境。位置接近汉口的盘龙城宫殿区,在第六、七期之间出现毁灭的痕迹,恰好相当于武丁时代,很可能与《诗·商颂·殷武》所言:“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有关*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十三經注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页2216-2217。。而且,盘龙城被毁灭后,第七期恰好出现了很多北方的兵器等遗物,有可能与北来的殷人有关。是故,笔者认为,武丁晚期殷人掌握的领土到达汉口,而虎方国地理位置在此之南,是为江南。
根据目前考古资料,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假设:第一是虎方位于湘江流域,曾经在岳阳、长沙宁乡、邵东县出土的青铜器(包括虎食人卣、四虎铜镈、虎纹铜钺等)属于虎方国的礼器。第二是虎方位于赣江流域,吴城文化即是原称为“虎方”的古国网络。虎形的大礼器,实可以视为古国命名为“虎”的指标。宁乡虎食人卣揭示了崇高虎神为当时当地身份极高的神兽。荆州江北农场出土的西周早期虎尊也可以视为同一文化脉络的礼器,出土的地理范围也相符。虽然在吴城文化遗址出土的虎形礼器可以表达一个系统,但湖南零散出土的虎形器不比江西少或差。
此外,笔者认为,虎方此一国家文明的发祥地究竟为何的问题,可能离不开早期华南地区拜虎信仰的发祥地的原因。从新石器以来,虎形的礼器普遍出现在两湖地区,并且,考古资料显示其来源乃是位于湖南山林地带以高庙为代表的文化;不过与此同时,凌家滩的虎形礼器亦说明了一件事:神虎的形象早已跨过了罗霄山脉,而从雪峰山脉、武陵山脉、南岭扩大到怀玉山、潜山脉等范围广大的江南地区。因此,虽然从原始的发祥地来看,湖南似乎较为符合虎方所在之地的条件,但到了青铜时代早期,江西地区一样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定虎方就是位于这两地的其中之一,而仅能期待更多商周时期的地下材料出土,好让我们能更进一步地了解商周时代江南地区,不属商周的古国文明。
从吴城地望来说,新淦离汉口距离较远,但顺着赣江,新淦到九江的地区,可能都是古吴城文化网络。另外,汉口和吴城地区之间恰好有颇为关键的金属矿,对殷室和周室来说,掌握金属矿的可能性无疑值得发动战争。从殷周发动战争目的来看,往洞庭湖湘江的战争,可能多有一些中方鼎所录“反伐”的意义,即掌握汉口核心据点,以及掌握一些其它资源。往鄱阳湖赣江的战争,虽不大可能涉及“反伐”,但会有掌握金属矿的关键动机。换言之,从目前资料来看,洞庭湖湘江和鄱阳湖赣江,两地都有可能是虎方所在之地。


传世文献也有可供思考的线索,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言: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佰、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页523―524。
司马迁所载的传说,或许与虞侯簋的铭文所表达的事情相关,即显示出西周中期周和吴的关系;或在古代吴城的北疆上,周王室建设了吴(虞)侯国,以南、北之“虞”的分别,画上了周室影响范围的南北之线;又或者,春秋时期晋吴之间的关系,即奠基于此背景之上。

“虎”和“虞”的关联性,同时亦可成为支持虎方为湘江流域的假设之原因,是在传世文献中,“虞”为舜帝的朝号,而舜又被称为湘君,指涉湘江的地域范围。虽然后期传世文献皆把舜的活动地解释成河南、山西地区,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情况隐藏着后期神话遭到人为修改,以及涉及到殷周以来统治中心位于黄河流域的因素,所以记载过去历史时便把殷周以来的统治中心连接到记录者的国家中心。从文献中所透露出的,少数和正统历史不相符的痕迹,包括舜为湘君的说法也在内,可能都恰好保留原来的传说意义。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正义》引《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兴县东南一百里。皇览冢墓记云舜冢在零陵郡营浦县九疑山。”*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页30―33。《汉书》亦描述武帝在元封五年“望祀虞舜于九嶷。”*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96。湖南永州宁远县迄今被传为舜陵之地。这也是虞舜之地与湘江流域有关的痕迹。此线索及直接将湘江流域称为“虞”之地,在讨论虎国的源地亦值得参考。
换言之,所有的资料给我们指出湘江、赣江的地域,但不能让我们选择其中之一为最有可能的范围。《春秋左传·哀公·四年》载:“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李学勤先生认为,“夷虎”即是商周虎方先民;根据《春秋左传·哀公·四年》这一条文献所言,虎方之地不在荆楚之北*李学勤,《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事实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页5-9。。虎方为湖南地区的国家可能性很大,只是可惜没有材料能够提供绝对的答案。
以笔者浅见,现有的虎神崇拜线索、甲骨金文的记录、传世文献中零散的痕迹,均可以支持彭明瀚先生的看法:虎方的地望应在长江以南、南岭以北、鄱阳湖——赣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东,可能也是湖南地区的古国或古城文明的网络,或者是吴城文明的总称、虎国的国名(有可能在历史上曾被改成虞国),或表达“虞”和“吴”字的关系,又或者涉及到虞舜的神话。湖南地区对虞舜的传说极多,可以作为用来间接地补正虎国其源在湖南地区的参考,然而却难以确定实际位置。再进一步思考,虎方未必只是一个小国而已,虎方可能是相对殷或周的一个南方大型的古国网络:华北以殷周,江南以虎方,而湘江和赣江流域的古城都是虎方此网络下之属国。
三 结 语
从零散考古资料可以推论:整个广大的江南地区崇拜老虎的传统,乃是源自于蜿蜒逶迤的江南山脉中古老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本传统的发祥地范围,是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时代则是从新石器中期开始,便可见其逐渐形成。到了青铜时代早期,崇拜老虎的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甚至有可能,公元前2000年左右,拜虎的江南山地族群下到平原开始统治石家河国家网络。到了商周时期,在长江中游的江南地区,或许也曾存在着此一古国网络的广大体系,并以湖南、江西为主要的范围,甚至从其北界跨到湖北、江苏、安徽。而这个古国网络,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之为“虎方”。这些古国的统治者,原本来自山地,从游猎的生活方式,逐步发展出石器和玉器加工业、铸铜业,并学习制造青铜兵器,因此获得并藉以维持其统治者身份。
TheOriginofTigerWorshipinSouthChinaandHistoric-geographicalAnalysisoftheLocationofTigerStateOlgaGorodetskaya
GUO Jing-yun
(The History Fasten,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Jiayi 62102,Taiwan)
The tradition of tiger worship was originated in ancient nomadic cultures. In South China, the tradition of tiger worship has distributed in the area from Wuling to Luoxiao, and possibly reached the Wuyi Mountain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he worships of wild boar and tiger have merged; and later, tiger has generally superseded wild boar as the worship object. The tiger-worshipping mountain people have affected the formation of, so-called, post-Shijiahe culture. During the Yin and Zhou period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especially in the Hunan and Jiangxi areas, there existed a tiger-worshipping network of ancient states, which named as Hufang in the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Southern Chinese tiger worship;Bronze Age in the South of Yangzi River;Gao miao;Hou Shi jia he;State of the Tiger (Hu fang)
2014-01-06
“理论粤军”教育部在粤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资助项目
郭静云(1965—)女,台湾嘉义人,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 广州中山大学珠江学者讲座教授, 史学博士.研究方向: 先秦历史与文化.
K87
A
1008—1763(2014)02—00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