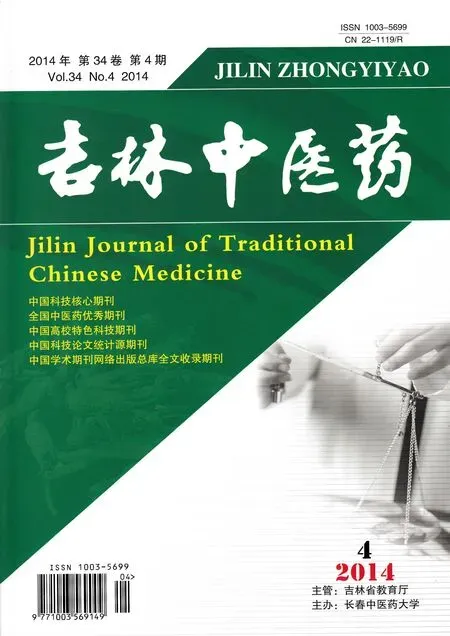《伤寒论》“结胸证”辨析
杨 栋,张培彤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肿瘤科,北京 100053)
“结胸证”见于《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篇,在病因病机及处方用药上有其独特之处。同时,又与“脏结证”“痞证”“少阳证”“胸痹病”“瓜蒂散证”“十枣汤证”等在症状上有相似之处。明确“结胸证”的脉因证治,辨析其与类似证的区别与联系,对于领会仲景处理以结滞不通为主要表现病症的思路大有裨益,同时也为临床上正确辨识“结胸证”类病症并施以正确方药打下基础。
1 “结胸证”的脉因证治
1.1 “结胸证”的病因病机 仲景将“结胸证”的病因总结为“病发于阳,而反下之”,张隐庵认为此处“病发于阳者,发于太阳也”[1]。阳经有三,即太阳、阳明和少阳,仲景在“病发于阳”后面用了“反下之”,可见此处应用下法是属误治。在三阳为病中,太阳宜汗解,阳明宜通下,少阳宜和解。可见,若此处的“阳”是指阳明,则下法属于正治,而不应以“反”字对此加以否定;若此“阳”是指少阳,则病当有“寒热往来”的少阳证表现,因而,此处的病发于“阳”应是指太阳而言。而对于太阳为病,或寒伤营而为伤寒,或风伤卫而为中风,前者为阴,后者为阳。舒驰远[2]认为此处“病发于阳,为风伤卫”,因阳位高居于上,所以误下后容易引邪深入而结硬于胸部。因而,更确切的说,此处的病发于“阳”应该是指太阳中风证。而若是太阳中风证,出现诸如发热、汗出、恶风、脉缓等表现,医者自当应用桂枝汤类方剂以发汗祛风,但此处却使用“下”法,因而可以推测此处的太阳中风证必有内入阳明之势,必伴有口渴、便干、心烦等“可下”之症状,黄元御[3]曰:“病发于阳者,多入阳明而为热”。在脉象上,这种太阳中风证伴有里热渐成的脉象,表现为“脉浮而动数”,“数”即是阳气不得通达累积在表之象。里热虽见,但表邪未解,病在表者,当先解表,若过早使用下法,容易损及中气,使得升降逆施,表阳内陷,与水气互结于胸部而成结胸。综上所述,结胸证的病因为太阳中风证误下所致,核心病机为水热互结于胸膈。

“结胸证”的基本脉象为“寸脉浮,关脉沉”,关部脉沉为中阳不足,阴邪盘踞之象,为“医反下之”,挫伤中气,升降逆施,浊邪停滞所造成,这个中气受损的过程在脉象动态变化上体现为“动数变迟”,而下法所造成的脉象结果自然是“脉沉而紧”。此处脉象之紧,汪苓友[1]认为是指实邪结聚之深而言,非指寒邪凝滞,指出:“邪热当胸而结,直至心下,石硬且痛,则脉不但沉紧,甚至有伏而不见者,乌可以脉沉紧为非热耶。”[1]水热结于胸部,上焦之气壅阻而不得下行,气机壅滞于胸膈之上在脉象上体现为“寸脉浮”。
1.3 “结胸证”的治疗 针对“结胸证”的病因病机以及临床表现,仲景处以大陷胸丸、大陷胸汤以及小陷胸汤予以治疗。大陷胸丸由大黄、芒硝、葶苈子、杏仁、甘遂、白蜜组成,其中,大黄、芒硝通降腑热,给胸中之热开通去路,葶苈子降泄肺中之饮浊,杏仁通肺气之滞,甘遂逐胸胁之水,用白蜜为丸,意在缓和诸药之力,防中伤阳陷,体现仲景固护脾胃思想[4]。此处用丸剂意在缓和,因此证病程较“大陷胸汤”证病程稍长,“项亦强,如柔痉状”可为时间较长之佐证,病程长则正气虚损,因而用丸剂可以起到缓下结热、顾护正气的作用。故尤在泾[5]言:“大陷胸丸以荡涤之体,为和缓之用,盖以其邪结在胸,乃至如柔痉状,则非峻药不能逐之,而又不可以急剂一下而尽,故变汤为丸,煮而并渣服之,乃峻药缓用之法。峻能胜破坚逐实之任,缓则能尽际上迄下之邪也”;相对而言,大陷胸汤证的病程则稍短,正气尚足,因而其主要由大黄、芒硝、甘遂3味药组成,效专力宏,意在速下结热,以防日久伤及正气[6];除大陷胸汤和大陷胸丸外,在“结胸证”的治疗上还有小陷胸汤一法,小结胸证较大结胸证范围小、病势缓、病情轻,汤既有大小之别,证亦有轻重之殊,小结胸证在病机上与大结胸证亦稍有不同,大结胸为水结在胸腹,故其脉沉紧,小结胸是痰结于心下,故其脉浮滑,因而在用药上并未应用诸如大黄、甘遂等峻猛之药,而是以黄连、瓜蒌和半夏3味为组成,黄连可除心火之烦,瓜蒌可去胸中之浊,半夏可降胃气之逆,三药相合使得热去结散,自然小结胸证邪祛病愈。该方组方简单,剂量较轻,因邪气仅陷于中焦脉络,未及于下焦,是名小。
2 “结胸证”与类似证的辨析
2.1 与“脏结证”的辨别 “结胸证”与“脏结证”有共同的特点即“结”,即两者都存在结滞不通的症状,因而仲景在描述“脏结证”的临床表现时指出“如结胸状”。然而,“结胸证”与“脏结证”在病性上有阴阳之异,“结胸证”属阳,“脏结证”属阴,因而,原文中特别提出“脏结无阳证”,意在与“结胸证”区别开来,而原文中所说的“不往来寒热”显然是为了与同样具有结滞不通症状的“大柴胡汤证”相鉴别,而“饮食如故,时时下利”的描述也提示病在脏间非在胸胃。“脏结证”的阴象突出表现在舌象上,即“舌上苔滑”“舌上白苔滑”,此种舌象表明阳气微弱,一派阴霾,故“难治”,更因阳气衰微而“不可攻也”。在脉象上,虽然“结胸证”与“脏结证”均有寸脉浮的表现,但是关脉的形态却大相径庭。“结胸证”表现为“关脉沉”,而“脏结证”表现为“关脉小细沉紧”,小、细、沉、紧的脉象再次表现出“脏结证”的阳气微弱。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经方名家胡希恕[7]提出“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的“痞”实为脏结而非痞证,认为此痞是指痞块而言,后文中的“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脏结,死”可以作为佐证,从文中描述可以推测,此处的“痞”与现代的恶性肿瘤类疾病有相似之处。
2.2 与“痞证”的辨别 “结胸证”与“痞证”在病位上同属于心下,在病因上均是由于“医反下之”所造成,所不同的是,“结胸证”在下之前是“病发于阳”,而“痞证”在下之前属于“病发于阴”,“病发于阳”者阳气偏盛,“病发于阴”者阳气不足。在应用下法之后,下伤中阳,脾胃升降逆行,导致脾气不升,胃气不降。对于“病发于阳”者,胃气不降导致胃腑之阳阻于胸膈,与水互结而成结胸;对于“病发于阴”者,胃气不降导致胃中浊阴阻于心下,阻隔胆胃之气而成痞证。就临床症状而言,“结胸证”以“心下痛,按之石硬”为主,而“痞证”以“心下痞,按之濡”为主,“结胸证”以阳热表现为主,故多以峻下之药通腑泄热,“痞证”以上热下寒为主,因而用药多寒温并用以清上温下。黄元御[3]指出:“未成阳明,下早而成结胸,将成太阴,误下而为痞,则阳明不成阳明,太阴不成太阴”。
2.3 与“少阳证”的辨别 少阳经循胸胁,夹胃口。若少阳之气不降,阻于胃口,浊阴壅塞易成心下硬满之证,因而与结胸证有类似之处。陈亮斯认为“结胸证”乃“邪留胸而及于胃,胸胃俱病,乃成结胸”“如胸有邪而胃未受邪,则为胸胁满之半表半里证,如胃受邪而胸不留,则为胃家实之阳明病,皆非结胸也”[1]。可见少阳证之心下硬满多偏于胸胁,且往往伴有往来寒热、痛连胸胁的症状。病在少阳则以和解为法,故多以柴胡剂治之,《伤寒论》中大柴胡汤、柴胡桂枝干姜汤、柴胡桂枝汤所治之证均有心下或胁下硬满的症状。此外,若太阳与少阳并病,太阳不升,少阳不降,浊阴壅塞于胃口而见心下硬满,也与结胸之情形相似,然而太阳与少阳并病除胁下硬满外多兼有“颈项强”等太阳表邪未解及“往来寒热”等少阳枢机不利的表现。若妇人经期伤寒或中风,邪热入于血室,结于厥阴肝经,也会出现胸胁硬满的状况,而妇人经期感寒因热扰血室,在出现胸胁硬满的同时会伴有精神异常症状。
2.4 与“胸痹病”的辨别 与“结胸证”类似,“胸痹病”亦以疼痛为主要表现。从病位而言,“结胸证”多位于胸膈、心下部位,甚则累积少腹;“胸痹”多涉及胸背,甚则“胸痛彻背、背痛彻心”。从病因而言,“结胸证”为“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经热内陷胸膈而成;“胸痹病”则“责其极虚也”,为胸阳不振,阴寒凝滞所致。从脉象而言,“结胸证”主要表现为“寸脉浮,关脉沉”;“胸痹病”主要表现为“阳微阴弦”。从治疗上而言,“结胸证”以陷胸类方剂为主,主通腑泄热,逐水涤饮;“胸痹病”则以瓜蒌、薤白、白酒等药为主,主温振胸阳,逐痰涤浊。

2.6 与“瓜蒂散证”“十枣汤证”的辨别 “瓜蒂散证”乃痰浊横塞胸膺,出现胸中痞硬的症状,此处与结胸证的不同点在于由于浊阴填塞胸膺,气机不得下行,在一派浊阴之象的同时出现“气上冲咽喉,不得息”的表现,可以作为与“结胸证”的鉴别。“十枣汤”证同“结胸证”的共同点在于水饮结于胸胁,但“十枣汤”证水饮重而无热,故其临床表现以下利、呕逆、汗出、心下痞等水气中阻的表现为主,治疗上以甘遂、大戟、芫花峻逐水饮,使水祛病止。
3 结胸证的现代临床治疗
根据临床表现,大陷胸汤证与急性腹膜炎、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急性肝炎等急症类似。李常吾[8]认为,《伤寒论》中大结胸证与急性腹膜炎在病因病机、病变部位、临床症状方面具有高度相关性,其病机相似,病变部位相对应,临床症状又因腹膜刺激征,表现为腹痛,甚至呈“木板样”强直,与“心下痛,按之石硬”“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的见症相同。可以说,急性腹膜炎的大多数症状体征,如发热、腹痛拒按等均可用大结胸证的病变机制加以阐释。杨爱华等[9]化裁应用大陷胸汤治疗176例结胸患者,疾病类型涉及急性化脓性胆管炎伴有渗出性腹膜炎、急性胰腺炎等,经治疗后,166例患者获得成功,药后12 h出现排便排气,症状缓解,疾病向愈,治愈率达94.3%。小陷胸汤证与胆心综合征、冠心病心绞痛、哮喘性支气管炎、胸膜炎、胆道蛔虫症、顽固型便秘、眩晕等病症类似[10-11]。聂丹丽等[12]将57例非酒精性脂肪肝随机分为2组,治疗组予小陷胸汤加减,对照组予血脂康口服,治疗后发现2组患者肝功能及血脂均有明显改善,其中,尤以治疗组为优,治疗组B超结果亦有明显改善。郭思景[13]运用加味柴胡陷胸汤(柴胡、黄芩、黄连、半夏、瓜蒌、白芍、枳实、木香、槟榔、大黄、芒硝、金银花等)治疗急性胰腺炎56例。结果显示临床治愈54例,治愈率达96.43%,平均治疗时间5.32 d。与抗生素对照组相比,中药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疗程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1)。
4 体会
通过对“结胸证”的病证分析可以看到,《伤寒论》的条文前后互参,左右互证,条理清析,层次分明。学习《伤寒论》的过程应该做到全局把握,前后联系,注重细节,揣测医圣言外之意、话外之音。金东明教授[14]认为,学习《伤寒论》,应从伤寒学术脉络入手,知其始,知其传,整理、校注、阐释、法方类证、后世发挥,应无一不通。只有不断的体会、玩味仲景在字里行间表达的医理,才有可能领会仲景的深意,掌握六经辨证的精髓。
[1]南京中医药大学.伤寒论译释[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10:560.
[2]舒驰远.伤寒集注[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134.
[3]黄元御.黄元御读伤寒[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115.
[4]冯兴志.《伤寒论》“保胃气”思想源流探析[J].吉林中医药,2010,30(5):452-454.
[5]尤在泾.伤寒贯珠集[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43.
[6]郭强中.《伤寒论》中“控水论”之下法探析[J].吉林中医药,2012,32(1):10-13.
[7]胡希恕.越辨越明释伤寒[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135.
[8]李常吾.大结胸证与急性腹膜炎的相关性探讨[J].新中医,2007,39(10):5-7.
[9]杨爱华,赵业勤.结胸证176例辨治体会[J].浙江中医杂志,1999,34(10):16-17.
[10]杨锦国,杨泱.小陷胸汤治验举隅[J].陕西中医,2012,33(2):239.
[11]裴惠民.小陷胸汤的临床应用[J].基层医学论坛,2010,14(14):439-440.
[12]聂丹丽,杨成志,崔大江,等.小陷胸汤化裁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临床研究[J].中国中医急症,2005,14(2):116-119,196.
[13]郭思景.加味柴胡陷胸汤为主治疗急性胰腺炎56例[J].陕西中医,2004,25(1):23-24.
[14]金东明.《伤寒论》教、学、研、用、考方法探究[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29(3):563-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