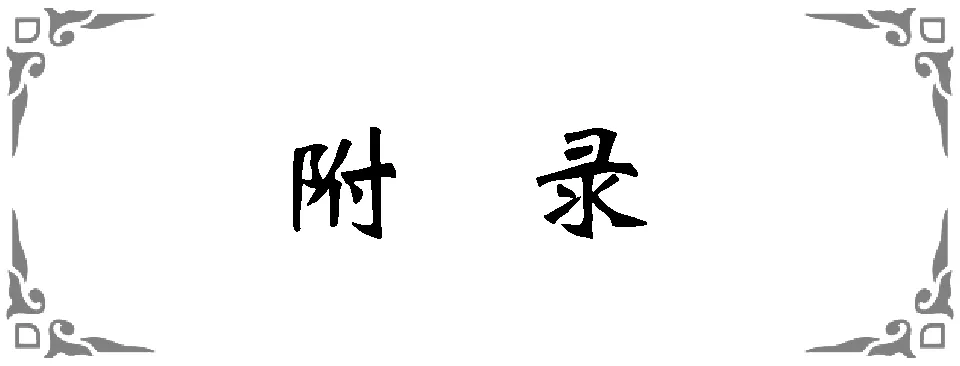忆贾芝兄弟二三事
贾芝的故乡是山西省襄汾县古城镇候村,家里共有四个兄弟姐妹,他是长子,弟弟贾植芳生前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他最小的妹妹——贾宜静是我祖母,她一直生活在家乡,她的生活轨迹与哥哥姐姐大相径庭,在丈夫去世后一直在小城镇与三儿一女相依为命。1997年元旦她先两位哥哥而去,在此根据她孩子们的口述与我自己的记忆完成下文,谨此纪念我最敬爱的祖母。
一、 传说中的“盛世大家”
生活在小城镇,但是曾经在延安抗大二分校完成学业,奶奶的经历与周围生存环境格格不入。小城镇邻里间最大的喜好就是妇女间吃穿用度的攀比。她从来不参与这一行列,总是在家淡淡地说:“我家当时都有,这些算什么,黄金、珍珠、貂皮多了去了。”当时尚处于20世纪80年代初,粮油等日常用品都还紧缺,何况这些奢侈品。儿子,尤其媳妇总会笑笑,但是困窘的生存环境,他们只当作神话听听而已。这并未影响她对自己家的描述。
她说自己家房子是伯父仿照《红楼梦》中的格局建造了两座一模一样的院子,一座在山东济南,一座在古城镇候村。院子的石雕、木雕都极其精美,石匠和木匠在他们家做了三年工才建成。他们兄妹在院子里一起生活,家里请了专门的私塾先生,大哥贾芝学习很好,经常被老师表扬,二哥贾植芳不喜欢学习,是批评的对象。40年代他们全家从黄河渡口——山西吉县壶口到陕西宜川避难,这座院子交付家里的长工总管负责,当他们回来的时候,院子已经成了一堆灰烬。日本人进驻后,院子一度是日本驻军司令部,当他们撤离时,当地一个汉奸力劝烧毁,因为这座院子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奶奶经常说起的一句话就是,什么财产都没所谓,人活着最重要,他们家最大的成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家没有伤亡。大哥贾芝在北京工作,二哥贾植芳在上海工作,姐姐(因病早亡)全家也在北京。现在生活的“两进三处”的大杂院,曾经是她父亲于新中国成立前购买的住宅,现在自己家也就住着三间北房,两小间南房。“盛世大家”只存在于她的描绘中,我父亲、叔叔、姑姑谁都没见过,现在仅存的建于清代的院子,也是六七家拼着住,原本精致完美的砖混清代院落变得杂乱无章。
倒是偶尔有两三位候村人到家里做客,老人们经常描述“老东家”贾国恒(他们的父亲)的一些闲闻趣事与贾家的财大气粗。记忆最深的就是奶奶讲述她们到陕西避难(到宜川和延安居住过),因为当时“二战区”要搜身,但他们不搜女人,所以她父亲让她随身携带着几斤重的一块黄金,途经一户人家,在那户人家借住的时候,她到厕所的路上,不小心把金子掉了。她很是难过,最初不敢告诉父母,神情沮丧地躺在床上,父母以为她病了,后来无奈她告诉了父母真相,她父亲只是淡淡地说:“没所谓,丢了就不是咱家的。”他们都清楚就掉在了那户人家。奶奶说,后来那家人一直出事,直到把几斤黄金花费完了。这个讲述最后总是以“我们全家都认为散财消灾”结尾。尽管童年时期,对几斤黄金没有概念,但“散财消灾”却深入心灵。
二、 引以为傲的两位老舅
当时全国交通很不发达,北京、上海对于小镇人而言只是两座大城市的名称。但是因为有奶奶的两位哥哥,这两座城市与我们家有了联系,家里经常会有北京和上海的来信、著作,北京果脯、上海大白兔奶糖等。著作因为家人的学术水平有限,阅读的人很少,主要读者就是奶奶自己。她经常告诉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书,这才是最重要的财产。
物资匮乏的年代,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果脯和大白兔奶糖。以至于我第一次到了北京、上海,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传说中卖果脯的王府井大厦和大白兔成堆的南京路。对于奶奶的两位哥哥——老舅(山西襄汾如此称呼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舅舅)们的学术成就,我估计包括奶奶在内谁都不明白,只知道大老舅贾芝在北京社科院(当时不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社会科学院是两个单位),看到过他的作品,都以为是诗人。
在我们读小学时,奶奶讲起她大哥是李大钊的女婿,我们小学课本上《我的父亲》一文就是李星华口述,大老舅记录整理的。二老舅贾植芳是复旦大学的教授,给家里邮寄过《狱里狱外》,奶奶经常“强迫”我们阅读,但当时谁对书籍都不感兴趣,只是瞄过几眼,知道这些书是老舅们的作品。奶奶总是强调:“他们才是大人物,比咱们那些镇长之类的(当时脑海中最大的官员就是县长)出名多了。”
三、 老舅们的故乡之行
传说中的老舅们进入现实生活是1986年的事情。两位老舅在很多人的陪同下到了古城家中,这是家中的大事,向学校老师请了假,专门回家照相。因为年岁较小,不太理解家长的行为,但是照相当时尚未走入寻常百姓家,提起照相激动无比,但对老舅们倒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在大院的中间,灰突突古旧的两层楼外,全家二十几口人一起照了“全家福”。至今家中还保留着这张照片,老舅们在家住了两三天就离开了,留下的是大老舅贾芝稳重温存和二老舅贾植芳爽朗谐趣的印象。
之后奶奶家客厅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就压着两张重要的照片,一张彩色的“全家福”,一张兄妹三人开怀大笑的彩色照。至今父亲、叔父、姑姑、母亲依然记得,贾芝当天晚上请大家讲民间故事,我母亲很擅长,专门请她讲述了“金砖窑”(南蛮盗宝型)的故事。对于贾植芳的印象,大家只记得“提到古城房子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咱们觉得冤枉,就到县府大堂外举着状子喊冤去。”贾芝很无奈地说:“你总是那么调皮、没有规矩。”
我们家记忆力最好的是二叔毛顺明和姑姑毛荣明,他们能够记住家中所有事情的细节,对古城镇也非常熟悉,几乎认识小城的所有人,尤其是东街社区的。现在由于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家人相聚甚少。只要团聚,二叔除了做大量我喜欢吃的美食外,就是讲述我奶奶家的事情,他希望我可以记述这些事,只可惜我笔拙词钝,他们的希望也付之东流。2008年、2009年、2012年在相聚的不同场合,二叔毛顺明都给我讲起过贾芝和贾植芳前往陕西延安和秋林镇的事情。下文根据他的口述整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贾芝无法到北京继续读书,他从家中到了陕西西安,后来去了延安。有一天李星华和弟弟李光华(当时比我妈大一岁)一起到了候村老家,姥爷姥姥知道他们两位的出身,因为大姥爷在济南做生意,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知道李大钊是谁,也知道他们是李大钊孩子,家人以极高的礼遇招待着他们姐弟。他们在老家呆了一个多月,他们提出想到延安,当时晋南小山村候村到延安的路程极为遥远与艰难,而且阎锡山的战时总部就位于黄河边上吉县的克难坡,当时这是到延安的必经之路。姥爷最后派了长工玉玉(记音),赶着几头骡子,带着干粮,拿着银元将他们先送到了在秋林镇供职的贾植芳处。后来贾植芳联系,将姐弟两人送到了延安。我妈和姥爷姥姥因为日本人打到了古城,他们全家带着必备之物经过黄河渡口——壶口,千难万险地先到了宜川,在那儿我妈跟着二舅找的一位老师学习,这位老师曾在四个国家留过学(笔者注,奶奶的英语一直不错,我们表姐妹、堂姐妹每个人在学习英语前,26个字母都是她老人家教授的),后来又到她大哥工作的地方——延安居住,她也就到了延安中学和延安抗大二分校读书。日本人投降后,他们迅速地回到山西老家。
上述事件与经历,贾植芳在多处撰文提到过,家人的记忆没有年代和历史背景,可能只是事件的一个剪影。
最后还想用几句话说说我的奶奶。奶奶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为了遵照父母之命,她留在了家乡,后来几十年都过着与自己身份、经历极不协调的生活。在艰难的岁月里,她以浆洗衣服、照管自行车、做手工花圈为业,但从来没见她悲伤过,留在我记忆中永远都是她虽然瘦弱,但坚强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