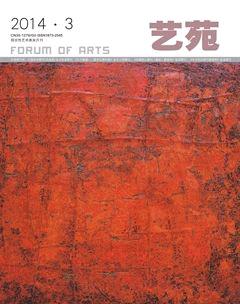“群像”的意义
刘柒否
【摘要】 筇竹寺五百罗汉像是雕塑家在群像观念的指导下完成的。群像并不一定非要有庞大的数量,而是多个个体形象能够融合在一个整体当中;由个体间的互动组成一个或多个组群,并且可以作为整体而存在。这就必然要求整体作品有主次之分,而非简单的排列。正因如此,筇竹寺五百罗汉像便打破了寺院中五百罗汉像简单排列的千年传统,这便使得筇竹寺五百罗汉像在五百罗汉像塑造的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对筇竹寺五百罗汉像的考察研究中,可以揭示雕塑家群像观念的形成及其意义。
【关键词】 筇竹寺;黎广修;五百罗汉像;整体;群像
[中图分类号]J31 [文献标识码]A
晚清,1891年,一位雕塑家完成了自己在云南的创作,准备返回四川老家。临行前,油然而生的不舍之情与常挂于心头的归乡之念,一齐拉扯着他。一幅幅被时光雕琢、早已镶嵌在他的记忆中的画面,轮番在他的脑海中呈现。回想自己当初携弟子不远千里、越崇山峻岭赶来这里,不觉中已是八年前的往事了。八年里,他往来于玉案山上下,居于幽静禅林,与参天古树为伴,与大德高僧为友。晨钟暮鼓间八年光景转瞬即逝,制作雕塑时遗留在身上的泥土、为雕塑着色时沾染在手上的色彩,它们还没来得及被玉案山的清泉所洗涤,苍老的雕塑家便走到了自己的作品前,凝视它们如回望自己逝去的岁月。许久后,一丝难以捕捉的微笑在他的脸上一闪而过。友人的召唤打破了这份宁静。雕塑家随即被邀至古刹的客堂,这是多年来他与友人谈禅论道的地方,而今却成了道别之所。为表达彼时的思绪,雕塑家挥笔落墨,一幅水墨山水出现在客堂的墙壁之上。画中山水交映,一片淡然空寂之境,渔翁泰然,孤帆渐远,旅人惆怅。以此画赠与友人。落款:德生弟,黎广修。
黎广修,字德生,四川合州云门(今重庆合川县云门镇)人。《合川县志》记载,黎广修(1815—?)幼年读书学画,后随其父精学塑像。成年后,能书善画,尤精雕塑,为当时四川著名的民间雕塑艺术大师。1883年,68岁的黎广修应时任筇竹寺住持的梦佛大和尚之邀前往云南昆明,他的任务是完成筇竹寺五百罗汉塑像的创作。黎广修师徒合力,历时八年,终成经典之作。
一、五百罗汉群像
筇竹寺坐西向东,进入山门便是天王殿,然后是大雄宝殿。在天王殿两侧,南有天台来阁、北有梵音阁,两阁是罗汉像的“居所”,另在大雄宝殿内的三世佛的南北两侧也都有罗汉像。以上罗汉像皆出自黎广修师徒之手,这便是著名的筇竹寺“五百罗汉”。
天台来阁与梵音阁,两阁均为三间,其正门皆设在中央一间且都向西开,即朝向大雄宝殿。进入天台来阁,阁门两侧分别塑有罗汉像一尊,迎面正对供奉孔雀明王,其上塑有罗汉像六尊,两侧分别塑有两层罗汉像,每层12尊,共48尊。左右两间根据阁内结构又为充分利用阁内的空间,罗汉像在墙体上的布局有一、二、三层不等,每间76尊。加上从阁外橱窗可见的10尊罗汉像,天台来阁共有罗汉像218尊。梵音阁罗汉布局与天台来阁基本一致,只是在迎面正对供奉的千手观音之上的罗汉像为5尊,比天台来阁中少了1尊,所以梵音阁的罗汉像为217尊。大雄宝殿内的三世佛两侧各塑有罗汉像34尊,即共68尊罗汉像塑于大雄宝殿内,加之在天台来阁与梵音阁的罗汉像,还不止500尊罗汉像。
筇竹寺的五百罗汉像虽名声远播,但是却并没有像其他供奉五百罗汉的寺院那样,设有独立的罗汉堂予以安置。独立的罗汉堂因有足够的空间,便可以将众多罗汉像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布局;每尊罗汉像都要均匀的占用空间;众罗汉像间的间距也需要精准的测算,以便众多罗汉像进行整齐的排列。与宽敞的罗汉堂相比,筇竹寺五百罗汉像的“居所”就显得简陋了,仅天台来阁与梵音阁就聚集了400多尊罗汉像,多少会显得有些拥挤。要想对天台来阁和梵音阁中的罗汉像进行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布局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必须让两阁的立体空间得到利用,所以两阁中的罗汉像多至可上下排成三行;因黎广修师徒所塑的罗汉像追求肢体语言的丰富,常常是弓腰、伸手、抬腿或手持器物,所以每尊罗汉像所占用的空间也不能等同;又因黎广修师徒有意对罗汉像进行世俗化的还原,所以所制的罗汉像往往是两三尊为一组,以形成一种生活化的场景,于是众罗汉像之间的间距也很难做到完全一致。总之,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天台来阁与梵音阁中的400多尊罗汉像绝对算不上是排列整齐。但是尽管如此,观看者还是会得到一份因错落有致而达到在视觉上和谐的感觉,即不整齐但有序。原因在于黎广修师徒在制作这些罗汉像时始终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尽管每个罗汉像体量的大小、肢体动作的幅度、罗汉形象表情的张力等等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却可以在人的视觉整合中达到乱中取静的效果,这有赖于在整体中讲究众多个体轻重缓急的分布,以及对节奏感的把握。从而最终达到风格统一、浑然一体的视觉效果。尤其在塑于大雄宝殿三世佛两侧罗汉像,南北两侧各34尊罗汉像毫无破绽的被雕塑家组织在了一起,虽然人物造型与动态都十分夸张又各具特色,但却不失整体感,如此塑造必然会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俨如一幅蔚为壮观的壁画或浮雕镶嵌于大雄宝殿内壁两侧。
筇竹寺五百罗汉像虽是公认的艺术精品,但是数量众多的罗汉像也不免出现艺术水准参差不齐的面貌。如在天台来阁的左右两间,处于中间一层的罗汉像各有14尊,左右两间共28尊罗汉像明显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准。此种情形同样也在另一侧的梵音阁里出现,即两阁都将最具艺术水准的罗汉像安置在同一个位置,它们在人物造型、动态、神态,衣纹处理等各个方面上都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这一情形向人们传达了两种信息,其一是这56尊罗汉像应该是直接出自黎广修之手,而非他的弟子所塑,而两阁中其他的罗汉像则在黎广修多大程度上参与创作的问题上就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了;其二是黎广修师徒在安排罗汉像布局的时候,顾及到了观看罗汉的视觉问题,因为这56尊罗汉像精品都塑于三层罗汉像的中间一层,常人若观看它们是采取一种微微仰视的视角,而这种适度的仰视较于观看下面一层罗汉像的平视、较于观看上面一层罗汉像的大幅度仰视是一种最佳的观看视角。这56尊罗汉像因对人们观看视线的把握,可以最快的吸引到观看者的眼球——雕塑家们利用人类视觉的选择性,悄悄的提升了观看者对众多罗汉像的整体视觉印象。对此还有另一个佐证,即在需要大幅度仰视的最顶层,或罗汉像整体布局边角,还有需要人们回望才能注意到的地方,有不乏缺少艺术价值或艺术水准相对较低的塑像出现,这些也反过来证明了雕塑家们对视觉效果的重视。不过这种对视觉效果的重视也可能是黎广修师徒塑造能力等差距的权宜之计——首先是五百罗汉像工程量巨大,尽管创作过程持续八年,可凭黎广修一人之力而面面俱到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弟子及助手必然要参与进来;其次黎广修不仅塑造能力超群,而且在书画、诗文、佛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远非其弟子可以轻易企及,所以五百罗汉像艺术水准参差不齐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把黎广修的作品安置在重要的视觉位置上也是合乎情理的。
由此可见,黎广修师徒在寻求五百罗汉像实现一个或多个错落有序的整体时,并没有在这五百余尊罗汉像的塑造上面平均用力,而是根据人的视觉习惯做了主次关系的区分。这一点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是在使用群像的观念来塑造的五百罗汉像。群像并不一定非要有庞大的数量,而是多个个体形象能够融合在一个整体当中;由个体间的互动组成一个或多个组群,并且可以作为整体而存在。这就必然要求整体作品有主次之分,而非简单的排列。筇竹寺五百罗汉像之所以可称为群像,也正是满足了这一要求,整体有主次、人物有互动。对比北京碧云寺和武汉归元寺等寺院保存的五百罗汉像,筇竹寺五百罗汉像最出色的地方恰在于此。前者并没有使用群像的观念来塑造,虽然排列整齐,更抹平了主次关系以及艺术水准的差异,若说凭此便可以容五百尊塑像达到一个整体的效果的话,那么这一整体终究是借助佛教经典中对五百罗汉的记述给出的,而这些五百尊罗汉像自身则不具备将各自组织到一个整体中的能力,所以只能简单称其为五百罗汉像,而不能称其为五百罗汉群像。
二、群像观念的形成与意义
筇竹寺五百罗汉像以群像的观念来进行塑造,这在五百罗汉像塑造的历史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甚至在中国雕塑的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下文重点分析雕塑家群像观念因何种契机而形成及其意义。
首先,筇竹寺五百罗汉像突破了罗汉堂为五百罗汉像提供的总体布局规划的制约。因为寺院中为供养五百罗汉而建罗汉堂时,便要求建筑师们为五百罗汉像的布局做了一个大体的规划,即五百罗汉像在罗汉堂中的布局是建筑师们所考虑的事情,而雕塑家们只负责五百尊罗汉像的制作,制作完成后再按照建筑师们当初对五百罗汉像的布局构想进行摆设即可。与罗汉堂要求众多罗汉像的整体布局相反,筇竹寺五百罗汉像在制作之前便要求雕塑家去考虑如何进行整体布局的规划。筇竹寺中,无论在天台来阁还是梵音阁或是大雄宝殿,它们都不是特意为罗汉们准备的“居所”,这时若雕塑家想在其中陈设众多罗汉像的话,就必须考虑如何利用空间的问题。前者是建筑师在五百罗汉的总体布局中扮演了主角,而这一点于后者则是由雕塑家来完成的。众多雕塑是由谁来负责进行整体的布局规划,决定了雕塑完成后的样态。前者的整体布局规划由建筑师来完成,雕塑家仅仅是个体雕塑的塑造者,这自然不会促使雕塑家形成群像的观念;而后者则因将众多雕塑的整体布局规划交由雕塑家负责,这也自然为雕塑家群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前提。
其次,以群像的观念来塑造五百罗汉像,标志着雕塑家对传统观念的突破。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五百罗汉是中国特色,或者说是汉传佛教造型艺术的特色,而五百罗汉当初之所以能够被请到汉传佛教的寺院当中,最初就是众生平等、世人皆有慧根的象征。所以雕塑家对罗汉形象的制作经常可以摆脱如佛像、菩萨像、天王像那样的限制,它允许雕塑家自由发挥,因为制作罗汉形象就是制作世人的形象,“罗汉眼中皆罗汉,庸人眼中尽庸人”。这其中也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是五百罗汉形象的制作应该体现众生平等的佛教教义;其二是五百罗汉形象的制作应取自于世人凡夫的形象。对于罗汉像取自于世人凡夫的形象这一点来说,并没有什么疑问,因为全国各处保存的罗汉像基本上都具有这一特征,生动且生活化,这也为罗汉形象增添了艺术性;然而在体现众生平等的佛教教义上,五百罗汉像的制作便陷入了语言的困境,因为体现这一佛教教义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将五百罗汉像无主次的平行排列,由于这样的方式根深蒂固,以至于将其他可能性拒之门外,这必然阻碍了五百罗汉像作为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自律进程。黎广修师徒所塑筇竹寺五百罗汉像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并没有顾忌传统五百罗汉像因附会佛教教义中的平等原则而采取的无主次的平行排列方式,而是化零为整,将众多罗汉形象视为一件整体作品,而在这一件作品当中的每个个体形象都成为作品整体中的构成元素——群像的观念已经在指导黎广修师徒对五百罗汉像的创作了。
以群像的观念来塑造五百罗汉像是雕塑家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它突破了传统五百罗汉像的制作因附会佛教教义中的平等原则而采取的将众多罗汉像平行排列的方式。其实还可以把问题放在更广的视野中来看待,即黎广修师徒所塑筇竹寺五百罗汉群像所突破的不仅仅是佛教造像中的传统观念,而是将五百罗汉像,这一传统佛教造像,从佛教造像的范畴中解放出来。因为,筇竹寺五百罗汉群像的塑造已经从原来的受佛教教义主导转换到受视觉艺术的审美原则主导。经此转换后,雕塑艺术的自觉意识开始凸显。既然如此,那么筇竹寺五百罗汉群像便不能再被归之为佛教造像了,因为佛教造像的意义本身就带有宗教色彩,它制造出一个供人膜拜的对象,所以造像一般都要受到教义的限制,而筇竹寺五百罗汉群像则完全是在视觉艺术的审美原则的指导下完成的。
第三是以画入塑。筇竹寺五百罗汉以群像的面貌出现,这与黎广修的能书善画有着很大的关系。有必要先陈述以下两个前提。首先是上文讲到的,罗汉像相对于其他佛教造像有其特殊性,因为罗汉像极少受到经典和风格的限制,以至于罗汉像较于其他佛教形象属于相对允许雕塑家自由发挥的一类。可尽管如此,制作罗汉像的雕塑家们大多已是谙熟佛教形象制作的群体,这是一个十分专业化的群体,他们对各类佛教形象十分熟悉。不论是佛像、菩萨像、天王像,还是罗汉像的制作其实都是同一群体,各类佛教形象通过这一群体的制作也共享着同一制作或思维的套路,所以尽管罗汉像的制作赋予了他们更大的自由空间,但也难有更新鲜的血液注入。这里的问题便是,作为中国古代艺术主流的画家们一般不直接参与佛教造像,包括罗汉像的制作;也就是说画家们和专业的佛教造像雕塑家,包括罗汉像的制作者完全是两个群体,使用的也是两种逻辑。其次是,五百罗汉像工程量巨大,另有工期和财力等因素限制,又因甲方通常是寺庙而非相关艺术机构,所以五百罗汉像很难出现艺术精品,也同样很难跟两大罗汉像或十八罗汉像这样中小规模雕塑的艺术性相比。另者,承接佛教造像任务的人日趋专业化,不仅出现了佛教造像雕塑家群体,也形成了独立的佛教造像系统,至此,佛教造像已经非一般性视觉艺术的审美原则所能介入的了,所以这些雕塑家们一般也不用主动去顾及自己作品的艺术性。实际上,佛教造像雕塑家的首要任务是把佛教形象请进来,而不是它们有多漂亮,况且五百尊真人大小的罗汉像齐聚于罗汉堂中已经是足够壮观的景象了,而非一定要用艺术性原则来衡量。佛教造像雕塑家相信,宗教与信仰的力量自然会赋予这些形象以庄严与神圣,而这些可不是单靠视觉艺术的审美原则就能给予的。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佛像可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它夹杂着信仰与神秘性在其中,而艺术性等“外道”的标准并不一定重要。
画家们虽不直接参加罗汉像的制作,可罗汉的形象却也经常出现在他们的绘画作品当中。画家作品中的罗汉形象与佛教造像雕塑家的罗汉造像,两者的区别恰好契合我们的主题,前者的罗汉形象所遵循的多是视觉艺术的审美原则,而后者则更多注重其宗教意味。
中国古代雕塑家能在历史中留下姓名的极少,戴逵、杨惠之名列其中,不过他们除了雕塑家的身份以外,还是画家。黎广修也是如此,除筇竹寺客堂中保留有他的水墨壁画以外,在客堂外的门柱上还有他一副楹联,书有:“大道无私,玄机妙语传灯录;仙缘有份,胜地同登选佛场。”可见黎广修在书画方面的才华也不可小觑。尤其从筇竹寺大雄宝殿内壁三世佛两侧的罗汉群像中可以看出,黎广修对筇竹寺五百罗汉像的塑造正是得益于他对绘画艺术的理解,他将绘画艺术的诸多元素带入了雕塑当中,所以可称之为以画入塑。这样的方式只有像黎广修这样,将画家和雕塑家集于一身的时候才能得以实现,而这也使画家作品中的罗汉形象与佛教造像雕塑家所塑的罗汉造像的分立局面得到调和。黎广修所塑的罗汉像,既可以用画家的方式遵循视觉艺术的审美原则,也可以同佛教造像雕塑家的方式重视其宗教意味,这是黎广修超越一般佛教造像雕塑家的地方。如,筇竹寺大雄宝殿内壁三世佛两侧罗汉群像以洪涛巨浪为背景,其中所有人物及神兽、法器等都在这一背景下被组织起来,穿插纵横,整体的画面感非常强烈。雕塑家对画面感的追求,必须讲究经营位置、整体构图的疏密分布等相关秩序感问题,并且必须是要有所预设的,这与绘画的标准并无二致。这样画中有塑、塑中有画的创作方式必然会催生出群像的观念,而融画塑为一体也成为雕塑群像的特色之一。不过,黎广修以画入塑的方式或许多少会弱化雕塑自身的语言特征。如因对画面感的追求,作品中人物衣着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这使得雕塑家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人物衣纹的处理上,聚于一堂的人物形象被一件件随风飘扬的彩衣抢去了风头。这样画面感自然是增强了,可是雕塑语言特征中表现物象形体结构的直接性却被弱化了。这应该是用以画入塑的方式来进行群像创作所难以避免的缺憾所在。但必须承认的是,若反过来用微观视角来关注作品细节的话,我们也许就会发现黎广修作品中的衣纹处理及其精彩之处,不仅衣纹的堆积与舒展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在这一点上,作为雕塑家的黎广修一定从作为画家的黎广修那里受益不少),而且他对它们的处理与人物形象的形体和体态的呈现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其艺术水准之高是中国雕塑史中罕见的。
三、结论
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群像观念得以出现的前提以及意义。罗汉像的制作者摆脱了罗汉堂布局的限制、对传统佛教造像的突破、以画入塑的方式,这三种为群像观念提供的前提及意义都标志着雕塑的制作者已经被赋予了足够自由的创作空间,而这是中国传统雕塑家所缺乏的。
中国雕塑源远流长,可熟悉中国雕塑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雕塑的历史往往是只重作品,而并不喜欢为雕塑家留下一席之地,原因在于中国雕塑的历史没有经历过一个由雕塑作品的历史向雕塑家的历史的转换过程,即,中国雕塑的历史没有经历过一个雕塑家的艺术家身份意识自觉的转换过程,这与西方雕塑的历史或者和中国绘画的历史相比起来,有着明显的不同。不经此转换,雕塑的制作者很难被称之为“家”,而称“匠”,技艺高超者则称“名匠”。黎广修因在筇竹寺五百罗汉塑像中展示了高超的技艺,所以被世人称之为“名匠”。黎广修“名匠”的身份是由传统手工艺行当的标准给出的。“名匠”的事迹一方面在民间传颂,另一方面又缺少史志或者画谱之类的记录——中国古代没有为“名匠”作史的兴趣,所以总免不了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走了样,或者传着传着就传丢了,最终只剩下作品而遗忘了作者。然而黎广修这位“名匠”又有其特殊之处,因为尽管有关于他的传闻佳话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如今筇竹寺的僧人、居士及工作人员都能说出些关于黎广修的故事,如黎广修到总督府筹款、师徒下山速写收集素材、师徒将自己的形象塑成罗汉像等等,然而这位“名匠”却在今人编著的各种中国雕塑史中以雕塑艺术家的身份被记录。简单说就是,黎广修以雕塑“名匠”的身份在民间广为流传,又以雕塑“家”的身份出现在现代学术著作的记述中。在雕塑“名匠”与雕塑“家”的拉扯中,可以提取的信息便是中国雕塑的历史在19世纪末期正在经历一场由雕塑作品的历史向雕塑家的历史转换的困惑时期。中国雕塑的历史自此不再只是关注作品,同时也不再将雕塑家这一身份忽略。而在中国雕塑史上,雕塑制作者如何摆脱工匠的身份,而以艺术家的身份去创作,这本就是一个重要的雕塑史问题,这便需要进行专题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