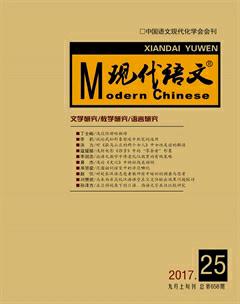浅析电影《推拿》中的“零余者”形象
寇嫒丽 赵明慧
摘 要:郁达夫小说“零余者”形象的塑造影响了娄烨电影的创作。《推拿》既整体描绘了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盲人推拿师的群像,又凸显了特异个体的情感诉求。影片没有把盲人仅设定为存在视力障碍的特殊群体,而是透过他们与健全人同样富饶的情感世界,试图在“正常人”盘踞的主流社会和盲人用沉默坚守的灰色地带间架构起沟通和理解的桥梁。这也体现了娄烨对郁达夫看重个体命运和价值的创作态度的认同。
关键词:《推拿》 郁达夫 零余者 群像 个体
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的影片《推拿》以超越同情和怜悯的,有深度的人文主义姿态关照盲人这一文学艺术作品中较少出现的边缘群体,基于人类共通的尊严、欲望、理想等母题,试图在“正常人”盘踞的主流社会和盲人用沉默坚守的灰色地带间架构起理解的桥梁。这彰显了影片对原著小说创作态度的认同与呈现。导演娄烨近年来的影片《春风沉醉的夜晚》《推拿》等,都带有浓重的郁达夫色彩:以昏暗的色调、晃动的镜头和芜杂的音效聚焦爱情主题,展现当代社会边缘群体的追寻与失落,充斥着灵与肉的冲突,交织着狂热与压抑,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忧郁的情调。娄烨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谈到郁达夫作品给他带来的影响:“打动我的还是郁达夫对于个体的人的尊重和关照。重读郁达夫,我感觉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像郁达夫那样如此亲切地接近个体的人,那样温和的接近个体周围的环境,那样直白的接近真实的自我。我们今天仍然缺乏这样的对个体人的尊重和关照。”显然娄烨认同郁达夫“私人化”叙事的方式以及看重个体命运和价值的态度,他有意识地引导人们解读其电影作品中的欲望暗流和“私人”之于“社会”的价值。电影《推拿》便是这一创作态度的典型呈现。
一、“零余者”群像的塑造
小说《推拿》的每一章节以一个或几个核心人物命名标题、展开情节,并穿插相关的人物关系,从而立体地呈现出盲人群体特殊而又丰富的悲喜人生。影片沿用了这种情节架构,以人物关系为结构要素,既整体地描绘出盲人推拿师的群像,又凸显出不同人物的个性和命运。透过“沙宗琪推拿中心”这一相对封闭的盲人生存空间浓缩的悲欢离合,让观众获得了“管中窥豹”的思考效果,以唤醒健全人对盲人群体的关注与理解。
“零余者”,亦称“多余人”“漂泊者”,源自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郁达夫在20世纪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塑造了一系列中国式的“零余者”形象。“郁达夫与娄烨的作品都着力于探讨漂泊者的灵魂以及他们在城市里的无根生活。”[1]《推拿》中的盲人群体和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有着相似的精神气质。他们都是遭受主流社会排挤、无法掌控自我命运的小人物,身上混合着极端的自尊和敏感的自卑,在理想与现实、灵与肉的冲突中陷入精神困境,生活的压抑和苦闷造就了他们孤独漂泊的灵魂和忧郁感伤的气质。
电影旁白指出“盲人们一直拥有一个顽固的认识,他们把有眼睛的地方叫做主流社会”。健全人对盲人的漠视和盲人的自我放逐,导致了两个群体间厚实冰冷的壁垒。健全人对盲人的廉价同情和侮辱伤害,噬啮着他们敏感脆弱的自尊。盲人往往选择沉默以对或极端爆发,愈发加重了与健全人之间的隔膜。找寻不到归属感和安全感的他们,变成了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零余者。主流社会对残疾人做出的最伟大的让步,就是不再以“残废”指称这个群体。然而却不适用于残疾人与健全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仍会以盲人最忌讳、愤慨的称谓对其进行言语侮辱,从而在群体优越性上不战而胜。例如影片中王大夫挥刀自残,守住了血汗钱,却因追债人的一句“你这个臭瞎子”,失掉了体面,丢掉了自尊。王大夫为了钱,像人渣、流氓一样撒泼了,而对方的妥协无非是不屑与一个“臭瞎子”玩命。王大夫用盲人的尊严换来了屈辱的胜利。盲人往往被健全人一厢情愿的作為同情和怜悯的弱势群体,从一开始就失掉了平等的权利。
盲人沦为“零余者”除了缘于主流社会的放逐,还因为群体成员间的疏离与漠视。“盲人的自尊心是雄浑的,骨子里瞧不起倾诉——倾诉下贱。”[2]这就造成了盲人群体在人际关系上的疏离。尽管他们朝夕相处,拥挤的厮守在狭窄的生存空间里,然而他们的灵魂却是各自流浪,彼此遥不可及。相似的生存困境并没有拉近他们心灵的距离,非要遭遇激烈冲突或突发状况,他们彷徨无依的灵魂才会有所关照。如同伴们对沙复明日趋严重的胃病一无所知,直到他夜宴吐血被送至医院,王大夫等人才意识到天天在一起的他们彼此间是何其的遥远和冷漠。再如小马嫖娼被抓,整个推拿中心除了张一光洞悉其中缘由之外,其他人第一次惊讶地发现沉默的小马居然有着如此汹涌的欲望。然而他们的发现也就到此为止,他们只会把小马迷途的糊涂行为视为一时的冲动,却丝毫不了解小马是为了排解“沉默中的沉默”[3]带来的性的压抑和苦闷。
二、特异个体的情感诉求
娄烨的影片充分尊重同质化群体中特异个体的情感诉求。作为一部群体性影片,《推拿》在勾画盲人技师这一现代社会“零余者”群像的同时,也面貌清晰地特写出一个个性格鲜活、独具性灵的生命个体。影片改写了原著小说对人物个体平均用力的处理方式,把较多的笔墨集中于沙复明和小马身上,让观众解读盲人群体共性的同时,还能深入触及这些在尘世中与我们共沉浮的特异漂泊者的灵魂。这体现出创作者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爱与尊重,也与郁达夫对待其笔下的“零余者”的态度是相通的。
(一)沙复明——追逐爱与美的悲情诗人
小说中交代,沙复明有着一般盲人缺乏的长远的战略性眼光。他在事业上雄心万丈,不满足于做“沙宗琪”的半个老板,而是立志在四十岁前当上真正的老板。所以他面对病痛一忍再忍,这不能成为他实现理想的障碍。沙复明自有一套企业管理经验,把推拿中心的生意打理得规矩,有模样。他是改革大潮中成功的创业者形象,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累积着未来事业的资本。沙复明已然摆脱了盲人靠手艺吃饭的生存模式的局限,而他的多才多艺、博学多识,更是在盲人群体里卓尔不群。沙复明要做的是“将军”而不是“手艺人”。他坚信通过读书,累积的知识可以让他“复明”——把内心的眼睛“打开来”。而之后铺就的成功之路,会让他更接近光明的主流社会。他是整个推拿中心最渴望融入“主流社会”的“非主流”。复明是不可能了,但是能被主流社会认可和接纳,对沙复明来说无疑是更深层次的一种“复明”。这种强烈的欲望也导致了他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的苛刻。盲人通常都希望能找到一个视力优于自己的恋人,这既有现实的需要,也有虚荣的成分。而沙复明巍峨的自尊心和卓越的才华让这份虚荣过度的膨胀了。他一定要得到一份“长眼睛”的爱情。只有眼睛才能帮助他进入主流社会。endprint
影片弱化了沙复明在事业上的雄心壮志,着重通过他对正常人爱情生活的诗意渴望,塑造了一个在爱情路上孤独苦闷,彷徨漂泊的零余者形象。娄烨创造性地引入原著小说没有的诗歌元素,影射沙复明在情感世界里的挫败与无助。一处是影片开场沙复明和小向相亲,他介绍自己欣赏海子和三毛的诗歌,并朗诵了海子《黑夜献诗》中的诗句: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对盲人心存偏见的母亲粗暴地打断了他的朗诵并带走了小向,沙复明落寞无奈地站在湖边,以舒缓伤感的语调朗诵出接下来的诗句: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取走了粮食,取走了马。海子的诗句很好地映照了沙复明与爱情失之交臂后内心的荒凉与无奈。影片旁白道出了沙复明此刻的内心活动:“他突然意识到一种比相亲更动人的东西,那东西叫做主流社会”。海子的诗句被影片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阐释的不仅是爱情错失的感伤,更是沙复明借由同健全人恋爱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望的落空。他与海子作为边缘人都渴望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却都落得一个“荒凉”的结局。“对海子的欣赏,正体现了他孤独、徘徊、流浪、苦闷,希望融入主流社会,然而却一次次被主流社会抛弃的特征。”[4]
另一处是临近影片结尾,都红意外断指,万分悲痛的沙复明用头猛烈撞墙,之后他反复地吟诵三毛《如果有来生》中的诗句: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这展现了沙复明对自己疏于安装门吸酿成悲剧的悔恨以及对命运不公的控诉与无奈。都红的美像灾难一样让沙复明得了癔症,他对主流社会赞叹的“美”百思不得其解。在“美”面前的无能为力,让沙复明再一次被主流社会拒之门外。影片中有一组镜头展现沙复明用舌头舔舐抚摸过都红面庞的手指,他试图动用眼睛之外的感官品尝出“美”的味道。他悲哀的发现这是徒劳的,便狠狠地咬了自己的手指。沙复明对都红狂热的追求,并非是因为爱情的伟大让他放弃了恪守的“长眼睛”的爱情信仰,而是源于他长久以来对主流社会的热望。因为主流社会界定了都红的“美”,沙复明倘若能拥有这份“美”,也就意味着他融入了主流社会。都红一语道破了沙复明这份爱的本质:“你以为你是爱我,其实就是你的虚荣心,迷恋上了一个概念,仅此而已,那不叫爱情。”而都红断指成了残废,意味着“美”的残缺。突如其来的命运的碾压,让沙复明在失去了打通主流社会通道的同时,也痛苦地领悟到她对都红的爱其实是超越虚荣心的。三毛的诗句透露出沙复明对命运残酷的深刻领悟:盲人想要在黑暗中追寻光明的爱情是何其的艰辛?在命运面前无能无力的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来生,而此生注定只能在黑暗的荒漠中流浪。
(二)小马——青春涌动的生命狂想曲
影片开头和结尾是由小马牵出和完结的。儿时的那场车祸,夺去了小马生命中最宝贵的两样东西——眼睛和母亲,之后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夜里,到处是黑暗。小说讲述了小马这个后天盲是如何艰难地穿越炼狱重塑自我的。他不爱这样的自己,于是他陷入了沉默。小马有着年轻人少有的忧郁和颓废。因为“在涅槃之后,他直接抵达了沧桑”。[5]而小孔的出现却让小马蕴藏在年轻肌体里的生命力如脱缰野马纵横驰骋。他陷入了性的压抑和苦悶中,并寻找着救赎的通道。这样的小马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沉沦》中的“我”。“嫂子”的气味和乳房,让小马儿时关于母亲的模糊记忆瞬间复活。对母性气息的找寻也是他对于九岁那年失去的光明的找寻。对“嫂子”掺杂着恋母情结的爱恋,让小马陷入了情欲的幻想与冲动。面对心有所属的小孔,爱而不得的小马,把“嫂子”情节转移给了小蛮。小蛮让他获得了情欲和苦闷的释放。小马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小蛮,抓住了那模糊记忆背后残存的母亲的气息,也就抓住了他在沉默中压抑的、对失去的光明世界的渴望。一方面获得肉欲满足的小马像做了错事的孩子同小孔道歉,另一方面,他沉溺于小蛮的温柔乡不能自拔。直到嫖娼被抓,痛哭流涕的小马就像一个找寻母爱庇护的孩子,面对无序凌乱的人生是那样的痛苦和无助。
同样挣扎于社会底层的盲人推拿师小马和色情按摩女小蛮延伸出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同命相连的关系。娄烨在影片结尾增添了小说中没有的情节,让小马在被暴打后意外的恢复了视力。面对彪悍的三哥,小马像一个真正的男人执着而霸道地捍卫着自己的爱人和她带给他的生命中的光亮。小马在完成了人生又一次涅槃的同时,模糊晃动的镜头暗示着小马冲出了混沌走向了光明。满脸鲜血的小马绽开了笑容,宛若蹒跚学步的孩童雀跃着奔向新生。结尾处,与“沙宗琪”其他盲人再次踏上命运漂泊的旅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马和小蛮开始了看得见的、有把握的人生。娄烨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很喜欢这样的结局,“因为这是一个‘个体的结尾,相对于小说的群体结尾来说,这正好是一个对话。”正因为这一象征希望和新生的结尾,《推拿》被评为娄烨最温暖的电影。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项目编号JC1565]。)
注释:
[1]王鹏:《娄烨电影与郁达夫小说文本间性研究》,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6页。
[2][3][5]毕飞宇:《推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第116页,第38页。
[4]赵晶晶,李萍:《电影<推拿>与诗歌的“互文性”对话》,电影评介,2015年,第19期,第60页。
(寇嫒丽 江西南昌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人文学科部 330029;赵明慧 江西南昌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3001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