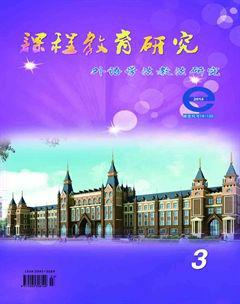创造的“美人”
【摘要】埃兹拉·庞德是20世纪英美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引领着浪漫主义向意象主义时期过渡,积极地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世界的发展。本文以《长干行》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译本为铺垫来解析庞德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中所使用的“创造性”原则,阐释了意象主义的理论,进而阐明庞德的翻译诗学观和艺术性。在创造过程中,中国古典诗歌为庞德的创作注入源源不断的灵感,“庞德时代”随着诞生。意象派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找到了创作同谋,中国文化一跃成为欧美文坛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关键词】庞德意象主义中国古典诗歌“创造性”翻译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3-0035-03
一、 引言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以其在诗歌创作和翻译理论实践方面的非凡造诣,当之无愧地成为二十世纪美国诗坛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巨匠之一。庞德的一生创作辉煌,硕果累累,除了诗歌创作和翻译之外,触角深入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等多个领域。在诗歌翻译研究方面,庞德所提出的“译作乃是新作”原则在美国文学界掀起了惊涛骇浪,传承和发展了西方翻译理论。创作初期的庞德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得益于菲诺罗萨的遗稿,庞德从中精心挑选了19首中国古典诗词,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整理及翻译,于1915年成功出版了中国诗歌的译本《华夏集》。《华夏集》的问世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开创了美国“意象主义”的先河。其中,中国古典诗歌赋予他耳目一新的创作灵感以及中国诗人对诗作中意境出神入化的构建可谓功不可没。庞德的“创造性”翻译为意象派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使得中国文化在20世纪初一跃成为欧美文坛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美国诗人温伯尔曾说:“自《华夏集》起,二十世纪的美国诗歌和中国诗歌紧密相连,基本可以说,美国现代诗歌是中国古诗的产物。”本文以译本《长干行》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为铺垫,深入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产生的影响,进而阐明庞德的诗歌翻译观和他对西方意象派产生的推动作用。
二、译者的“中国情结”
庞德创作的年代,正逢西方社会的动乱之时。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周而复始的金融危机……硝烟四起的乱世和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芜使得西方文人志士对于欧洲传统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陷入深深的焦虑和惶恐。为了给西方文明创造一种适合文学艺术发展的社会制度,庞德开始了求索拯救西方文明良方的漫漫之路。在这种强烈欲望的驱使下,他有幸邂逅了中国文明。庞德的“中国情结”始于费城的中国博物馆之旅。此后,他对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及文明产生了深深的敬仰之情,几乎投入毕生精力将中国的古典诗歌和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庞德一生笔耕不辍,在中国经典著作《诗经》、《大学》、《论语》和《中庸》翻译中不遗余力,当之无愧被称作传播东方文明的使者。
庞德的创作期间大约可以分为三段:1915年成功出版了中国诗歌的译本《华夏集》,翻译了李白、陶渊明、屈原等诸位诗人的28首古典诗词;1920年至1945年,他专注于将中国象形文字的“表意方法”实践于自身的诗歌创作中;1945年至1972年,他成功翻译了《诗经》、《大学》、《论语》和《中庸》等多部中国儒家经典文献,试图以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应对西方社会中大规模的“混乱”。庞德曾说:“翻译为诗歌艺术提供模式,正如给鬼魂注入血液一样。”中国古典诗歌为庞德的创作灌输源源不断的养分:他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正面解读,借助其美轮美奂的意象抒发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极大丰富了他所提倡的“意象派”诗歌翻译理论。“庞德优秀的译论和译作给西方翻译带来了新的复兴。”通过古典诗歌的翻译,庞德开启了西方正视中国文明的大门,并将中国的哲学、历史、政治、艺术方面的经典传播到了太平洋东岸。著名的庞德研究专家休·肯钠(Hugh Kenner)称20世纪上半叶为“庞德时代”,充分肯定了他在英美文坛上无法撼动的地位。 三、“意象派”的功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正当维多利亚风盛行时:讲究格律、过分修饰、辞藻华丽却言无实物的诗风风靡一时。读者们对于这类文风日渐不满,欧美文坛的诗歌创作日渐衰落。作为开启“意象主义”先河的领军人物,庞德主张创作诗歌好比创作一篇好的散文,振兴诗歌之路必须始于振兴写作。他把优秀的诗歌创作标准定义为:“远离废话,更加理性……力量蕴藏在内部……简朴、直接、能自如抒发感情的。”庞德主张优秀的诗歌讲究清晰、简洁、深刻而含蓄的表达,并能够穿越时空,抒发原诗人内心的真切情绪和感受。
意象主义的理论基础起源于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象征主义和英国小说家福特的印象主义理论。象征主义的目的在于运用自然物体暗示实物的本质,从而将客观世界的事物升华到人们的主观精神层面。在庞德看来,诗人应当运用诗歌中的符号,以客观存在来反映复杂微妙的内心感受。印象主义提倡精确地表达客观事物,要求诗人运用清晰、准确的手法创造诗歌。庞德所提倡的意象主义完美地结合了两者,将客观世界和主观感受自然和谐地统一起来,呈现出清晰准确的意象。1913年,庞德在《意象派戒条》中表示:意象是诗歌中能瞬间使人顿悟,激发人们理智和情感的真实感受。庞德曾用“漩涡”比喻意象:有力、含蓄、清晰地向读者传递作者内心微妙复杂、难以言表的真实情感。庞德认为,优秀的诗歌应该具备能够让读者感受意象所带来的顿悟和震撼的能力。
西方著名学者尤尼·阿帕特(Ronnie Apter)将庞德的创意翻译原则归纳为三点:1.摈弃维多利亚时期生僻晦涩、矫揉造作的翻译措辞;2.优秀的诗歌译作可以看作是具有独立意义的新作;3.每篇译作都有必要看作是一定程度对原著的评鉴。
庞德的第一条翻译原则主要是针对诗歌翻译中的措辞问题。19世纪末的西方沉浸在“浪漫主义”风暴中,维多利亚时期的译作充斥着怪癖生涩却华而不实的仿古用语。面对日渐衰败的诗歌王朝,庞德主张运用现代词语反应古之气韵,即以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强调诗歌中现在与过去的文化差异,在译作中再现原诗的氛围和韵味。在《华夏集》译本中,读者可以深切感受到原诗人内心真实的感受是如何穿越历史,重新活生生地雀跃在当今世人眼前。
“译作乃是新作”是庞德翻译观中的核心思想,是他对翻译和创作之间渊源的创新所见。此原则提出的理论基础是约翰·德莱顿的三分法翻译观:直译法、意译法和仿译法。庞德认为意译法是在原作中增添表达美的新成分,仿译法则是汲取原作中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核心涵义并加以再创造,成就更美轮美奂的新作。庞德翻译诗作所选的题材主要是围绕两大主题:烽火绵绵的战乱之苦和凄楚悲凉的离愁别恨,此情此景与20世纪初世界动荡不安的战乱局面不谋而合。庞德希望以“创作性翻译”的手法把中国古代经典融入当代诗歌,从而重现原作中美好的意象和深刻的内涵。
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文学批评是庞德翻译观中最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点。在翻译过程中,庞德所追求的是一种译者和原作者思想感情对等,而不是简单的意义对等。通过巧妙运用了删节、夸张、增添等多种技法对原作进行“改写”,他努力挖掘诗歌语言背后隐藏的原作者的真实感受。庞德认为诗歌翻译是一种“诗歌重生”,翻译的重点在于重现原作的节奏和韵律,衬托原作的气氛和情调。通过“创造性翻译”,译者可以较为自如地“对作品注入一些美好的新元素,这些新的美好元素就是原作中某些东西的‘派生物或‘对等物”。
四、创造的“美人”
本文通过分析庞德的代表作《华夏集》中的两首著名译作《长干行》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旨在阐明庞德翻译的创意原则和诗学观,从而真正体会庞德翻译的艺术性。庞德在翻译《华夏集》所运用的“创造性翻译”的手法不仅关注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特性,同时也关照翻译对译语国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华夏集》的创作语言及体式基本遵循现代英语诗歌,但在诗歌内涵和文化韵味上又不失中国古韵。其中,《长干行》被誉为庞德最具代表性的意象派诗作,入选为《美国名诗105首》。《长干行》的解读可以使读者深切体会到庞德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古典诗歌文风的理解相当惊人。
原文:
《长干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庞德译文:
The River?鄄Merchants Wife:A Letter
While my hair was still cut straight across my forehead,
I played about the front gate, pulling flowers.
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 playing horse,
You walked about my seat, playing with blue plums.
And we went on living in the village of Chokan:
Two small people, without dislike or suspicion.
At fourteen I married My Lord you,
I never loved, being bashful.
Lowering my head, I looked at the wall,
Called to a thousand times, I never looked back.
At fifteen I stopped scowling,
I desired my dust to be mingled with yours.
Forever and forever and forever,
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 out?
…
They hurt me,
I grow older.
If you are coming down through the narrow of the river Kiang,
Please let me know beforehand.
And I will come out to meet you,
As far as Cho?鄄fu?鄄sa.
《长干行》以信中妇人年龄变化为线索,描摹妻子与丈夫幼时、初婚、婚后以及丈夫远行后的生活片段,将妇人幼时与丈夫相识的快乐,初婚时的羞涩腼腆,婚后忠贞不渝的信念以及对远方丈夫深切的思念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首先,在译文措辞方面,庞德保留了原作中的“长干”地名,引发读者想象一个充满东方古韵气息的小镇。“妾发初覆额”被译为“my hair was still cut straight across my forehead.” , 真切地向西方读者描绘了一个东方少女的形象。庞德将“折花”一词译作“pulling flowers”, 符合东方女子特有的婉约气息。“竹马”一词被译为“bamboo stilts, playing horse”虽是一处误读,让人感觉男孩是骑着竹子制成的高跷,玩着马而来。但译文保留了原文中的“竹”,使诗歌充满浓郁的中国地方色彩。“床”翻译成“seat”, 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人将坐卧之处皆称为“床”的特殊表达。原文中“两小无嫌猜”被译为“Two small people, without dislike or suspicion”,保留了英文诗歌独有的音乐节奏,并抒发了妇人心中的天真烂漫。“十四为君妇”中“君”一词,庞德选用了西方表达阶级地位的一词“Lord”,以仿古之风表现出中国封建时代妇女卑微的地位以及“三从四德”的品性。这一词的运用让读者在情感上认同中国传统并体会中国古典诗歌所传承的历史文化气息。
再从文化韵味和诗意方面分析,庞德的翻译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主人公幼时、婚前、婚后以及丈夫远行后微妙复杂的心理变化。在英文诗歌中要重现原诗文中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对于译者的翻译艺术手法着实是个巨大挑战。在原文开头,主人公回忆与丈夫幼年相识嬉戏的情景,这部分是全文中最轻松愉快的画面。与第一节的轻松活泼场面相比,第二节主人公叙述了自己与丈夫结婚后的生活细节,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对丈夫忠贞不渝的决心。这两部分的翻译,庞德力求和原作做到最大限度的“忠实”,译文章句工整对仗、语言朴素平实。从第三节开始,主人公的情绪由“欢愉”“担忧”转向“思念”“悲伤”。庞德的“创意性”翻译开始彰显,诗文不再完全与原文对应,诗句伴随主人公的情绪波动长短交错,犹如音乐朗朗上口。庞德将这部分译文定义为“言语诗”,在译作中充分发挥创意,将主人公“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的凄楚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诗词的最后一句“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是全诗中体现妇人情绪的高潮,若得知郎君返回,何惧路途千万里!在译作中,庞德出神入化地描绘了人物哀怨悲凉的心境,由于思念显得黯然神伤的神态,以及对丈夫至死不渝的深情。毋庸置疑,《长干行》当之无愧成为庞德翻译创作的“美人”代表。
庞德另一首体现“意象主义”翻译手法的名作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其精湛的翻译技巧突出表明了他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准则。
原文: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庞德译文: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鄄jin goes west from Ko?鄄kaku?鄄ro,
The smoke?鄄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庞德主张运用现代词语反应古之气韵,即以现代的眼光看待历史,在译作中再现原诗的氛围。在此篇译文中,他运用意象主义的艺术原则突出表现了原作中诗人送别友人“伤感别离”的主题。在庞德的译作中,李白勾勒的诗情画意似乎重现在读者眼前:江雾蒙蒙的黄鹤楼前,烟花朦胧,友人和孤帆顺着长江之水,渐渐隐没在浩瀚的天际,送行者泪眼婆娑,遥望着涛涛江水,心中充满对友人的记挂与思念。
在译文中,庞德的措辞也别出心裁:第一句对友人的称谓他摈弃传统的译法“the old friend”, 采用 “Ko?鄄jin”, 让人感觉是对即将离去友人的呼唤;对于“烟花”一词,作者采取直译法“smoke flowers”, 进而呼应了原作的意象, 蕴含了诗人对友人的依依不舍;“blur” 一词的使用,仿佛诗人早已泪眼朦胧,让读者从内心深处感受到诗人极想挽留友人的情意;“blot” 一词画龙点睛,惟妙惟肖地勾勒了一幅中国古典山水画:一艘孤帆点缀在水天交接的天边,诗人的悲伤惆怅之情油然而生。在此译作中,庞德近乎完美地再现出原文中的意象,充分表现出中国古典诗歌借景抒情的特征,做到了对原作深层次的忠实。
五、结语
“庞德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进程,加快了东学西渐的步伐。19世纪末,浪漫主义逐渐走向衰败,取而代之的意象主义成为西方文坛的新兴力量。作为意象派的开创者,庞德希望诗歌语言做到简约、凝练、意象清晰,提倡诗歌翻译不必过多追求形式和韵律,在体现诗歌内在的节奏感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庞德眼中的中国代表了一个古老,神秘、浪漫的国度,而古典诗歌是他探寻这个理想圣地的通道。庞德提倡的创造性原则和诗学观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觅到了“同谋”——自然、真实、质朴、含蓄之韵。庞德的“创造性”翻译处处彰显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技巧——意象清晰,情景交融,叠词叠韵尽显韵律美。在庞德的作品中,一首古诗译作增添了新诗韵味,历史和现时的交替感得以实现。他穿越历史,领悟出古典诗歌的精髓所在,随着将其巧妙运用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为意象派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开启了西方世界了解东方文明的窗口,加快了浪漫主义向意象主义转变的脚步。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成为西方文坛不朽的里程碑,于是,东方和西方悄然相遇,文化鸿沟得以弥合,中华文明“穿越古今”“融汇东西”实现了梦想。
参考文献:
[1]Eliot, T.S.(ed)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C].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68.
[2]Brita Lindbern. Syersted. Pound/Eliot: The Story of A Literary Friendship [C]. New York: Routledge. 1982.
[3]Apter Ronnie. Digging for the Treasure: Translation after Pound [M]. New York: P. Lang, 1987.
[4]Pound E. Gaudier-Brzeska: A Memoir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6.
[5]Pound, Ezra. Poems and Translation [M].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2003.
[6]许渊冲等编. 唐诗三百首新译 [Z].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7]王贵明. 论庞德的翻译观及其中国古典诗歌的创意英译 [J]. 中国翻译,2005,(6).
[8]王贵明. 译作乃是新作——论埃兹拉·庞德诗歌翻译的原则和艺术性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2,(2).
[9]蒋洪新. 庞德的翻译理论研究 [J]. 外国语,2001,(4).
[10]肖杰 庞德的意象概念辨析与评价 [J]. 天津大学学报,2009,(2).
[11]张剑. 翻译与表现:读钱兆明主编《庞德和中国》 [J]. 国外文学,2007,(4).
[12]王勇智. 庞德译作《华夏集》研究中的“东方主义”视角评述 [J]. 学术探索,2013,(3).
[13]郭建中. 美国翻译研讨班和庞德翻译思想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2).
[14]杨金铭,王治江. 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的影响 [J]. 河北联合大学学报,2013,(5).
作者简介:
郑灵芝(1985.09-),女,福建福鼎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外贸学院教师,英语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