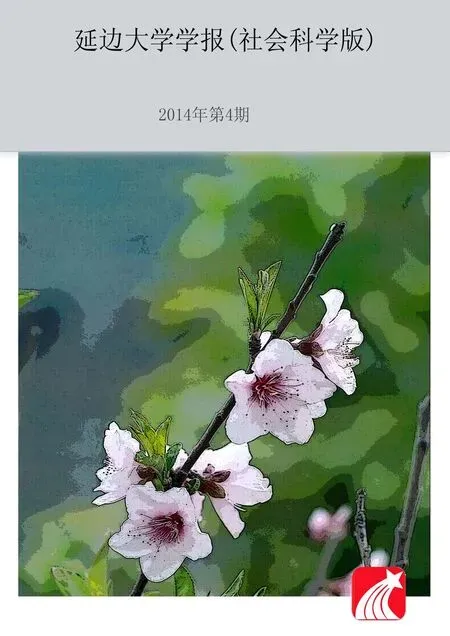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朝鲜族小说叙事方式探析
李光一
(延边大学 朝鲜-韩国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近年来,学术界对当代朝鲜族小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成果也较为显著。但研究方向大部分集中在作家、作品或小说历史沿革等方面,对文学外部研究的比重多于内部研究;即使是对文学内部进行研究,也大多以社会历史的批评方式来触及小说的内容层面。基于此,本文将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当代朝鲜族小说进行文学内部考察,分析研究当代朝鲜族小说在叙事时间、叙事视点、叙事文体等方面呈现出来的特点。朝鲜族小说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为是叙事方式的分界线,并以此将朝鲜族小说分为前期和后期。
一、叙事时间
文学是在时间中展开并完成的艺术。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总是连续不断地读到语汇,因此在读完一部作品以后,印象会比较模糊,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存于心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不同于建筑、雕塑、绘画等空间艺术,其本质与音乐一样是时间艺术。不过,叙事文学在时间问题上却十分复杂,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往往与两种时间相联系,即存在着故事时间和作品时间。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作品时间也叫叙事时间,是故事在作品中具体表现的时间状态。前者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根据日常生活的原理进行重新组合,而后者则是作家对故事经过加工和改造以后向我们提供的作品的现实秩序。由于在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因此叙事时间就成了作家们叙事思考和叙事策略的重要方面。
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关系能够从时序、时距、频率等方面进行研究。[1]在此我们主要从时序来进行考察。时序区分为叙事时序和故事时序。叙事时序是指作品中展开的叙事的先后次序,即从开头到结尾的排列顺序,叙事者叙述故事的时序。故事时序是被叙事者叙述的故事的自然时序,即故事从发生到结束的自然排列顺序。故事时序一般固定不变,而叙事时序能够发生变化。根据叙事时序和故事时序的关系,作品的叙事时间大致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顺叙”形成的相同的故事时序和叙事时序;另一种情况是故事时序和叙事时序的交替(或颠倒),由“倒叙”和“预叙”而形成。
(一)前期小说叙事时间
从建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大部分小说作品,都是按“顺叙”的叙述方法形成的,具有作品时序与故事时序相同的特征。换句话说,作品是按照一个完整的故事发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的顺序进行叙述的,即作品的时序与故事的时序是相一致的。金昌杰的短篇小说《新村》,是以延边农村的冬季为背景,按照故事的时序叙述了以甲植为首的新社会农民们的生活面貌,描述了农民们冬季里编草袋、办夜校等生活。虽然在办夜校的过程中加入了插叙的手法,但是整个作品的流程依然是按照故事时序进行的。另外,《牛头岭》(廉虎烈)、《花儿在新的爱抚中》(白浩然)、《我的爱情》(崔贤淑)等作品,也都具有按照故事时序进行叙述的特色。《牛头岭》是按实际进行的顺序讲述了名叫南洙的农民去缴公粮的故事。《花儿在新的爱抚中》在故事开头简单地交代了基奉4岁时父亲去世、9岁时母亲亡故的事实,接着以顺叙的方式叙述了一个名叫明勋的老师对学校里的调皮鬼基奉加以爱护并使之转变的故事。《我的爱情》是一篇书信体小说,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置在4年前,然后依次叙述了以后发生的事情。
金学铁是活跃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的朝鲜族中坚作家,其作品同样使用了“顺叙”的叙述方式,叙事时序和故事时序一致。《烟叶汤》以幽默生动的形式,表现了主人公文正三的部队生活,在叙事时间上按照其在运输队时的故事、炊事班时的故事、当通信员时的故事等先后时序加以排列。《乔迁之日》、《琥珀烟嘴儿》、《来自现场的信》、《内线见习工》、《奇怪的休假》等大部分小说作品,都是在作品中把故事时序直接变成了叙事时序。长篇小说《说吧,海兰江》同样没有摆脱这样的叙事方式。
1957年,由于“反右”斗争的政治风波,许多作家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从文坛上消失,一批新作家随之出现。可是这些作家的叙述方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并未能摆脱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叙述方式。1962年出版的《老虎崖》(李根全)即是如此。该作品开头的第一叙事起点“现在”,明确规定为1945年10月,作品的全部内容都是在这叙事起点以后发生的事情,即按照故事的顺序记录了主人公金根泽在抗战结束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解放自己的家乡、消灭阶级仇敌韩大棒子的过程。换句话说,故事时序原封不动地成为了作品时序。不仅是《老虎崖》,李根全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年代》,在叙事时序上也具有与《老虎崖》相似的特色。该作品分为上、下两卷,描写了从19世纪末到1945年期间近半个世纪内发生的移民血泪史。作品中使用的时序与故事顺序具有同样的叙述方式,即“顺叙”。作品按照自然时序叙述了1899年到1945年解放期间朴千洙、吴永吉、崔英世三个家族的移民史和垦荒史。作品在叙述三个家族不同人物的故事时,虽然使用了交叉叙述的方式,并且在故事与故事之间穿插了有关历史实事的叙述,但是整个叙述方式依然是“顺叙”,很难找到“倒叙”和“预叙”的叙述方式。从作品的时序来看,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苦难的年代》与60年代创作的《老虎崖》具有相同的特色。由此可见,李根全作品叙述方式的特点就是“顺叙”。
虽然这一时期小说文学的叙事时序具有等同于故事时序的主流特征,但并非一切作品都是如此。有一部分作品与此不同,使用了叙事时序与故事时序交替的叙述方式。短篇小说《扎根的地方》(金学铁)使用了“倒叙”的叙述方式,因此作品的时序与故事时序并不相同。该作品是书信体小说,作品的开头首先讲述了故事的最后部分,即首先交代了收到一封从朝鲜战场上复员的战友写来的信,劝说与他一起搬到市郊去住,接着再讲述故事的开始部分。作品中的“现在”为1953年,但是时间的跨度达37年,从爷爷移居垦荒时开始,经历了“九·一八”事变、1945年解放,一直到“现在”,都是用“顺叙”的方式来讲述的,然后与作品开头衔接起来。《皮鞋的历史》(金学铁)也是如此。作品的开头先描述了故事的最后部分,即描写穿着“不成双的皮鞋”的生产队长的形象,然后叙述了为什么皮鞋会不成双的过程。另外,短篇小说《沙漠遇难》(朴泰河)也运用了“倒叙”的叙述方式。该作品使用了将故事的中间部分放在作品开头(中间前置)的方式。作品叙述了这样的故事:(1)泰熙给位于600多里以外沙漠的×××勘探队运送物资;(2)在沙漠中不仅断了水,还遇到了暴风;(3)离开车前去找水;(4)部队得知泰熙失踪的消息,“我”也知道了这个消息;(5)部队出动,终于找到了泰熙;(6)泰熙得救了。该作品在这样的故事顺序中,将第(4)项提前放到了作品的开头,然后再根据故事发展的顺序构成了作品,从而起到了激发读者强烈好奇心的作用。
(二)后期小说叙事时间
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朝鲜族小说不仅在作品的题材和主题方面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在叙述方式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作品中,也使用了在以前的小说作品中占有主流地位的“顺叙”的叙述方式,但是许多作家更多地采用了“倒叙”的叙述方式,使作品的叙事时间与自然的故事时间发生了倒置。
文化环境的转变使得以前作为禁区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成为了小说的题材,大大扩展了小说能够涉及的题材领域,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谴责和控诉,更是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关注。因此,当时的作家们对作品的题材选择和主题倾向的关注胜过了对小说叙事方式的关心。以前作为主流叙事方式的“顺叙”,在当时依然被不少作品所运用。《绸缎被子》(柳元武)、《压在心底的话》(郑世峰)、《亲戚之间》(林元春)、《被蹂躏的贞操》(金学铁)等作品,在当时的朝鲜族小说文坛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作品都采用了故事的自然时间与作品的叙事时间同一的“顺叙”的叙事方式。
虽然如此,当时的作家并不全都是使用上述方式。郑世峰的《压在心底的话》虽然使用了“顺叙”的方式,但是他在《“布尔什维克”的形象》中却将相当于故事最后部分的父亲临终场面作为作品的开头,并在作品的结尾部分又与作品的开头连接起来。崔红一的《城市的困惑》分别在两个地方讲述了“我”与美顺相遇的过程,而且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与美顺有关的两个故事也采用了倒置的手法。另外,金溶植的《闺中秘史》把相当于故事结尾部分的白兰堂之死作为作品的开头,通过阐明白兰堂死亡原因的过程讲述了自然的故事。在李元吉的作品中,大量使用了“倒叙”的叙事方式。短篇小说《百姓的心》采用了把已经过去的往事插入故事中间的方式。长篇小说《雪夜》把故事中间部分的枪声事件放在了作品的开头。曾在朝鲜族小说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个党员的自杀》,不仅在题材和主题上触及了极其严肃和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且在叙事方式上也颇具特色。作品中讲述的叙事时序如下:
⑴郑熙峰收到金浩天自杀的急电。
⑵一个多月前,金浩天代替患痔疮疾病的郑熙峰去了修建水库的工地马蜡山。
⑶郑熙峰一边上山,一边通过与香莲的关系、通过都市卫生队的事情等,重新确认了金浩天的无条件的党性原则。
⑷到了工地以后,了解到金浩天贪污党费的事情。
⑸金浩天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参加过敢死队,赴战场之前将银制小刀作为党费上交。
⑹郑熙峰来到民工队,金浩天已经被包在草袋子里。
⑺金浩天到马蜡山后,鞋子已经破烂。工地没给他发鞋,只好先用党费买了鞋穿。
⑻民工队的人们普遍对民工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表示不满。为此,金浩天去找工地负责人陈国凯了解情况,并目睹了陈国凯与民工女青年的不正当关系。
⑼陈国凯听到了金浩天用党费买鞋的事情,就到处宣扬应该把他开除党籍,送到劳改队去。
⑽金浩天不堪重压,自杀身亡。
⑾民工队扛着金浩天的尸体下山。由于事态严重,陈国凯最终被开除党籍。
上述叙事时序,与自然的故事时序显然不一致。作品中叙述的故事自然时序应该是这样排列的:⑸⑶⑵⑺⑻⑼⑽⑴⑷⑹⑾。把该顺序替换成ⓐⓑⓒⓓⓔⓕⓖⓗⓘⓙ 后,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对应关系是,⑴ⓗ—⑵ⓒ—⑶ⓑ—⑷ⓘ—⑸ⓐ—⑹ⓙ—⑺ⓓ—⑻ⓔ—⑼ⓕ—⑽ⓖ—⑾ 。图表显示如下: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该作品在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上,只有最后部分是一致的,其他都采用了倒置的手法。像这样打破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同一性后,作品在结构上就摆脱了单纯性和单一性,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作品的篇幅越长,所包含的故事量就越多,作品的叙事时序就很难与故事时序保持一致。人们的思维和对往事的回忆,不会总是理性、次序和连贯的,因此小说作品越是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就越难以遵循自然的时序,也就使叙事时序的倒置更富有魅力。于是,朝鲜族小说文学在叙事时间上,就逐渐从单纯、单一发展到了复杂、多元的层次。
二、叙事视点
一切叙事文学作品都必须具备故事和故事叙述者两个要素。话剧有故事,却没有叙述者;抒情诗有抒情者,却没有故事,因此故事和叙述者是叙事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艺术和文学体裁的最基本特征。[1]叙述者既可以是作家本人,也可以是作品中的人物。具体的问题是谁给读者讲故事?站在什么角度讲?运用什么样的方法?站在多远的距离上讲?弗里德曼把这些问题与“视点”的概念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同时,还有许多研究者对小说的叙述视点进行了讨论,综合起来有三种见解:第一,全知叙述。叙述者可以在任何地方,而且知道一切,不仅知道作品中任何人物的秘密,而且还明确知道人物的外貌、内心世界以及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结果。第二,限制叙事。叙述者与作品人物知道的都一样,人物不知道的话,叙述者也没有叙述的权力。叙述者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众人。叙述的时候,既可以使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也可以使用第三人称的手法;既可以通过作品中一个人物直接的经历或感受进行叙述,也可以让叙述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叙述其他人的事情,还可以通过几个人的叙述使叙述视点移动或交叉。第三,客观叙述。叙述者只是对耳闻目睹的人物进行叙述,绝对禁止同时加上叙述者的主观评价和人物的心理分析。[2]全知叙述和客观叙述普遍使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一般使用第一、二人称。
(一)前期小说叙事视点
从建国到20世纪70年代,朝鲜族小说在叙事视点上呈现的总体特征主要是全知叙事。譬如,20世纪50年代金学铁的长篇小说《说吧,海兰江》、金东九的中篇小说《花荷包》以及20世纪60年代李根全的中篇小说《虎子》和长篇小说《老虎崖》等作品,在叙事视点上都具有全知叙事的特征。
今年的收割比往年都晚。尽管天气比较暖和,用不着冷得发抖地往手上哈气,但是为了尽快打完场,大家还是显得十分忙碌。
不过,毕竟已经是初冬季节,天上没有什么阳光。
刚刚从遥远的龙井隐隐约约地传来12点的汽笛声,正在场上打短工的人们就着刚腌的咸菜吃起了煮得又松又软的土豆。中午时间没过多久,干重活儿的人肚子还没觉得饿,太阳已经晃晃悠悠地挂在了西山头上。[3]
基峰4岁的时候,父亲就因为思想嫌疑受尽折磨,死于狱中。他9岁那年,母亲在水田除二遍草的时候不幸患病,三天以后去世了。父母的亡故似乎来得太突然太快,年幼无知的基峰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那还是1944年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在五年级里,他是谁都畏惧的刺儿头。可是,刺儿头好像正在村子的角落里暗暗伤心。[4]
透过玻璃窗能够看见车间的大办公室里,有3个人围坐在中央的一张桌子旁边,神情都很紧张。他们已经吸了第6支烟。烟雾久久地萦绕在半空中,像是在燃烧着他们烦闷的心脏。[5]
不过,这个时期金学铁的部分作品中在视点上表现出来的特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首先在人称方面,他刚解放时在韩国首尔创作的《烟叶汤》、《蜈蚣》、《裂纹》等作品和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创作的《军功章》等作品,都运用了第三人称的手法。但是在定居延边以后,他创作的作品中大部分都运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虽然崔贤淑的《我的爱情》等作品也运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但无法与金学铁相比。金学铁的《乔迁的日子》、《扎根的地方》、《走过的桥》、《不适宜的喜悦》、《皮鞋的历史》、《奇怪的休假》、《内线见习工》、《苦闷》等作品,全都运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不仅如此,在一部分作品中叙述者充当了第一人称配角或代理叙述者,即中心人物的周边人物。
这是我从一个穿着不成双皮鞋的年轻生产队长那里听来的故事。右脚上穿着干净的咖啡色皮鞋,而左脚上却穿着破烂不堪的黑色球鞋。由于鞋底高低不一,所以他走起路来有些一瘸一拐。
好在他丝毫没有局促不安的样子,反而给我说起了下面这段不成双皮鞋的来历。[6]
今天我在这里要讲的故事,其实是发生在我现在所带的学生之一徐润峰身上的事情。[7]
从上面的例文中可以看出,尽管两篇作品都是第一人称小说,但是作品的中心人物都不是叙述者“我”。《皮鞋的历史》中是年轻的生产队长,《内线见习工》中是“我”的学生徐润峰。作品的叙述者“我”是作品中心人物的周边人物。《皮鞋的历史》中,“我”是听年轻的生产队长讲述的听者,同时又是传达者。由于“我”是听者,因此对生产队长身边的事情不如他清楚,只是通过他的讲述,把听到的故事传达给读者。由此可知,该作品使用的是限制手法。《内线见习工》中,“我”是中心人物徐润峰的老师,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徐润峰的事情有较多了解的叙述者,但毫无疑问依然是徐润峰的周边人物。也就是说,在这篇作品中,“我”并不是中心人物的“我”,而是配角的“我”。
虽然在金学铁的一部分小说中表现出了这样的叙事视点特色,但是包括金学铁在内的这个时期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并没有认识到叙事方式的重要性,因此也不会有意识、有目的地重视叙事视点。上述的金学铁的作品,虽然在叙事视点方面表现出了一部分特色,但不能说都是成功的作品,因为其作品并没有比较明显地超越当时文坛上盛行的歌颂文学的范围。
(二)后期小说叙事视点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叙事视点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在小说创作中显示出真正的意义。虽然这个时期的小说大多运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但也出现了第二人称,这使得作品的叙述视角更加多样化。该时期发表的长篇小说的叙事视点大部分为第三人称。在《激情时代》(金学铁)、《苦难的年代》(李根全)、《黎明的回声》(金云龙)、《雷电交加的早晨》(金松竹)、《咆哮的牡丹江》(尹日山)、《破晓》(金吉连)等作品中,叙述者站在全知的视点上,并且选择了与全知视点相应的第三人称手法。在需要包含社会的、历史的广泛内容、展开大量情节的情况下,作家不可能采用仅仅依靠一个人物所见所闻所思进行叙述的具有局限性的第三人称,而是选择能够涉及全部人物,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叙述全部人物所见所闻所思的全知式第三人称视点。
这个时期的作家还喜欢运用第一人称的手法,特别是在新时期初期创作的许多作品,几乎全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如《怨魂》(朴千洙)、《绸缎被子》(柳元武)、《远房侄子》(洪天龙)、《压在心底的话》(郑世峰)、《家庭问题》(徐光亿)、《斗士的悲哀》(尹林浩)等作品,都是运用了第一人称进行创作。另外《亲戚之间》(林元春)、《红色“彩笔太阳”》(郑世峰)、《学习之路》(李元吉)、《城市的困惑》(崔红一)、《送你去远方》(李惠善)、《孤独的等待》(李惠善)等作品,也都采用了第一人称。从叙事学的视点来看,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的实质性区别在于作品中表现的虚构的艺术世界与两者的距离不同。第一人称叙述者生活在这样的艺术世界中,与这个世界中的其他人物一样,也是一个鲜活、真实、生动的人物。尤其是自传体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其亲身经历和历史就是叙述的基本对象,因此,“叙述”的“我”与“经验”的“我”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第一人称的手法揭示“文化大革命”的痛苦和创伤以及解放后政治动乱根本原因的伤痕小说和反省小说得到了读者的肯定。与此相反,第三人称叙述者虽然自称为“我”,但是被安排在虚构的艺术世界以外,尽管也带有一定的个人特征,可这样的个人特征具有不能证明其在艺术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弱点。
两种叙述者与艺术世界的不同距离,造成了叙事活动的重要区别,这就是叙述者不同的叙述动机。从第一人称叙述者来看,叙事动机是根据自身现实经验和情感需要出发的,因此必然十分强烈。可是,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叙事动机并不是出自内在的生命冲动,一般都来自某种审美的思索。尽管第三人称叙述者也有自己的爱憎倾向,也会对人物的命运流下同情的眼泪,也会使用各种必要的叙事方式进行叙述,但是与一种本体存在意义上的冲动是无法比拟的。
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还出现了采用第二人称手法创作的作品,在叙事学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禹光勋的短篇小说《啊,你》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该小说以勘探队员的生活为创作素材,如同题目一样,整篇作品运用了“你”的独特视点,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朝霞一点一点渗进了帐篷的窗户。你从睡铺上猛地坐起身。不知为什么,不快和郁闷涌上心头,恨不得大哭一场。分明是做了一个不快的梦。只想起有谁在梦中对你进行了谩骂和侮辱,可以后的事情怎么也想不起来。真的令人不快。
你叹了一口气,郁闷地整理起被褥来。还有人在睡觉,看来不像是睡了懒觉。[8]
该作品中的“你”换成“我”或“他”,也能传达同样的意思,但其感情色彩会变得完全不同。该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是清教徒的“你”,而对“你”进行叙述的叙述者为隐藏的叙述者。叙述者最终也没有在作品中出现,只是进行了叙述。为此,在“你”和叙述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距离,使得读者在感受到这种距离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好奇心。当然,也存在着与视点不符的部分,如果从非全知的限制视点来看的话,虽然观察者或者目击者能够观察中心人物清教徒的行动,却无法观察其内心世界。若要观察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称中的第三人称是最合适的,同时不应该运用限制性的第三人称,而应该采用全知式的第三人称。然而,在该作品中,观察者却连中心人物做的梦也了如指掌,这不能不让人更多地怀疑作家是否真的没把视点放在心上,而是想在人称上做什么试验。
这个时期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戏剧化的叙述者,相比与作家保持一致、不与作品中的任何人物并用的非戏剧化叙述者来说,戏剧化叙述者以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出现,作为叙述者受到许多限制,而且在叙述的过程中也显得不太自由,他们一般不是主人公叙述者,而是作为配角叙述者的身份出现。《亲戚之间》(林元春)中的叙述者是刚嫁过门的儿媳妇,而中心人物是铜佛寺女人;《绸缎被子》(柳元武)中的叙述者是县委干部,而中心人物是宋熙俊;《斗士的悲哀》(尹林浩)中的叙述者是教师,而中心人物是廉昌禄。上述作品中的叙述者都是配角叙述者,同时又是不可信任的叙述者。
戴着婚纱迈过李家门槛以来,我从没有见过那个女人。公公不无自豪地说,光堂房亲戚就有24人之多。既然有那么多的亲戚,也许我已经认不出那女人了。
不知因为婆家是贵族后裔,还因为是门第高贵,总之,到婆家来的亲戚的确为数不少。光用眼睛粗粗一看,也有好几十人。其中,我也没有见过那样的女人。[9]
自我表露(Self Disclosure)是将个人信息呈现给其他个体的行为,也就是向他人倾诉关于自我的信息,真诚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与感觉等,目的是让他人更加了解与认识自己。[19]事实上,我们经常所说的“酒后吐真言”就类似于对自我表露的理解[20],自我表露受到性别[21]以及其他个性特征如自我意识和自我监控等的影响。[22]
以上是《亲戚之间》的开头。由此可以看出,作家把刚结婚的新媳妇“我”设定为叙述者,而且叙述者的视点十分有限。离开熟悉的娘家,嫁到生疏的婆家,再加上婆家还是个庞大的家族,刚结婚的新媳妇根本无法很快弄清楚婆家的姻亲关系,而且因为风俗习惯的限制,又不可能贸然去问别人。因此,叙述者与读者所了解的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叙述者并不比读者了解得更多。鉴于这样的设定,读者首先会原封不动地相信处于客观立场上的叙述者的讲述,从这一点上来说,叙述者的观察和叙述具有真实性。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品通过叙述者连续两次的观察,使读者对那个女人产生了联想,这是十分吸引读者好奇心的段落。接着,作品中的中心人物铜佛寺女人在叙述者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即过门头一天做早饭的时候出现了,并帮助叙述者摆脱了困境。这是足以博得叙述者好感的设定。从那以后,通过叙述者“我”的观察,作品中的中心人物铜佛寺女人走进了读者的视线。于是,读者就不可能不再原封不动地相信“我”的叙述了。
该作品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素材的取舍选择和主题的确立,但同时也是因为叙事视点的巧妙设定,假如该作品采用第三人称或叙述者为男人与老人的话,就会大大降低作品给读者带来的美的魅力。
《斗士的悲哀》的特色是叙述者并非一个人,而是两个人。该作品中的第一叙述者是学校的金老师,第二叙述者是金老师的母亲,中心人物是廉村长的儿子廉昌禄。该作品首先通过第一叙述者的叙述引出事件,并通过第一叙述者引出第二叙述者,再经过第二叙述者的叙述,讲述了作品中心人物的故事。作品中第二人物的叙述并不是孤立的,始终与第一叙述者保持联系,而由第一叙述者把第二叙述者直接经历和目击的内容传达给读者。
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了解到,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之前,在朝鲜族小说中,视点问题并没有引起作家们太大的关注,作品的视点还比较单一,而进入后期以后,作家们对叙事视点的关心逐渐提高,从而使作品的视点也日趋多样化。
(三)叙事文体
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中,文体占有重要的位置。文体不是语法学或修辞学的类型,而是正确地传达作家特有的感情或思想,以及相应世界的一种语言特质。文体可以分成作为作家特异性的文体、作为表现技巧的文体、作为普遍意义的内容通过作家个性的表现而体现出来的文体等,其中最后一部分是能够决定作品价值的小说文体。
1.前期小说叙事文体
大学领导认为,毕业生们对统一分配多少会有一些不满或顾虑。与其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如在这次参观中加以解决。于是,领导打算先决定分配,并在今天上午召开动员大会。
毕业生们其实都已做好了无条件接受分配的思想准备,因此很痛快地同意了领导的方案。领导为了以防万一,觉得应该在参观以后再宣布统一分配的结果。
“反正要有这么一次,干脆痛痛快快地就在今天算了!”
“是啊,道理虽然是不错,不过也不能伤了任何一个人的感情嘛……”
“不管怎么说,这次分配中‘运气’好的人一定会高高兴兴地去北京工作,去不成的人也许会垂头丧气的。”[10]
办公室里的说话声戛然而止。
自从像掉了牙的人似的,对把二号机的全部技术一一传授给自己的技术员越来越感到不满足以后,无论在车间里还是在工作讨论会上,成泽总要与经常意见不一的父亲发生冲突。
因此,那些捣蛋鬼总是讥笑他们是“父子战争”。[11]
互助组变成生产合作社以后,共产党来之前晚上睡觉时用一条补了又补的被子勉强遮住一家五口人——两口子加上三个孩子半身的东俊家也盖了新房子。李泰万用这条又惊人又喜人的消息,把父亲从60里外的山沟沟里叫了出来。这到底是惊人的消息呢,还是喜庆的消息呢?[12]
虎子静静地躺在那里佯装睡觉,等着孝植入睡。可是,孝植也久久不能入睡,躺在那里辗转反侧。虎子不由得焦急起来。
夜不知已经有多深,窗户上一片漆黑。由于今天进行了长距离行军,同志们早已经疲惫不堪地睡着了。虎子假装闭上眼,依然等着孝植入睡。不料,孝植抓住虎子的肩膀摇晃起来。
“你回不回家?”
虎子不明白孝植问话的意思,假惺惺地反问道:
“你胡说什么呀?”[13]
这些是20世纪50年代文坛中坚作家金昌杰、金学铁、金东九等和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初文坛尖子李根全的作品中的章节。这些小说的共同特征是叙述故事,作品中除了故事以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对于人物的心理世界几乎没有任何触及,以致作品结构十分简单,其要素也非常简单,作家想要说的故事线也十分明确地传达给了读者。
2.后期小说叙事文体
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汉族文学新思潮的兴起给朝鲜族小说带来了许多变化。效仿汉族文坛的文学思潮,朝鲜族小说也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等,这样的作品主要运用了第一人称手法或书信体手法。书信体小说是解放前在华朝鲜人小说文学中很难见到的文体,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金学铁、崔贤淑等作家的小说作品中。在真实表现当时处在急剧变化时代中的人们的激动心情时,书信体是最合适的文体。到了20世纪80年代,郑世峰成了以书信体小说获得极大成功的作家。郑世峰因创作书信体小说《压在心底的话》而一跃成名。此作品采用了妻子给丈夫写信的形式,尽情地显示了朝鲜族小说中书信体小说的魅力。不过,尽管出现了类似部分文体上的变化,但是与小说在主题、题材等方面的变化相比,这些变化依然显得十分微弱。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朝鲜族小说的文体有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作家们在小说作品中热衷于“描写”超过了“叙述”,对生存环境中人们深层心理的关注超过了在客观现实中展开故事,用主要精力来客观描写人物心理变化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革新了原先作品中叙述和对话严格区分的文体,作品中叙述和对话的区别开始逐渐消失。
在吃早饭的时候,儿子无比自豪地告诉大家。
我作文得了98分。
看来是那篇观察日蚀后写的作文。上个星期六,他为了买一副有色眼镜纠缠了半天,不得不给了他50元钱。既然给他买了有色眼镜,当然应该得98分喽。儿子的作文的确写得不错。他在理科方面的才能也确实强于文科。不过,一旦上了大学以后,也许也会像自己一样选择文科的。
98分不错。作文很难得100分。
锡恰如其分地称赞道。
爸爸,可我……
儿子哲民像是要说什么,支吾了半天,闭上了嘴。[14]
从形态上来看,上述例子很难看出哪个是叙述,哪个是对话。以前对话必须要使用引号的语法规则失去了约束力。不仅如此,“既然给他买了有色眼镜,当然应该得98分喽”这句话,也很难区分这是锡的心理活动还是说的话。这句话既可以是锡的想法,也可以是自言自语或对儿子说的话。可见,在这个时期,小说作品中叙述和对话的区别已经像这样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与以前的小说相比,人物的心理世界更加具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通过比较《苦难年代》(李根全)、《浸透泪水的图们江》(崔红一)、《间岛传说》(崔国哲)这三部同样以朝鲜族的迁移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能看出在小说文体上发生的变化。虽然这三部小说在以朝鲜族的迁移历史为题材这一点上具有同一性,但这三部作品的文体都表现出了显著的变化。
润民听了父亲的话以后,眼眶发热。于是,他重新低下头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大伯,大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恩情!”
“哎呀,快别这么说。我们只是有点同情心罢了。我现在的日子过得也比较紧,明明知道你们家有困难,也没能帮什么忙。这怎么能算什么恩情呢,唉!”
“还不止这些呢,孩子。”
金成女也插了一句。[15]
听了小个子专门挑出来的话以后,德三红着脸不知如何是好。小个子说的是死皮赖脸缠着玉粉,被玉粉爸爸扇了一巴掌的事情。
“我决不会放过这臭丫头的,总有一天……”
“你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听说她家要搬回去了。”
“搬回去?你说什么?”
听了小个子的话,勇达连忙追问。
“好像是因为不愿意穿这里的衣服,所以要搬回去。听说万洙家也要回去。”
“怎么会这样呢?”
勇达实在弄不明白。[16]
一个脸长得像凹进去的木饭勺一样的男人,提了提裤腰,油腔滑调地喊叫起来。
“呸,真不要脸!驴犊子就是不一样,只会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小子,你是不是偷看过哪个贱丫头的裙子底下,被人抓住了把柄?”
“哇呀,你也太小看人了!哼,你才织过几天网,网眼多得数也数不过来。”
光洙的玩笑话气得木饭勺大声吵了起来。木饭勺的名字叫白千奎,外号驴子。
“好哇,了不起!被驴子踢了一跤。像咱们这样的光棍儿,能看一眼那个丫头的脸也就知足了。”
“嘻嘻,再看也还是像油缸里救上来的小母鸡,嘎嘎响的臭丫头!”
男人们停住手上的活儿,参差不齐地站在那里,朝着墙根哗哗地撒起尿来。他们听着光洙与千奎之间你来我往的污言秽语,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17]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引用了这三部作品中叙述与对话同时存在的部分,并集中在年轻人的对话上。李根全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年代》虽然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文体依然与之前的文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可以认为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文体。这样的文体形成了规范化,其特征是缺乏个性。崔红一的长篇小说《浸透泪水的图们江》的文体开始有了自己的个性,摆脱了规范化、图式化的语言,开始倾向于生活化,对话中也开始使用生活化的语言,由于《苦难的年代》中人物的对话不使用方言,因此很难看出人物的地方特色。《浸透泪水的图们江》中富有地方特色的词语不时出现在对话中,开始流露出地方特色。崔国哲的长篇小说《间岛传说》中几乎看不到图式化、流行化的痕迹,从叙述到对话全都达到了个性化,尤其是该小说中大量使用了咸镜道方言,毫无保留地表现了生活着许多咸镜道后代的延边地方特色,不仅如此,这样的方言还十分生活化,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由此看来,李根全的文体具有传统性,崔红一的文体具有民族性,而崔国哲的文体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地方性。
由上可见,当代朝鲜族小说的文体从再现客观现实的现实主义小说文体,开始逐渐向表现作家主观心理的心理主义小说文体过渡。
四、结论
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当代朝鲜族小说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的叙事方式如下:叙事时间为“顺叙”的“故事时序”;叙事视点单一,作家与叙述者相同,叙述者不是戏剧化的叙述者,大部分作品使用第三人称手法;叙事文体为“叙述”,叙述与对话明确区分开,只关注反映客观事实,叙述比描写占有更大的比重。后期的叙事方式如下:在许多作品中虽然在叙事时间上还是使用“顺叙”的叙述方式,但是也有不少小说使用了“倒叙”的叙述方式,作品的叙事时间与自然的故事时间之间出现了倒置的现象;叙事视点以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为主流,同时还出现了第二人称,从而形成作品的叙述视角多样化,另外,这个时期的长篇小说大部分都是第三人称视点;叙事文体有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小说关注“描写”超过了“叙述”,对生存环境中人们深层心理的关注超过了在客观现实中展开故事,用主要精力来客观描写人物心理变化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革新了原先作品中叙述和对话严格区分的文体,作品中叙述和对话的区别开始逐渐消失。
[1]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33,158.
[2]饶芃子,等.中西小说比较[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154.
[3]金昌杰.新村[N].东北朝鲜人民报,1950-04-(7-21).
[4]白浩然.花儿在新的爱抚中[J].教育通讯,1950,(6).
[5]金东九.第二号机[J].延边文艺,1954,(5).
[6]金学铁.皮鞋的历史[A].金学铁短篇小说选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7]金学铁.内线见习工[J].延边文艺,1956,(8).
[8]禹光勋.啊,你[J].延边文艺,1981,(9).
[9]林元春.亲戚之间[J].延边文艺,1983,(1).
[10]金昌杰.知道幸福的人们[J].延边文艺,1954,(5).
[11]金东九.第二号机[J].延边文艺,1954,(5).
[12]金学铁.乔迁之日[N].东北朝鲜人民报,1953-05-27.
[13]李根全.老虎崖[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62.
[14]崔红一.黑色的太阳[A].崔红一作品集[C].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
[15]李根全.苦难年代[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2.283.
[16]崔红一.浸透泪水的图们江[M].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9.205.
[17]崔国哲.间岛传说[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