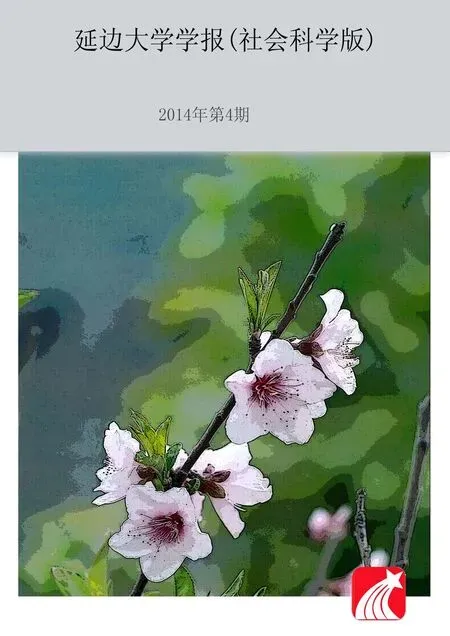国际体系文化背景下韩国国家身份的转换
谢桂娟
(延边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国家身份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1]本文重点考察身份形成的外在结构,即国际体系文化。①在温特看来,国际社会存在着霍布斯、洛克、康德三种无政府文化,这三种文化之间是一种线性发展关系。按照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的依次演进逻辑,东北亚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国际次体系,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文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承认主权平等关系时代的洛克文化。当西方世界处于相互为敌的霍布斯文化结构之时,东北亚世界处于类似康德文化的状态之下。近代,西方列强将条约体系强加给东北亚各国,条约体系不符合霍布斯文化的特征,因此可以说东北亚国际体系没有经历过霍布斯文化阶段。与欧洲国际社会相比,东北亚世界有着独特的发展逻辑,东北亚国际体系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主要考察在冷战前后不同的东北亚国际体系文化背景下,韩国国家身份的转换以及这种身份转换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文化中依靠强权的缓冲国身份
历史上,韩国(朝鲜)先后置身于中国和日本主导的东北亚国际体系内,其国家身份始终处于等级制国际体系中的“下国”地位,韩国(朝鲜)为了寻求国家的独立自主,曾历尽艰辛。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独立主权的韩国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霸权稳定论”与历史上的“朝贡体系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方面有效地控制了地区民族主义以及极端国家主义,另一方面也使东亚各国和地区在不自觉间成为“霸权国”手中的“玩偶”。[2]事实也的确如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韩国在美国的长期占领和控制下,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在美国霸权体系文化背景下,韩国的国家身份由于受制于美国霸权的支配而不能自主选择,因而其国家身份仍然没有发生积极的变化,其对外政策也难以摆脱对美国强权的依附。
首先,韩国对美国的依附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的依附。韩国尽管民族主义情绪强烈,但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性很强。这主要是因为,历史上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小国,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被周边大国环绕的国际环境,韩国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来自周边的威胁。因此,保障自身的安全就成为韩国对外战略优先考虑的问题。为此,朝鲜战争后,美韩双方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虽然声称美韩是“联合与协作”的关系,但实际上,美国在为韩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对韩国的内政外交加以干涉,使得美韩关系带有明显的“从属”性质。很显然,美韩同盟的主导权由美国掌握,韩国则成为美国在东北亚的一个“小伙伴”。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美韩同盟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边联盟,而是美国在全球战略布局中维持地区实力均势的工具”。[3]基于冷战对立而建立的美韩同盟,使得美韩关系在整个冷战时期都处于一种不对称的、等级制的支配-依附关系;美国在对韩国提供军事保护的同时,也扮演领导者和施惠者的角色;韩国则唯美国马首是瞻,进而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4]究其实质,美韩同盟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同盟关系,加之美国在韩国战后重建中的巨大贡献,可以断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论韩国国内反美浪潮如何高涨,由于韩国与美国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和军事同盟关系,其对外战略都很难突破这一框架,其身份定位也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地位。
其次,韩国在经济上的对美依附。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经济在一片废墟中开始恢复,20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初见成效,70年代起经济开始腾飞,到80年代末韩国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此后,韩国在经济上创造了超高速发展的奇迹,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而且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韩国已经跻身于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行列,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15位,贸易总额居世界第11位。[5]从朝鲜战争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末短短40多年的时间,韩国在国内人口和资源等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其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得益于美国的支持。所以说,美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倒退或者崩溃,韩国经济也将面临重大打击。
最后,从文化上来看,韩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虽然没有完全西化而保持着强烈的儒家文化底蕴,但近代以来,韩国的儒家文化不断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复合文化。其中,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对韩国影响更大。韩国在经济上创造了“汉江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与曾经的屈辱历史形成强烈的反差,韩国开始在文化认同上重新确定目标。“20世纪80—90年代,韩国的一些精英人物公开声明在文化上韩国属于东亚的一个例外。这些精英人物再三强调与韩国文化接近的是西方文化而不是东亚文化”。[6]此外,韩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美国的翻版,总统制、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已经被韩国接受。可见,近代以来,韩国更加认同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
综上,冷战时期,在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文化背景下,韩国不仅依附于美国强权,而且,从地缘政治意义上来看,韩国位于亚洲大陆东北部朝鲜半岛的南半部,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在战略上,韩国国土东西狭窄,没有战略纵深,而北临中国和俄罗斯,南临日本,这种地缘特征决定了韩国除了依靠强权之外,还要平衡与周边各大国的关系。实践也证明,韩国始终在中、美、日、俄四大国间发挥着缓冲和平衡的作用。故此,笔者认为,将冷战时期韩国的身份定位为依靠强权的缓冲国更为合适。韩国在自身身份建构上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地位,使得韩国的对外战略很难突破韩美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和军事同盟关系,从这一层面上来说,韩国的身份始终没有发生积极的变化,即仍然不能完全自主。这种身份定位决定了韩国对外合作空间的局限性,也使韩国难以独自在东北亚地区或其他地区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摆脱依附性、寻求自主性将成为韩国身份建构的目标。
二、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平衡者(均衡者)身份的建构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际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变,美苏主导的两极体制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东北亚国际体系处于转型中。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的国家身份是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也就是说是否摆脱了对美国强权的依附?
1993年金泳三总统上台之初,针对当时美、日、中、俄四极关系取代了原来的中、美、苏三角关系这一国际形势,认为韩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半岛统一等问题上都与美、日、中、俄四个大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于是开始推进“四强外交”,即与美日维持同盟关系、同中俄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外交格局。金大中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和强化了与周边四强的外交关系。金大中指出,韩国位于美、日、中、俄四大强国之间,这就决定韩国在外交上必须慎重从事,力求均衡。[7]可见,从金泳三到金大中都力争建构韩国在四大国之间的平衡者角色的身份。
卢武铉上任后,正值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日本经济缓慢恢复时期,韩国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担心成为“三明治里的夹心”。为了避免陷入边缘化的境地,韩国开始建构新的国家身份,即卢武铉总统提出“东北亚均衡者论”。在美韩同盟关系上,主张驻韩美军部署到东北亚其他地区时,必须事先征求韩国的同意;韩国军队决不会追随美国卷入东北亚纷争;韩国把美韩同盟作为维护其国家安全的同时将发展“自主国防”,建成一支拥有作战指挥权的自主性军队;韩国力争要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势力均衡者”。显然,韩国的“东北亚均衡者”,既是对“美主韩从”同盟关系的挑战,也是韩国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谋求建立“自主国防”的正当需求。韩国的东北亚均衡者身份定位,表明韩国要摆脱对美国的依附,追求自主的愿望。
然而,这种追求自主的身份定位却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卢武铉所主张的东北亚均衡者身份的战略定位不仅严重刺激了美日盟国的敏感神经、弱化了韩美同盟,而且并未使朝鲜在核问题上有所松动。[8]由此可见,韩国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格局,决定了韩国在自身身份建构方面,如何在摆脱对美国强权的依附和追求自主方面寻求一种平衡,这是至关重要的。
鉴于卢武铉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所引起的极大争议和质疑,尤其是美国的强烈不满和担忧,李明博选择了“有限度”的平衡外交,[8]即从韩国地缘政治的现实出发,提出“四强平衡外交”,并在全球推行其实用主义外交战略。可以看出,李明博力推四强外交并开展全球外交,表明韩国不仅要做大国关系的平衡者,而且要做亚洲新兴国家的领导者。
首先,韩国要在四大国之间扮演“平衡者”的角色。李明博的“平衡者”论,主要是为了回归以美日为主导的东北亚战略轨道,在重视加强美韩同盟的基础上,也把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其外交的重要一环。正如张琏瑰教授所分析的,“虽然笼统称为‘四强外交’,但李明博是把这‘四强’排了顺序的,重要性依次是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9]对于“三明治说”(即韩国感觉自己就像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三明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人的危机感,韩国认为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位于中、日、美、俄四国之间,且与各国关系都不错。韩国认为自己可以在东亚起到特殊的作用,成为各国关系的平衡者。就此而言,韩国并不担心自己被边缘化。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意义,韩国在力争做大国之间平衡者的同时,也开始了其全球外交。
其次,韩国力争建构亚洲新兴国家的领导者身份。近年来,韩国在政治上大力推行联合国外交,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在朝核问题上,韩国日益显现出有别于其他大国的姿态;在军事方面,韩国精心打造“自主国防”;在文化上,不遗余力地推进韩国文化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形成了所谓的“韩流”。2009年,韩国为推动与东盟的合作,又提出了“新亚洲构想”的东盟新战略,这充分表明韩国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也反映了韩国外交将扩展到全亚洲,以此来加强韩国的主导力量。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韩国希望利用所谓中日争夺‘东亚主导权’之机,将韩美军事同盟提升为‘全面同盟’,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合作,超越中日,成为亚洲新兴国家的领导者,成为在国际社会代表亚洲利益的中心国家”。[10]可以肯定的是,韩国试图超越中国和日本,成为亚洲新兴国家的领导者,这对韩国来说是不切实际的。
2013年2月25日,韩国进入首位女性总统执政时期。鉴于李明博政府时期推行的“重美亲日轻中”的外交政策,朴槿惠政府摒弃了李明博时期的实用主义外交,在与大国关系的排序中,一改以往的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的次序,重要性依次是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上,朴槿惠政府提出由“美中韩”三国来推动战略对话的新构想。她尤其强调中国参加合作机制的重要性。朴槿惠政府“重视中国、排除日本”的主张,以及试图平衡美中两大国关系的做法,表明朴槿惠政府建构东北亚均衡者身份的倾向。
首先,在对朝政策上的均衡。朴槿惠政府摒弃了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的理想主义式对朝援助和李明博时期的实用主义式对朝强硬的做法,本着构建对朝“信赖”关系的外交原则理念,确立了以“朝鲜半岛信赖进程”为核心的对朝政策构想。“朝鲜半岛信赖进程”既具有金大中“阳光政策”的色彩,又与卢武铉的“均衡者”有所不同,同时具有李明博强硬政策的影子。总体看来,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是一种“均衡政策”,这种“均衡”不是简单地选择前几任的中间路线,而是对“强硬”与“包容”的超越,力争做到“安全与交流合作间的均衡”、“南北对话与国际合作间的均衡”、“协商与遏制的均衡”、“政治安全与对朝人道主义援助间的均衡”,②以克服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在进展与后退之间反复交替的困境。
其次,在对美中两大国关系上的均衡。朴槿惠政府上任伊始,在巩固韩美战略同盟关系的同时,对李明博政府时期“重美轻中”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进一步深化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对美关系上,继续强化韩美同盟,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与美国的传统亲密关系,并在外交政策中保持“平衡”,以最大限度实现其国家利益。2013年5月7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次首脑会谈,双方发表了《纪念韩美结盟60周年联合宣言》,韩美同盟由军事同盟升级为全面战略同盟。这意味着韩美同盟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也反映出韩国借此提高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构建韩美平等合作伙伴关系的愿望。在对华关系上,朴槿惠政府上台后,韩国首次将对华关系排在对日关系前,并积极寻求有助于充实和提升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具体路径,借助中韩首脑会谈,发表《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奠定了与中国“未来20年合作的基础”,夯实了韩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此可见,在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韩国希望能够“联美和中”,使韩国与美中两大国关系能够在均衡中发展。
三、韩国国家身份的转换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韩国国家身份的转换,首先是基于韩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韩国所处的朝鲜半岛是大国利益的交汇处,因此,如何在周边大国间周旋,平衡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国家利益,是韩国历届政府的重大外交课题。其次,韩国东北亚均衡者身份的建构也是立足于其国家利益。为此,韩国积极调整对美、中、日、俄的外交政策,推行“均衡者外交”,以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也为自身发展赢得和平的国际环境。再次,是提高其国际地位的需要。近年来,韩国经济迅猛发展,其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正逐步赶上一些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就要求韩国应当拥有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韩国建构东北亚均衡者身份。随着韩国国家身份的转换,其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
冷战时期,置身于美国霸权体系下的韩国,由于其国家安全主要由美国提供保障,因此,在处理同东北亚其他国家关系时,韩国首先考虑的是与美国的关系,然后才是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就是说,依附美国强权的缓冲国身份,使得韩国在外交方面追随美国是其不变的政策目标。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际体系处于转型中。美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在减弱,美国虽然仍有能力制造东北亚事务议题(如朝核问题),但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控制这些日程的演变方向。而中国的迅速崛起正逐渐成为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助推力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韩国的国家身份实现了由缓冲国到平衡者的转换,其外交政策的重心也随之发生变化,即由一味地追随美国而转向“四强”协调外交,尤其重视对华关系。金大中执政时期,韩国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其“四强协调外交”的重要一环。卢武铉2003年上任伊始,就将中韩关系提升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强调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安保以及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中进行全面合作。2005年,卢武铉适时提出“自主安保”和构建东北亚均衡者身份的新战略,这种新的身份定位,既是对“美主韩从”同盟格局的挑战,同时也表明韩国要在东北亚大国关系中发挥协调者的作用,避免再次成为大国对抗、地区冲突的牺牲品。也因此,卢武铉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被评价为“亲中疏美”政策。[11]客观来看,卢武铉的东北亚均衡者身份定位并非要否定韩美同盟,而是在维持韩美同盟的前提下改变过去一味追随美国的情形,是对韩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当然,东北亚均衡者身份的定位也是韩国摆脱对美依附性,主体性增强的表现。而且,事实上,卢武铉执政时期,韩美关系的确处于“疏远”状态,而同一时期的中韩关系却发展迅速。李明博政府时期,韩国外交具有亲美的色彩,但李明博不会因亲近美国而疏远中国。[11]中韩睦邻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因此,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将卢武铉时期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朴槿惠政府更是将对华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她明确表示,中国的发展和美国的亚洲政策“不冲突”,韩国不需要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朴槿惠追求与美国的“对等伙伴”关系,以韩美同盟关系为基础,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其处理与美中两大国关系的基调。韩国能否在与美国发展传统“同盟关系”的同时,加强与中国的战略互信,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复杂背景下,如何构建韩国的东北亚均衡者身份将是对朴槿惠政府的外交新考验。
四、结论
综上所述,冷战时期,韩国在自身身份的建构上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就此而言,韩国的国家身份始终没有发生积极的变化。这种身份定位决定了韩国对外合作空间的局限性,也使韩国难以独自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际体系文化处于转型中。在这种背景下,韩国历届政府开始构建东北亚均衡者身份,试图在摆脱对美国强权的依附和追求自主方面寻求一种平衡。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韩国的身份定位,即追求与美国的“对等伙伴”关系,体现了韩国力争摆脱对美的依附,追求自身的主体性。而李明博政府时期的身份定位,不仅没有体现出韩国自主性的提高,反而对美国的依附进一步加强。朴槿惠政府则试图采取折中的路线,即追求与美国的对等伙伴关系,在大国关系中做一个真正的均衡者。事实上,要想在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均衡”绝非易事。卢武铉政府也曾试图构建东北亚均衡者身份,但事实证明韩国难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李明博政府也曾强调“平衡者”,但却始终将韩美同盟关系置于对华关系之上。朴槿惠政府能否突破东北亚传统政治格局的框架,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前任,在对美中两大国关系中找到真正的“平衡点”,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东北亚均衡者身份,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
①所谓国际体系文化,是指国际体系中的观念分配,其中有些观念是共有知识,有些观念是私有知识。本文重点探讨“共有知识”,即行为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
②关于“朝鲜半岛信赖进程”的解读,参见韩国统一部网 站 http://www.unikorea.go.kr/Cms Web/view-Page.req?idx=PG0000000709(检索时间:2013年9月10日)。
[1][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81.
[2]韩东育.东亚的病理[J].读书,2005,(9):101-110.
[3]王传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美韩军事同盟[J].现代国际关系,2002,(5):13.
[4][韩]苏俊燮.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析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38.
[5]庄起善.世界经济新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94.
[6]韩彩珍.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131.
[7][韩]金大中.金大中哲学和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M].冯世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411.
[8]马建英,韩玉贵.论李明博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J].东北亚论坛,2009,(1):53,53.
[9]王国培.李明博力推四强外交 不做“三明治”[N].东方早报,2008-02-26(A14).
[10]张慧智.中日韩东亚共同体构想指导思想比较[J].东北亚论坛,2011,(2):15.
[11]王生.韩国外交的美国情结与现实抉择[A].黄大慧.变化中的东亚与美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43,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