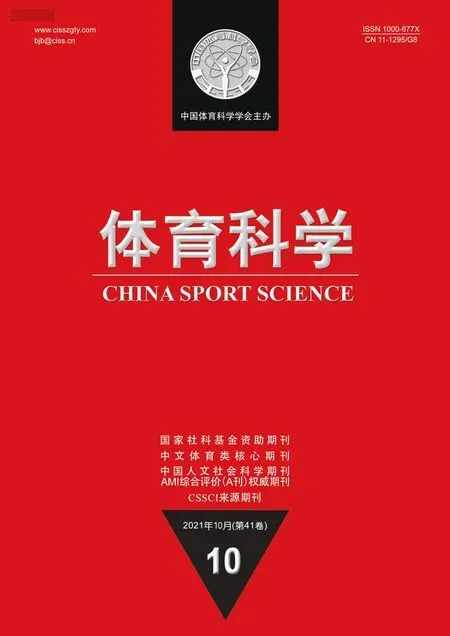对中国近代体育学术史分期的讨论
王颢霖
对中国近代体育学术史分期的讨论
王颢霖
以近代体育学术史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研究、内容分析以及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先就中国近代体育史的时间区间进行讨论,继而结合中国近代体育史分期,讨论中国近代体育学术史分期的划分。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晚清时期的体育学术(1890—1912年)和民国时期的体育学术(1912—1949年),并将民国体育学术划分为民国体育学术初建时期(1912—1919年)、体育学术理论体系肇造与欧美化时期(1919—1927年)、体育学术理论体系建设时期(1927—1937年)、体育学术理论体系成熟期(1937—1949年)4个阶段。
中国;近代体育学术史;分期
学术史,是关于一门学科从初创、建构到成熟个体的演变过程,如果现在重新审视近代中国体育的历史进程,就不难发现,中国近代体育的产生是在一种趋于被迫的状态下而形成的。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一直求索于“强国之道”,“体育”是被当做“强种强国”的一种工具,引入“西学”理念后,中国传统体育渐向近代体育转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近代体育学术是从译著中获得了学术上的启迪,而后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但论及到近代以来的体育学术,目前为止,鲜有研究,而“中国近代体育史”相关研究一直以来不在少数。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学术史的视角对中国近代体育学术的发展历程进行划分,先就中国近代体育史的时间区间年限进行讨论,并结合中国近代体育史分期,继而讨论近代体育学术史时间区间的划分。
1 从“中国近代体育史”时间区间说起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近代体育”应是1840—1949年,如谷世权、杨文清(1981)认为,中国的近代体育史是指鸦片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体育发展史[11]。徐素卿(1986)提到:“目前我国体育史学界摆脱其他学科的传统习惯,把中国近代体育史的年代定为1840—1949年。这不仅是为了遵循1957年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在制定编写《中国体育史》的工作计划时提出的‘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近代史’这一正确主张,更主要是这一提法符合中国体育自身发展的特点,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包括了半殖民地半封社会体育的全过程。因而,这个主张被广大体育史工作者所接受。”[44]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的《中国近代体育史》(1989)所持观点也与徐素卿一致:“《中国近代体育史》写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体育历史。”[14]《体育史料(第16辑)·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1991)中“前言”部分写道:“‘近代’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15]《体育史料(第17辑)·中国近代体育文选》(1992)一书 “按照中国近代体育史的年代划分,……收录自1840年至1949年10月止的作品”[16]。罗时铭、赵諓华(2008)认为,中国近代体育是指1840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在中国流行和实践的体育[25]。另外,何叙(2013)也持此观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起点是1840年,……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史的终点……应延至1949年”[18]。上述学者所持之观点是较为一致的。
然而,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对“中国近代体育”时间区段的界定有所不同,区别主要是在“近代中国体育史”的时间起点上,他们认为应从1842年算起,但还是比较认同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终点。徐元民分别在其著作《体育史》、《中国近代知识份子对体育思想之传播》中都认为近代体育应从1842年算起。主要理由是:“1842年(清道光22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大门,西洋体育思想透过各种管道入中国,同时引发了中国本土体育思想的复兴与重组,朝现代化的理想迈进”[52],“吾人将1842—1949年这段期间定位为中国‘近代’,在此之前中国的体育发展尚以养生运动、武术运动、嬉戏运动和礼乐运动四种类型为主流”[53]。许义雄、徐元民认为“中西文化的接触直至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才有突破性的发展”[47]。
其实,对于近代体育起始时间的问题,国内早在1985年中国体育史学会举办的“中国近代体育史专题讨论会”上就有所议论过,会上主要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因鸦片战争使得近代西方体育传入,故而应以1840年作为近代体育史的上限,这一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第二种意见以洋务运动的时间为上限,但具体有1860年、1862年与1880年三种观点;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应以太平天国定都的时间1853年为上限;第四种意见提出应将五四运动作为新、旧体育的分界点[30]。
尽管大陆与台湾学者在“中国近代体育史”时间区间上相差并不是很大,仅仅只是对“近代中国体育”的起始年份略有区别,但基本上还是比较一致地认同鸦片战争(1840—1842年)对中国近代体育的产生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笔者认为,倘若非要将时间统一到某一确定的年份上,一味地究根到底是没有必要的,学术争议是必然存在的,应允许“百家争鸣”。
2 对中国近代体育史分期的述评
截止目前,虽尚未看到关于针对近代体育学术史分期的论文与著作,但是,对于近代体育史分期的讨论颇多。
我国对于近代体育史的分期讨论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各持己见,并没有统一定论,其中,程登科(1948)划分时期时考虑到了体育思潮、教材输入、体育期刊以及中国式体育系统的创建;苏竞存(1981)在对近代体育史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进行划分时是以当时的思潮与学术观点进行的。与之类似的划分还有徐素卿(1986),其在划分第二个时期时将1917年作为分界点,是因为其认为“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恽代英的《学校体育之研究》等著作都是在1917年发表的,而我国近代真正对体育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是从这时开始的”[44]。这三位学者在划分时,还是或多或少地考虑到当时体育学术发展的特点。而肖冲(1986)与李宁(1986)对于近代体育史的分期比较特殊,是从体育自身发展的轨迹为划分标准,其他学者更多地是以政治或是历史事件为划分依据,如“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1937年“七七事变”等。
显而易见,上述的各类分期并不适用于近代体育学术史的分期,如果仅仅只是套用近代体育史分期或是以此作为近代体育史分期的标准,就会很难体现出近代体育学术的发展历程与发展特征。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比葫芦画瓢”的划分标准套路,并不是以近代体育学术史为对象,很容易忽略近代体育学术史的特殊性,即“学术性”。所以,划分的依据与标准除了要考虑到民国时期政权斗争对近代体育学术走向的影响,即近代体育学术的发展“以应国情”或是为了“政治需要”以外,还应该注意到只有将体育学术置身于当时政治、教育和学术环境中加以权衡,“时代变,斯学术亦当随而变”[27],惟穷源竟委,厘清内在联系,才能准确地划分近代体育学术发展的时间阶段。下面,将先从近代以来所出版的体育著作以及所发表的文章入手,来进行深入探讨。
3 中国近代体育学术史的时间分期
3.1 就“体育著作与体育文章”而言
就著作而言,从建国后所出版的关于“中文体育书目”书籍来看,如《一九○三年—一九八四年中文体育书目》(张大为,1985),从书名可以看出将最早所刊的体育图书推至清末1903年;《百年中文体育图书总汇》(刘彩霞,2003)中所收录的最早体育图书也是于1903年刊出的,即由科学仪器出版(上海)的钟观光所译《孙唐体力养成》[23],但是,从《近代译书目》(王韬、顾燮光等,2003)、《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熊月之,2007)以及《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张晓,2012)所记载的体育书目来看,近代体育图书有时间可查的最早可以追溯至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由[英]庆丕、瞿汝舟所译的《幼学操身图说》。早期的体育著作大多数仅限于译著而已,如上三本再加上《一九○三年—一九八四年中文体育书目》(张大为,1985)、《百年中文体育图书总汇》(刘彩霞,2003)、《中国体育发展史》(吴文忠,1981)及《中国近百年体育史》(吴文忠,1967年12月初版)、《中国近代体育报刊目录索引》(许义雄,1994),可以统计出,截止到1912年2月清宣统退位时,晚清译书共计27本(表1)。

表 1 清末体育译著[23,37,42,58-60]一览表
如果就晚清时期发表的体育文章与发行的体育期刊而言:《体育史料(第17辑)·中国近代体育文选》(1992,12)一书中所收录最早的两篇论文是于1897年发表在《利济学堂报》(第三册)中的何炯《中西体操比较说》与王维泰《体操说》(发表在《知新报》第二十九册);中国最早的体育期刊是由中国体操学校(上海)于1909年刊发的《体育界》。
不论是从著作,还是从发表的文章来看,其“学术”性的特征尽管显得过于单薄,但已带有学术意味,其出版的专著大多数为“体操”类的译著(日本译著居多),准确地来讲,晚清体育学术是从译著中获得了学术上的启迪,而后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而且,文章多以“体操”为论题,研究内容多是将“体操”与国事相联系,研究性虽不强,但已有一些学者群体已经开始关注“体操”。
那么,该如何对近代中国体育学术的发端时间进行界定呢?有一点要肯定的是中国近代体育学术史绝不等同于中国近代体育史。换言之,近代中国体育学术发端应晚于近代中国体育的起始时间。为了能够准确地划分这一时间上限,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概念:何为学术?
无论“学术”意指何为,笔者认为,“学”与“术”是“学术”构成的两个最可靠、最基本的要素。“学”应指具有一定规模与规范的基础理论体系;“术”指用以建构与扩建理论基础体系或能用以验证其理论与原理真伪的方法与技术。简而言之,“学术”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统一体。
3.2 关于对近代体育学术分期的论证
近代体育学术多样化、自由化,尤为重要的,是它并不完全类似于现在的所谓综合性大学或者专业性学院(研究院/所)偏向“技术、实践之学”。近代体育学术就是两个过程:一是从“学”到“术”的转换过程;一是“学”与“术”的水乳交融的过程。所以,在近代体育学术史分期问题上,应把握以下几点:第一,从“学术”词义的发展演变来看,晚清西学东渐之前,“学术”一词的重心仅仅只是落在“学”字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唤醒了国人对“术”的注重。从字义来看,“学”除了“理”的意思以外,还有模仿的意思,像引入西式兵操、翻译国外体育著作、仿学制,其本身就是“学:模仿”,只有在“学”的基础之上,才会“学有所思”而后形成自己的体育学术观点,才会达到“术”的层次,也就是“学以致用”。第二,要注意“学”的构建时间,时间上要结合近代政治、教育、文化的背景以及之间的历史联系,譬如,要注意近代体育的“军国民教育”、“洋土体育之争”、“体育军事化与军事体育化”这三个体育思潮所发生的前因后果,还有就是要注意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日本、德国、美国、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导向是如何的。第三,“术”的“两面性”。“术”不只是简简单单体育意义上的技艺性“操术”与体育运动项目。从西式兵操到《奏定学堂章程》的“体操科”设立,再到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体育科”的出现;从单调、呆板的体操到游戏、舞蹈、球类、田径、游泳等多种项目的出现,这是“术”的显性表征。更深的层面还指体育科学研究的方法,即“术为应用”,这是“术”的隐性表征,也是“学以致用”的表现载体。第四,“术”到“学”的回归。从起初的“学”兵式体操、翻译外文体育专著、“学”改学制、“学”设运动项目,“学”开竞技比赛,在“术”的过程中加以实践,而从中反映出来的种种弊端或存在的问题,慢慢地从“术”开始又转回到“学为理”,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风范”。这里要注意“术”构建或扩建“学”的成因,或是“术”的转变成因,要考虑到促使其产生、转变的因素,像“国术”由20世纪20年代的“国术改良”,在30年代转向“术学兼备”的缘由。最后一点就是:“学术”必须要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学术”的基本载体就是文本。
当然,还有几个关键的事件值得考虑:1)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兵操体育在学校推广,至1915年达到最高峰”[12];2)1915年之后的“双轨制”体育(官办学堂);3)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4)1922年“壬戌学制”,废除“兵操”,以美国“自然主义体育”为主导,1923年“体操科”正式更改为“体育科”;5)1924年8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6)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7)1927年成立“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8)1928年“戊辰学制”,中学以上实施军事训练;9)1938年“中华体育学会”(1935年10月成立)迁至重庆复会;10)1940年教育部颁布《体育实施方案》。
就目前来看,有资料可查的且最早出现的体育“文本”应该是1890年庆丕所著、瞿汝舟所译的《幼学操身》①注:因资料有限,故将体育学术史发端时间暂定为1890年。。因此,本研究认为,应该以该书的出版时间作为近代体育学术史的开端。准确地来讲,近代中国体育学术应该是萌发于晚清(1890—1912年),形成于民国(1912—1949年)。这样一来,可将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分为两个大的时期:1)晚清时期的体育学术(1890—1912年);2)民国时期的体育学术(1912—1949年),其又可划分为如下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民国体育学术初建时期(1912—1919年);第二个时期:体育学术理论体系肇造与欧美化时期(1919—1927年);第三个时期:体育学术理论体系建设时期(1927—1937年);第四个时期:体育学术理论体系成熟期(1937—1949年)。
4 民国时期的体育学术分期论证
晚清时期的体育学术分期比较容易划分,虽然本研究将民国体育学术发展的时间区域限定在1912—1949年之间,是不存在任何异议的,但是,这期间的体育学术发展时间段划分是最难的。这是因为民国政事纷扰,袁世凯称帝、《二十一条》、张勋复辟、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北伐革命,体育思潮因政治更迭,变动之多,可谓艰辛迂远,彼此交织同时存在。下面将结合民国政治、教育环境与当时体育思想家、体育教育家的学术活跃期,对民国体育学术发展的四个分期进行详细而客观的论证。
4.1 第一个时期:民国体育学术初建时期(1912—1919年)
本研究将民国体育学术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之所以如此划分,理由有三:一是,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带来了全新的“文化革命”,“从旧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8];二是,1919年春,长沙雅礼学校率先废除兵操,部分学校开始自行将“体操课”更名为“体育课”;三是,民国体育学术初建时期,前期主要延续了晚清的“军国民主义”的教育思想主张(内容包括了“尚武救国”与“教育救国”),且也以此为主流思想,但因新文化运动,从而由前期的“军国民主义教育”这一主流思想转型到了后期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这一转型过程呈现出了两个特点,第一,上层建筑不再成为决定教育走向的主要“决策”因素,尤其是自1919年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后,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成为“1919年至1925年间,中国资产阶级教育主要思潮的代表”②吴俊升.杜威在华讲演及其影响,教育文化论文选集第360页,台北1972年.转引自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272.,并为中国教育界所接纳,也动摇了所奉行的军国民主义教育。促使了之后在1919年10月召开的第五次(届)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案中提到:“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新教育之潮流,故对于学校自应加以改进。”(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决议案“改进学校体育案”)③转引自邰爽秋.历届教育会议决议案汇编[M].上海:教育编译馆,1935.15.就连早先支持军国民主义的蔡元培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德之军国主义以全国人民之机械,而供野心家之利用。……则军(国)民教育之不能容于今日,已可概见(1919)(《欧战后之教育问题》)”[13]。由此可见,“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体现出了一种由下往上的“民主教育”的思潮趋势。这一“民主教育”思潮为“壬戌学制”(1922)的“民主化体育教育”[48]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思想凸显、学术淡出”[22]是这一时期主要表征。从《百年中文体育图书总汇》(刘彩霞,2003)看,其收录了1912—1919年间所出版的图书,共计69本著作,其中,武术26本、国外拳术2本、体操9本、球类6本、田径2本[23]。单从这69本图书著作书名来看,教材占据大多数,显而易见,学术研究从著作上来看是以学校体育为主;而从当时所发行的三类体育期刊——《体育杂志》(1914年6—7月)、《体育研究会会刊》(1918年1月)、《体育周报》(1918年12月—1920年10月)来看,体育学术思潮则大致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最早源自于晚清“维新运动”中的“尚武”思潮,而民初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张因袭晚清的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惟该思想系以德育为基础,纯以保国自卫为目的,而非穷兵黩武的侵略目的”[51]。1915年,因“二十一条约”,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不少教育学者、进步人士也纷纷撰文热议“军国民主义”,像《东方杂志》连载关于“军国主义”文章,[日]文水野广德撰写、章锡琛译的《日本军国民主义》(1915年第十二卷第六、七号);[日]石川四郎、许家庆译《军国主义之将来》(1915 年第十二卷第十号);胡学愚所译《论学校军事教育》(1916 年第十三卷第六号)。这三篇文章都是以介绍德国、日本军国民主义与学校军事教育为主,其中,石川四郎的《军国主义之将来》一文则与当时鼓吹的军国民主义“背道而驰”,批判德国、日本所奉行的“军国民主义”实为“浅薄与卑劣”,且深恶痛绝其侵略行径。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人对“军国民主义”的观念发生转变,加上前文所提到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与“新文化运动”,“军国民主义”由盛转衰,继而引发20世纪20年代“兵操废立”之争。
2.“静坐体育”之论。由于洪宪称帝、张勋复辟,民国初出现复古封建思潮,“静坐体育”就是此时之产物。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体育之研究》中反驳了其“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体育之研究》1917,《新青年》第三卷2号)[6]。鲁迅则讽刺其“羼进鬼话”(《随感录三十三》)。1918年,衍仁在《体育周报》连续就“静坐与体育”进行了探讨:第三期(民国七年12月23日)《静坐与体育家》、第五期《致田寿昌君论静坐术书》、第六、七期《致田寿昌君论静坐术书(续)》;黄醒分别在第十期(民国八年2月24日)《为什么提倡静的体育》、第十一期(民国八年2月24日)《为什么提倡静的体育?(续完)》加以回击。1919年,方维夏在撰文《策体育》(发表在民国八年四月七日《体育周报》第十六期)指出:应结合“‘动的体育’与‘静的体育’各自方法,才能有真正的体育效果”[33],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后,这场“静坐”与“新体育”之争论才逐渐平息,告一段落。在这场争论中,可以看到一股浪潮涌动,即激进的民主科学思想。
3.“国粹主义体育”。体育界一些武术家发起“国粹体育”,开始重新审度传统体育,为能与西方体育对抗、制衡,应保存与发扬我国固有体育。为此,当时的政府将马良所编排之“中华新武术”推广至中等以上学校。1918年,沈书珽《提倡国技刍言》中认为:“日之柔术,因胎孕于我国之拳艺也。其收效也如是。我国方有内忧外患,所以固邦基而强国民者,如提倡拳艺,使普通男子皆精此道。其为功岂可小视哉。提倡之法。于学校体操,编列为教课。”[29]1919年,方维夏在《体育周报》第16期撰文《策体育》一文中说:“体育”一词,我国本来就有,因“体育历史,间见错出”[33]。徐一冰早在1914年就提出了相似看法:“我国技击为最高尚之运动,……较之东西洋之所谓高等体操术,有过之而无及也。……保存国技之菁华,强种强国,亦教育之急务也”(《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体育杂志》1914年第2期)[52]。从某种层面上来说,20年代的国术派“排洋”思想就源于此时。
4.自然主义体育思潮。其实,从民国元年(1912年)的“壬子学制”中就可以看到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然主义体育身影。杜威(1919年访华)的“教育即生活”、“儿童本位教育”的教育主张,对国民教育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壬戌学制》(1922)颁布后,基本上超越了军国民主义教育而占据主导地位。1915年起美国人麦克乐(1913来华)编撰了《体操释名》(1916)、《网球》(1917)、《篮球》(1918)等新式体育教材,以及发表《篮球体操秩序》、《柔软体操次序》、《田径赛运动详解》、《高等小学男女学生合理的运动系统》等一系列文章,将自然主义体育的一些理论与研究方法推介到中国学校体育当中,重新树立了体育的真正内涵与意义,体育教育及运动项目的相关理论逐渐为中国体育研究者接受,并加以借鉴。自然主义体育思潮在此时期内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经“五四运动”之后,即在第二个时期(1919—1927)才逐渐在中国体育学术界占有一定地位。
这样一来,学术与思想两相比较下,“思想凸显于学术”是最为明晰不过的。话说如此,但回溯体育学术思想潮流,杂糅了当时人们的矛盾、抵触以及追求进步的复杂心理:矛盾——一方面仍抱有“天朝大国”的幻想;另一方面,急于寻找“救国、强国”的捷径。抵触——一方面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强国之道”;另一方面,还在支持着“固有体育”。追求进步——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思想;另一方面,用“科学思想”来批判落后的“封建思想”。自1919年之后,旧有的体育开始“分崩离析”,在客观上,瓦解了民国初建以来所倡导的“军国民主义”教育体系。正是由于这种瓦解,影响到之后的学术研究转向,反而生成了新的体育学术气象,也自然孕育出了民国的第一批体育学者,如徐一冰、徐傅霖、邵汝干、吴蕴瑞、吴澂、方万邦、黄醒、鲁也参、傅延栋、陈奎生等。
4.2 第二个时期:体育学术理论体系肇造与欧美化时期(1919—1927年)
选择截止时间为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这是因为:
第一,北洋政府执政期间颁布了两个学制。一为仿日的《壬子学制》(1912—1921年),是以军国民主义教育为主,以尚武为体育目标,但兵操与普通体操在学校体育中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兵操课时已有所减少;另一为仿美的《壬戌学制》(1922—1926年),从1919年的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就有提出应“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48]以新学制代替《壬子学制》。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5—1926年)和中华教育改进社(1922—1925年)这两个学术组织对当时的教育界影响较大,教育部对于这两个学术组织以及一些教育会议所提出的决议进行认定,一旦可行便加以采纳,这一模式“凸显了教育独立、学术自主的民主精神”[48],为体育学术理论体系的构建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第二,从相关的体育图书书目来看,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与之前的北洋政府相比,中、小学的体育教材与体育著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尤其是国民政府还对大学体育教材做出相关规定,这与民初围绕小学而编纂体育教材有所不同。
第三,1923年在《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中规定将“体操科”更名为“体育科”,意味着“双轨制”并行的学校体育向欧美化转变。此时期欧美化的体育发展主要有2条主线:1)推广运动项目竞赛,以美国春田学院(Springfield College)学派为主;2)发展体育理论,以哥伦比亚大学威廉姆斯(J·F·Williams)、麦克乐为首的自然主义体育学派为主,欧美式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蔚然成风,在北洋政府执政后期占主流。这与南京政府的“军事训练教育”——1928年所修订的《戌辰学制》(即《整顿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对“中学以上实行军事训练”[34],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期间产生出三股学术思潮:
其一,是由“军国民主义”教育引发而来的“兵操废存”之争。如《体育周报》第四十六期(1919年11月24日)连发关于“废止兵操”三篇文章。1)黄醒在《学校应否废止兵操》一文中例举了当时“废止兵操论”的理由:“有的说‘兵是凶器,是不人道的东西,同是一样的人,不应该相残杀,所以主张废兵;废兵用不着习兵操,所以废兵操’,有的说‘共和国家,应该发扬民治的精神,用不着讲强权的军国民主义;含着军国民主义意味的兵操,也违背德莫克拉西的精神,当然废止’,有的说‘兵操是机械的动作,束缚个性自由发展;兵操是偏枯的动作,妨碍身体平均发育;所以应该废止’。”2)张宝琛在《学校应否废止兵操?(一)》中认为:“近来主张废止兵操,提倡正式体育运动之理由,以为兵式教练之性质,为机械的,形式的,偏颇的,强制的,不能自由发表意思的,不以生徒个性为本位的,不合于生理解剖的,正式之体育运动,系根据生理心理诸学,能使青年得以遂其自然发育的,……。”3)江孝贤在《学校应否废止兵操?(二)》中指出:“常见学生于上兵操时,輙疾首蹙额,畏葸不前,一若将受莫大之痛苦,是即就学生之本心,亦不欲兵操立足于学校也。”[33,62]傅延栋在《体育研究》(南京高师)1921年10月发表《沙井特博士对于学校兵操之意见》,从生理学的角度论述兵式体操应予以废止。王庚在《教育与人生》中发表题名为《学校兵操是否有存在之价值》(1924年第13期)的文章讨论兵操废立,姜长麟、姜远麟则在该刊以《兵操自有它的价值》(1924第17期)一文进行反驳。随后,王庚又撰写《学校兵操确有绝对废止的必要》(《教育与人生》1924年第19期)加以还击。“兵操废立”也导致了“兵操教材”不再适宜于新学制下的学校体育教育,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这其实推动了学校体育新教材的编制工作。另一方面,兵操造成了体育与军事训练“合二为一”的混乱局面,影响了体育的正常发展。在1923年之后此趋向衰微,但奈何国家内外交迫,并没有因为《壬戌学制》而完全使体育与军事分离开来,从而复有第二股体育思潮“军事体育化与体育军事化”出现。
其二,“军事体育化与体育军事化”思潮。“军事体育化”比之“体育军事化”的提出较早,王子鹤1924年在《体育与卫生》上发表连载文章《军事体育》(从第二卷第4期开始至第三卷第1期连载三期)指出:“军事体育之目的,简单之:在使无一经验之新兵,在短少时间内,与以种种体育之训练,而成一有能力之良好军人”,1925年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鼓励军警界提倡及实施体育”[1]……强调了“军队中体育之重要。故吾国之军警界应有体育教练员,此等教练员,亦须由体育学校毕业者(承担)”[1]。如此看来,军事体育的现象由来已久,但军事又与学校体育总是纠缠不清,其源头就是因为清末将兵式体操引入至学堂,再加上民国早期奉行“军国民主义”教育,后屡遭战乱与国难,军事与体育、教育三者的关系越发密切。因此,“体育军事化”这一观点的提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不过,还是有学者提出“体育与军事”是不能等同划一的。袁敦礼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体育及国民游戏组所作的事和个人的感想》(1922)一文中对“体育与军事”的区别作出了如下论述:“惟兵事训练之目的与体育不同,军事学亦系一种专门知识,犹非体育所能概括,且兵操上种种动作多有不合于生理及体育原理者,故不得以之代替体育。”[1]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济南)时以民族自卫为由,建议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校设军事学科及兵式教练列为选科,但不得以之代替体育,还提出“中学以上学校实行兵操教练。……又临时提议一件,如下:请以中国武术对中国体操规定为体育上必修之科编入教授细目,俾普及全国各学校,发扬国民固有之精神,并编订教科,设法试验;……军队训练在学校课程中不得替代体育”[1]。可以推之,此时“体育军事化”还未能完全在学校课程中实施。
其三,自然主义体育思潮。进入20世纪20年代,“民十年(1921),美国人麦克乐回华,任东南大学体育科主任。麦克乐以新颖之资料、自然之方法,介绍于吾国,并主废除体操;共理论思想均以心理学、生物学为根据。此时期我国体育受其影响至深,而种下今日我国自然体育之基础”[36]。次年4月3日,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推广运动比赛。期间,麦克乐还编制了“竞技运动能力检验之用途及其分数表”、“体育审定标准”、“运动技术标准”、“测量肺部的研究”、“检查身体方法”等①转引自“行政院”体育委员会.一百年体育专辑——体育思潮[M],台北:“行政院”体育委员会,2012,10:35.。大多数中国体育学者受到影响,开始注意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融入进理论研究中,如罗一东的《体育学》(1924)、庞醒跃的《体育哲学管理》(1924)、程瀚章的《运动生理》(1924、1925)等体育理论书籍都毫无例外地反映出对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认同。
从学制与课程标准来看,学校体育在北洋政府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从体育学科发展来看,出现了“运动学”、“运动生理学”、“体育哲学”等体育学科。值得一提的是,王庚在《体育学与体育教学》(1923)一文中提出“体育学是一种科学”,还将体育教学、卫生学包含在“体育学”中;罗一东(1924)将体育学划归为“导以方法而训练人体之各器官促其发育适宜之科学也”[26]。可以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术思想层面上不仅呈现出“构建学科”的意识趋势,而且,还使得学理研究的学科特征更为显著。
4.3 第三个时期:体育学术理论体系建设时期(1927—1937年)
将1927—1937年作为第三个时期,一是,因为体育被施于行政化管理始自于1927年12月,国民政府大学院设立了“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意味着国民政府要统一规划、管理全国各项体育事业活动,不再以学校体育为主要管理对象。1932年,教育部设体育委员会(之后变更为国民体育委员会),聘任知名体育学者,协调、指导全国体育计划工作。
二是,“七七事变”之前,即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的最初十年(1927—1937年)间社会稳定,是“1912年以来最充满希望的时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9],期间,教育与学术受到重视[10]。受此影响,体育学术理论成果斐然,出现了《体育概论》(如陈咏声,1933、1934)、《体育原理》(如方万邦,1933、1936;吴蕴瑞与袁敦礼,1933、1935;宋君复,1933、1934)、《体育学》(如罗一东,1931、1938)、《运动生理》(如程瀚章,1929、1933)、《体育教学法》(如孙和宾,1932)等多种体育学术理论专著,尤以学校体育发展最为迅猛。“近十年来我国学校体育,可谓酝酿时代而入成熟时代矣。所谓成熟时代者,即于此时代中,学校体育学成,已想普及方面发展而有一定计划也(郝更生《青年进步》第一○二册,1927年)。”[7]由此可见,体育学术理论体系处于建设与发展之中。
三是,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宣布实行“训政”,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 作为政治体制。1928年10月的《国民政府宣言》提到:“首在普及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充实中学以上教育之内容,注重学生体格之训练。”②国民政府宣言.国民政府公报,第4号,1928:4.转引自许义雄,徐元民.中国近代学校体育(上)——目标之发展[M].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9:147.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军事报告之决议案》:“全国军队之训练与教育,应根据国防计划实施军队之三民主义主义化,实施三民主义化之方法,应在事实上使军事教育与三民主义成为一体为原则。”[49]4月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规定将军事训练纳入到中等学校与大学体育教育中,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使“全国军民感于国难当头,倡‘体育军事化’,或军事化的体育。即磨砺坚毅意志与锻炼强壮体魄为主,并以行军、越野、长跑、国术为主要内容,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必须参加每日的课外运动”[19]。蒋介石1932年对湖南教育界强调了军事化在“救国教育”中的作用[49]。至此,军事与体育教育在政治权利的作用下交织在一起,“军事化体育”思潮在政府的倡导下成为主流。
主张“军事化体育”的是以程登科、吴澂、萧忠国等留学德国的体育学者为代表,其中,程登科是这场思潮中的“领军人物”。其自1933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一改他就读东南大学体育科所接受的“美式”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反而推崇德国军事体育,提出了军事化体育的思想主张。方万邦发文《我国现行体育之十大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发表于《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三号,1935)与之对质,程登科随即以《读方万邦先生“我国现行体育之十大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中所持对体育军事化不切实的检讨》一文,反驳方万邦的“体育教育化”主张,以国家形势“内观我民族性,几乎散失殆尽”,质问方万邦,认为体育军事化与国情相符。其“军事化体育”主张包括了两个内容:“体育军事化,是用原有的体育术科,不改体育内容,而以军事精神管理之,训练之,务使受训者绝对服从,是以军事精神,完成体育军事化。……军事体育化:就是先分析军事上的战斗力,视何者运动对于军事有帮助者,则尽量地应用到军事上去,这是以军事为主的,故与学校体育稍有不同。”[3]1933年10月19日与刘慎旃主编《国术、军事、体育周报》(1933—1934年,南京:《中国日报》副刊)还提出将国术融入到军事,赞同洋土体育互补,促进民族体育;主张以“十化主义”达到救国目的,即倡导“体育军事化”与“军警体育化”并行[4],并提倡利用军警实施全民体育化[5]。
与“军事体育化”并存且相悖的是“体育教育化”思潮,体育教育化其实就是自然主义体育的衍变体,是被中国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当时对“体育”的英文译词“Physical Education”来看,体育被视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是以留学美国的袁敦礼(芝加哥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吴蕴瑞(芝加哥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郝更生(春田学院)、方万邦(哥伦比亚大学)等体育学者为主。他们均接受了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熏陶,回国后致力于发展、推动中国体育理论体系的建设,“体育即教育”成为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主要理念。徐元民将体育教育化特性归纳为:“体育教育化,旨在强调体育是在‘教人’,而不只是锻炼身体,促进健康而已;没有教育意义的体育活动即运动竞赛,是没有价值的;体育教育化是属心物合一论,其领域除机体的发展,技能的训练外,另含社会道德规范行为、人格发展、适应社会的生活、休闲生活、政治之道德,以及文化的传承等;体育教育化思想为教育界所认同,并列入中小学课程标准,颇受教育界重视。”①徐元民.战前十年之体育思想(1928—1937),收录于许义雄等著.中国近代体育思想[M].台北:启英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531.“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军事化体育支持者以时局为由,反对体育教育化,而体育教育化主张者认为其军事化体育目标与体育教育目标不同。但因国情战事,军事化体育主张占据上峰,体育教育化反受其制约。
自近代西方体育传入,国人在学习与接受新生事物的过程中,在对待西方体育的态度方面就一直褒贬不一。至五四运动,国粹体育思想以及20世纪20年代国术派的出现,本土意识被重新唤醒。1927年,国民政府于南京所成立的“国术研究馆”(1928年更名为中央国术馆),成为“土体育”的支持者,以《大公报》为阵营,而提倡“洋体育”的吴蕴瑞、谢似颜等人,以《体育周报》(天津)为阵营。双方论争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全盘接受“洋体育”,是否应只提倡“土体育”。1932年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百米预赛被淘汰事件激发了“洋体育”与“土体育”之间的正面交锋。随着讨论的深入,不少学者认识到“洋土体育”惟有互补并行,才能促进中国体育的发展。
“体育教育化”与“洋土体育之争”对于体育学术理论体系构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体育教育论者,如袁敦礼提出体育是“从身体活动中施教育”[56],应以自然活动作为主要体育教育内容;还指出,近代体育是以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为主要理论基础依据的[57];吴蕴瑞着重于“体育本身之科学,如原理、教学、生理、组织行政、建筑设备等,相关科学方面,如物理、化学、教学原理、统计、教育心理等科目,均应修习”[40]。
1930年,吴蕴瑞编著了中国第一本关于“运动生物力学”的著作《运动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与袁敦礼合著了《体育原理》,其还发表了《体育建筑》(《体育杂志》,1929)、《运动成绩的进步有限制的还是无穷的》(《体育杂志》,1929)、《一个不规则的场上建筑适宜跑道的计算法》(《体育杂志》,1929)、《踏步式与摆动式两跑法之力学根据》(《体育季刊》,1933)、《由物理方面观察的体育》(《科学的中国》,1933)等与之相关的许多论文研究,受此影响与带动,呈现出了一种多学理的学科研究倾向。而“洋土体育论争”则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体育学者们认识到: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西方体育,显现出较之中国体育要更有优越性和科学性;反观国术,在教学、教材等方面尚未系统化,研究上缺乏“术学兼备”[63],更谈不上有什么所谓的国术科学理论。总之,无论是多学理的学科研究,还是传统体育向科学理论靠拢,对于当时的体育学术研究来说,都是一次质的突破,意味着在此时期的体育学术,整体而言是从“学科研究”向“科学研究”逐渐转型,体育学术理论得到了深化与加强。
4.4 第四个时期:体育学术理论体系成熟期(1937—1949年)
一是,自“七七事变”之后至1949年,历经八年抗战与四年内战,社会动荡,与前一个时期截然不同。虽然当时国统区、日伪区与解放区“三区”共存,但是,从学术的视角来看,国统区的体育学术发展相对于后两者来说是比较成熟的。
二是,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于1937年在《建国运动》一文中强调振奋民族精神、复兴民族,从“民国二十六(1937)年7月“七七事变”,日本兵临中国,至民国二十七(1938)年10月武汉撤守之期间(戴伟谦,《民族精神教育之体育思想(1937—1945)》)”[50],民族主义体育思潮基本形成。
受此影响:第一,学校体育方面。国民党政府以抗战时期为“非常时期”,对学校行使法西斯式的专政管理,宣扬军国民主义。学者专家也纷纷配合政府工作,像力倡体育军事化的程登科,1938年任职“三青团”中央体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体育学会在重庆复会,又任该学会常务理事,提出“体育与军训及政训”、“创造民族体育”以及“复兴民族的体育目标”等[38],还编写了《战时体育补充教材》(1944)。自抗战以来,政府对体育教材的编写加大管理力度,经由政府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体育教材及其相关教学参考书累计达一百多种。因配合国情所需,体育教材也体现出“政府意识”,出现军训及童子军训练等内容。但无论怎样,学校体育理论已逐渐成熟,并具有一定规范性。
第二,研究方向而言,除出版相关“体育原理”、“体育概论”书籍12种,以及中国第一本《体育心理学》(萧忠国、吴文忠)以外,期间为配合国民政府倡导国民体育运动,研究方向逐渐偏向于国民体育。如黄金鳌《抗战与体育》(1938)、程登科《国民体育》(1939)、吴澂与王子鹤《国民健身操》(1942)、赵汝功《国民体育常识》(1942)、万籁声《中国国民体操》(1943)、刘昌合《国民体育训练与实施》(1947)、张觉非《新国民操》(1948)等,以及与之相关的“体育场地与设施”、“体育行政”等著作。而体育期刊除了学术专业性的期刊外,还出现了一些以宣传西方健美运动为主的期刊,像王学政主编的《健与力》(香港健与力杂志社,1938年创刊,1943年复刊)、赵竹光主编的《健力美》(上海健身学院,1941)、《健与美》(香港李氏健身体育学院,1941)。尽管这与当时“国难当头”的政治、社会局面极为不合时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人们内心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强身健体来达到救国、强国的愿望,这也更能说明,民族主义体育思潮不仅激起了国人对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还引起了全社会对体育的关注。
三是,出现体育课题研究。迁至重庆的中华体育学会在1938年决定继续以“体育主张、体育测验、体育名词”三个体育问题(1936年就已经拟定)作为研究工作,至1940年,像“学生体格标准,中等学校学生运动技能测验法,体育与抗战武力的关系,体育名词(A部)初稿展览,女子不适用的运动项目研究,体育计分法等”[38]部分工作已经结束,“1943年‘学生体格标准’及‘中等学校学生运动技能测验法’编制完成,分发各校试用”[39]。这些标准的制定,反映出了自然主义体育思潮对中国体育学术达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
该时期的学术研究在民族主义体育思潮的影响下,转向国民体育、体育标准、体育设施等领域,也正是由于这种研究的转向,使得体育学术内容得以扩充,学者专家已经认识到:无论是国民体育研究,还是学生体质标准制定,将“科学研究”推至以实践性研究的做法,是保证学术规范性与科学性的前提。
5 结语
晚清体育学术是从译著中获得了学术上的启迪,而后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体操(洋务运动与维新派的尚武强国之思想)与学校体育是晚清体育学术的两个焦点议题。进入20世纪以后,民国体育学术的研究视角因国情时局发生变动:1)1912—1919年,“军国民主义”、“静坐之争”、“国粹主义”、“自然主义体育”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角,呈现出“思想凸显于学术”的现象;2)1919—1927年,“自然主义体育思潮”使得学理研究的学科特征更为显著,学科构建成为该时期的主题;3)1927—1937年,经过“体育教育化”与“洋土体育之争”的洗礼,学者很快就认识到多学理的学科研究需要立足于研究的科学性;4)1937—1949年,即体育学术理论体系成熟期,在民族主义体育思潮的影响下,学术上开始注重通过实践来保障研究的成果服务于“学理——学科”的构建。
体育学术史研究,不仅具有史学的特点,更主要的是对一门学科从立科、到发展、再到演变这一整体建构过程的回溯。“回溯”是需要以学者、时代、著作、思潮、政治、前人等作为若干个“点”,再“以点带面”来解释与总结一些学术经验,这样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但我们对于自身学科的学术传统与发展脉络并没有达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学科的发展决不能仅仅只是依靠几个学科前沿,或是建构一些什么所谓的指标体系,还应该注重对前人学术的研究。但这绝非“厚古而薄今”,我们所做的“厚古”是为了能够积累一点学术“本钱”。钟嵘有云:“披沙拣金,往往见宝。”
本文对中国近代体育学术史分期的探讨,主要是基于长期以来对近代体育学术发展的一些认识与思考,仅是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近代中国体育的历史进程,其发展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讲,显然无论是学术沉淀还是学术实力都是不足的。当然,对于每一时间区段的划分把握以及理由的一一陈述,可能会有一些出于个人的理解,也受到个人学识的局限。
[1]本书编委会.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三十一)[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14997-15016.
[2]程登科.世界体育史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228-229.
[3]程登科.读方万邦先生“我国现行体育之十大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中所持对体育军事化不切实的检讨[J].体育季刊,1935,1(3):353-361.
[4]程登科.军警体育标准测验[J].体育季刊,1933,1(4):9-12.
[5]程登科.怎样利用军警权利辅助民众体育使全民体育化[J].体育季刊,1935,1(2):181.
[6]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
[7]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12-119.
[8]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6,166.
[9]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M].张理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76.
[10]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39.
[11]谷世权,杨文清.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体育理论教研室,体育史教学组,1981:284.
[12]谷世权.体育理论与体育史论丛[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123.
[13]谷世权.中国体育史(下册)·近代部分[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77.
[14]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1989.
[15]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体育史料(第16辑)·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
[16]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体育史料(第17辑)·中国近代体育文选[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17]郭思乐.论大学学术观念的更新[J].教育研究,1998,(11):41-44.
[18]何叙.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演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
[19]教育部体育大词典编订委员会.体育大辞典[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84.
[20]李宁.中国近代体育史分期问题试议[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86,(1):8-11.
[21]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6,(4):48-53.
[22]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4.
[23]刘彩霞.百年中文体育图书总汇[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3.
[24]刘贵华.大学学术发展研究:基于生态的分析[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4.
[25]罗时铭,赵諓华.中国体育通史·第三卷(1840-1926)[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26]罗一东.体育学[M].上海:中华书局,1924:11.
[27]钱穆.中国学术通义(新校本)[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28]沈善洪.蔡元培选集(上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569.
[29]沈书珽.提倡国技刍言[J].体育研究会会刊,1918,(1):1-2.
[30]谭华.中国近代体育史时期划分问题探讨综述[J].体育文史,1985,(6):39-40.
[31]谭华.中国近代体育史分期问题之我见[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4,(4):11-15.
[32]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体育史料·第三辑[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26-27.
[33]体育周报[M].长沙: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7.
[34]王华倬.中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4.
[35]王庚.体育学与体育教学[J].中华教育界,1923,13(12):1-20.
[36]王学政.体育概论(人人书库)[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95-98.
[37]王韬,顾燮光等.近代译书目[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587-589.
[38]吴文忠.中国体育发展史[M].台北:三民书局,1981:425-427.
[39]吴文忠.体育史(2版)[M].台北:“国立”编译馆,1961:344-345.
[40]吴蕴瑞.国立中央大学体育概况[J].体育杂志,1929,(1):113-121.
[41]夏征农.辞海:音序(1999年版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1934.
[42]熊月之.晚清新学书目提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334-335.
[43]肖冲.中国近代体育史分期论略[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6,(2):17-22.
[44]徐素卿.浅谈中国近代体育史的分期问题[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6,(1):8-12,27.
[45][汉]许慎撰,(宋)徐鋐校定.说文解字(附检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44,69.
[46]许苏民.也谈学术、学术经典、学问与思想:对梁启超、严复、王国维观点的质疑兼评“现代学术经典之争”[J].开放时代,1999,(4):107-114.
[47]许义雄,徐元民.中国近代学校体育(上)——目标之发展[M].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9:65.
[48]许义雄,徐元民.中国近代学校体育(下)——思想之演进[M].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9:438-441.
[49]许义雄,等.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史论集[M].台北:台湾师范大学体育学系(所),近代中国体育研究室,1990:389,393.
[50]许义雄,等.中国近代体育思想[M].台北:启英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597.
[51]徐恩华.学术越轨批判[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2]徐元民.中国近代知识份子对体育思想之传播[M].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9:1,91.
[53]徐元民.体育史[M].台北:品度股份有限公司,2005:283.
[54]姚廷华.一部使空白属于过去的教科书——清末《湖北武学》评介[J].浙江体育科学,1989,(S1):14-24.
[55]严复.原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6]袁敦礼.心身关系与体育[J].体育季刊,1933,1(1):1-7.
[57]袁敦礼.近代体育理论之基础[J].勤奋体育月报,1937,4(8):581-582.
[58]张晓.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M].北京:北京大学,2012:240-242.
[59]张大为.一九○三年——一九八四年中文体育书目[M].西安:西安体育学院学报编辑部,1985.
[60]张正中.近代中外体育交流史两个问题考辨[J].体育文化导刊,2008,(9):122-123,126.
[61]张俊宗.学术与大学的逻辑构成[J].高等教育研究,2004,25(1):6-11.
[62]张天白.我国中文体育报刊篇目索引(1909—1949)[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63]张之江.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M].中央国术馆,1931:74.
[64]章清.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79-280.
[65]张意忠.学术与政治:和谐共融[J].复旦教育论坛,2008,(1):59-62.
ResearchonPeriodDivisionoftheSportAcademicHistoryinModernChina
WANG Hao-lin
This paper,taking the sport academic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using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content analysis and logical analysis,discusses the time interval of sports history in modern China.Combined with the period division of sports history in modern China,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division stage of sport academic history in modern China,which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from 1890 to 1912 of sports academic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from 1912 to 1949 of sports academic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latt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the initial foundation period of sport academic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19),the creation and occidentalize period of sport academic theory system(1919—1927),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sports academic theory system (1927 to 1937) and the maturity period of sport academic theory system (1937—1949).
China;sportacademichistoryinmodern;perioddivision
1000-677X(2014)10-0083-10
2014-04-14;
:2014-08-25
王颢霖(1978-),女,吉林镇赉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与运动认知神经科学,Tel:(0373)3326352,E-mail:haohaowhl8022@163.com。
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G80-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