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书评人”差异
韩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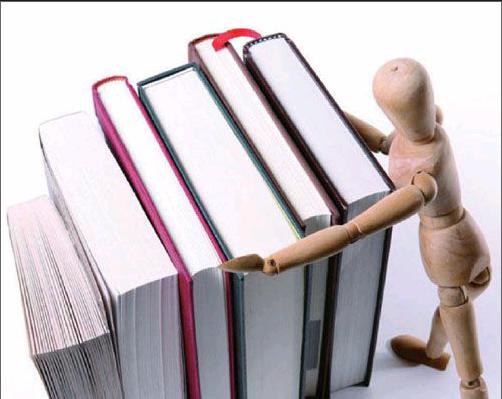

何为“书评人”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个图书评论者》的自白中,曾对“书评人”(即“图书评论者”,Book reviewer)有着如是犀利的描述:他们住在“一间空气污浊、到处是烟头和茶根杯子的阴冷卧室里”,样子则是“一个身穿满是蛀洞破睡衣的男人”,而且“已经35岁,但看上去像50岁。他有些谢顶,长着一个动脉瘤,戴着眼镜”,而要做的事情,则是“在编辑送来的五本书里(有三本说的都是他根本不懂的话题)写书评”,但事实上,“他必须至少要读上50页,才不至于闹出大笑话,让作者臭骂不说,还会招读者臭骂。”
这样一个近似鲁迅笔下孔乙己的文学形象,着实令人哀叹,用当下中国社会的流行话语来形容,他们是活生生的一群“屌丝”。但不容否认的是,奥威尔确实描述了一群最具代表性的西方书评人形象。他们的职责就是利用自己还算勉强的“补白”文笔,为一些书商所出版的新书进行文字上的吹捧。但事实上,“在十本书里,对九本多的客观而真实的评价都应当是‘这本书毫无价值”,书评人所做的工作,在旁人看来,很可能是一种笑料或是了无生趣的努力。
毋庸置疑,书评人的出现是出版产业化的结果,他们所付出的努力,皆是为了在公共媒体上引发读者对一本书的关注与好感,进而刺激图书的销售。当然,我们亦不排除有少量的书评人确实是发自内心对某本图书确实充满兴趣,但对大多数书评人来说,他们却是“读三行、写三页”的应景之笔。
现代书评人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十六、七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而与英、法等国图书业、出版传媒业同步勃兴。一批书商敏锐地发觉报纸、杂志对普罗大众的影响(当时一本书发行量不足千册,但一份报纸却很容易发行上万份),他们开始主动雇佣一些有文笔的媒体人或“大学才子”,为自己出版的著作摇旗呐喊。在书评的带动下,《纽约时报书评》《时代文学周刊》等刊物成为书评人的乐园。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偶尔操刀为之的书评作者,应不属于本文书评人之范畴。因为他们与书商本身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利益关系,而是出于对某本图书的喜爱或学术研究需要,主动撰写类似于“读后感”的文字,这类文本在目前国内文学、出版媒体的“副刊”上只占极少数,而且并不常有。
因此,笔者拟对“书评人”的概念做一个学理上的定义:所谓书评人,就是出于图书营销的目的,受图书发行者雇佣,为其新出版的图书在公共媒体上撰写短评或推荐性文字的职业或半职业化作者。对于这类作者及其写作动机的研究,则构成了本文的核心主旨。
中国的书评人
中国的书评人起源较早,但现代书评人这一概念却是对西方书评人意义的赓续。早在唐宋时代,中国就有专门的“书话”作者,但这类“书话”决非基于商业利益的书评,而是文人之间对一些经典著作的述评,有点类似于今天人文社科学术中的“文本研究”。
至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出版业萌芽,伴随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报纸期刊也相继涌现,以《开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为代表的文学副刊诞生。在这些副刊中,现代意义上的书评出现了,当时许多作家如夏丏尊、李长之、杨昌溪、朱自清与巴金等人,都曾有过书评的写作活动,其中李长之乃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流的书评人。但他们的写作动机各不相同——其中有的本身就是编辑(或书局老板),有的是受朋友之托,有的是落魄文学青年,出于谋生而沦为报社的“补白文人”。
1949年之后,中国的书评人曾一度消亡,直到1978年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出版产业化的兴起,一批新的书评人又应运而生。因此不难看出,无论古今中外,书评人都是出版产业化的结果。但对当下中国书评人的探讨,又必须注意两个关于他们身份归属的问题。
首先,当下中国的书评人多半游离于文化与商业之间。他们对图书的评介,本身是一种文化活动,但这种文化活动又具有特殊的商业性质。
在当代中国,图书生产与期刊出版说到底都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化行为。因此书评写作的本质就是一种与广告无异的产品推广。只是这种推广在形式上有别于烟酒、电器的直观广告——通过直接演示或镜头叙事来告诉受众其功能、用途与样式。书评乃是采取“读后感”的形式,向受众告知图书的内容、特点及其趣味,而且无法采取镜头、图片叙事,只能采用最简单的文字表达,无疑,这很考究写作者的文字功底。
因此在当下中国,书评人存在于一个文化与商业的夹缝中,他们必须要用短小精炼的语句,来向大众推荐一本书——也许他对这本书根本不感兴趣,但是他必须要从文化而非商业的角度来向读者介绍这本书的功用及趣味。这迫使书评人又必须将这本书读完或至少读个大概,否则就会像奥威尔所嘲讽的那样,受到作者乃至读者的“臭骂”。
其次,这种游离于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写作,决定了其不稳定性。因此,中国的书评人以兼职者居多。
笔者曾对国内书评人的生活现状做过调研,由于书评人收入的不稳定性(出版社一般不会雇佣一个专职从事书评写作的人士),因此绝大部分的书评者为高校教师、研究生、作家与媒体从业者。所以,奥威尔笔下的“屌丝书评人”,在中国并不多见。
当下较多的书评人仍是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在收入上无法与企业经营者、知名医生相比,但是仍然属于这个社会上有一定话语权与文化地位的人士,收入不多但却稳定,精神世界也相对丰富,因此写书评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副业而不构成谋生的主要手段。
西方的书评人
与中国相比,国外的书评人与书评地位则更高。
在美国,有专门的“全国书评人协会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该协会是一个由约500名图书编辑和书评人组成的非赢利性组织,每年评奖一次,与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并称美国三大图书奖。书评人可以担任评委,决定作家、作品的命运。譬如印度旅美女作家姬兰·德赛(Kiran Desai)的小说《失落的遗产》(The Inheritance of Loss)就曾获得该奖。
近年,由于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读者习惯于通过亚马逊、Worldcat等网站来了解一本书的影响力,因此,美国的书评人与书评的影响力呈现下滑的趋势。除《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外,美国各大报纸的书评版面皆面临缩版或与其他版面合并的命运。如2007年3月,《洛杉矶时报》宣布将“周日书评”与书评版合并,合并之后书评版面从16页缩减为12页;而《芝加哥论坛报》也将书评版由星期日移到星期六并缩减版面。
相比之下,老牌书评大国英国的书评人则好过许多。110多年历史的《时代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在英国的文学艺术界仍然处于“德高望重”的地位,一批较有名望的书评人如托比·利希蒂希(Toby Lichtig)、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等在英国文学界仍颇有声望,而且英国还有一个民间的“斧头奖”,专门颁发给犀利的书评。书评在英国的影响力,应该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法国与英国类似,拥有悠久深厚的书评传统。譬如《法兰西晚报》与《文学杂志》等期刊一直拥有较为丰富的书评版,并在法国文化界影响深远,而龚古尔文学奖、法兰西学院文学奖等,在评审过程当中都会考虑候选著作在书评界的影响力,甚至部分授奖辞都摘自有影响力的书评。
不难看出,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因为出版产业化进程与文化传统的不同,书评人的角色亦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值得公认的是:随着纸媒的剧烈滑坡,导致书评亦不断被边缘化,中国也不例外。许多地方媒体的书评版面与副刊合并,一些书评走向了电子版、微信版等新媒体形态,书评人的稿酬越来越低,以至于许多书评都是出版社约稿的敷衍之作。
因此,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书评人相比,中国的书评人则更有研究意义与价值。笔者认为,这一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书评与书评人反映了出版社、媒体与作者三者之间的利益互动。实际上,许多“评”都是“赞”与“荐”,除《东方早报书评周刊》《新京报》等专业书评刊物外,许多书评刊物或一些大型刊物的书评专栏都难保其客观性。据笔者了解,部分刊物甚至长期和某家出版社、出版公司合作,几乎只刊登该社或该公司所出图书的书评,沦为“某家吹鼓手”,失去了公共媒体的公正性与公平性。
其次,在出版业的转型期,分析书评及书评人的存在形态,有利于透视中国出版业的话语权力。书评人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先前的评论家角色,反映了出版业在转型期的营销策略,如何以书评的形式来进行产品营销,以及如何构建出版业与公共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之间的关系。
书评人与文学评论家
文学评论家是一种职业,也是高校、作协、研究院中的事业编制人员,他们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旨在对文学作品做出客观判断,进而为作家的创作提供进一步指导。在中国人事部门的职称评定中,还有“文学评论一级”的高级职称,相当于正教授或高级工程师。
而书评人显然不仅仅局限于对于文学作品的评论,他们还必须涉及各个门类图书的评述,而且存在于市场语境下的书评人也很难像一些文学评论家一样,用尖刻直白的语言抨击图书作者(除非受一方雇佣),因此,书评人在当代中国文化体制内部的身份相对尴尬。这种尴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们会有选择,但这种选择又较为有限。
在当代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出版的复杂性迫使书评人必须是“百科全书式”。因为编辑给书评人的任何一本书,都并非他所擅长的领域或是对书中的内容完全赞同,但是书评人又很难主动去找到一本与自己阅读旨趣相投、观点又颇为一致的读物。
这就决定了书评人未必能够做到“言为心声”,但大多数书评人仍会对编辑所推荐的书有所要求。从微观上看,这是书评人与编辑之间的思想博弈。譬如有些书评人就主动提出“流行小说、保健养生类的书评不写”或“不写科技类著作评论”等,因为他们并非以书评为谋生手段,并不希望公开媒体上的署名文字由于一些硬伤或不当之词使得自己的声誉受到损害。
另外就是“身份归属”的问题,对当下大多数书评人而言,写作主观动机相对复杂,有的是因为交情,有的是因为自身的需求,有的是因为利益驱动,但客观动机确实存在着“将好书介绍给读者”这一美好愿景。
在这种情况下,书评人既会对编辑提出的要求有所选择,又会尽可能地协助对方推广这些读物——尤其是面对一些经典著作与名家好书时,书评人亦非常愿意为他们撰写评论,因为这样会让他们觉得受到重视。尤其是一些知名度高的出版社,会将这些书评送到非常体面的刊物、报纸上发表,而这对许多书评人来讲,又可以为他们提升自己的名声,甚至对工作晋升起到重要的帮助,当然,也有不少书评人是基于利润的驱使而写作。
这是当代中国书评人的复杂写作动机,其中不排除一些特别优秀的书评人。一方面,他们与编辑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自己的著作也交给这些编辑出版;另一方面,编辑将他们为其他知名作者所撰写的书评拿到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使得作者、书评人与编辑获得共同的双赢——这不但取决于书评人的知名度,更与出版社、作者的影响力以及图书、书评的质量密切相关。因此,大多数书评人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仍处于一种“雇佣写手”的状态。
因此在许多书评中,事关书评人职业的提及,很少落“书评人”三字,多半是“XX大学教授”“XX杂志高级编辑”等。笔者调研时曾发现,在当代中国大多数书评人都不认可自己这一身份,甚至部分书评人自嘲是“吹鼓手”“软文写手”,在这样的语境下,书评人今后在中国的发展趋势,理应受到学界的指引与审思。
结论
据笔者统计,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尚无一篇论文对书评人进行系统研究,仅有一篇止庵的《史前阶段的书评业——书评业现状二人谈》初步以对话的形式探讨了这一问题,但亦限于对书评业的探讨。此外,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赵都陵的硕士论文《李长之书评研究》(2008年)爬梳整理了1930年代李长之的书评活动。其余多半是对书评业或国外书评状况译介评述的短论。因此,国内学界对书评人的研究,目前还算空白。
笔者希冀,结合对书评人的定义、当下中国书评人的生存状况、身份归属与写作动机进行初步的探索,并就书评人在今后中国的发展提出如下几点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首先,书评人必须要做到“言出必实”,杜绝“红包软文”式的虚假宣传或望文生义式的草率写作,这是书评人行业良性发展的前提。
书评人不构成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但它却是出版产业化合理有序发展、作家与读者良性互动的助力器。在一个健康的出版环境中,书评人的地位不可忽视,他们第一时间利用公共媒介向社会推介新书,构成了社会对于一本读物的最初印象。但是这种最初印象并非权威性的,如果读者一旦发现,一本极烂的书,被书评人吹捧为上佳之作,那么书评人就会沦为奥威尔笔下“里外不是人”的地步。因此,书评人对于一本书的评价,必须要基于自己的理性判断而非利益的驱动。
同时,书评人也要忠实于批评对象与自己的文字,决不可马虎应付。部分书评人可谓是“手写八方”,犹如书评制造机。虽然书评写作可以有近似于模板的套路,但其写作的前提必须是对文本有精细的阅读与深刻的了解,否则难免会张冠李戴甚至离题万里,最终使得“书评”丧失公信力。
其次,书评人作为一种职业,必须要规范、客观化,可以没有所谓的行业标准,但是必须要承担文化建设的基本责任。
书评人出于图书营销目的,撰写书评以作推广,这无可厚非。但书评人却不可随意溢美、任意拔高,甚至虚夸内容,使得作品名不副实,造成欺瞒读者的恶劣结果。这就好比是广告从业者进行虚假宣传会受到惩罚一样,书评作者也必须自律自己的行为,让书评写作客观化,否则不但会毁掉自己的名誉,也会给作者、出版方带来很大的信誉伤害。
中国图书产业化才十余年时间,与西方国家相比算是蹒跚起步,许多规章制度尚不规范,出版商亦是良莠不齐。作为有一定知识修养、文化素质的书评人,必须要在这样一个正在自我完善的市场中起到文化建设者引导、规范的基本责任,而不是为一些“枕头拳头”类的小说摇旗呐喊,对于图书市场中一些低俗、媚俗的不良倾向,书评人要勇于明辨是非,敢于举起批判的大旗。
“作为图书审查者的图书评论者一定要说真话,至少应该不说假话,因为你将会决定一本书在公众视野里的第一印象。”确实,书评人应是“图书批评人”,而非“图书赞扬人”,书评人应该对一个文本有着自己的深刻见解、批判态度与怀疑精神——哪怕面对的是名家大师的经典著作。只有这样,中国的书评人才会与读者、编者产生积极、和谐的互动,进而推动中国出版业朝着健康、有序的趋势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