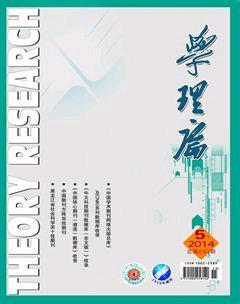康有为1888年第一次上书失败原因初探
周珈伊
摘 要:中法战争结束后,列强加紧渗透,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清政府并未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面对复杂的形势,康有为主动向光绪帝的上书,主张改革,但因此次上书内容的不符合当时清政府的实际,大多数官员不予代递。试图以《上清帝第一书》为中心分析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5-0125-02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赴京参加顺天乡试,并准备向皇帝上书,此时正值中法战争结束不久,列强势力深入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作为统治者的清政府,对改革缺乏理性的认识。康有为的此次上书遭到了包括改革派官员在内的封建士大夫的反对。本文试图从此次上书对民族危机的分析、官场腐败的痛斥及对传统礼仪观念的无视三个方面分析康有为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失败的原因。
一、对民族危机加重的分析
中法战争后,我国西南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对此,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开篇记述道:“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法煽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1]123这仅仅是一个总结性的开头,随后,康有为对日、俄、英、法各国的侵略活动一一呈现,加以描述,指明,日本改革后,迅速崛起,侵略的野心与日俱增,“内治兵饷,外购铁舰”[1]124,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俄国加紧筑路,不出两三年,铁路即可到达我国境内,运输兵力将不再成为俄国势力扩张的障碍;此时,英已占领缅甸,此举即可便于其掠夺云南地区的矿产资源,又可窥视清政府在西藏地区的防卫,为下一步的侵略做准备;而法国此时已占领越南,并于越南筑路通商,最为重要的是,法国注重文化侵略,建设教堂,法国对于我国滇、粤地区的侵略亦采用此种方式,天主教对当地的普通百姓影响巨大,使其与官府的隔阂不断加大,法国利用天主教的影响,其势力范围已扩大到越南、暹罗、老挝等小国。同时,康有为对英法就势力范围的争斗亦有记录,指出,“法国因英海外殖民地众多,近几年也不断扩展势力范围,与英争夺埃及未果,将精力集中于越南以窥视中国,康有为预测到:数年之后,经营稍定,以诸夷数十万与我从教之民,内外并起,分两路以寇滇、粤,别以舟师扰我从海疆,如我长江,江楚教民从焉,不审何以御之?[1]125”对各列强侵略活动的记录极大地冲击封建士大夫自尊心,此时多数封建士大夫正沉溺于中法战争后暂时的“和平”之中,而康有為却在肯定西方船坚炮利的基础上,就列强对中国及其当时的藩属国不断侵蚀的严峻情势加以论述,同时,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予以极大地肯定,预言日本可能会侵略朝鲜及我国边界地区。中国与日本相邻,多数传统读书人对其持有鄙夷的态度,迫使封建士大夫完全接受日本的发展程度已超出封建士大夫的认识范围,使大多数官员所不能接受;而此次上书亦指明天主教在我国南方发展迅速,并威胁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更为封建士大夫所无法接受。而康有为认为,民族危机是变法图强主要原因之一,而变法亦是摆脱此种危机的唯一途径。对当时中国社会民族危机的认识,康有为无疑先于大多数官员以及读书人,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常熟谢戊子不代上书之事,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惭云。”[2]33这是康有为对乙未(1895年)年间的记录,可见,甲午战后,朝廷官员尚未认识到列强蚕食中国的严峻形势。更何况此次上书原早于甲午中日战争。所以,就当时朝廷官员的水平而言,康有为直指民族的危机深重,并称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无疑会遭到封建士大夫的反对。
二、对官场腐败的痛斥
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的大量篇幅是对当时官场的弊端的描述及痛斥,《康南海自编年谱》开篇的概括为:“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败俗,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公,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1]123首先,文中多处出现此时的军队将士与十到二十年前的进行比较,直指当时的军队根本无法抵御外敌与内乱,其中一段直指此时的朝廷在列强的侵略势威逼下,只能束手无策,对此的描述为:“昔甲申之事,法仅以一、二舟师惊我海疆,我沿海设防,内外震动,皇太后、皇上宵旰忧劳,召问诸臣,一无所措,乃旁皇募兵购炮,所费数千万计,而安南坐失矣。且是时犹有左宗棠……皆知兵宿将,布列边外,其余偏裨亦多百战之余,然已兵威不振,人心畏怯如是。今则二三宿将重臣凋谢,其余旧将皆已耄老,数年后率已尽,即偏裨之曾列戎者亦寡,而邻四逼于外,教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1]125随后又指出:今水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财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患无学,此数者,人皆忧之痛恨焉,而未以为大忧者”[1]126军队抵御能力的下降,直接决定列强获利的多少,而军队与官场形式的联系密切,对军队实力的反面论述,必然会招致封建士大夫的反对。
其次是对官场的描述:“窃见与强夷和后,苟幸无事,朝廷晏安,言路闭塞,纪纲日隳。顷奇灾异变,大告警厉,天心之爱至矣,不闻有怵惕修省之事,上答天心。又古者灾异策免三公,枢臣实秉国钧,亦无战兢之意,未闻上疏引罪,请自免谢,泄泄如是。而徒见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驰驱乐游,电灯、火车奇技淫巧,输入大内而已。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1]126此段文字道出了清政府与法国议和后,朝廷上下均认为列强的问题已解决,并沉迷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而正是在这种喜悦之中,康有为上书直指官场的腐败无能,并建议朝廷改革,必然会遭到反对,加之其直指太后注重个人的享受,大兴土木,花费众多,并挪用海军军费众,这不仅会遭到后党官员的反对,在以翁同■为代表的改革派眼里,也是行不通的;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在朝廷占有重要地位,对后党腐朽的直观描述令多数改革派官员无法接受。
更令许多封建士大夫无法接受的是,康有为欲将日本作为改革的榜样,以提醒清政府应适时进行改革,他称:“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况以中国地方之大,物产之沈,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礼治之美,列圣所缔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1]129以同是东方的区区小国改革的成功案例作为改革的依据,冲击了封建士大夫的传统的天朝大国的观念,遭到了以翁同■为首的改革派官员的反感。
直指当时的国势衰败,朝廷上下不修内政,这是对身居官场的封建士大夫的痛斥。虽然,一部分开明官员早已忧于官场的种种弊端,但是出于自身的利益的考虑及多年来形成的中国读书人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加之当时的民族危机较之于戊戌年间并不明显,所以,在他们的眼中,外患问题已基本解决,再要求改革内政无疑是荒唐之举,“不予代递”就成为必然。
三、对传统礼仪观念的无视
除上述两个方面内容外,康有为的此次上书存在多处不符合某些官员对读书人固有礼仪观念,这是此次上书失败的又一原因。文中多次出现“皇太后”和“皇上”的字样时,均是“皇太后”在前,而“皇上”在后,如:“今皇太后、皇上即不自为计,独不为天下计乎?即不为天下计,读不为列祖、列宗计乎?”[2]18这是令许多官员无法接受的,虽然,此时的光绪皇帝并未亲政,但在改革派官员的传统观念中,皇上才是国家当之无愧的统治者。将“皇太后”置于“皇上”之前的表述是其不能接受的,梁鼎芬认为,康有为的极力上书只不过是为了求得仕途上的发展而已,于《康有为事实》中称:“康有为复试京师,因不重举人,遂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已故工部尚书潘文勤公祖荫……皆与康有为素无渊源,乃屡次求见,上书谀讼,皆公以康有为一年少监生,初到京师,遍谒朝贵,实属躁进无品,皆甚鄙之。潘公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此函人多见之。曾公偿告人曰: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徐公、志公见其言嚣张卑蹈,皆将原书掷还,都下士大夫无不鄙笑。”[3]64
梁鼎芬的《康有为事实》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旨在劝说日本政府驱逐当时在日逃亡的康有为,虽然,其中的言辞不免有夸张之处,但它从侧面反映出大多数官员对康有为及其变法运动不予支持的态度。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1888年的纪录渗透着康有为个人性格的高傲,认为其不成熟的变法思想无人能及,以至于称:“是时学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于人中,倜傥自喜。”[2]17而后又称:自黎纯斋后,无以诸生上书者,当时大恶洋务,更未有请变法之人,吾以至微贱,首倡此议,朝士大攻之。”[2]33在其弟子依其年谱作的《康南海先生传》亦有偏于康有为的纪录:“先师与许、李本无隙,只以抵京时不往投谒,先师尝曰:“彼若以吾为贤也,则彼可来先我,我布衣也,到京师不拜客多矣,奈何独怪我。”然许、李竟以是恨之。国子监既不得达盛昱持。”[4]27由此可见,康有为过于骄傲。康有为身居朝廷之外,其变法的主张大多脱离清政府的实际情况,加之其自身的骄傲与自满更招致了许多改革派官员的不满,使其得不到合理的建议,以至于第一次上书及后来整个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
此外,依康有为年谱的记载:“归政大婚,典礼重叠,吉祥止止,非痛哭流涕之时,朝士久未闻此事,皆大哗,乡人至有创论者相逐之。”[2]19就光绪帝大婚,《上清帝第一书》称:“明年皇上大婚礼成,亲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色之防;圣德日新,宜慎近习之选。”[1]130康有为本认为光绪帝大婚,即將亲政,是实现变法的良好时机,而于这个吉祥的时刻,直指民族危机深重,必然会为大多数的官员所无法接受,即便些官员同意其要求改革的主张,但也认为这时并非是上书的良好时机。
综上,此次上书的失败之处在于其中的内容大多脱离当时清政府的实际情况:此时正值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与法国签订条约后,大多数官员沉溺于中外关系良好的暂时安逸之中,而康有为却在此时就直指列强侵华势力增加,民族危机加深,力请清政府进行内部改革,这必然会招致官员反对;此次上书的内容中多处涉及当时政府的种种弊端,言辞犀利,而康有为身居官场之外,其改革的思想存在多处不成熟之处;康有为对传统礼仪观念的无视自身及其性格的高傲,使许多主张改革的官员敬而远之,最终招致其第一次上书的失败。
参考文献:
[1]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G]//杨家骆主编.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二册.台北:鼎文书局印行,1973.
[2]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G]//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3]汤志均.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附录八[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4]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G]//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