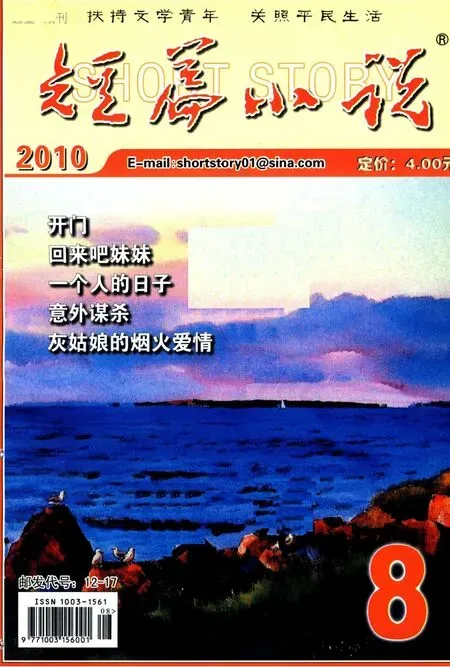两个学生
◎梁 爽
两个学生
◎梁 爽
坏学生小奎
太阳一出来,大地就烧着了。
太阳地儿下,开小卖部的田翠花正撒开腿往地里跑,一边跑一边喊:“大奎——大奎——你家小奎来电话啦——”
王大奎听到喊声,扔了锄头,几步蹿到田边,抓起衣服前襟抹掉脸上的汗水,焦急地问:“咋啦?小奎说的啥?又在学校闯祸了吧?”
田翠花半猫着腰气喘吁吁地说:“小奎这次闯大祸了,说是砸了哪个同学家的玻璃,校长要开除他,让你赶快去呢。”
小奎是大奎的儿子,三岁没了妈,是大奎一把屎一把尿一个人拉扯大的。小奎从小脑袋瓜儿好使,就是不好好学习,不是逃课就是打架,三天两头地惹祸。
前几次小奎打电话过来,都是班主任找家长,这一次竟然惊动了校长,还要开除!田翠花的话没落地,大奎撒开腿便往家里跑。
搭汽车,转火车,一路奔波。下午上课铃刚刚响过,大奎已经风尘仆仆地站到了校长面前。递烟,赔笑,满脸的谦卑,像小学生被罚站一样半低着头聆听教诲。放学后把校长老师都拉到餐馆里,掏光了路费以外所有的钱。
小奎总算没被开除。大奎回去的时候,小奎执意要送。大奎想狠狠地教训小奎一顿,想说你爹我今天把半辈子的笑都赔了,可话到嘴边心又软了。一路上爷俩儿没说一句话,只听到大奎的唉声一个接着一个。
走到离火车站不远的桥上,大奎说,就送到这儿吧,赶快回去上晚自习。小奎说,那爹你慢点儿。大奎快走到进站口的时候,回过头见小奎坐在桥栏杆上。太远看不清,只看见小奎的两条长腿在晃晃悠悠地荡。大奎三步并作两步跑了回来。小奎从桥栏杆上跳了下来,爸你咋又回来啦?该赶不上火车了。大奎说,你咋还不快去上自习?小奎说,我这就去。大奎又说,儿啊,今天的事儿你千万别想不开。人这一辈子,总得过些沟沟坎坎,过去了,也就顺当了。说这话时,小奎看见父亲的嘴唇在微微地抖动。小奎一下子明白了,方才父亲见自己坐在桥栏杆上,以为自己要投河自杀!小奎的心忽地沉了一下,一股暖流从父亲那边辐射过来,倏地涌遍全身,他的双腿软了下去,跪倒在地,重重地给爹磕了一个响头。然后,爬起来,头也不回地朝学校跑去。
又一个下火的日子,锄地的大奎被田翠花喊去接电话。大奎不住地点头,一声接一声地说着谢谢,握着话筒的手抖个不停。田翠花在一旁着急地问,咋啦,到底咋啦?小奎又闯啥祸啦?挂上电话,大奎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哗啦啦地淌个不停。大奎说,小奎考上大学了。
好学生守银
我,叫王守财。因为我大哥叫王守金,我二哥叫王守银,我还有个弟弟叫王守富。一顺排下来,应的是“金银财富”。我们哥儿四个是我爹的得意之作,他常常唠叨我娘,你这辈子干什么都不像样,就生孩子像样。“金银财富”这四个名字也很让我爹得意,他跟我娘说,村东头儿老王家那四个小子叫“龙腾虎跃”,老于家的更能吓唬人,叫什么“雷达舰艇”,都不如咱家的“金银财富”来得实在。我还记着他说这话的时候,正蹲在厨房灶火旁,眯缝着眼睛,卖力地吸着手里的旱烟卷,那张惬意的脸在一团团淡蓝色的烟雾中若隐若现。
我和我二哥是双胞胎,都在县中学,并且在一个班。我没什么故事,正如我的人生乏善可陈。我想说说我二哥。
我二哥长得白净,说话也斯文,村里的大娘婶子爱开他的玩笑,他总是脸红。我二哥成绩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年级的前三名,在我们班上绰号叫“秀才”,是同学和老师公认的好学生。
在我们十五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准确地说是发生在我们十五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刻,那件事发生得没有任何征兆。
那天上午的第一节课是生理卫生课。我们像往常一样端坐在教室里,等那位头发稀少的陈老师来上课。陈老师也像往常一样踩着铃声走进教室跨上讲台。
陈老师五十多岁,已经是快退休的年龄。他以前是教物理的,后来年纪大了得了肝硬化,不能再挑重担,学校照顾他让他改教生理卫生课。
陈老师站到讲台上,把书往讲桌上随便一放,说今天讲生殖系统这一章。我们都坐得笔直,像一排排齐刷刷长在椅子上的豆苗,这其中也包括了二狗他们那些调皮捣蛋的。我们当然都知道今天讲生殖系统这一章,这是我们心里隐隐约约一直期待的一节课。
咳——咳——在我们静悄悄的等待中,陈老师莫名其妙地咳嗽起来。“大家先自学一会儿,我去拿点资料。”陈老师走出门,教室里传出一阵低沉的唏嘘声,嘘声里带着失望。我们步调空前一致地都把书翻到了那一章,细细地读起来。其实,对于这部分内容,大家并不陌生。班里绝大多数学生,都已经偷偷地看过了,有些还看了不只一遍。可是现在,大家仍然愿意光明正大地再读一遍。不一会儿,二狗扯过前面钱小军的衣领不知在嘀咕什么,很快窃窃私语的嗡嗡声弥漫了整个教室。
陈老师回来了,手里抱着一摞材料,又是一阵咳。乱哄哄的教室在陈老师的干咳声中又一次静了下来。我手里的材料是关于青春期生理卫生知识的,请课代表来发一下,每个同学一份,正好今天也自学一下。说完,陈老师又走出了教室。
发下来的材料是一张淡粉色的宣传简报,跟县报大小差不多,样子没什么特别。可一到学生们的手中,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一下子把大家的注意力从课本中吸引过来。简报上的每个题目,甚至很多字眼都让这群中学生脸红心跳,插图上还画着梨形的子宫蝌蚪状的精子等。
我二哥和其他同学一样认真地看着,很快他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儿,好像有人在一个劲儿地看他,先是前面的二狗,接着是钱小军,看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脸上带着诡异的笑。二狗转过身拿着简报,指着一个标题里的 “手淫”两个字,问我二哥:“秀才,帮我看看这俩字咋念?”我二哥有点不屑一顾地说:“这都不认识,不就是——”他停住了,这两个字的发音,竟是自己的名字!二狗还在故意追问:“念什么,念什么呀!”钱小军陈明跟着起哄:“哦——哦——秀才念不出来啦!”我二哥脸涨得通红。
我二哥不知道他的名字居然会和那么龌龊的事扯在一起,他低垂着头,沮丧到了极点。我看到他咬着嘴唇手在发抖。我看到二哥的样子非常心疼,要不是在课堂上,我真想冲过去给二狗两拳!
下课铃响了,我二哥像逃命一样奔出教室,身后响起二狗钱小军他们高一声低一声的喊叫:“手淫——手淫——”长长的尾音被拉成了怪怪的腔调,腔调里面夹杂着戏谑讥讽的笑。
二哥连续两天没来上课。老师问我,我只有摇头。第三天,二哥突然出现在教室里,面容十分愁苦的样子。原来,二哥跑回三十里地外的家里,要求父亲去派出所给他改个名字,父亲一听就火了:“你们兄弟四人的名字,关系到咱家的风水,怎能说改就改?我看你这书是越念越糊涂了。干脆别念了,回家跟老子种地算了!”二哥不敢再争辩,蔫蔫地回来了。二狗一伙见二哥一副颓丧的样子,马上来了精神,他们把“手淫”两个字大大地写在黑板上,然后一哄声地喊:“秀才,请你读一下,这两个字的准确发音——”二哥的脸红得如石榴,继而又慢慢变白,在全班同学的哄笑声中跑出了教室。
我出去寻了一圈儿,没看到我二哥的踪影。我二哥面子窄,不知道他躲到了哪个角落去了。
第二节课,我二哥没来教室,第三节课他依然没有回来。快放学的时候,突然一个喊声划过天空,打破了校园的宁静,有人在喊:“出事啦,出事啦!”全校正在上课的老师全都跑了出来,这时我感到很怕,也连忙跑了出去。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向学校西边的水库跑去……
责任编辑/文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