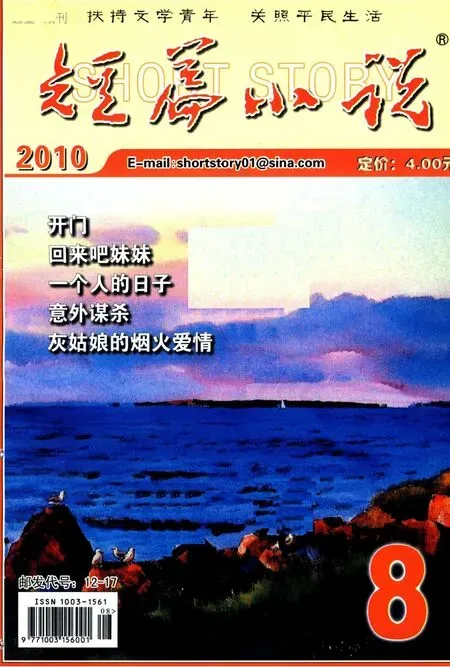二黄
◎王晓峰
二黄
◎王晓峰
黄文忠
黄文忠是李庄子矿黄建寅的儿子。
黄建寅是矿调度室的老主任。说黄建寅老主任,是说他资格老,在调度室一当主任就是十五年,光矿长就熬走了六任。
因为黄建寅资格老,所以黄文忠矿院毕业不到四年就提拔当了机电队副队长。这里面固然有黄建寅的影响力,但关键也在于黄文忠有学历有技术有能力。
黄文忠因为家里条件好,再加上年纪轻轻就提拔当了副队长,所以找老婆就挑剔,眼看着就是二十七八了,还是单身,黄建寅就着急。黄建寅是个很传统的人,就对黄文忠下了最后通牒,年底前如果再找不下对象,就从家里搬出去。
其实,黄文忠心里早就有了人,是矿总机室的花丽萍。那时候,矿上用的还不是程控交换机,还是人工转接的那种。
花丽萍也喜欢黄文忠性格沉稳、才华内敛。花丽萍人长得好,脸是脸,腰是腰,是李庄子矿有名的矿花。
花丽萍是工亡职工的子女,是顶替父亲名义上的班。这种顶替父亲上班的,大都学历不高,花丽萍也不例外,初中没毕业就当了工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花丽萍的妈作风有点那个,名声不太好,这一点,李庄子矿的人大部分都知道。
花丽萍的父亲在井下出事故后,按说,矿上一般情况下都是为工亡职工解决一个指标,有的是工亡职工的妻子接班,有的是子女接,反正只能解决一个,而花丽萍家,却是花丽萍接了父亲的班,她妈矿上又另外安排了工作,在矿井口洗衣房上班,是个集体工。集体工也就是企业的用工,没有纳入国家正式用工系列,企业承认,国家不承认。集体工也有劳保福利,退休也有退休金,除了不是国家的正式职工,退休金比正式职工稍微低一点外,其他差别不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花丽萍她妈不一般。
听人说,花丽萍她妈和矿上一个副矿长关系好。还说,在花丽萍的父亲还活着时,那个副矿长就和花丽萍的妈有一腿,有的人还说得有鼻子有眼,说一天花丽萍的父亲下晚班回来把他们按在了床上,还说那个副矿长写的还有悔过书,花丽萍的妈拿着。包括花丽萍接班,花丽萍她妈当集体工都是那个副矿长一手办的。
黄文忠这次见父亲逼得急了,就说了和花丽萍的事。果然,黄建寅没听儿子说完,就跳了起来,说在李庄子矿找谁都行,就是花家那丫头不行。
黄文忠也是个拧种,狠狠地说,除了花丽萍,我谁也不要。
说完,就摔门而去,搬进了队里的宿舍。把黄建寅气得手都是抖的。
一连两个多月,黄文忠都没回家里去,有时候,就是在街上看到黄建寅,也是脸一扭就过去了。
黄建寅的老婆见黄建寅从外面回来气得像吹猪的样子,就耐心地劝他,儿大不由爷,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主见了,要我说,花家那丫头也没啥不好的,她娘不好,女儿就一定不好吗?龙生九种,各不相同,何况花家那丫头?
一番话,说得黄建寅气消了不少。那年“十一”的时候,黄文忠和花丽萍结了婚,婚礼很隆重很排场,我和一帮跟黄文忠一块光屁股玩尿泥长大的都去了。那一天,黄文忠很幸福,也很兴奋,喝了不少的酒。
一年后,黄文忠的女儿出生了。黄文忠给女儿取名叫黄鹂,取他的姓和花丽萍的“丽”字的谐音。
又一年,黄建寅也退休了。退休后的黄建寅有了大把的时间。黄建寅对孙女很宠爱,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在街上走,经常能看到黄建寅带着黄鹂在矿俱乐部玩。
黄鹂5岁那年,黄文忠和花丽萍家里起了战火,原因是因为孩子。那时候,黄文忠已经是机电队的队长了。
黄文忠虽然当了队长,在单位里说一不二,但本质上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人。黄文忠是家里的独子,他给花丽萍说想让再生个孩子。但花丽萍不同意。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很紧了。花丽萍说,如果生第二胎,她的工作肯定保不住,连黄文忠也要受牵连,甚至会免职和撤职。花丽萍舍不得现在拥有的工作。
黄文忠很苦闷,于是就经常找我喝酒。那时候,我在矿办公室当秘书,给领导写报告。
再后来,就传出了黄文忠和花丽萍婚变的事。说花丽萍和新来的矿长刘全旺好上了,传得很邪乎。
作为矿办公室的秘书,我亲眼看到过花丽萍来找刘全旺,但当时我从没有多想。
再后来,就传出了黄文忠离婚的消息。
黄文忠离婚后,郁郁寡欢。下班后,有时候,也会到我家里坐坐。有一次,他喝多了酒,动情地说,当初父亲的决定还是对的,悔不该当初不听父亲的话,否则何至于到今天这地步。
我妻子也劝他,有机会再找一个,天涯何处没芳草。并自告奋勇地当起了红娘。
黄文忠也真的见过几个女的,其中包括工会会唱歌的夏性美,夏性美当时年龄差不多有30岁了,没结婚,还是个姑娘,据说以前曾受过伤害,我们都认为黄文忠和夏性美挺般配的,但不知为什么他们没能走到一块。
再后来,我因为在办公室干了多年秘书得不到提拔,一气之下,调到了矿务局医院。
从此后,和黄文忠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两年后的一天,我正在医院办公室里写材料,通讯员小田过来说有人找我。
我抬起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你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竟然是花丽萍。
花丽萍比以前更漂亮了,更丰满了,也更白了。她站在我面前,有点扭捏,好像挺不好意思的。
我忙不迭地伸出手去握手,“怎么是你?”
花丽萍说,孩子病了,文忠下井了,麻烦你带我找儿科高主任看看。儿科高主任是我老乡,这点小事自然不在话下。
于是我就带着她去找高主任。下得楼,在病房拐角处,我看到花丽萍的妈抱着一个两岁多的男孩在候诊椅上坐着,看到我过来,连忙站起来。花丽萍向她妈介绍我,这是大伟,文忠的同学,局医院的办公室主任。
看到那孩子,我一下子愣住了,那孩子胖嘟嘟的模样,那眉眼,简直就是和黄文忠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那一刻,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黄月芬
黄月芬是李庄子煤矿张大栓的老婆。张大栓在三采队杂工班干修护工,为人老诚实在,不论是队长,还是职工,让他干啥就干啥,从不会反一句嘴,因此,在三采队,大伙儿给他的评价就两个字:老实。
在李庄子矿,有句俗话,龙配龙,凤配风,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张大栓和黄月芬的婚姻也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般配”。
黄月芬是1991年从豫东新蔡农转非来矿的。农村出来的媳妇闲不住,到了矿上,看到楼前房后一片片的空地,黄月芬就想,这要是都种上蔬菜多好啊。于是,矿区赶集的日子,她就去买了一些西红柿苗、茄子苗,把楼前的一块空地深翻了一次,栽上了西红柿苗和茄子苗。刚栽上的菜苗比较娇贵,怕晒,每天都需要浇水,黄月芬天天吃过晚饭后就挑两个塑料桶去地窨子里挑水,地窨子里的水都是从各家各户卫生间排出来的废水,包括粪便,上到地里很是壮实,但很臭,黄月芬有的是气力,也不怕臭。没几天,黄月芬的菜地里的西红柿苗、茄子苗就长得黑油油的,很是喜欢人。于是,楼上住的一些媳妇们也闲不住了,她们也从家里拿出铁锨,有的自己去开地,有的督促丈夫去开地,没多久,楼前屋后的空地上都栽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
于是,矿上的农转非楼前就有了生机。夏秋季节种的是四季豆、丝瓜、黄瓜、西红柿、茄子,冬天种的是大萝卜、大白菜、菠菜、蒜苗、香菜,春天种的有小葱、春萝卜、油菜等,让来来往往生活在矿区的双职工们很是羡慕,这些农转非的婆姨们干得更欢实了。
又一年夏天到了,农转非楼的婆姨们看到矿区附近的农村一片热火朝天,心里都是痒痒的。刘丽英、白秋香几个就约黄月芬出去拾麦子,黄月芬同意了。第二天一大早,她们五个人就每人找了一顶草帽、一个蛇皮袋子、一个塑料网条编成的提篮,里面放了几根黄瓜、几个西红柿、两个馒头就出发了。黄瓜、西红柿、馒头是她们的午餐。
她们从矿区后面的沟壕里穿过,再往里去是一片坟地。坟地里埋的都是一些在矿上出了事故或者终老在矿的老工人,因为老家没人,都埋在了这里。
黄月芬每次经过这里,心里都是揪成一疙瘩。黄月芬就想,一家都在矿上,将来自己老了会不会也要客死他乡,埋在这里。
黄月芬往这一片乱坟岗看了一眼,见一个长满荒草的坟堆上又添了几锹新土,黄月芬知道,这是谁家的儿女给父亲上坟了,黄月芬就忍不住多瞅了几眼,心里竟莫名其名地起了一阵惊悸,凉嗖嗖的。黄月芬走快几步撵上刘丽英、白秋香几个,快步向前走出。
再往前走,就开始爬坡了,上去坡,就是南大岭,南大岭上面有杨大池、张大池等好五六个村子。地里的麦子大部分都已经收割过,只有极个别的地块没有收割,她们知道,这些没收割的都是家中缺少劳力的。于是,她们就拣收割过的麦地去拾。她们有自己的原则,没收割过的是别人没采摘的果实,不能动。只有收割过的地块才是她们这些人能去的。
黄月芬刚来矿上那一年就听说,矿上有些职工家属去拾麦子拾秋,不是去拾,而是去偷。其中矿上有个家属,有一年去拾麦子,因为收割过的麦田里麦子少,她就一个人钻进了还没收割的麦子,疯狂地抢掠起来,时候不大,就弄了满满一蛇皮袋子。第二天,她也没招呼别的同伴,就一个人出去拾麦子,当她看到四下无人时,就故技重施,结果被村里人抓住。麦田的主人是个老鳏夫,见到一个四十多岁风韵犹存的妇女偷他的麦子,哪里肯放过,就一下把她扑在地上,发泄了一番兽欲。因为自己确实偷人家的麦子了,这个妇女白白吃了个哑巴亏,回去也不敢跟丈夫说。从此后,只是再也不去拾麦子了。
地里的麦子不算多,也不算少,刚捡起这一穗就又看到一穗,看到袋子里的麦穗越来越多,黄月芬心里充满了成就感。中午吃饭的时候,她们找了一棵树,坐在树下吃她们带的黄瓜、西红柿和馒头,由于正中午太阳太毒,她们就把自己上午捡的麦子搓干净。到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她们才又开始起身捡麦子。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黄月芬她们就每人拾了大半袋子麦子,怕有三四十斤。
回到矿上的家里,黄月芬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头昏沉沉的,想睡,张大栓摸摸妻子的额头,有点烫。张大栓以为是中暑了,就给她找了两支藿香正气水让喝下去。喝下去半个多小时,黄月芬的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出现晕厥现象,昏了过去。张大栓吓坏了,叫来邻居帮忙把黄月芬送到矿医院,值班的医生王力给黄月芬量了体温,翻开黄月芬的眼皮看了看,说是中暑了,没事,输几天液就好。
然而,一连输了7天液,黄月芬的症状还是没有见轻,黄月芬头脑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有时候还说胡话。晚上,白秋香过来看黄月芬时,对张大栓说,莫不是中邪了,遇到啥邪气的东西了,并说了她们去拾麦子那天在后沟从坟地边过的事情。
吃过晚饭,值班的医生护士都在值班室空调下乘凉,白秋香把矿上会跳大神的王朝带了进来。王朝进门,先朝医生值班室方向瞅了一眼,张大栓说,他们正在乘凉,一时半会儿不会过来,你放心。
王朝从带的手提袋里掏出一个香炉,然后点燃三炷香,随后又从里面拿出几张黄表纸点燃,让张大栓拿来一个盛满水的碗,随后从兜里掏出三支木筷子,一边扶着筷子在碗中站立,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他所念叨的都是一些死人的名字,当念到一个名字时,筷子在碗里站住了。病房里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咳一声。王朝停了一会儿,说是一个姓贺的人来讨债,缠住了黄月芬。
姓贺的,贺战德?张大栓叫了起来。
王朝点点头,你认识?
张大栓一脸惊悸地点点头。颤声说道,他是我的工友,我们一个班,他1989年在井下修护作业时,被弹起的钢丝绳打中脑袋出的事故,死后没有运回老家,就埋在后沟的乱坟岗。
就是他来找你讨债。王朝说,你想想你欠过他啥东西没?
张大栓头摇得像拨浪鼓。
王朝说,那你就晚上十二点,在通往后沟的十字路口,用白灰圈一个圈,烧几张纸,他以后就不会缠黄月芬了。
张大栓照办。
第二天,张大栓又从贺战德的老乡那里问清了贺战德儿子的地址,然后照着地址给贺战德的儿子寄去了500元钱。500元钱,是他1989年初老家有事借的钱。
下午黄月芬病愈出院。
张大栓问她,她啥也不知道。
责任编辑/文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