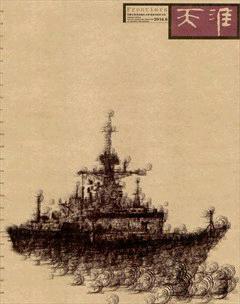由“漂泊者”出发,想象一个世界
王翔
如果有一首歌,能让我感到既悲哀,又温暖,那么就是李叔同的《送别》。“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歌词里的辗转飘零和曲子的哀而不伤,形成一种感觉,好像在天涯海角,心里却又有某种慰藉;似乎孤苦伶仃,却又与世界相通。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感觉,我愿意说是“漂泊感”。《送别》写于二十世纪初,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
有一次和几个朋友聊天,大家都提起了“漂”的感觉。这让我想到,用同一个词,“漂泊感”形容出来的,是不是同样的感觉?而这样的感觉,如果不是孤立的,那么应该被放在怎样的状况里来理解?我们这代人,生在改革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建设的世界。在快速的变化中,有多少东西是需要送别的?从《送别》中听出的“漂泊感”,恐怕不能离开我在这个时代的经验而独立存在。迷惘、希望、路在脚下、路在何方?个人的不安在国家崛起的背景下被凸现出来。“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还是二十世纪的感觉吗?当我感到改革在强力地塑造着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无数人,和我自身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从中产生的“漂泊感”,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人的感受,而是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
漂泊者:改革生产出的青年主体
把“漂泊感”放在改革的脉络里,至少有五个面向。
第一,改革开放催生了国内大面积的流动人口。1980年代后,户籍制度松动,中国人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国内流动。从1970年代末恢复高等教育开始,出现了异地求学的学生群体;1980年代的文化热催生了到处流动的诗人、北漂、艺术家群体;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出现了大量的持续至今的打工人口等等。在这大面积的人口流动中,出现了丰富的“漂泊”经验。他们在异乡是什么感受?他们有什么理想?他们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们能不能回家?
第二,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催生出了对故乡的陌生感。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被快速地推进,房地产强势崛起。在一、二线城市,城市的变化非常大,过一两年就是一副新样子,而这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状态是有很大影响的。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在变。在这样快速的变化中,对故乡的归宿感、依恋感也在快速地丧失。
第三,改革开放意味着集体主义理想的失落和个人主义理想的建立。“文革”结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种理想的失落和混乱。在青年中间,理想五花八门,甚至是空有一股理想的热血,没有理想的内容。我把这样的一个理想形态,看作是个人主义式的理想。一个巨大的共同体破碎后,理想变成了个人式的、漂浮的尘埃。
第四,现代性体验中产生的“漂泊感”。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交通工具的普及和网络对人的影响。飞机、地铁、汽车、摩托,在这些交通工具中,人的身体是被机械带着移动的,人可以很快地在城市里面移动,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而在网络上,面对各种信息的流动,与他人用各种工具互动,人的精神和阅读纸质书是两种状态。在网络上,人的注意力是分散的、流动的、跳跃的,而不是凝聚的、集中的。这样一种被现代的工业和科技带动起来的体验之中,也存在着一种常态化的,以致难以被意识到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漂泊感”。
第五,全球化下跨国和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全球化的动力,是一个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带来了更广泛的交流,甚至形成了跨国的合作、家庭、认同等等。在这其中,如何理解和自己处于不同状况的人?如何面对不同的历史叙述?如何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在什么意义和基础上能发展一种跨国的认同?这些都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青年的问题。
通过“漂泊”这个视角,这五个面向被集中了起来。这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青年面临的新的问题和状况。这是我们的父辈在他们的青年时代不曾经历的。我所谓的“漂泊者”,是被这五个面向所辐射,形成于改革开放这个脉络里的青年主体。
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的漂泊感。通过将这种感觉历史化,我期望可以借着“漂泊”的感觉展开一个视野,看到人们在这历史的转折期,体验着一种可以让彼此相通的“漂泊感”,一种“躁动不安、无根、迷惘、寻找理想”的中间状态。坦白说,在改革的脉络里,我认为没有人可以在这种“漂泊感”之外。漂泊感经过改革催生,或多或少地进入了不同主体的内部。可以说,这是一种与改革所画出的疆域同在的感觉,它涉及到改革所抵达的所有范围。有一次我在上海打车,司机是上海本地人,下了高架桥他忽然找不到方向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新修的路太多了,他不熟。他开着车在街上转来转去,我不知怎么形容那一刹那的感觉,快速的城市建设让这个上海司机不认识上海的路了,我也不知要被带到哪里去。那样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我不知怎么处理,只好让它自然地过去。这种体验很快就过去了。即使事后提起,也像是一个笑话那样微不足道。可以想见,那个上海司机,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继续活在一种对上海非常熟悉的感觉里。但是,如果不放过那一刹那的感觉,如果以它为视角,可以看到,在那个置身于现代交通工具、在新修的街道上转来转去的瞬间,在那种“恍惚、不安”之中,司机和我都现出了“漂泊者”的原形。这是被改革所生产出来的。试想,在改革的脉络里,城市里一天会出现多少个这样“恍惚、不安”的瞬间,这些感觉,即使没有被意识到,也存留在了人们的身体里面。这样来看,一个上海、广州、北京,或某二三线城市的市民,没有离开自己的城市,生于斯长于斯,就没有“漂泊感”了吗?有的!当一个北京市民,把自己和外地人严格区分开来的时候,他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漂泊感”在一种现代性体验的层面上或许并不亚于他者。在一些情况下,外地人的漂泊感可以转化成具体的现实问题,比如居住、异地求学、高考、打工二代等等,本地人的漂泊感在这种对比下看不见了,但不等于不存在,也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处理。
这是一些身体经验,而从主体的精神状态来说,漂泊感更是一种普遍状态。在这个时代,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有什么是可以被称为信仰和理想的呢?究竟还有没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想到外面去,到别处去,他们想体验什么,寻找什么?如果信仰和理想可以被确定为一种精神上的归宿,那么在这个时代,没有精神归宿的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有精神归宿的人是会停留在某地,还是更加无畏地漂泊?当这些问题被不断打开,可以看到,情况变得比以前更加复杂。也许会有这样一种情况,身体上处于漂泊状态的人,在精神上是有归宿的;而身体上处于稳定状态的人,在精神上反而躁动不安。在这复杂的状况中,有一条线索是可以把握的,就是相较于革命时期的集体主义式的理想和信仰,在改革的脉络里,理想变成了个体的事情。对我们这一代的父辈来说,理想、信仰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这样的理想召唤出“社会主义新人”。理想在那个时期不是个体的事情,而是集体的事情,在一个巨大的共同体里面,个体确认了自身的存在感。这是打在我们父辈身上的社会主义烙印。那种烙印之深,不仅停留在思想上,更烙印在语言和气质上。当我试着去理解父辈,我感到的是改革这个转折所产生的巨大的推动力,集体主义式的理想在这个转折点上失落了,随后出现的是个体式的理想在涌动,这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共同体破碎之后,理想炸成了不同的碎片,再没有一个共同体去包揽个体理想和精神上的问题,个体需要自己去建立、寻找理想,与此同时,个体要被迫通过“成功”来证明自己。“漂泊感”从中出现了。理想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精神、一个幽灵,因为它再也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了,它被各种势力深深地压抑住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我看到很多年轻人说不出话来,或者说,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就只能“隐忍”地,默默地活着。你说什么,他听着。为了生存他得忍受很多事情。但你很难说他的这种“隐忍”里面没有东西。也许在某个点上他里面的东西就显现出来,或者爆发出来。同时,大量的年轻人过上了漂泊的生活。到别处去,到远方去,到发达地区去,这种主体精神状态里难道就只有“赚钱”二字吗?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情绪。理想因为找不到内容,甚至形式来表达,所以化身成了一种无休止的寻找、一种持续的无聊、一种不满、一种恐惧。这就是我所谓的“漂泊”状态。我不是简单地在空间的移动上来理解“漂泊”,我也把它理解成一种年轻人主体的精神状态。那么这当然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是很不一样的。这里面有一些快速流动的东西、正在汇聚的东西、无法命名的东西、鱼龙混杂的东西。
在这里,当我说到“漂泊感”的时候,我到底指的是什么?我指的是在改革的脉络里,出现的身体和精神的“躁动不安、迷惘和寻找理想”的中间状态。当我说到“漂泊者”的时候,我到底指向谁?我指的是在改革的脉络里,所出现的青年主体。在我们通常的理解里,漂泊意味着边缘化的生活,意味着一种动荡不安,也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困境,一种需要被克服的状态。随着改革的深入,它还在加深。资本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了时空体验。人口流动的加快,人们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去,从大城市回到小城市,小城市已经变了样子;交通工具的普及和多样化;网络对生活方式的塑造等等。当我把“漂泊感”描述出来,通过它,来联系不同的个体,并把在改革的脉络里所产生的青年主体,定义为“漂泊者”时,我所看到的是无数不同的个体,和汪洋、汹涌、无穷的漂泊的经验。一个孕育无穷的漂泊的中国。
“漂泊者”、“成功者”和“失败者”
这些无数的、多元的“漂泊者”,和这其中无数的、多元的漂泊经验,没有被看到。他们没有“漂泊者”这个名字。在主流的意识里,“漂泊”意味着一种边缘、不安的状态,在这个被划小的范围里,“漂泊者”被约等于打工者、北漂、上漂、异地考研一族等。漂泊者因此不见了,漂泊的经验因此被缩小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
可以说,是改革的脉络生产了“漂泊者”,而在将他们生产出来之后,同样是改革的脉络里出现的资本机制,遮蔽了漂泊者,以致人们对他者和自身的漂泊经验视而不见。具体来看,这些漂泊者被生产出来之后,被资本机制吸纳,变成一种原料,生产出“能够在市场上调动资本”的人,他们被看作是“成功者”。而那些没有成功的原料,则被认为是“失败者”。
1990年代以来,成功的定义可谓是相当狭窄。什么是成功?就是“在市场上能够调动资本的人”。否则,任你有多大的志愿,走过多少路,做过多少事,没有转换成实际收入,都算是落了空。用俗话来说,就叫“不干正事”。这种心态得以形成,来源于市场改革所形成的资本机制。资本机制的强势崛起,生产出一套现代化的繁荣景观,不想落伍,不想被碾碎,就得想方设法在资本机制里站住脚。在这种状况下,整个社会都弥漫起一股“向钱看”的风气。对于在这个脉络里生活的青年来说,理想是一件空虚又奢侈的事情,从小一路考上去,为了读好学校,为了出来找好工作,到头来没能赚到钱,没房没车,这一路的辛苦就算泡汤了,就算是失败了。这是资本机制作用在人身上的结果。在这种状况下,那个多元的、丰富的“漂泊者”的形象不见了。资本机制把“漂泊者”吸纳了进去,碾成粉末,生产出一种“能够在市场上调动资本的主体”,他们被看作是“成功者”。而资本机制的结构规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获益,都能在这繁荣的盛世分一杯羹。从这一点来看,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里面,弥漫着一股那么强的“失败”的情绪,一股那么强的挫败感。因为在这个机制里面,无论多么努力、拥有了什么,只要不愿、不能将这些东西转化成资本,那么就会被边缘化,甚至污名化,“看他那没出息的样子!”而这绝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这是整个物质世界,整个社会所营造出来的实际状况。在这些“失败者”的背面,少数的“成功者”却可以呼风唤雨。这就可以理解,恶俗文化、炒作、算计、厚黑、各种不择手段的底气是从哪里来的,只要能赚到钱,赚大钱,那么就能把各种资源集于一身,就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在这背后,一个更清楚的现实是,资本机制使阶层分化日益凝固。在这种状况下,大量的资源在封闭的圈子里流动,而大量的“漂泊者”,为了生活苦熬,看不到未来。
在改革的脉络里,“漂泊者”作为原料,被资本机制生产为“成功者”和“失败者”。可以说,这三个形象,三种青年主体,是同在于这个脉络里的。而从现象上来看,“失败者”被社会意识到了,但是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用一种“失败乃成功之母”的语言来表达。“成功者”被全社会都看见了,成为一种骄傲,他可以插科打诨,可以励志,可以尽情表演。然而“漂泊者”被遮蔽了,他甚至没有被主流意识到。举一个小例子。前些年有一个号称“打工皇帝”的,宣称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作为一个“成功者”,他的形象在主流媒体上覆盖了打工群体,并成为了某种标准。在这跨度三十多年的打工群体中,有多少故事、多少经验,岂是“赚钱”二字就可以全然收编的?难道他们都是经济动物?这些人背井离乡,有多少心情遗失在路上?这些“漂泊”经验,如果能够得以呈现,“宛如一片叶子展开所有植物丰富的经验世界一样”(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可以呈现多少不同个体的具体状况?资本机制遮蔽了这个“漂泊”的视角,吸纳了这些“漂泊者”,从而把这些艰难的,也是丰富的经验转述成了同一个故事:一个为了赚钱,在异乡打拼的故事。在这其中,被提炼出来的“成功者”,成为了代表。更多的人,被掩埋在“失败”的尘埃里。
由“漂泊者”出发,想象一个世界
当我说到“漂泊者”指涉的是一种多元的青年主体,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无法再用一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来解决,也就是说,没有一包药,能包治所有人的病。在大的关怀之下,应该发展一种视野,来进入不同的主体内部,看到不同的状况。高屋建瓴的感觉是很好的,革命时期所培养出的“威权人格”延续到了新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时期并没有过去。在改革的时代,革命的能量以一种“思维”和“气质”的方式存留了下来。这是一种威权人格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思维。这使我常常产生一种感觉,好像人人都是集体的代言人、国家的代言人,唯独对具体的个体视而不见。比如说,我听过好几次这样的对话,A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有问题,B说那你有什么办法来代替吗?在这段问答里,A的抱怨被上升到一个体制代言人的位置,个体经验在这种思维里被湮灭了。在这其中,一个简单的事情是,个体的发言位置是什么?他在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经验里面有了抱怨?从他自身的状况出发,能做些什么?这些问题在被上升到一个“整体”的讨论以后完全看不见了。
当我说到“漂泊者”,是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方法,让这种来自威权人格的、集体主义思维的外壳,可以从不同个体的身上脱落下来,让不同的个体可以看到自身的具体状况。这意味着一种经验和情感上的解放。也就是说,要把“方法”从集体主义的一方,转移到不同的个体一方。要做这种视角的转换,首先需要的,是不同个体的充分发育。
不同个体的充分发育,也就是不同的中国人的充分发育。我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是某种不证自明的实体吗?在不涉及具体状况的讨论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幻象。在这里,需要被追问的是,什么是“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近现代的屈辱?社会主义理想的试验?崛起的欲望?等等。中国的镜像在不同的语境里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在这样一种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比如仅仅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视角来理解中国)中国的镜像中,一个应该被打开的问题是:中国人应该往何处去?在改革催生出的“漂泊感”里,中国人呈现出了什么不同的形象?也许现在是一个时机去追问这样的问题。
我有一个感觉,在新世纪以后,中国逐渐进入了一种“大国崛起”的氛围里面。1990年代,还处在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忐忑心态里面,社会上还有很多对“亚洲四小龙”的羡慕之声,人们觉得台湾、香港那么发达,我们还比不上。新世纪以后,中国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底气。现在很少再会听到说“亚洲四小龙”怎么样,听到最多的就是美国怎么样。美国变成了一个参照对象。在这其中,国内产生了一种按捺不住的集体情绪,尽管伴随着很多混乱的局面,比如恶性的公共事件、对体制的不满、对贪腐的痛恨等等,这种情绪还是很强地起来了,就是“大国崛起”,而这其中的核心,则是“经济崛起”。这样的“经济崛起”不仅仅是一个赚钱方面的事情,它承接了一个二十世纪“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记忆,所以一旦有机会翻身,就来得特别猛烈,也特别急切,有种恨不得要一步登天的感觉。在这种亢奋中,国家似乎与个体更牢地捆在一起了。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时机,就是大国崛起的情绪在尝到了经济崛起的滋味之后,可以暂时地松弛下来(但也有可能是更加强烈),这使得“中国人”的形象有可能从一个大中国的幻象中脱离出来,在不同的状况里看到自己。这里需要细致说明的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与中国的国家意识是牢牢被捆绑在一起的。著名的例子有郁达夫在小说《沉沦》里的结尾,“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在这篇定稿于1921年的小说里,郁达夫写了一个在异乡的学子,孤独、颓废,在迷惘和色欲间飘零,最终走向了自杀。这些可以被归为私人的情感,在小说的最后,上升到了一个国家的层面上,青年的失落被扩大到整个国家的失落。个人的主体性无法离开国家意识,而国家意识,在这里,横向来看,是被外来列强的侵略所形塑出来的一种向内凝聚的共同体意识;纵向来看,则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尊严被挫败之后,产生的一种屈辱和崛起的欲望。让中国崛起的欲望积压在民族的内心深处,这使得个体在这种欲望得到释放之前,无法从国家意识中脱离出来。而当中国崛起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即使仅是经济上的满足,个体也就有可能从国家意识的压力中松弛下来。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人在海外开始不再束手束脚、抱成一团,而是敢于表达物质上的欲望。这种挥霍背后,则是一种积压了太久的集体的屈辱感,得到了释放。中国人有钱了。中国是大国了。这样一种感觉产生了出来。这是一个时机,让中国人可以从受屈辱而形成的集体意识里松弛下来,发展出一种有差异的个体意识。在不同状况里的个体被看到了以后,很难再用一个上升到整体性的问题把个体的困惑封闭掉,而是由不同的个体,开始以自己的经验来丰富对“怎么办”的追问。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抽象的构想,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回到教育体制的问题。说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一个人应该怎样发展自己?这些问题应该交给别人来处理吗?交给权威、上级、官员来处理吗?同样,什么是好的生活?一个人应该怎样建设自己的生活?这些问题应该交给社会吗?交给父母、世俗?还是交给看不见摸不着的命运?现实的情况是,“大国崛起”的氛围形成了一种内部的压力,由市场机制产生的“外力”在强力地塑造、规范着个体。这种“外力”之强,以致有国外观察者认为,赚钱成为了中国人的信仰。这都是现实的情况。但在这其中,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个体选择的空间?青年主体有没有可能不按照市场机制产生的“外力”,而是从自己的精神世界发展出的“内力”来生活?
很可能,这是一些正在发生,但还没有被主流社会意识到的状况。漂泊的经验,迷惘、不安、流动,以及其中蕴含的理想,发生在个体身上,而当这样的个体越来越多,这样的经验跨度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个可以想象的事情是,在这些不同的个体身上,出现了一种相似的“感觉结构”。“感觉结构”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还没有在现实世界成形、在政经秩序上表现出来的东西,作为一种感觉的、情感的胚胎,出现在经验和意识里。那么“漂泊”的经验在这里是否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现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是,资本机制无法把全部的“漂泊”的经验转化成“成功”与“失败”,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把“漂泊”的经验全然规范起来,转化成一种“正能量”。而这些漂泊的经验,这些面目模糊的漂泊者,从他们自身的生活状况和轨迹中,能不能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想象?这个世纪所出现的种种“漂泊”经验在模糊、打散上个世纪所出现的知识和想象。比如,在上个世纪“落后就要挨打”的经验里出现的,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是否需要全然复制到新世纪,并在中国崛起的状况里,形成一种大国角逐的局面?在新世纪的资本机制已经进入人的外部和内部,是否只能复制上个世纪的“乌托邦”想象,以此来在资本主义文明之外“寻求另一个世界”?在全球化的进程里,怎么处理“外界”和“他者”?怎么理解和自己不一样的主体?“外界”仅仅意味着把自我放大吗?“他者”就是自我的投射吗?在不可避免的与外界和他者的接触中,从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出来的知识和认同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举个具体的例子,香港的回归,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意识里,是前殖民地回归了祖国,由此,“中国人”重新成为了香港人的认同。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回归的问题在回归那一刻就得到了解决?进而意味着香港在历史转折中出现的复杂心情不需要处理?近现代屈辱的记忆使中国向内,凝聚起一股民族主义的情绪,这与大国崛起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国在改革的脉络里,在与外界的接触中,当自身受到外界刺激(不公、欺压、不满、隔膜等等),这种被二十世纪历史塑造出来的民族情绪就很容易涌动起来。
在新世纪全球化继续加深,流动性继续加快,不同区域的人被压缩在一起的状况下,复制二十世纪产生的对“个体”的想象,并将它限定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面;那么可以预测的是,在流行文化所塑造出来的“相同的人性”背后,是不同区域的个体对彼此更深的隔膜。在对“漂泊者”个体的想象中,包含了一种尚未被看见的,然而可以感知的新的集体意识。这种新的集体意识是指向民族国家,一种理想、跨国的认同,还是别的什么,其实是随着“漂泊”的经验在不同的状况里而变化的。是否可以想象一个世界,并不是把“漂泊者”都纳入一个轨道,加工成“成功”和“失败”的产品,而是能让他们各行其是,创造自己的生活?是否可以想象一个世界,其中可以包容不同的梦想和没有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