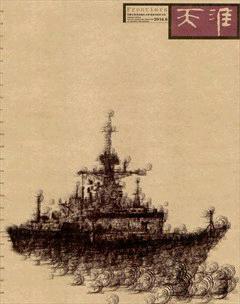银色笔记
夏商
经典
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须在经历光阴沉淀后,成为能证明某一时期风格的“有非凡价值的艺术文物”。它竖立在时间之河的中央,成了一座艺术的分水岭,或者是岛屿上的一支标杆。
虽然电影的历史不如其他艺术种类漫长,但其经典作品存量,已与古老的文学、音乐、美术并驾齐驱。经典往往给人以深刻却又模糊的印象,因为毕竟是过往的作品。经典这顶桂冠是对一部作品的最高封赏,也构成了整个艺术史的核心。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史就是经典作品史,那些值得被记录、研究、回顾的作品被反复阅读、倾听或播映。
经典的意义在于它从浩瀚的作品中筛选出神品妙构,同时为艺术家提供一盏跨入不朽之阃的气死风灯。经典最终将成为一种有意味的模式(这个论点脱胎于克·贝尔的著名释条: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而被供奉和神化。
具体来讲,一部电影——当然也可以是其他艺术种类——在它所产生的时间和欣赏趣味上,具备了一种非凡的价值,似水流年之后,它逐渐消失了历史的属性,脱离了原始的背景,就有可能在观念和形式上落伍,但这种落伍不会削弱其价值,就像一匹死去的骏马被制成标本,仍以优美动人的姿态嘶鸣在博物馆的座台上(须知,当年的马群如今已腐骨无寻,而它保留了皮囊并流传至今)。
需要指出的是,经典作品虽然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艺参数,但并非说经典必然完美,更不是说,同时代的其他创作皆无价值,被湮没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平庸之作,但平庸之作不乏闪光点,并可能给创作出经典的艺术家带来启示。更何况,还有少量被时代遗漏或严重低估的杰作,那些永恒的遗珠之憾。
结局
一部放映中的电影,就像拂晓的潮汐,朝黄昏推进。经过一夜轮回,河流又恢复原来的姿态重新流淌。而观众,在一部电影中只能获得一个故事。影片开始前,观众不知道故事将以何种方式开始,与之相对应,未知的结局为观众提供了猜谜的乐趣。随着剧情展开,联想也开始了搜索,所以说,为故事寻找答案是观摩电影的乐趣之一——因此任何剧透对观众而言都显得非常无礼——当然,电影故事的结局本已存在,只是眼下还深藏不露(观众的胃口还未吊足),等到线索和情节都交代完毕,答案自然会跃入眼帘。
对猜中谜底的观众来说,既已预判准确,再将影片看完是否削弱美感?而对未猜中的观众来说,则不免为自己推理的错误而涌起沮丧。
表面上看,故事人人会讲。难度在于,从寓言、神话、戏剧到小说,世间已无新鲜事可讲。此刻,讲故事的方式成了唯一的出路,此乃实现“伟大虚构”的前提:将看似平常的情节置入全新的空间维度,通过不同的人物塑造,整合出迥异的叙事架构。诚如匈牙利影评人伊芙特·皮洛所言:因为电影的挑战性的多元的结构、电影的客观性和具象化本性真实地反映出统一与差异的辩证法。
故事成败的关键在于原始的剧本或念头,一部影片再怎么玩形式主义的花拳绣腿,毕竟还是要叙述一个故事(电影的历史本身也是一个故事)。而如何去感召观众,并让他们都成为失败的猜谜者——构思必须做到既不落窠臼,又避免不合逻辑——需要专业而扎实的基本功,不管怎么说,故事在片尾曲奏响前就丧失悬念,属于拙劣的败笔。
绯闻
你得承认,一个绯闻层出不穷的演艺圈是让人嗤之以鼻的。但同时也得承认,一个绝迹了花边消息的演艺圈也是乏味不堪的。已故台湾散文家三毛女士曾说,一个人死亡固然是可怕的,但无边无际的永生却比死亡更加恐怖。这句禅机之语,阐述了事物的两面性。当然某些真相只存在于假设之中,无法在现实中变现,却能让我们换一副认识世界的眼光。
绯闻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明星的重要程度,感召力和知名度越高的明星越容易被绯闻包围。绯闻包括一部分杜撰的故事,一部分永远难以证实的真假莫辨的流言,以及一部分确有其事的真正的桃色新闻。它们共同融入明星的人格,被公众津津乐道。
明星的绯闻和工作是孪生姐妹,共同维系了明星的新鲜感,一个明星甚至可以持久没有作品,但不能持久没有可被人引为谈资的绯闻。明星不再走红往往是从不再出产绯闻开始的,绯闻经过断章取义式的演绎,成为市井打发无聊的八卦,而一个不再有吸引力的明星,人们是不屑于绕口舌的。
艺人们对这个传播学的秘密了如指掌,通过各种渠道,隔三岔五透露出一些风声,吸引拥趸的眼球,满足受众的窥视癖——那些空穴来风甚至荒诞不经的幕后花絮或生活片断——他们宁可被人讥笑、诋毁与唾弃,也不愿被人遗忘。
而绯闻的另一功能是用来填充传媒的版面和镜头,养活八卦撰稿人、猎奇摄影师和小报记者,也养活了四分之一的传媒业。
机遇
现在,如果你想满足一颗八卦的心,可以从街头报摊上捞起一本娱乐杂志,从拙劣的文字中看看那些关于明星的秘史、绯闻和发迹史。不难发现,差不多每个明星都得到过好运的眷顾,一个修长性感的美人在贝弗利山庄蹀躞徘徊,她在等待什么呢?一个洗车店男孩在调笑打逗时赢得了好莱坞女大亨的芳心,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呢?
须知,一个刻意寻求运气的人,成功概率不见得比无心插柳者更高。经常漫步果园的人不一定被苹果砸中,反之,误入果园者倒可能接到一只从天而降的苹果——牛顿脚下也曾有苹果落下,但真正的机遇却是一个期待中的灵感,这可不是规范外的特例——那么机遇究竟是什么?手中翻着一本诗集,有这么两句“:有时就像瞧着似曾相识的脸孔,但又不能确定它到底像谁。”正好充作注释。
机遇作为命运的馈赠,是成功通途上的一束鲜花,小机遇可以使演员上一个台阶,重大机遇则能跨入电影史的殿堂。但机遇的出现并无时间表(它躲在何处呢)。好演员在守株待兔的过程中,努力使自己变成吸引兔子的树(请允许我修改一下那棵树的寓意),在低谷或逆境中自我完善,博览群书,以提高人文和艺术修养,或者加强台词训练、形体训练、体能训练,学习游泳、攀登术、驾驶、马术、舞蹈、武术乃至方言——某些技艺在现实中未必常用,但对一个演员来说,不存在无用之用,自身实力会促成机遇的产生。
事实上,机遇看似毫无规律可循的客观存在,却并不虚无。机遇和纯粹的运气不同,人们常说机遇只赐予有准备的人,从这个角度说,它更像是一种理性之侥幸。
模式
电影当然具有模式——严格说,这是任何艺术形式的通病——导演未必乐意承认这一事实,那样的话,自以为是的风格焉在?事实上,拥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雄心历来被视作创作的美德。在具体作品中,为彰显个性,各种古怪念头亦层出不穷,而电影是最易于产生模式的介质之一,门类繁多的类型片可见一斑。譬如黑帮片(真相从时间的画轴中图穷匕现,徒留下清算和忏悔),再譬如贺岁片(一种被节日化的档期,属于时间的细分市场)。
另外,美并非艺术的唯一定义。这里的“美”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审美,也可以是残酷美学、暴力美学甚至审丑——作品完成后,受众介入评判赏析,使作品染上主观色彩。受众艺术修养的差异决定了感受到的作品的不同——它同样适用于模式的抵抗者,或风格的缔造者(多少南辕北辙的创作)。艺术家试图寻找别人尚未发现的灵感,却悲哀地发现,别人玩剩下的花样确实不多。
艺术的幸存者拖着疲惫的步伐,何处才是原创的目的地?是模式的牢笼还是风格的运动场?风格是短暂的,而模式永恒。上一部电影立刻成了下一部电影的模式,一个新的风格就是一个新的模式。就是说,风格永远包容在模式之中,而不是模式像油脂中的纸被风格浸透。
但是,坚持革新的艺术家仍受到普遍尊重,他们驾驶着技巧和形式两辆卡车一路莽撞,不能否认,是他们用冒险接近了艺术的真相。时间为先行者默哀,悼词镌刻在银幕之上:“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墓碑背后,返璞归真的叙事小径探入了广袤的现实主义森林。
替身
作为影子演员,替身至少解决了两个问题,其一,台前演员对自身能力的遮丑;其二,帮助台前演员完成对隐私的遮蔽。和假唱类似之处在于,替身同样扮演着欺骗观众的角色(有时候也像是愚弄),但假唱是主体用预先录音的方式担任自己声音的冒牌货,替身则是用客体完成或补充对角色的塑造。
替身的出现,除了可以让影片完成度更高之外,对市场的迎合也不容忽视。观众之所以踏进影院,盖因电影是视觉神话,感官刺激亦是其典型的技术特征后遗症——更多的暴力、恐怖和性爱镜头,使观众在变本加厉地索取官能快感的同时,视觉逐渐变得麻痹和迟钝。若干年前一个令成年人毛骨悚然的镜头,如今司空见惯得连孩子也能承受。同样,一些往昔被认为与伦理相违的画面,也早已是小菜一碟。
随着刺激形式的周期越来越短,电影越来越近地向惊险和伦理的极限靠拢。越来越多的演员力不从心,与此相对应,替身们用冒险和自尊伪装那些自动隐身的台前演员:一个凌空跃下的动作可以由训练有素者来完成,一个拒绝暴露的女星可以用另一具赤条条的身躯来迎合观众的目光。
如果我们对动作替身尚能理解的话(某些危险或高难度动作确实超出了台前演员的能力),那么,隐私替身基本是一个悖论(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凸显演员的身价和自我尊重),但观众若有意淫的念头,其对象依然是台前演员,而不会是代行其躯的替身(哪怕利用传媒澄清,也只是掩耳盗铃式的掩饰)。从这个角度说,隐私替身完全是自欺欺人。
配音
一部业已完成的影片,基于语种传播障碍的因素,抽去原有对话进行重新配音——作为背景的音乐、大自然之声、道具间的摩擦声和异动之声无须修改,一些无关紧要的对白亦可酌情保留——这样,影片便由成品变成了半成品,须经历再回到成品的创作过程。
被配音的通常对象是外语片,将它翻译过来,用本国语言让剧中人进行流利的对话或独白,以使不懂外文的观众也能身临异国他乡。少数不常有的情况是为本国演员配音,这些演员一般都具备绝妙的表演天赋,或者能饰演别人难以胜任的角色(譬如特型),但带有地方口音,或口齿不那么清晰,这种情况也给予配音。
配音人来到译制片厂,熟悉故事、角色与台词,渐次进入角色:注意力集中在画面上,嘴唇随着镜头更替而翕动,依照剧中人物的声调配上母语台词,口型与角色保持吻合。
表面上看,配音是一种听觉的替身,究其质还是有很大差别。替身不会刻意去让观众识别其真相,配音却不必担忧这些,特别是经过翻译的外语片,观众毋需猜测,便知外国演员背后站着自己的同胞,某些出色的影迷,还能从典型的声韵中判断出是哪一位配音演员。
另外,在观众印象中,替身和配音人的职业属性也迥然不同,前者包含了敢于冒险的草莽硬汉、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杂技人、习武者、不惧暴露身体隐私者,后者则是用嗓音作为文化桥梁的声音艺术家。
情色
性爱镜头向来被视为触犯了隐私,作为禁忌,它必须隐在道德与伦理背后。当在银幕上公示于众时,便可能被斥为色情——淫秽的标准大致是模糊的——不同于情色。
我们知道电影是艺术和技术相糅合的产物,最初的观摩者来自城镇与都市,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文明社会的公众。表面看,城市人对蛮荒土著所崇尚的“裸体比袒胸露背更接近美德”的观念不以为然,但在本能上,人性的欲求几无差异,所谓“文明人”同样乐于接受来自生命本源的“放纵”,然而文明社会在公序良俗框架下,对原始欲望产生约束和修正,使公众恪守程式化的规条。
于是,当厕身影院,共同观赏性爱画面时,观众的目光开始变得羞涩。通常情况下,他们宁愿观赏“干净”的镜头而免得彼此尴尬——实际上,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内心并不排斥情色,这基于快感除了来自性器官,也可以来自视觉想象。亚里斯多德对这种无害且“合法”的“放纵”有过精确定义:唯有一些身体的快感属于放纵范围,其中要排除视觉、听觉或嗅觉的快感。从色彩、姿势或绘画中“获取快感”并不能叫作自我放纵,更不必说戏剧或音乐了——那些放肆的、具有挑逗性的镜头令观众如坐针毡。银幕上角色的动作却在继续,直至摄像机把镜头移开。
片商掌握了观众半遮半掩的心理,将情色与暴力、悬疑、幻觉、恐惧等人性中隐秘的情愫添加到影片中,只要电影一息尚存,作为一种招徕观众的商业手段,这些蛊惑人心的叙事策略永远不会绝迹。
故事
银幕讲述的故事有一个隶属于电影的专业名词:剧情。剧情的完整结构与原始的剧本无关。换言之,作为剧情的故事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文本的核心。亦即,电影的剧情是可以被肢解的故事,这一点与文学创作中内容与事件的联系颇为相似。
剧情是连贯而缜密的,能化成无数细节,这些细节本身也互为连贯(故事是穿起珠子的引线),之所以可以被化开,约等于文章中标点符号或自然段落的缘故。电影的标点符号可以是音乐,可以是无关紧要的景物,可以是空镜头,甚至可以是剧中人抑扬顿挫的语调。电影的自然段落则只须用一个镜头的转换,或蒙太奇就可以完成。
“故事”一般起源于某个传说或真实事件,更多则纯属虚构。不管怎样,在搬上银幕前,故事以凝固的姿态记录于纸上——也有将故事装在脑子里就开机的导演——于是这里就又冒出一个有待解释的词语:剧本。
故事保留一个构思的框架,表演则要靠临场发挥。在剧组中,对故事感兴趣的是导演。对演员来说,故事却可能仅仅是一个外置。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故事中的“人物”以及更细微处:性格、癖好、手势、眼神、步态、口型,而对观众来说,那些看似各个不同的故事其实早已被分门别类。
回到中国内地的电影,其不长进的首要原因是导演是文学的外行,甚至还发生过导演攻击小说的言论,认为无须从小说中获得故事。文学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渊薮,好小说更是无数经典电影的始发地。导演对文学无敬畏之心,不是傲慢而是无知。但若完全偏重人文,而忽视电影的技术发展,也会误入另一条歧途。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电影的文学性和技术性皆不可偏废。
剧本
与剧本对应的是编剧:一部电影最初的灵感之父。绝大多数观众喜欢表述明确、有趣、不晦涩的通俗电影,偏重于内涵的艺术电影则拥有小部分忠实爱好者。这两类电影在剧本之初,所呈现出来的文本形态或许就不同。前者,编剧用简略(甚至粗糙)的文字来搭建叙事框架,凭借喋喋不休的台词,逐渐还原一个完整的故事。后者,编剧在叙事的同时,会打磨结构和文字,使之看上去更像一部文学作品。
艺术电影往往是复调、解构、故作深奥的代名词,不时要让观众动动脑子。此乃小众产品的外因。从诞生伊始,电影便过于强调其通俗性,娱乐价值大于人文价值。长期的视觉强制灌输,导致观众退化成信息接收器,逐渐丧失思辨能力。越来越偷懒的观众直奔情节而去,不愿体会叙事之美——须知,观众和读者一样需要培养——这也是电影的原罪之一,而按顺序,编剧是电影的第一创作人。
需要指出的是,虽有艺术电影和通俗电影之分,但两者本身并无高下,不成功的艺术电影很多,杰出的通俗电影也不少,这跟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情况相类似。
剧本的写作需要激情,也需要克制。在创作过程中,用对话来谋局,脑海里要有预设的镜头感。电影和小说一样,故事的脉络有其自身规律,试图篡改其走向必然走进死胡同,这也是为何很多电影没有逻辑的原因。
剧本将幻想和梦境浸润于文字之中——编剧可以由导演亲自担纲,也可以委托职业编剧执笔,更多则是默默无闻的新手——影片公映了,剧本为编剧争取到一个一闪而过的名字。导演和演员被传媒频频曝光,在鲜花掌声镁光灯中摆拍,在各处华丽走秀。而编剧在半掩的窗帘旁,面对电脑或一摞纸,构思起下一部剧本。
怀旧
怀旧如同本能,是心灵敏感者不请自来的乡愁。一个人的老去不仅是身体的凋敝,更是灵魂的日渐枯萎。我们无法用怀旧来证实内心依然柔软,过去的时光于今已成泛黄的电影,而过去的电影亦在这个夜晚对着青春叫魂。怀旧者反刍着逝去的往事,泛黄的老电影是怀旧的一部分。
一部老电影重新放映,似曾相识的情节如同复活的故人旧事,映照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拔开一只思绪的木塞。观摩者浸淫其中,旧年的余脉在此延伸,一丝伤感被回忆的青草地覆盖而无法释怀。银幕上在讲述与己无关的故事,流动的图像似曾是今日的渊薮,却让人有形同虚设之感。我们有时会混淆电影和梦境,强烈的体验使回忆与现实彼此互为镜像,一些深刻的暗示也同时被揠苗助长。
怀旧交织在悲喜之间(那是一种缠绵的情绪),怀旧的电影挣脱了艺术羁绊,缅怀者不会专注某一部电影,只要是旧片,只要是过往的影像,便成了今天的背影,银幕上的叙事宛若流淌的溪水,洗涤着怀旧者纷乱的思绪——怀旧掺杂着对今天的不满,本质上是一种失意的诗意——于是,老之将至的梦中人、清醒的人、理智上的旁观者,试图借助一部过时的影片触摸遥远的世事细节。他们坐在影院之中,四处的灯光暗下来,奇迹好像真的发生了。
影迷
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盗版无疑该受到严厉谴责。但不能否认,猖獗盗版海外电影以半公开的方式流通,为中国内地贡献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影迷。
现如今,我们拥有的影迷可能比任何时期都要出色——此处的“影迷”是一个被强化的专门名词——他们不局限于电影同仁范畴,而像一把溶解的糖丸稀释在公众之中。他们受过基本的人文训练,懂得遴选和甄别电影的优劣,甚至是这个领域的小小专家。在全部观众席位中,他们并不占多数,却是银幕真正忠实的伙伴。因此,“影迷”可以解释成半专业性质的电影鉴赏者,“观众”的释义则是纯粹消遣的电影消费者。
正如文学史由作家与读者共同创造一样,一部电影艺术史,同样由导演与观众共同完成,而影迷,作为观众中的精华,更是用挑剔的审美迫使导演们将电影的格调提高半格。从票房的角度,观众和导演一直是博弈关系,“影迷”作为观众中具有引导性的力量——和影评人的作用不同,影迷更具有口碑传播的价值——对一部影片的评价更易被身边的“观众”所接受,而真正控制票房的正是人丁繁众的后者。
在小众文化的影迷和大众文化的观众之间,绝大多数导演试图在雅俗共赏中找到平衡。品味与票房要像鱼和熊掌一样兼得,但刻意两全的影片很少达到两者的高度统一,艺术片和商业片之间终究难挪开一扇屏风,而影迷也变得越来越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