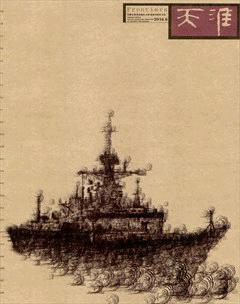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生存
杨碧薇
永恒的高贵单纯
2002年,许巍推出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时光·漫步》。在此之前,他的单曲《两天》(1994年)、《执著》(1997年)、《在别处》(1997年)、《那一年》(2000年)等,早已获得了不少摇迷的喜爱,被推崇为不可多得的经典。在压力重重的期待视野中,许巍沉寂近三年时间,潜心创作,《时光·漫步》由此诞生。
据说,这张专辑在录制期间,就已激起业内音乐人的广泛共鸣,更有人在录音棚中聆听新歌时掉下眼泪。然而,如此高的评价,并不能抹除一部分摇迷们的失望。他们在疑问:曾经那个咆哮、愤怒、痛苦的许巍哪儿去了?
摇迷们的失望并非无根可寻。作为二十世纪新兴的音乐形式,摇滚乐的历史不过短短几十年;但正是在这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摇滚乐与整个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幻共存亡,无时无刻不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在很多时候,它充当了青年、草根、知识分子等群体的文化代言人,表达了他们的种种个体诉求与现实理想。很大程度上,摇滚不是欢乐的产物,它所充任的社会角色与所担当的社会任务,令它的产生与焦虑、孤独、愤怒、挣扎、失望、控诉、鼓舞等情绪紧紧挂钩;它往往具有粗粝的、喧嚣的、浓重的、摧枯拉朽的底色。许巍初入乐坛时,其激进的、躁动的文化姿态,正好符合了民众对摇滚乐的惯常期许,正如他在歌里唱的那样,“每天幻想的自己,总在另一地方”(《在别处》)、“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希望,一天用来绝望”(《两天》)、“在生存面前,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那一年》)、“我不停地弹着不停地唱着,直到所有的力量尽了”(《浮躁》)——这个来自古城西安的青年音乐人,他迷惘、忧虑、清醒而又无路可走,他的每一首歌,都像是杜鹃啼血,字字沉重、力透纸背,缠绕着世纪末的感伤。
是的,早期的许巍,似乎生来就拥有这一姿态,亦可能在这个路数上继续走下去。可是,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居然呈现出与前两张专辑《在别处》《那一年》截然不同的面貌,也难怪摇迷们的第一反应是失望了,有人甚至绝望地认为“许巍已经不再摇滚”。
如今,又是一个十年的时间弹指而过,静下心来细细沉思,拨开岁月的迷雾,关于许巍的转向,我倒是有一些话可讲。
我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算是个铁杆摇迷。许巍《爱如少年》(2008年)之前的所有专辑,我在中学时期都已全部听过,其中的很多都是陪伴我多年的枕边歌。2002年,推出《时光·漫步》的许巍时年三十四岁,一些摇迷说他已“不再愤青”,其实,从“愤青”到“非愤青”,这或许是一个好的转向。“愤怒”,是一个人在成熟过程中应该经历的阶段,落实到个体,却不是每个人的必然阶段;总之,从“愤青”成长起来的人,他的人生与别人的人生有着明显的不同;他能在一次次的打击与对抗中逐渐明白:“愤怒”常常凭空就浪费掉宝贵的力量;“愤怒”对于解决问题、改变人的生存状态而言,最终往往无济于事。
先来看看《时光·漫步》的真面目。这张专辑里收录了十首歌:《天鹅之旅》《完美生活》《时光》《蓝莲花》《一天》《礼物》《漫步》《星空》《夏日的风》《平淡》。今天,几乎每一首都成为广为传唱的经典;其中《蓝莲花》还作为插曲,出现在伍仕贤的电影《独自等待》里。
这十首歌曲,从旋律、节奏、语言、思想等方面来说,几乎避免不了共同的特质:简单、明亮、灿烂、宽阔,有着雨过天晴后的清新与大气。《天鹅之旅》写对理想的追寻,采用的不是传统式苦情叙述,而是用一种“狂欢化”的积极态度说:“飞越这群山,飞过那洁白云海,飞过那万马奔腾的绿色原野,飞过那辽阔碧海蓝天,飞向那温暖春天”;《时光》写对爱情的追忆,润浸着淡淡的忧伤,却不失明朗:“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漫步》写人生态度,豁达而坦然:“让它自然地来吧,让它悄然地去吧;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这些歌曲,编曲越发清澈、柔和,旋律简单易记,歌词朗朗上口。这种风格,使得个人的世界在进入音乐中时,一切都回到了单纯自然的原点,丢弃了冗繁、铺张与晦涩,像是一名疲惫的旅行者突然甩开了沉重的行李,奔跑在一片初春的原野上;太阳明媚,蕙风和畅,草色浅嫩可喜,周围的人们都变得可爱。这张专辑甚至让我联想到古希腊艺术所秉承的审美风格:简单明了、直击情感、让人一见倾心。谁能否认,这种单纯,能让世界更加透明、让人心更加高贵呢?
风格上的转向,与许巍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从《时光·漫步》开始,他的生命体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既有对道家的广阔博大、不拘一格的向往,又有对佛家的空明透澈、无尘无埃的顿悟,也有西方现代文化资源的身影,即摇滚乐一贯所追求的个性与自由。就像他的一首歌里唱的那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曾经的你》,2004年)——他历经过北漂的困窘,体验过常人难以忍受的生活,陷入过理想幻灭的低谷期,最终选择了坚持信仰。曾有的一些思想包袱,随着阅历的增加、思考的深入而日益烟消云散。他从最初的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渐渐转变为积极调整自己的内心世界、主动适应外部世界的生存法则。可以这么说,《时光·漫步》并不只是许巍的一个单纯的文化选择策略,而是他的内心世界与他所身处的外部世界的冲突获得调和的一个产物,它鲜活,它生动,它有肌有理。它的酝酿有着许巍矛盾心境的背景,但在它诞生时,这种矛盾已经与世界取得了彼此的谅解。由此,《时光·漫步》便成为了不一样的摇滚产儿,它不是在愤怒中孕育的,而是在反思与思考中孕育的,更显温情。反思与思考,是而立之年的许巍争取来的一笔宝贵财富,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人生道路上,它们都给了他转变的契机,使他获得了新生,也为中国摇滚带来了不一样的面貌:作为个人,与外界的紧张关系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如果愿意调解、说服自己,愿意低头进行自我重塑,同时也依然坚持真善美的标准,那么美好的奇迹,就会纷沓而至。
中国摇滚的历史并不长。纵观2002年前的整个中国摇滚史,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不管是崔健、何勇、张楚、郑钧等音乐人,还是黑豹、唐朝、指南针等乐队,他们的作品更多地承载了绝望、挣扎、疑惑、愤怒等,采取的姿态往往是声讨、控诉、揭露、批判。这样的艺术,尽管能有助于人们在这个时代中持有更为清晰、警醒的心,却尚不能肩负起传达正面力量的历史重任。也就是说,在《时光·漫步》之前,摇滚乐的这个社会功效仍是盲区。但是摇滚这场艺术革命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揭开疮疤,还是为了寻找解药,它的产生与存在,都是为了人类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而《时光·漫步》的出现,刚好填补了中国摇滚的这一盲区,带给我们一种新鲜的启示,也使中国摇滚的面貌愈发多元、复杂、包容、全面。从此以后,在中国,一个摇滚乐的新时代来临了,它更怀有希望,更加感恩,也更能在这纷繁的世间保持一颗平常之心;新一代的摇滚音乐人们,能在这片更为完整的摇滚土壤上成长;而对于听众而言,这就是莫大的福祉。
从这个角度来说,《时光·漫步》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容忽视。它虽不是宗教,却具有一种与宗教一脉相承的超越性。它那高贵的单纯,是凸出于凡间的一个坐标,让摇滚与人生,都有了另一种仰望的可能。
摇滚的浪漫骑士
如今,中国的摇滚乐队越来越多,要说这态势像是雨后春笋,那也一点不夸张。如果要我评出其中最优秀的十支,超载绝对榜上有名。进入乐坛二十余年以来,超载就像一棵常青树,丝毫没有老去的迹象,至今仍在广大摇迷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要将超载的音乐风格归类,恐怕能摊开一堆标签:金属、英伦、雷鬼、朋克、电子……估计某些口味偏重的摇迷们,会死抱住重金属不放,以此作为标尺,来否定其他风格所具有的摇滚特性。这样恐怕不太好,对于摇迷们来说,损失的是所能吸收的艺术视野;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如果也秉持这种心态,损失的就是自己所能开拓的艺术园地的广度和深度。超载的风格很多样化,这很好,这虽是增加了乐评人阐释的难度,但却能激发起更丰富的回响。
与听其他一些乐队的专辑听得散有所不同,我听超载听得比较系统,就是从他们魔岩时期的同名专辑《超载》(1996年)开始听的。接下来接触的就是滚石时期的《魔幻蓝天》(1999年),然后理所当然便是《生命是一次奇遇》(2002年)、《生命之诗》(2006年)以及《祖先的阴影》等零散的单曲。
早期的超载,给人一种“狂飙突进”的感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金属席卷中国大陆摇滚的时候,摇滚音乐人都免不了长发飘飘、愤怒燃烧。这个时期的超载也不例外,通过音乐,他们建立了一种“破碎的残酷”的美学风格,与死亡金属貌似有着渊源联系。主唱高旗近乎绝望地嚎叫着“抖抖毛,修修我的窝,等待那最后埋葬我的烈火”(《荒原困兽》)、“我知道我在欺骗你,我仍然孤立无依,我无法跨越你我的距离”(《距离》)、“风吹过,我无法再退缩。你曾是我唯一的爱,失去后才知悲哀”(《梦缠绕的时候》)。从这个时候起,年轻的超载已经在关注“人的存在”这一存在主义的重要命题。内心强烈的冲突、撞击在激烈的音乐样式包裹下,以裸露的、咆哮的、坚硬的、黑死的形态呈现出来。正如《九片棱角的回忆》里所唱:“经过那个陌生的高台前面,我已忘记证明我的勇气;当在空中高高飞翔的世界里,我已明白存在的意义”,超载以音乐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悖论与无法逃脱的人生困境。这使得他们的音乐从一开始便充满了严肃的哲学思考,不同于一些乐队单纯地追求音乐上的快感,人生哲学这一立足点是决定他们能成为一流乐队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第一张专辑《超载》发行之前,超载乐队已经历经了五年的打磨。这期间,他们创作了《梦缠绕的时候》等歌曲,参加过不少现场演出,拍摄过电影《头发乱了》(管虎执导,1994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阅历与艺术经验。《超载》的产生,已站在比别人更高的位置上,有登高望远之势。原来中国摇滚还可以这样——赤裸而激愤的社会抗议在1990年代逐渐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音乐人更加关注自身,追求“人”的觉醒,试图处理好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超载》是一张穿着重金属礼服的唱片,它撕扯、震撼、大气、瑰丽,给人的视听以彻底的洗礼。其实在这张唱片里,超载乐队之后的转型已悄然显现——如果说,这是一张关乎“人的存在”命题的唱片,那么,人文关怀便是它的核心。这种强烈的人文关怀,在接下来的《魔幻蓝天》这张专辑中,演化为了更为浪漫的人文情怀。
从第二张专辑《魔幻蓝天》开始,超载的音乐多了不少温情。他们令人心动地演绎情歌、沉静地思索,得出了云淡风轻、世界美好、生命可贵的结论。同名歌曲《魔幻蓝天》非常激荡、振奋、恢宏、壮丽。卸下金属的妆容,洗去铅华,《魔幻蓝天》像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孩子,在一片湛蓝的天空下欢快地奔跑着,他的奔跑永无止境,指向远方:“童话的结尾人们永远相亲相爱……继续期待,高山背后无边的大海;荡尽尘埃,幸福仍然列队在等待,我们的到来。”歌曲那段轰轰烈烈的结尾,包含着升华了的生命体悟,融合了苦涩、辛酸、纯真、坚持、乐观、热爱、向往,让人无限感怀,有着非同寻常的艺术感染力。这样的超载,似乎更为本色,他们原是对生命怀有热爱的,哪怕艰难,哪怕曾经疑惑。他们的抒情从未消失,他们的浪漫可见一斑。
这张专辑中另一首独具特色的歌曲,莫过于《快乐吗》。《快乐吗》从《魔幻蓝天》的亢奋情绪中走了出来,变得悠远、温和,字里行间飞翔着自如的禅意:“暮鼓晨钟、霜飞惊鸿、缘起缘空,谁会再相逢”,在淡淡的忧郁中,对人生的领悟却又多了份超然的态度:“知道我心中,已学会宽容……享受我生命深处的从容”。超载像是为眉头紧锁的生命耐心地描完眉,从此后,生命不再颦颦戚然,她展开了笑靥,变得成熟、宽阔、淡然、玄妙。而《私奔》与《不要告别》,则是天真烂漫的情歌,意气风发,情深意浓——超载越来越有儿童的态度,他们所呼唤的就像是孩子的愿望。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说过:“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超载正是怀有童心的真人,他们的浪漫中有着不可抗拒的天然风度,他们坚持求真、求善、求美,这对艺术而言,尤为可贵。
第三张专辑《生命是一次奇遇》,延续了超载浪漫抒情的风格,创造了一个更为多姿多彩的情感世界;第四张专辑《生命之诗》中收录了不少以前的曲目,经过重新演绎,更为圆熟的技艺与更为丰富的音乐元素,都凝结在超载对生命的更深层次的感悟中。
回顾超载所走过的路,不得不提到他们超强的阵容。主唱兼吉他手高旗,是超载乐队的灵魂人物。高旗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均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父亲是合唱团的指挥,母亲现任教于美国国家影艺学
院。在良好的家庭氛围熏陶下,高旗自年少起便接触了大量的西洋音乐及文学作品,在走上摇滚的道路前,他就有过多年的诗歌散文的写作经验。这些积累,对于他的音乐——特别是歌词与思想内涵,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精彩优美的歌词,超载的音乐质量要打一半的折扣。乐队的主音吉他手李延亮,被誉为中国内地的“首席吉他”,没有他,超载歌曲中的solo便会变得干瘪、失去灵魂。李延亮炉火纯青的吉他技术,也是决定超载的音乐质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鼓手刁磊,是公认的偶像鼓王;贝司手刘文泰与低音吉他欧洋,也在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此外,赵牧阳、张炬、王孝冬等都曾加入超载的阵容,为这支乐队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这样的一个阵容搭配,注定了超载的起点更高,它的光芒难掩,必定会星芒四射。
说了这么多,要真正领悟超载的魅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他们的音乐。我一直认为,上乘的音乐是精湛技艺与高尚灵魂的统一体。一部音乐作品,不管是技艺欠佳还是思想贫乏,都将使它被排除在经典的门外。对摇滚乐而言亦是如此。摇滚乐的审美价值与时代意义,都建立在“技艺”与“灵魂”的基础之上。作为一支摇滚乐队,超载在寻求技术突破的同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人文关怀,以及他们所能达到的人文深度,都彰显了艺术的价值与意义。真正动人的艺术,绝对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超载让我看到了中国摇滚的希望。
摇滚在中国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由于其边缘化与小众化的特征,不少摇迷沮丧地呼喊“中国摇滚死了”。其实,将这三十年的时间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它甚至微小得难以计量。中国摇滚面临的一切挫折与问题,都只不过是这种艺术形式在新生时期所必经的磨难。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起点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摇滚是一场启蒙革命,它必须从改变一小部分人开始做起。我相信中国摇滚会继续成熟,会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使他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超载赋予摇滚以浪漫,浪漫又为他们的音乐增添力量。我希望中国能有更多的超载,就像唐朝乐队的《浪漫骑士》所唱,他们是一群大情怀的摇滚骑士,恪守不可磨灭的浪漫主义理想,用尽他们的所有,带给这世界无限的力量。超载在《陈胜吴广》中唱道“挺起我沉重的胸膛,选择这唯一的篇章”,这群摇滚骑士正是这样,纵然深知路漫漫而修远兮,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将时代的担子勇敢地扛在自己肩上。
给我一座孤独城堡
记忆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在岁月的喧腾中,它很容易被沉置;然而,在某些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刻,它却又从脑海中浮了上来。比如说,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一幅佚失许久的海报,记忆的浪花便开始细碎地涌来,最终海浪翻腾。没错,那是木马乐队的专辑《果冻帝国》的宣传海报,当年曾被我贴在卧室的门上,每天进进出出,我都会扫上几眼。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一次匆忙的搬家,使很多物事默默地离开了我,等到我想起时,它们的沉浮命运,我已不可知。
至今看来,《果冻帝国》仍是一张非常不错的唱片,木马也是我一直以来所喜欢的一支乐队。尽管这支乐队已在2007年秋天宣布解散,但是他们以“木马”冠名时所发行的音乐,注定不会退离中国的摇滚史。
《果冻帝国》是木马的第三张专辑,2004年9月,由国内著名的摇滚音乐厂牌“摩登天空”发行。其实,我正是从这张专辑才开始认识木马的。当时去买唱片,唱片店老板,外号“胖子”的,送了我一张《果冻帝国》的海报,从此,木马的音乐走进了我的生活。在此之前,高中一年级的我对这支乐队一无所知。在秋意阑珊的故乡小城里,木马的音乐陪我走过整个秋天,又走过了整个冬天,并持续到现在。说来好笑,当时是去买哪张唱片,我反倒忘了。
在没有任何乐评与必要的背景知识的情况下,我开始听《果冻帝国》。我听歌素来比较随心所欲,这次也不例外,我零零散散地听着,并不是一口气听完的。我听的第一首是《如果真的恨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因为这首歌的名字比较长。其中“吉他发出巨大的声响,优美的段落里,失真了情绪;而这一切就像是在梦里,超越了自制力,虽然无奈,但是又无法不跟随它”成为我所能记诵的经典歌词。我感受到逝去的美。木马打造了废墟之上正在衰老的美丽,这就像是残月照耀下的疼痛的城市,它在低低呻吟,在冷漠地叙述,一种后工业时代的孤独感由此而生。
这是我个人的解读,不知他人是否有同感。作为一名聆听者,也许在我个人的情绪中,这种感觉与生俱来,所以我能很容易地在木马的音乐中得到契合与共鸣,轻车熟路地进入它。在这些歌曲中,一种“天生悲观者”的立场隐约闪烁。我的聆听体验,第一反应是感觉木马的音乐很哥特,甚至联想起了Theatre Of Tragedy(通译为“悲情剧院”,挪威哥特金属乐队),当然随后我很快就发现这种联想的准确性有待商榷。随后,木马又让我联想到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它们都激荡着一股带有颓势与末日情绪的黑色华丽;我还联想到这样一些东西:风筝、小巷深处、黑白电影、破碎的城市、霓虹与流光……不管联想到了些什么,很快,我就放弃了以“哥特”的标签来定义木马,他们的音乐风格及其精神内涵并不能如此简单地归类。
木马表达了在此之前的中国音乐人未有过的一些特性:他们的姿态很“精英”,并不试图为底层代言;他们的创作很文艺,有深厚的艺术功底;他们的语言、旋律、风格,一切都是为了惺惺相惜的“小众”而设计。在《果冻帝国》的文案里,木马写道:“唱给所有不喜欢大声说话的人。”不喜欢大声说话的人,就是社会中沉默的一群,在无声的表象之下,掩埋着很多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情绪。木马钻进了主流的缝隙之中,为这一小群人充当了音乐上的代言者。这样的创作定位,使木马的音乐传播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却能让懂得它的人,将它追捧、热爱到骨子里。
木马所有的音乐,都是建立在这个“精英”姿态之上的。木马乐队的灵魂人物——主唱兼吉他手木玛,曾有过在美院混迹多年的经历。作为一名模范文艺青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离开美院后的北漂历程也是势在必行的。也许和他那学美术的头脑有关,他的音乐作品中总是有着强烈的画面感,有着无限阐释的空间:“无能的木马,被分裂后的假人,因爱而兴奋的脸,陌生,却紧贴着”(《美丽的南方》),“星斗被镶嵌在天幕,不管有多少猜测,轨迹都不变动”(《如果真的恨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在这里,各种意象,无论是人为的“木马”、“假人”,还是自然界中的“星斗”,都被他信手拈来,自然而然地化用到歌词中,赋予其强烈的后现代气息,造型艺术也由此与音乐艺术相关联。这些意象都是高度提炼高度抽象的,听众须得具备一定的想象力与艺术直觉才能感知其美。
能将木马从众多乐队中区别出来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他们的风格。虽然木马已经解散了,但直到如今,在中国大陆仍然找不出类似的第二支乐队。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独一无二来自于他们的才华,来自于他们的骄傲,来自于他们的个性,还来自于他们对自身审美风格的营造与把握。木马的音乐风格,像诗歌一样,因为具有“含混”的特质,意义更为多重复杂。华丽自然不言而喻:“我们沉醉,我们卑微,我们在各自的世界里孤寂的坠毁。即使破碎,姿态也要优美,装作只是在庆祝一次巧妙的轮回”(《庆祝生活的方式——献给胡湖》)。木马的华丽不同于洛可可,洛可可是流于艳俗的,木马的华丽却在精致的堆叠中不失宽敞的空间,这是木马所独创的“灰色的华丽”。木马也是迷离的,这种迷离并不是现代文明所推崇的乡村消逝的忧伤,而是城市人的生存困境的直接反映,人与人的紧张关系、爱情的不确定性、生活的难以把握、生命的神秘性,都促成了木马音乐的迷离,再加上电音制造的各种噪音效果,迷离更是得到了淋漓的体现。木马还是冷漠的,他们的冷漠很艳丽,像是一名身穿黑色大衣涂着大红色口红的女人,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也使人在接近她的时候感受到冰冷,带来锥心的感觉,却又无法逃脱。木马也是“拒绝”的,他们在刻意与世界保持一点距离,虽然无时无刻不身处在世界之中,却试图使内心与其间离,以此来强调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精神个体的独立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木马是“狂欢”的。这种狂欢化倾向,在之前的中国摇滚乐中难觅踪迹。在《果冻帝国》这张专辑中,频频出现“party”(如《超级party》)、“宴会”(如《超级party》)、“舞会”(如《庆祝生活的方式——献给胡湖》)、“剧场”(如《情节》)等语词,这些集体活动的热闹喧嚣反衬了个人内心的孤独与焦虑、空白与失落。根据巴赫·金的理论,这种带有狂欢性质的社交活动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个人对社会压力的一种对抗,另一方面,它是一个自足的颠倒世界,在这里,易位、换装、改变角色都可以发生,以实现人的无限宣泄。但以“精英”姿态进行创作的木马,他们的“狂欢”虽然也承载了种种的对抗,却又有着与民间的“狂欢”所不同的一面:狂欢并未使木马的风格变得诙谐,相反,在狂欢中,木马越发成为痛苦的清醒者,坚固地捍卫着自己冰冷、华丽、低迷的姿态:“热烈是假的,冷漠是美的……我们是糖,甜到哀伤。”(《超级party》)
就如一篇乐评所说,木马并不是“摇滚专业户”——他们似乎也不急于主动表现出摇滚的姿态。但毫无疑问,木马用音乐搭建起了一座现代都市人的孤独城堡。这座灰色低调的城堡里,小心翼翼地盛放着都市人的脆弱、疑惑、撕裂、漂泊、放逐与忧伤。它是一个避风的港口,有着party结束后的孤独,凝结着木马的思考:“世界在说谎,青春在谎言两旁”(《果冻帝国》)、“不清晰的词语构成了世界”(《Feifei run》);还有他们特有的哀愁:“我内部的众神啊,准确地将我撕裂吧。使我在高处默然地观望,又在低处的狂暴中,坠向轮转,迷途深远而悲凉,而悲观而绝望”(《美丽的南方》)。也许,只有在这种喧哗过后的寂静中,静静聆听木马,我们才能抓住生命的本质里最扣人心弦的东西:孤独不一定一无是处,我们需要孤独,需要孤独城堡保存我们的高傲,这样我们才能在证明自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如今木马已解散五年,乐队的各成员业已单飞,这不能不说是摇迷们的一大遗憾。赖以使人得到安慰的是,精神贵族的“精英姿态”这面旗帜不会倒下。在孤独城堡中,木马依然是主人;在孤独城堡之外,他们是暗涌所磨不平的石头,继续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并歌唱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