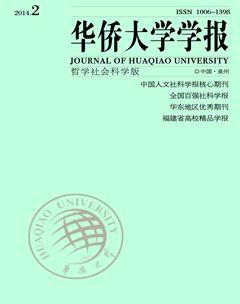从 《第二性》 和 《金色笔记》 看波伏娃和莱辛的女性主义思想
王丽丽林凌
从 《第二性》 和 《金色笔记》 看波伏娃和莱辛的女性主义思想摘 要:《第二性》和《金色笔记》的问世不可避免地将波伏娃和莱辛与女性主义紧密联系起来。评论界都注意到波伏娃和莱辛对女性问题的共同关注以及她们各自对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影响,然而却忽视了波伏娃和莱辛在各自作品中所传达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差别。她们不同的女性主义思想维度源自她们对女性生存和女性出路的不同视角,而这一点恰恰是导致她们后期对女性主义运动持不同态度的关键。了解这一点,不仅会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变化轨迹,也给予我们对女性主义发展前景的巨大启示。
关键词:《第二性》;《金色笔记》;西蒙娜•德•波伏娃;多丽丝•莱辛;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9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4)02-0145-09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与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1962)被许多学者并称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姊妹篇以及女性主义的“圣经”。国内外学者(如苏珊•拉德纳和一丁等)都曾指出《第二性》是女性主义的“圣经”。参见Susan Lardner. “Angle on the Ordinary.”New Yorker, Sept.19,1983.p.144. 转引自 Gayle Greene. Doris Lessing :The Poetics of Chang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17;一丁: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与第二次国际妇女运动浪潮,《中国妇运》,2011年第2期,第45-46页; 瞿世镜把《第二性》和《金色笔记》称为姊妹篇,详见瞿世镜主编:《当代英国小说》,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虽然波伏娃和莱辛各自采用不同的话语方式(《第二性》是理论著作,而《金色笔记》是小说),但是对女性问题的共同关注和深刻剖析,使《第二性》和《金色笔记》成为女性主义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经典。爱丽丝•史瓦兹在《波伏娃访问录》中谈到:“她的作品《第二性》从生理、心理、经济、历史各方面来探究女人置身于男人所控制的世界中所经历的内外在的各种真实情况,是一部无出其右的划时代巨著。甚至在《第二性》出版三十三年后……它仍然是论述新的女性主义最周详、最深刻的理论性著作。”[1]15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提到:“《金色笔记》对知识女性以及政界女性的分析……引领着西方妇女解放运动。”[2]307-308因此,尽管波伏娃和莱辛本人一开始都试图在自己和女性主义阵营之间划清界限,但《第二性》和《金色笔记》的问世却不可避免地将这两位20
--------------------------------------------------------------------------------
收稿日期:2014-01-09
作者简介:王丽丽(1960-),女,河北定州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世纪伟大的女作家与女性主义联系在一起,莱辛甚至被称为“英国的波伏娃”Margaret Drabble和Elizabeth Wilson都把莱辛和西蒙德•波伏娃相提并论,参见Gayle Greene. Doris Lessing:The Poetics of Chang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18.另外在访谈中,特尔科尔也提到了莱辛被人称为“英国的波伏娃”,参见Studs Terkel. “Learning to Put the Questions Differently.” in Doris Lessing: Conversations. ed. Earl G.Ingersoll. New York:Ontario Review Press.1994.p. 30.。十三年后《金色笔记》的问世使许多评论家在分析论述这两部著作的女性主义思想时,都注意到波伏娃和莱辛对女性问题的共同关注以及她们各自对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影响,然而他们却忽略了波伏娃和莱辛在各自作品中所传达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差别,而这一点恰恰是导致她们后期对女性主义运动持不同态度的关键。波伏娃和莱辛女性主义思想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反映出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也预示了女性主义的发展趋势。本文试图通过对《第二性》和《金色笔记》这两部著作的比较,从波伏娃和莱辛对女性生存和女性出路的共同探索入手,来探讨这两位作家女性主义思想的不同及其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
一 人的存在与女性存在
二战后的西方世界,平等观念、人权观念以及人道主义思潮空前活跃。女性主义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如火如荼地展开,两性不平等的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波伏娃目睹了这场女性主义运动给西方女性带来的变化,但她敏锐地察觉到这场女性主义运动明显的局限性,即仅停留在追求具体的教育、就业、选举等权利,却未触及到父权制文化及滋生父权制的社会土壤。于是,她根据个人的体验和对其他妇女的观察,对女性的历史处境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哲学式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第二性》一书。《第二性》的诞生,可以说是顺应女性主义运动发展潮流的产物,也为随之而来的女性主义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波伏娃在《第二性》开篇便提出:“女人是什么?”[3]3波伏娃用“他者”[3]4一词形象表征女人的身份和处境,并对这种处境进行阐释和分析。她认为,生理学的论据能够让人理解女人,理解女人的处境,但它们不足以确定性别的等级,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女人是他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恩格斯的经济决定论也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女性何以成为他者,因为仅仅以性和技术来解释人类生存的现实是不合理的。在她看来,“身体、性生活以及技术只有在人以存在的总体观点把握它们的时候,才能具体地存在”[3]83。一战后,存在主义思潮风靡欧洲,其理论核心便是孤立的个人“存在”。存在主义者在论述“个人存在”这一哲学根本问题时,把人的意识、内心感受、体验、情绪等等看成人生存在的本质,并且反对以人受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等制约的观点来研究人。[4]813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拥护者和继承者,波伏娃立足于存在主义,从人的存在出发来把握女性的存在,揭示女性的处境。
波伏娃认为,一切生存者同时具有“内在性”和“超越性”。[3]345这里的内在性和超越性是波伏娃对萨特关于人的“自由”的具体化和延伸,也是她对海德格尔关于此在(Da-sein)的“非本真的存在”[5]216和“本真的存在”[5]216的沿袭。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萨特认为,自由是以主观性和超越性为特征的纯粹意识活动,自由不是人存在的某种性质,而是人的存在本身,人就是自由。而人的一生就是不断选择的筹划,并通过筹划选择创造自由的本质,不断向着未来的道路自我造就自己。[6]173-174海德格尔则将此在归结为两种不同形态的存在:本真的存在和非本真的存在。所谓非本真的存在,是指此在被技术和制度物化、异化的状态,失去了他本身的独立性和自由;而本真状态是,尽管人无法逃脱环境的支配,但他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逃出非本真状态,获得他本身的独立性和自由,从而按其本性而存在。[6]156-159同样,波伏娃以“超越性”描述个体自由地从事一项筹划,从而能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在世界上行动的生存状态,而与之相对立的“内在性”则是封闭、被动、停滞、止于空想而无所作为的生存状态。在波伏娃看来,事实上,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它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自由。[3]23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只有男性能够不断超越既定的现实,通过他们的活动改变外部世界,实现创造,而要求女人呆在家中的父权制则将女人的使命囿限在延续物种或料理家庭的活动中,并用“永恒的女性”[3]6以及“女性气质”[3]6将女人推至封闭、被动的内在性。女人的所作所为,被认为不能直接影响世界和未来。她只有在以丈夫为中介时,才能超出自身,延伸到社会群体。这是父权制给女人指定的命运,绝非女人的天性。在萨特那里,人的自由决定了他可以自己选择存在的状态,而且人的自由所带来的是无限的责任,人因此要承担起自由选择的后果。同样,波伏娃认为,女人作为人的自由本质也决定着她可以自己选择存在的状态,并对这一选择承担责任。但同时,人身上都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意图以避免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7]82-83恰恰是这种逃避的意图,使女人在自由选择生存状态的时候选择了非本真的存在状态。这样一来,她就成了父权制的同谋,将自己推至“内在性”和“他者”的牢笼之中。[3]14
波伏娃坚持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思想,但她认为个人存在又绝不单纯是孤立的个体存在。她从一开始便将“自我—他者”[3]5的二元论视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范畴。也就是说,任何群体在将自身确定为一个群体的同时,也必然引出与他共存的“他者”之概念。海德格尔提出人的本质就是存在。他认为,人的存在(此在)从本质上说是在世之存在,即存在的基本结构是与他人“共在(Mitda-sein/Mitsein)”。[5]40、112-113波伏娃认同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共在”之说,但问题在于倘若人类社会的现实是建立在团结和友谊基础之上的“共在(mitsein)”,那么女性何以一直被束缚在“他者”和“内在性”的巢穴里?为了进一步揭露男人和女人这两个对立群体共在的本质,波伏娃沿用黑格尔“自我—他者”意识的辩证法来分析两性之间的关系。[3]10黑格尔把人归于自我意识,并认为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8]122。也就是说,真正的人,真正的自我意识是产生和存在于自身和他人的关系之中,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自我意识和另一个与之对立的自我意识之间的相互承认。但同时,两个对立的自我意识之间又处于不断的斗争中,这种斗争是建立在要对方承认自己,而自己不承认对方的基础上进行的。每一方都想要消灭对方,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主体性。[8]125这种情况下,任意一方被消灭都会导致相互承认的关系失效,这样一来,真正的自我意识或真正的人也就无从谈起。主奴关系便是这种斗争的消极产物:一方面,主人需要另一意识(奴隶)的承认,但他却不承认另一意识的存在;另一方面,另一意识(奴隶)放弃了他自己的自为存在或独立性,践行着主人要求他做的事。[8]128同样,波伏娃认为,“自我—他者”的概念本身是相互的,每一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自我又是他者。但她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这种相互性。女性这种非本质的他者状态,从一开始确定,就成为一种绝对性,被强加于女性身上。波伏娃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男人在历史进程中总是占据着主宰的地位,他们送给女人“女性气质”这种虚假的财富,以交换她的自由,而女性的自我意识则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另一个体的意识所超越和压制;另一方面,女性放弃要求对立的一方承认她自己,如此一来,她也再次成为压迫自己的同谋。显然,波伏娃通过对女性长久以来所处的“内在性”和“他者”处境及其根源的本体论分析,指明了自我意识的存在对个人实现超越性和自由的重要性。这对于唤起女性的自我意识,号召她们为摆脱“他者”和实现自由的理想而努力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性》问世13年后,在海峡彼岸,《金色笔记》的出版引起广泛关注。虽然此时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刚燃起星星之火,但多丽丝•莱辛以惊人的预见力,洞察妇女解放运动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它所引发的种种观念的偏激性,以小说的形式对女性主义运动作出客观而冷静的回应。《金色笔记》真实地描述了现代女性所遭遇的“自由”困境和恋爱、家庭等所引起的情感困惑,揭示出单纯的妇女解放运动并不能化解社会给人的生存带来的种种约束,妇女解放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给女性带来自由。因此,与其说《金色笔记》是莱辛为妇女解放吹响的号角,不如说是莱辛通过女性用以观察生活的滤色镜来触摸20世纪中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脉搏,并阐释社会气候对女性生存不可避免的影响;而她在《金色笔记》中对“自由女性”[9]1的书写与其说是一种理想和诉求,不如说是在呈现现代女性生存现实的基础上对女性“自由”不现实性的一种揭露。
《金色笔记》所呈现的是一幅关于20世纪中叶整个世界局势和英国妇女生存境况的画面。科技的高度发展,商业经济的兴起,使人类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上,还是思想上,都有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与此同时,苏联的大清洗运动、美国的政治清查、麦卡锡主义、斯大林去世、氢弹试验等等问题把整个西方世界引入了意识形态纷争和文化思想领域巨变的转型期中。在这样复杂多变的社会变革中,思想的纷繁导致了精神的混乱和分裂。就女性而言,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兴起使女性在政治、经济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权利。然而,现实中,女性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获得很大改观。女主人公安娜的写作障碍症、政治上的彷徨、生活和感情的极度困惑就是这一时期女性生存境况的生动写照。
在经济方面,《战争边缘》的出版给女主人公安娜带来经济独立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了烦恼。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变得物质化、商业化。电影商试图把揭示种族歧视的《战争边缘》打造成为一部具有异国情调的爱情故事,以满足当时英国社会和观众对殖民地生活猎奇的期待和刺激的视觉效果。安娜对此倍感失望。失望之余,安娜自己对《战争边缘》创作中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也深感不满。处在这样一个混乱分裂的社会状态中,写作似乎已经不能帮助她排解困惑,写作障碍在她身上也愈演愈烈。她已经无法写出唯一令自己感兴趣的小说——“那种充满理智和道德的热情,足以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的作品”[9]68。安娜想要寻找自己的信仰,期待着有一种信念能够挽救日常生活的混乱和分裂,因此她加入了英国的政治组织。然而,她逐渐意识到“这是个小心慎微、充满娘娘腔、等级分明的团体”[9]165,“她成为某种事物的化身,而这种事物是她不得不以适当的态度来对待的”[9]168。在感情方面,像安娜这样的“自由女性”摆脱了传统婚姻的束缚,似乎充满了自由的快感和幸福,实则不然。她们一样对爱情和婚姻充满渴望,但她们不仅受到单亲母亲照顾子女等家庭琐事的羁绊,又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或被旁人冷眼相待,当成是不需要婚姻的放荡女子,或被别人利用,成为男人感情生活的调味剂。安娜的生活在离婚之后变得一团糟。她对感情和爱很执着,却屡屡遭遇情感失败。她感觉不到幸福,写作障碍、精神分裂也随之加剧。这便是莱辛笔下“自由女性”的真实处境。莱辛从职业、政治生活以及感情等方面全方位地描述了女性的生存困境,揭示了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发展变化对女性生活所造成的各种影响。从表面上看,20世纪的女性在选举权、教育权以及就业等方面已经取得平等,多元社会文化的发展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但这种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掩盖了实际的社会问题:商品经济催生的以经济利益为一切事物价值的评判标准;政治组织的专制性和狭隘性;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女性实际生活角色的困境等等。如果说波伏娃是把女性的存在放置人的存在的基础上来考量,那么莱辛却是把女性放置于具体的社会中,从人类生存这一整体视角,揭示女性具体的生存问题,强调社会环境对女性生存,甚至是整个人类生存所带来的影响。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金色笔记》探讨的也是人的问题,这同样体现了莱辛本人的人文主义思想。[10]212-213但不同的是,波伏娃从本体论角度出发,将人的存在抽象化为意识存在、精神存在,并认为人的本质就是自由——与他人“共在”的自由。莱辛关注的则是人的社会性存在。在她笔下,任何个人的生存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影响,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自由。因此,莱辛通过社会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分析探讨造成女性当前处境的关键,而波伏娃则转向人的本体存在和意识存在来剖析父权制文化成功将女性囿于“他者”处境的根本。
二 女性的出路
作为20世纪杰出的女性作家,波伏娃与莱辛关注女性生存、洞悉女性处境之根源,但这显然不是她们创作的根本目的,其真正意图是为女性的困境探索出路。波伏娃提出,女性要改变“他者”处境,取得经济独立是首要条件。在《第二性》中,她指出虽然法律承认女公民和男性一样享有选举权等等,但这些公民自由和权利如果没有伴随以经济独立,就仍然是抽象的、不实际的。波伏娃认为,女人只有通过工作才能保证她的具体自由。只有女人在经济上不再成为寄生者,才能瓦解依附之上的体系;只有作为生产者和主动的人,她才能重新获得超越性,在自己的计划中具体地确认为主体。[11]543同时,她还指出,选举权和职业的简单并列,也不意味着完全的解放。这是因为,在外工作并没能免除女性在家里的繁重劳动。绝大多数工作的女人不能摆脱传统的女性世界,她们从社会和丈夫那里没能得到必要的帮助。也就是说,经济上摆脱了男人的女人,在道德、社会、心理状况中并没有达到与男人一模一样的处境,这样的平等依然只是抽象的。[11]545、592在这种情况下,波伏娃认为,亟需变更社会制度,以保证女人得到和男人平等薪酬的同时,家务劳动也得到平等分工。只有通过鼓励更多男人承担家庭责任以及鼓励雇员从事更具弹性的工作,女人才能从双重的工作负担中解脱出来。除此之外,安全而合法的堕胎途径、可以承受的避孕措施、人工受精的有效性、父母以及社会福利机构的支持等等也都是帮助妇女实现自由的重要措施。在波伏娃眼中,“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革命,没有革命就没有妇女解放”[1]33。对妇女而言,将命运操在自己手中是绝对必须的。
莱辛笔下的 “自由女性”安娜的处境恰恰也印证了女性的经济独立并不能带来完全的解放和幸福。写作的障碍、信仰的迷失以及情感的缺失带来的精神崩溃使她转而求助于精神分析,并试图寻找理想的男子以弥补内心的空缺。安娜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抗争——与社会文化以及与自我意识的双重抗争,但这并不能免除她内心深处对情感的需要和对婚姻的渴求。因此,她虽然经济独立,但精神的分裂和情感的匮乏仍然使她丝毫体验不到幸福。可见,莱辛对社会文化机制禁锢人的生存以及对女性心灵的真正需求有着清晰的认识。那么,在这样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女性通过妇女运动是否能摆脱社会对人的禁锢?女性主义运动一定能使女性获得解放和幸福吗?莱辛的回答是:“妇女解放运动不会取得多大成就,原因并不在于这个运动的目的有什么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耳闻目睹的,社会上的政治大动荡已经把世界组合成一个新格局;等到我们取得胜利时——假如能胜利的话——妇女解放运动的目的也许就会显得微乎其微,离奇古怪。”[9]xiii事实上,莱辛在小说中呈现出的复杂的时代问题、社会现实和社会压力,是当代男性和女性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在莱辛看来,女性的对立面并非男性,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因此,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单纯提倡妇女解放并不能解决女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男权社会的斗争也不会使“自由女性”得到真正的自由。女性要解决自身的问题就要处理好自身与社会的关系。而小说中提到的“家庭主妇病”[9]245看似是对传统女性妻子和母亲角色的控诉,实际上是夸大男女不平等的一种“受害者”哲学。[12]173-175安娜清醒地意识到,除了(女性)自身的独立自由之外,她只有在双重身份——迈克尔的情人以及简纳特的母亲——之间取得平衡,她才有幸福感。最终,安娜在自己分裂的精神状态中不断审视自我,寻找和现实的最佳平衡点,并重新融入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而莱辛通过安娜政治生涯的探寻、精神崩溃的疗伤、重新寻找爱情、重塑人生观的艰难过程以及追求新生活的结局安排,也揭示了现代人不仅要努力经营好事业、社会关系等一切外在的事务,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建构和谐爱情、婚姻和稳定健康的内心世界,将一切混乱、分裂的状态归整统一,从而实现人生完整的必要性。
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作为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波伏娃不完全赞同激进女性主义者提倡的与男性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她认为,男女两性的在世之存在是一种“原始的共在”[3]13,但这种共在必须建立在男女两性互相认可对方主体性的基础上。她指出,“为了取得最高一级的胜利,男女超越他们的自然差异,毫不含糊地确认他们的友爱关系,是必不可少的”[11]599。未来是一种抽象,但在两性之间会产生一种建立在友谊、竞争、合作、友情的基础之上的肉体和感情关系。[11]597可以看出,波伏娃对两性关系的观点是乐观温和的。但她坚持:“女人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与男人平起平坐,必须要有进入男人世界的途径,就像男人要有进入女人世界的途径一样,她要有进入他者的途径。”[11]548在两性关系上,解放女人,就是拒绝将她封闭在她和男人所维持的关系中,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些关系,而是女性和男性都既自为地存在,也同时为对方而存在。双方互相承认是主体,并且当一般人类的奴役状况及其所带来的整个虚伪体制被消灭时,人类的两性划分才显示出其本真的意义。[11]598
不过,波伏娃对确立女性主体性的强调以及对如何建立两性和谐关系提出的设想,不管是立足于男女“共在”,或是男女主体互相认可的理念,都是建立在自我和他者二元对立的基本范畴上。这种对立的态度恰恰是新时期女性主义对现代女性主义批判的焦点。新时期女性主义认为,对于男女不平等问题不宜以对立态度提出,而应以寻求两性和谐的态度提出。这一点莱辛其实早就在《金色笔记》中进行了阐述。莱辛借“自由女性”揭示了绝对自由的非现实性。她认为,男女构成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任何一方的生存不可避免要受到另一方的影响,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正如小说中人物朱丽娅对爱拉所说:“如果他们[男人]不自由,我们自由有什么用呢?”[9]438莱辛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女性和男性组成的,女性需要男性正如男性需要女性。两性之间的关系不应是相互敌视和对立,而应当相互依存、相互理解。任何试图通过与男性斗争或决裂来取得自由的途径都是不现实的,并且是荒谬的。在小说的最后,索尔和安娜互为对方的写作写下了第一个句子,这是安娜和索尔治愈“写作障碍”的良方,也是他们各自走向正常新生活的起点。
三 女性主义之死?
波伏娃和莱辛以各自的话语方式关注女性的生存,思考女性的现实困境,洞察女性的精神世界与生命体验,并探索女性主体的未来走向,在各自的文本中体现了不同的女性主义思想维度。在分析女性的生存时,她们都不仅仅从女性角度认识女性本身,更从人的生存来诠释女性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的生存本质。不同的是,波伏娃关注妇女的意识层面存在、本体论存在,而莱辛对女性的关注更多与时代、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之上,波伏娃提出要解放女性,就必须在确立女性主体性的基础上,争取女性经济独立,通过妇女解放运动来变革不利于女性生存的社会制度,从而创立一个适合女性自由,实现其超越性的社会环境。而莱辛却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看到了人类生存绝对自由的非现实性,并探索出女性生存的新途径:审视自我,完善自我,在经营好事业等一切外在事务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的男女关系。她们思想的不同视角导致了此后她们对女性主义运动的不同态度。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以1848年在纽约州赛尼卡福尔斯召开的妇女大会为起点,旨在为妇女争取教育平等、财产继承权、选举权等等具体的权利,并通过平权抹除男女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波伏娃敏锐地觉察到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对妇女的文化身份和处境的忽视,在《第二性》一书里提出振聋发聩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1]9波伏娃将矛头指向父权文化,颠覆了生理决定论的谬论,这不仅对旨在瓦解滋生父权文化社会土壤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有着重大的启发,而且对当前关注女性问题的研究者而言仍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波伏娃相信社会主义的发展会使妇女问题自动获得解决。然而,《第二性》出版之后20年,波伏娃发现,法国妇女的处境并没有多大改变。即使在苏联,男女之间的平等亦未达到。由此,波伏娃意识到妇女问题不可能自动得到解决,并且阶级斗争并不等同于女性解放。她认为,女性主义应该是结合阶级斗争,但又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专门为女性问题而奋斗的主义;妇女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必须采取主动。[1]281971年11月,波伏娃加入MLFMLF的全称是Mouvement De Liberation Des Femmes en France(法国妇女解放运动团体)。激进分子的游行。自此,她以实际行动参加并全力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的各项活动——担任“女权联盟”的主席、大力赞助“受戕害妇女之家”的设立等等。在波伏娃看来,在这一阶段,以这样激烈的策略来获取妇女解放仍是必要的。[1]34
然而,早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之初,莱辛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洞察社会环境与人的生存之间的关系,清醒而冷静地认识到女性主义运动的偏狭,并认为单纯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可能带来多大改变。她是在全面洞悉社会风貌的基础上来理解社会的发展前进。正如肖瓦尔特所说,莱辛对社会气候有着敏锐的感知,但她不是用小说给社会潮流作结论,而是以此预言社会的发展。[2]307莱辛认为,完美的人格只有在安定、统一、和谐的社会大环境下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而社会政治运动只会导致新的世界分化。难怪莱辛1998年在伦敦接受采访时说:“妇女运动,在我看来,一直都是令人失望的事情。它有过激情……60年有过激情,但在我看来,大部分都浪费在空谈上面……它对白人和中产阶级年轻妇女有益,对别的人没有做多少事情……女性主义反映了一种对磨难、失败和痛苦的深深迷恋。”[13]75可以说,在莱辛这里,所有的“主义”(isms),包括女性主义,都毫无意义,它们终将为整个人类生存的全面考量让路。
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陷入相对沉寂的局面。“女性主义终结论”甚嚣尘上,甚至连“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先驱弗里丹也发出“女性主义之死”的慨叹。[14]294但实际上,如沃尔比所说,女性主义并未消亡,而是以新的形式来代替传统的“社会运动”形式。[15]2女性主义追求女性解放和幸福的主题,如推翻建立在自然秩序之上的男性主导的观念、建立没有等级的家庭关系等,对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始终有积极的意义。[16]77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去中心说、反对宏大叙事以及倡导局部理论及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其他思潮的影响之下,不再关注“父权制”,或纯粹地追求社会的变革,而是呈现学科化的转型,并转向了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紧密的微观层面,开启了第三次浪潮的序幕。总的来看,女性主义呈现出从斗争到合作、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际的思想演变。
21世纪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给人类带来种种新问题,如生态危机、人口危机、信仰危机等等。但归根结底,这些危机所关涉的都是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实现。社会的发展前进最终也必然指向人的生存、人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和谐发展。新时期的女性主义,同样呈现出性别界限模糊化、以寻求人性的全面丰富和完善,以及人类价值的全面实现为终极目标的发展态势。[17]231从波伏娃的《第二性》到莱辛的《金色笔记》,虽然其出版时间间隔短短13年,但两者所反映出的女性主义思想的不同,即从激进地寻求女性解放到客观冷静地看到两性作为人类共同体共同发展的必然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成为近四五十年来女性主义思想发展的缩影。在50到6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兴起之时,《第二性》的问世无疑为女性照亮了一条路,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但从社会和人类的发展来考量,莱辛为女性甚至是整个人类所指明的出路显然更高一筹,即立足现实,做自己能做的事,使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而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应该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契合时代语境的新的女性主义的要义所在。
结 语
波伏娃和莱辛本着对女性以及人类解放的高度责任感,在洞察女性的生存及其本质之后,不约而同地拿起笔杆为女性的解放书写出路。在20世纪中期浩浩荡荡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如果说波伏娃拿起笔杆扮演的是身先士卒的女权战士,那么莱辛则更像是一个冷静理智的观察者和具体行为者,正如西西弗斯的推石者。莱辛在全面把握社会风貌及其发展本质之后,更清醒地认识到包括妇女解放运动在内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偏狭和短视,并认为女性的幸福只有在两性作为共同体和谐共存时才能实现。虽然人类前进的脚步是沉重、艰难的,甚至是重复的,但只要努力,就有希望,而这正是莱辛给予新时期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爱丽丝•史瓦兹. 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娜•波伏瓦访问录[M].顾燕翎,等,译. 台北:妇女新知杂志社,1989.
[2]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3][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I[M]. 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全增嘏. 西方哲学史•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M]. Joan Stambaugh. tran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6]黄见德,毛 羽,谭仲鹢.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M]. 北京: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7]夏基松,段小光. 存在主义哲学评述[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8][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M]. 贺 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Doris Lessing. The Golden Notebook[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Publishers, 2008.
[10]R.P.Mahto. The Golden Notebook: A Study in Humanism [A]. in Tapan K.Ghosh(ed.). Doris Lessings The Golden Notebook: A Critical Study[C]. New Delhi: Prestige Books, 2006.
[1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II[M]. 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2]李银河. 女性主义[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3]Cathleen Rountree. A Thing of Temperament: An Interview with Doris Lessing[J]. London, May 16,1998. Jung Journal: Culture & Psyche, 2:1(2008).
[14][美]贝蒂•弗里丹. 非常女人[M]. 邵文实,尹铁超,译.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
[15]Sylvia Walby. The Future of Feminism[M]. London: Polity Press, 2011.
[16]R. 科沃德.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女性主义吗?[J]. 国外社会科学,2000,(3).
[17]邓 利.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