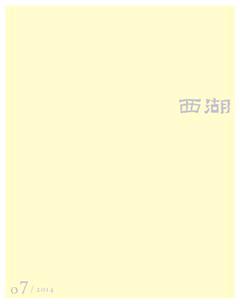“小说家都喜欢给自己设置障碍和难度”
毕飞宇+姜广平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我们从《推拿》说起吧。随着舞台上的《推拿》出现,这本书再一次热了起来。就我所知,人们感动的是:用卑微的心也能照亮世界。甚至,正是这些卑微的心照亮着世界。我们很想知道你在创作前与创作中的一些情况。
毕飞宇(以下简称毕):没有什么特殊的,《推拿》的写作和别的写作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当然,在写作过程中,我对自己也提了一些要求,那就是处理好人物的关系。你知道的,《推拿》的体量很小,人物却非常多,如何在这样小的体量里头包裹那么多的人物和人物关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考验。为什么要选择小体量呢?原因很简单,盲人的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天高地迥”的世界。如何保证小说内部的逼仄和拥挤呢,只能是小体量。小说家都贱,都喜欢给自己设置障碍和难度。解决障碍和难度,你只能从小处入手。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在大处想,往小处做。
姜: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你写《推拿》的?
毕:这些年我反反复复地交待这个问题,交待来交待去,能说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一个人的宽度。在大部分时候,我们痴迷于生命的长度,其实,宽度一样有意思。一个人如何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生命呢?写小说无疑是一个好办法。小说有小说的魔力,它会引领我们进入那些看起来无法进入的世界。本质上说,促成我写《推拿》的原因和我写别的作品没有区别,那就是我对别人有好奇心,这好奇远远超出我对自己。
姜:《推拿》里有很多教育内涵可以挖掘,诸如生命教育、特殊教育、励志教育及价值观的建立等。看来,大学读的是师范学院,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工作,这些经历,让你无法忘情于教育了。
毕:是的,我无法忘情于教育。这些年来,我真正关心的其实是教育和计划生育之间的关系问题。你也知道,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家庭格局变化了,家庭伦理也变化了,这些东西必然会体现在教育上。我说过一句话,因为独生子女,我们做父母的都是神经质的。为什么呢?我们输不起。一个人输不起是很不好看的,一个家庭输不起也是很不好看的,一个民族输不起就更不好看了。什么时候我们输得起了,我们的文化就会变得大气、从容,我们的教育也就跟着大气、从容。
姜:我们不妨列举一下你的关涉到教育的作品:《哥俩好》、《好的故事》、《地球上的王家庄》、《哺乳期的女人》、《彩虹》、《玉秧》、《家事》、《写字》、《白夜》、《相爱的日子》等。当然了,这些作品,是写了教育,可又觉得光是教育也装不下这些作品。像《好的故事》、《玉秧》,只不过是因为事情发生在学校,可能也并不能被当作真正的教育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儿童视野,则又具有浓郁的哲学的色彩。
毕:我一直关注教育,这是真的。在我看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比教育更大的事情了。和教育比较起来,GDP实在算不了什么。无论GDP有什么闪失,过几年都能调整过来,实在不行,十几年二十几年也就够了;可是,教育一旦出了问题,一代人就废了,一代人废了,文化就会变异,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事实,它的影响力可以延续一百年,甚至更久。就说我们这一代人吧,我们都是“文革”中长起来的,接受的是文革教育,文革的思维模式依然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因为潜移默化,又会影响我们的孩子,这是很可怕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是人口大国,教育的正能量和负能量都特别巨大,人类历史上都绝无仅有。中国的教育实在是半点也马虎不得。事实就是这样,一条小舢板撞上冰山了,晃悠一下而已,泰坦尼克要是撞上去了,事情就大了。
姜:那篇非常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青衣》,剧团里筱艳秋与春来是师徒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教育关系了。当然,从文学关系上来看,她们的关系就更复杂了。
毕:剧团里的师徒关系就是任课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甚至是班主任和学生的关系,怎么不是教育呢。当然,这样的师徒关系有一点是特殊的,他们之间有竞争。我想这是有趣的,当师生之间、领导与部下之间有了竞争,会是怎样的一种盛况呢?
我很在意竞争之间的公权力,公权力会参与竞争么?我的想法是:公权力不参与个人竞争,这是一个好社会;公权力一旦参与了个人竞争,那就必然是一个不良的社会。
姜:对了,你早期有一篇《马家父子》,这里的教育也是有意味的,是父子两代的文化冲突,做父亲的觉得没有把小马“教”上他老马的路子。我觉得这小说有那么点意味。而且,这里面,文化意味也浓。说到文化,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快把这东西给忘了。不过,在苏州,现在苏州话已经作为一种对孩子们的考核内容了。
毕:你谈到了区域文化与方言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一个小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的,《马家父子》关注过这个问题,可是,我要说,写《马家父子》的时候我太年轻了,如果现在来写,也许不一样的。写小说就是这样,随着年纪的增长,你永远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其实也未必。
姜:我想到了你的长篇处女作《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那个耿东亮,既是音乐系的大学生,又是一个女孩子的钢琴教师。这是一篇真正的教育作品了。你拥有这么多教育作品,你应该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教育作家”了。过去有人说过你是“女作家”,写女性特别出彩。现在,我则觉得,你也是“教育作家”,你写教育特别深刻,其笔触伸到了我们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毕:“教育作家”是一个神圣的称号,我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可我真的不敢当。我关注教育说到底和我的家庭有关,我们这个家庭从事教育工作已经有祖孙三代了。我年轻时读的是师范学院,现在的身份也是大学教师,我关心教育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一个小说家和教育之间有点瓜葛,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
姜:最近读了你的《大雨如注》,有了些思考,便写了一篇文章《一场怎样的豪雨才能滋润我们和我们的教育》,我觉得,你这篇小说对教育的思考确实太深刻了,深刻到让我们这些做教育的人都觉得惶愧:很多问题,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啊!
毕:谢谢你的鼓励。这篇小说其实就写了一件事,我对汉语未来的担忧。你也知道的,我不可能是一个狭隘的种族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放弃对汉语的感情。这感情一点也不空洞,每一天都陪伴着我。汉语毕竟是我的母语,它的处境又是那样糟糕,我滋生出担忧的情绪是正常的。当然,《大雨如注》的难点就在于,不能因为我对汉语的处境很担忧,我对外语、尤其是对英语就抱有必然的敌对,事实上,我没有这样的敌对。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纠结,话又说回来了,我写所有的小说都纠结,没有纠结就没有我的小说。
姜:我自认为是很好的文学读者,可还是没有读出你的这层隐忧。看来,大作家的心灵空间,的确是浩浩莽莽无边无垠的,非等闲之辈能够窥得。而真正的作家那种情怀与意识,也非等闲之辈能够体认的。你对自己作品的说明,恰恰说明了一个真理,一部阅读史,其实就是一部误读史。而且,也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品才会存在误读。一条小溪,清澈见底,怎么也无法与大河大江大海相提并论。
毕:你过奖了,可你别忘了,我首先是个读者,然后才是作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误读了,我只觉得你高估了作者的自我阐述。相对于一部小说而言,“作者自述”真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么?不一定的。在文学这么一个范畴内,作者的自说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一旦进入文化这个空间,读者和作者必然是等值的。什么是阅读?什么是误读?其实也说不好。我的作品未必够资格,但是我想说,好作品必然经得起解读,这个解读包括阅读,自然也包括误读。
姜:好,说了这么多你与教育的瓜葛。在你眼中,教育究竟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毕:教育的本质是国家与民族的需要,国家与民族需要什么,教育就是什么。这么一说事情就简单了,国家是什么样子,教育就是什么样子。反过来说也一样,教育是什么样子,国家就是什么样子。
姜:依你看,现在的中国教育,是不是真的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有问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当然,你的《大雨如注》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
毕:我的《大雨如注》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企图靠一部小说来讨论中国教育的全部,那真是脑子坏了。一部小说最多可以面对一个局部,这还是在你写充分的情况下。
姜: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都为人父了。作为父亲,你更愿意把孩子交到什么样的老师手上?
毕: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伪问题,我们别无选择,一切都是孩子在撞大运。
姜:是啊,这让我想起你早期的一篇小说《九层电梯》,里面的毕小蓝被作业追击得身不由己。教育与老师的问题,对中国百姓来说,确实构成了某种无法言说的被动与别无选择。
毕:我有许多朋友是中小学的老师,谈起孩子的教育,他们也经常对我诉苦,诉说他们的被动,诉说他们的别无选择,这是一件十分喜感的事情。也许我用“喜感”这个词有点不够庄重,可是,你除了微笑,你还能做出什么表情呢?由此,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教育问题,不能局限在教师的身上,要往教师之外的地方去找。
姜:这就不得不说老师们的读书了。我对当下中小学老师的阅读现状不太看好。我身在教育行当里,我知道现在其实爱读书的老师可能太少了。他们当然也在读书,但一方面,他们读的是教辅类的居多,订阅的杂志也差不多是相关的领域的。能把一本《读者》置于案头,已经不错了。你觉得一个称职的老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读书人?
毕: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里,我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我想说,他们这个乡村教师真是合格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见证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生活里的每一天都围绕着他们的课堂,即使到了吃饭的时候,谈的还是备课、上课和批改作业的事。我的父母每一天都是读者,虽然书本不多。我觉得称职的老师就是“每一天的读者”。
姜:你曾说起过法国人买书以吨来计量,以读书获得安详与幸福。这样的境界,是多么令人神往!
毕:那也是极个别的法国人,普通的法国人也不是这样。不过再怎么样,欧洲的读书人口比我们要大得多,这个是没有疑义的。在我们身边有个普遍的说法,中国的孩子不读书,尤其不读文艺作品,是这样的,可这个不能怨孩子,他们哪里有时间哪。压力实在太大了。如果我的孩子有两个小时的空闲,我也不希望他去读书,我希望他好好玩玩,真正地放松一下。
姜:我多少知道你的读书经历。在大学里,你很啃了些哲学著作。后来呢?后来你都读了哪些书?
毕:我没有一个好的读书履历,这真的很惭愧。大学毕业之后,我读书再也没有系统了,都是乱看,说来说去,还是文史哲方面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几乎没有读过中国的当代文学,许多作品还是写作之后才开始读的。这也难怪,认识的人多了,朋友的书总是要看一看。但是,我直到现在都没有在网络上读书的习惯,还是喜欢端坐在桌椅旁边,捧着一本书来读。
姜:这些书给了你哪些营养?哪些书对你的影响是终生的?
毕:对我一生都有影响的还是年轻时读的书,比方说,西方文学的经典。这些阅读对我很重要,它帮助我建立了文学的美学趣味,我就此知道了文学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文学,尤其是,什么是好的小说与好的诗歌。当然,这里头也有变化,我在年轻时特别喜爱法语作家和西班牙语作家,人到中年之后,英语作家的分量上去了。这样的阅读也落实在我的写作风格的改变上,仔细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也许我还要说一说《红楼梦》,我读大学时没有读过红楼梦,读不进去。写了一群小丫头片子,怎么读得进去呢?我真正领略汉语小说的魅力已经比较晚了,我的导师不是鲁郭茅和巴老曹,而是《红楼梦》。的确,作为一个汉语作家,不好好地认识《红楼梦》是不会有大长进的。
姜:看来,一个真正的中国教师,也应该读一读《红楼梦》。对了,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毕:我最近在集中阅读李辉,中国有许多李辉,我说的是《人民日报》的这个李辉。最近我一直在读他的《封面中国》。
姜:李辉的文字,我主要是在《收获》上读的。确实是一位现实感与历史感都非常强的作家。过去,你曾向我推荐过何清涟、秦晖、朱学勤、王彬彬,你说他们是当今的财富。你在阅读李辉时,又如何定位李辉?
毕:我哪里有能力去定位李辉,那不是开玩笑么。李辉是记者,有他新闻人的特别的敏感。我可以说的是李辉的语言,我喜欢他语言的表情,是的,表情,这种表情很容易与读者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我想说,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他语言的表情比小说家还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阅读就是对话,在对话的时候,读者不是只看你说什么,他还会盯着你的表情。我很喜欢李辉的表情。
姜:在南京特殊师范学校教书的那些年,应该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人与事吧?可不可以与我们聊聊,这种教书的经历,对你的人生有哪些影响?
毕: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真正学会在语言当中使用逻辑,还是在做了教师之后,这里头有一个自觉性的问题。站在讲台上对一个人的帮助很大,尤其是一个小说家,他会更加敏锐,他的认知更加立体,他知道怎样建立语言的权威性。当然,做教师对人的内心影响也很大,他习惯于与人为善,他盼着别人更好,他也更耐心。我的很多坏毛病就是在做了教师之后慢慢地克服的。
姜:现在,你的身份是南京大学教授,我还了解到此前你便给研究生授课。你主要讲什么内容?
毕:我给南大研究生上课的时候从来不讲经典,原因很简单,在南京大学,讲经典的老师很多,都比我讲得好。我只讲学生自己的习作。我提前把这些习作拿过来分析,分出不同的逻辑模块,然后,和他们一块一块地讨论,这样的讨论可以延续许多课时。我的工作就是挑拨离间,让他们争论,他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写作方法来证明自己。我不做裁判,我只有建议。在给建议的时候,我会涉及经典、文学的基本理论,还有我的经验。同学们的感觉是怎样的我没问,但是,我自己很愉快。
南大学生的阅读我不用愁,他们读什么会有专门的老师去指导,他们的素质在那里。我想强调的是,南京大学就是南京大学,很有气度,善良。他们知道,在任何时候都会有特别的学生——有学生特别渴望写作怎么办呢?就为了这极少数的“特别”,南京大学把我调过去了。这是很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我呢,不贪婪,遇不上也不遗憾,一旦遇上了,我会做个好教师。
姜:你对当代大学生的阅读有什么建议?
毕:读经典。读经典永远正确。我的建议是,不要乱,先分语区,再分国家,再分时段,再分作家,这是比较靠谱的阅读经济学。我是一个失败的阅读者,失败之后我终于懂得怎样种地了:一块地,要种玉米就都种玉米,要种小麦就都种小麦。你要是在一块地里同时种上玉米、高粱、大豆、小麦和芝麻,你得到的将是一堆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