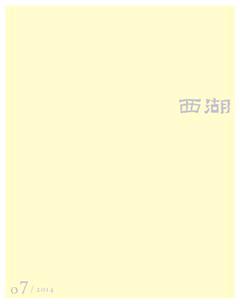自传与公传:一九七五 (二)
董学仁
想做一个不完美的人
有个词语,叫“三小一道”,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级别很低的几种工厂,一个比一个更低更小,却是解决城市就业的主要途径。长甸机械厂是街道办事处的工厂,属于“三小一道”之一。这个词语现在死了,没人知道它的具体内容。
还有一个词语不那么文雅,叫“王八铁”,虽然没死,也差不多消失了;就像有些人与你失去了联系,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减弱了与你相关的意义。
长甸机械厂有个铸造车间。一些工人把木制模型埋在黑沙里再取出来,留下一个硬实的空间;一些工人用小高炉融化铁水,把铁水小心浇灌到模型空间里;一些工人再把冷却凝固的铁铸件从黑沙中挖出来,整修一番,变成大型机器需要的零件。车间里黑色的粉尘弥漫,工人们脸上身上黑乎乎的,像他们使用的黑沙。
融化铁水必需的生铁原料,就是我要说的“王八铁”。它的名称来自它的形状:中间隆起,四周低下去,像个海龟的壳子——而在我们粗爽的北方,王八是海龟的俗称,王八铁是这种原料的俗称。
三块王八铁连在一起,投入小高炉前要用锤砸开。
砸王八铁的人,被大家叫做“傻大个子”。其实他不算傻,见人嘿嘿地笑,嗨嗨地打招呼,说话时会用正确的名词和动词,看到年轻女工也会嘴角抬起,眼光跟随。
让我好奇的是傻大个子用的那把锤。锤头很重,比我想象的还要重一点。它的锤杆细长,超过两米,颤巍巍的,弹性奇大。有一个多星期,在他和铸造工人都下班后,我去练习砸王八铁。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我要把大锤从右侧甩到身后,借着甩动的力量抡到头顶,在空中划一道弧线,再准确地落向王八铁连接处。
这活儿需要一定的力量,也需要一定的技巧,还需要刘长海的指导,才不会让大锤砸在我的腿上。刘长海是铸造车间工人,头脑聪明,为人忠厚,身材不高,和我同岁。在长甸机械厂上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悄悄练了一个多星期后,我成了傻大个子之外唯一会砸王八铁的人。如果傻大个子身体不舒服,歇一两天病假,我会替他砸一两天王八铁。但他从不烦恼,无欲无求,身体结实得很,无论谁有病他都不会。这样一来,我练成了砸王八铁的绝活,也没有任何用处。
除了刘长海知道我会砸王八铁,再没有别人知道。我担心的是,这事儿如果传了出去,一旦工厂安排我干这活儿,只会砸王八铁的傻大个子,就找不到别的工作了。
我在厂里办公室,干的是写文字材料和美工布置的活儿;对于喜欢读书、学过水粉画的我,那是个挺适合的工作。没人看见的时候,我悄悄甩一会儿大锤,出一身透彻的汗,只当是锻炼身体了,也不会抢谁的饭碗。
有些时候,你有能力也有精力,能同时做几件事情,但你不能把这些事情都包下来,显得这世界上只有你能干。如果你争强好胜,会有数不清的麻烦,落到你头顶。
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就有了这种想法。
一天上午,副厂长找到我,说来了两位外地客人,中午留在厂里吃饭。厂里没有食堂,当然要出去买些饭菜,碰巧负责这事的业务员没在厂内,找我临时顶替她,买些饭菜回来。
给你五块钱,二斤粮票,四个人的饭菜。副厂长说。
那些钱不多,但也够了。如果不来客人,三五毛钱也够一个人吃一顿饭。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已经在附近两家小饭店和一家小商店里转了两圈,问遍了饭菜与副食品的价格,头脑中产生了几个方案,然后淘汰了两三个,留下最好的那个。
这事对我来说不难。我家里没有姐妹,兄弟几个先后有过买粮买菜的经历,并且是一连几年,尽量用最少的钱,让一家人吃得好些。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足够了,只有比我家收入还少的家庭里,才有人能与我相比。
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天副厂长相当满意。拿同样多的钱和粮票,给同样多的人买饭菜,以前有过好多次了,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过了半个月,也许还没到半个月,又来客人了。副厂长悄悄找到我,要我再去买一些饭菜。我答应了,去街上转了一会儿,转够了就随便买了一些,送到了副厂长办公室。
那一天的饭菜糟透了,没人满意。
这件事的真实原因,我不会说出去,谁也不会知道。我不想做一个能力超过别人、道德完美无缺的人,不想让一件本来不该我做的事情,长久地落到我头上。这是我的秘密,永远不说出去。而心地善良的副厂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会有意买回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
像我预想的那样,副厂长以后再不找我买饭买菜。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仍然由业务员来做。
那名业务员,能力强不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对人忠诚,办事认真,工厂里需要这样的人。她说话总是细声细语,从不招惹别人。她比我大了两三岁的样子,像个挺好的姐姐。就拿买饭买菜这事来说,她永远不会比我做得更好,但在我有意做坏了一次之后,她也永远不会比我更差。
从那时候起,或者在那时候之前,我已经懂得了平衡的重要性。先做好一件事情,再做坏一件事情,一好一坏,两件事扯平。
在我读过的书里,没有谁写过这样的经验。其实古代有人写过,有用与无用之间的一棵树,有才华与无才华之间的一个人,都可以活得更加长久。但在我有类似想法时,还没有读到庄子的书。
在我成长的年代,许多人做事情小心谨慎,留有余地。开始时,他们有意遮掩自己,然后一步步表现出长处来,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进步。
只有我不那么做。我把第一件事做得超乎寻常的好,第二件事做得比一般人还差。二者接连出现,别人无法形成固定的评价、要求与期待。这样一来,我遇到的麻烦就少了很多。
其实,我不想做一个能力超过别人、道德完美无缺的人,只是出于性格软弱,只是一种无奈的逃避。在我成长的年代,身边环境里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圈套、风险、诱惑、威胁和邪恶,很容易毁灭一个人、一群人或者整个时代的人。
对张志新的忽略和误解
那场政治运动到来时,我就知道,我和编辑《新叶》文学杂志的几个同学,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文系一位教授说过,你们啊,阅历太浅,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学就离开了政治的阴影。他摇摇头继续说,作家王实味被砍掉脑袋,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这份校园刊物诗歌专号上,发表了徐敬亚四万多字的论文《崛起的诗群》,然后这篇论文有个压缩的版本,发表在公开出版的《当代文艺思潮》,不久由国家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发起了政治运动,叫做“清除精神污染”。
省里也有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叫省委宣传部,它派来一名姓谢的官员,对《新叶》杂志的情况展开调查。过了几天,有一位写作课副教授悄悄告诉我们,这名姓谢的官员,人称“大谢”,他身材高大,办事严谨,还有,他的前任就是省委宣传部的张志新。
张志新,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我们当然知道是谁。
就在我们读大学前后,全国报纸正宣传她的事迹,连续宣传了几个月,以至于普通的工人与农民都知道张志新是谁:她因为坚持真理,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枪毙了,几年后说那是一起冤案,又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就这样,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这名被人称为大谢的官员由于他的工作,与张志新的名字连在一起,而我们由于一本刊物的被调查,也与张志新连在一起。
一个人活着,我们还有全面了解这个人的可能;人死了,这种可能就没了。对于张志新,也是一样。一个在政治体制中工作的官员,因为思想罪被这个政治体制杀死,几年之后又被政治体制当成革命烈士宣传,你不能指望这种宣传让你了解足够的事实,而不是忽略和误解。
我和许多人一样,以为张志新是个被判死刑的女青年,忽略了她死时已经四十五岁的实际年龄。
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来自于张志新年轻貌美、气质优雅的一张照片,也来自于我们惯常的经验。在我们的常识里,怀疑和反对革命秩序而被杀死的,大都是些年轻人,因为他们感觉敏锐且阅历稍浅,对社会的现状不满,抱着理想主义不放。
她出生于1930年的天津,在中华民国生活了十九年,还遇到了那个朝代第一次总统大选,结果是胡适退出竞选,这一职位由蒋介石担任。天津地界举行庆祝活动,邀张志新和她的两个妹妹参加,她们上台演奏了《魔鬼舞曲》、《悲歌》、《终了曲》等一组器乐乐曲。据说这一组曲是她们父亲有意安排的,表示对选举结果不满。张志新在旧朝代和新朝代各自度过了十九年自由的日子,此后入狱六年,再被枪决。年迈的父亲知道这一消息后,在梦中见她和妹妹在舞台上演出《魔鬼舞曲》、《悲歌》、《终了曲》后与世长辞。
我们知道的林昭、沈元、遇罗克等人,死去时都很年轻。我们还以为社会的美好未来,是一棵饥渴的植物,需要年轻人的血来浇灌。在这一点上,我们忽略了张志新的另一个意义:作为一名中年人,在童年到青年前期接受了前一时代的完整熏陶,这会怎样影响到对新时代的判断,如此判断有没有参照系方面的优越感?
我还忽略过张志新被枪毙的时间。
时间是1975年。
按照我先前在《我想结束一场革命》中的描述,到了1972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结束,国家回到先前的发展轨道,甚至迈进了一步,中国最高领袖会见了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与西方国家纷纷建立外交关系。
1975年是个平静的年头,在经济建设方面继续向前。中国政府再次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大设想。如果一定要说那场政治大革命是在1976年结束,一定要说它是十年浩劫,我们又怎样解释,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年浩劫中确定的2000年之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怎么会成了国家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党的工作重点和战略决策?
我们知道的林昭、沈元、遇罗克等一批死难者,都死在1966年以后、1972年以前。那个特殊的时代像是割草机,专门收割中国思想者的生命。而1972年至1976年这几年,正是思想犯罪者很少被杀、社会比较正常的时间段。不幸的是,张志新恰好死于这段时间,并且在几年里经过了判处徒刑、改判死刑、再改判徒刑、最后再判死刑的完整过程,这让我们不能忽略,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疯狂的年代,才有思想罪处死的恐怖。
对张志新一案的误解的部分,可能会复杂一些。它不只是我们的认识局限,还是官方宣传的需要。比如,我们误以为张志新因反对革命领袖集团的阴谋人物而被判死刑,实际上,她仅仅对最高领袖本人作出了并不严厉的批评,就招来了杀身之祸。
张志新评价最高领袖,说他在“大跃进”以来,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她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说得更明确一些。“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她说,“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
她更加明确地反对个人崇拜。“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
差不多就是这些言论,并且没有在社会上散布出去。按理来说,这些还没有离开对当时人和事件的常识性评价,甚至算不上什么敏锐深刻的思想。但她仍然要被判死刑。
在我看来,也许是她的身份帮了倒忙。她与我们知道的林昭、沈元、遇罗克等人不同,她是属于革命体制内的低级官员,并且在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工作;如果有对革命事业的半点怀疑,就是极大的罪恶。还有就是,她在被关进监狱之后,面对高压不肯收回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偌大一个轰隆隆运行着的革命体制,留着她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只好把她消灭。
我们的民族很善良吗
在一位网友的回忆里,他说,十多岁时,同学去市中心的广场看公判大会,他等在郊外看枪毙犯人。有时候一起枪毙十多个人,那场面挺壮观的。有一次,被枪毙之前的反革命分子突然大声喊口号,喊的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那时候的群众大会上经常喊这两个口号,大家都要跟着喊,不喊就是不革命,是对伟大领袖不忠。被枪毙的人喊了,远远围观死刑的人群就跟着喊起来,喊得很响亮。那场面怪怪的,他说,那些被枪毙的反革命,喊的是革命口号。
即使隔了许多年之后,即使是写“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马尔克斯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十多年后逝世时,我还是觉得网友描述的事情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分。
在我看来,由于对革命大方向与小细节的解释不同,并且这种解释随时都在变化之中,一部分人被其革命同志当成了反革命分子。他们被枪毙之前,当然会像迷失的孩子呼喊母亲一样,呼喊他们投身的革命政党和革命领袖。
我记得的事情庞杂而浅显,就像我所处的网络时代。
我记得的最近的事情是,马尔克斯去世那天,我在网络上一个跟帖里说到了“荒谬现实主义”。亚洲生活中的现实,处处与荒谬合在一起,而亚洲的荒谬,是人类史上最大的荒谬。我这样写到,中国的文学写作者并不是纯粹的文学写作者,他们在写作时离开生活经验,拼命寻找那些不荒谬的现实。于是他们离现实和荒谬都很远,并且细弱无力。
有个例子,出现在离我最近的省会城市。某人还没等招供,就被严刑拷打折磨死了,让一场审判半途而废。法院里的家伙还不放过他,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五年。给死人判有期徒刑,一个不常见的事情,显示出亚洲人现实与荒谬的完美结合。
而我记得最远的事情是,中国古代,人们就喜欢到法场去看斩杀犯人。这里的看,无疑是混杂了听和感受的成分:看的是刽子手威风凛凛的行刑场面,听的是被杀之人临刑前的最后演说或呼喊口号,感受的是刀光闪处人头落地的瞬间快感。
在中国至少绵延千年的杀人文化与被杀文化里,这种看、听、感受合成一体,让人醉心。其中富有变化的是听的那部分,不同的死刑犯人有不同的最后演讲或呼喊口号,会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也留在可能有的死者传记里,让其人生变得完整。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亚洲,进入了从未有过的年月,那种比欧洲中世纪还要残酷的意识形态审判,夺去了更多的生命。中国的革命者企图改变古已有之的文化习惯,让被枪毙的人死前不发表演说也不喊口号,显然成了千百年里无人处理过的难题。
如果他们愿意采用没有人权、没有人道、没有人性、没有人格、没有人品的暴虐方式,那就不是难题了。
比如,女犯人张志新临刑之前,被监狱当局用一把刀子割断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由四个男人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旁边一个女管教员见状,惨叫一声昏倒在地,接着被拖了出去。剩下的人(如果我有一些情感倾向会称他们为魔鬼)毫无惧色,完成了这项恶行。
其他省份也有割断喉管的死刑犯。没有人去报道这种方式,只是在回忆一些比较知名的死难者时,这种方式被附带提及。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刽子手割断了她的喉管。
也有其他方式,让临刑的人说不出话来。
枪决官明华之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官方还是怕她呼喊口号,在她嘴里塞进压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
王佩英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为防止她喊口号,公判大会召开时用一根细绳勒住其咽喉,后面有人拽着。这样一来,她发不出声音,远处的民众又看不到。可是那天出了一点意外,在押往刑场的路上,王佩英已经被勒死了。
采用哪种方式并无统一规定。辽宁省革命委员会选择了更为残忍的割断喉管,作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加以推广。切开喉管,然后把不锈钢管插进气管里,再用线将连接钢管的金属片缝在刀口两边的肉上——既能维持刑犯的呼吸,又绝对喊不了口号。
张志新不是第一个被割断喉管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公开的数字是,几年里有三十多人被割断喉管。
这样做的另一个效果,是割断喉管的死刑犯吸氧不足,神态萎靡,更像是罪有应得的样子。
看管过张志新的一名女看守回忆说,1975年4月4日,张志新的公判大会上,她被人架上台来,低着头,也不说话,颓了似地全无往日里的孤傲。我当时奇怪:张志新临死时也会是这个样子?“过了不久,我才知道她上台前已在狱中被割断了喉管,是插管拔掉后上不来气,我于是一片心悸。”
读过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之后,我觉得法律也是一种契约。在那部戏剧里,法庭判商人胜诉,但他无法精确地割下一磅肉,无法保证不流血,于是只好放弃这个判决的执行。有了严密、神圣的契约精神,法律挺可爱的,有温柔和善良的一面。
按照莎士比亚的想法,张志新被判的是死刑,并不是死刑加上割断喉管。假如你不割断她的喉管,就无法保证她不在枪毙之前呼喊口号,你可以放弃这个死刑的执行。
亚洲有莎士比亚无法理解的更多事情。
比如,有个词语叫“陪绑”,说的是让一排人跪在刑场上,刽子手只向其中一些人开枪,把没挨子弹的人再拉回监狱。这些人本来就没判死刑,只是拉去恐吓他们,但是,有陪绑的人当场吓死了。
比如,回申娃给张德才一些毒药,并不知道他的目的是投毒害人,但两个人都成了反革命投毒犯,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处以极刑。第二天,公安机关收到工人、农民、学生送来的三百多封控诉书。控诉书中,人们为两个死刑犯设计了二十多种死法,有枪毙、杀头、割睾丸、解剖、放天灯、油锅炸、活剥皮、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挖舌、挖眼、钉在城墙、挂十字路、乱棍打死、吃五脏六腑、鼻子扎钻、两肩吊罐,等等。
不是这些民众的想象力丰富,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这些执行死刑的方式都有过了。
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
1975年,丰子恺去世了。他1898年出生,算起来七十七岁。他是画家、散文家、翻译家、音乐教育家、美学理论家,也是皈依佛门的在家修行者,政治运动中的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个标签,是我加上去的,他是中国古典文化养育的倒数第二代文人。
这大概是我的说法,没看到别人说过。
写下这个判断后我又确认了一次,丰子恺那一代不是最后一代,丰子恺子女那一代才是最后一代。他们在前一朝代经过童年少年,有条件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虽然那批人数量很少,只在纯正的文人家庭里出现。
我是在网络上搜寻丰子恺子女时,才产生这个想法的。
在女儿的回忆里,丰子恺的六七个子女从小学习中国古代名著,也听父亲读意大利的《爱的教育》。更重要的是知识以外的熏陶,30年代,父亲结束了十多年漂泊回到石门老家。他认为只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于是亲自动手设计、建造了一座具有深沉朴素之美的中式建筑。还有,他一言一行都饱含身体力行的对子女真诚、善良和美的教育;他希望孩子保持纯洁,快乐就好。
当然,通过他们的父亲,他们受到中国古典文化各方面的养育,但他们不比父亲一代更像中国文人。父亲一代人那种文化品格的完整与深邃,到了大清王朝颠覆后就不存在了。
像我这样描述一件事情,往往隐含着一些评价在内。这不是说中国古典文化多么好,而是说它被颠覆后的两个朝代,都树立不起来像点模样的文化,甚至还走到反文化的不归路上。你知道,这种说法够客气的了。
我不止一次羡慕过,丰子恺那一代人的勤恳和聪明之处。比如我不擅长的英语,他下些苦功夫学会了;而我同样不擅长的日语俄语,他用了自己独创的办法,很容易学习到位。
1921年,在一所专科师范学校教授西洋绘画的丰子恺,面对写生用的一个青皮橘子陷入迷茫,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半生不熟的橘子,卖给人家当绘画标本。于是他借了一些钱去日本留学,跟着日本人学油画。他要是借到更多的钱就会去欧美,那里才是油画的故乡。
他的英语基础好,就到一家教日本人英语的学校学习。先知道了英文课的内容,再听老师用日语讲解英语,就熟悉了日语的表达方式。在日本留学不到一年,这个异想天开的办法很好,让他英语日语一齐精进,能顺利阅读这两种文字的名著。
1951年,丰子恺53岁。聪明的他知道,到了新朝代,意识形态变了,在文学写作、音乐研究、漫画绘制等方面必须收敛,于是开始按照社会提倡的方向学俄语。他拿着日本人写的俄语入门书自学,自学九个月后,又用九个月阅读了俄文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然后用五个月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这样看来,会轻易产生一个判断,在原本可以创作得很好的中国人之中,有一些因为无奈才当了翻译家,而翻译出好的作品,对民族文化启蒙有近似的意义。我与另外一些人,算是他们的反面,原本没学好外文,当不了翻译家,只能在沉沦的无奈里坚守写作。
丰子恺不想当油画家以后,画了许多漫画。
以中国文人的目光,尤其是皈依佛门后的文人的目光,他看见动荡年代的中国百姓,仍然在传统文化的余晖里,充满平淡祥和、恬静善美的人间情味。他把这些一一画在纸上,让我们觉察生命的温暖。那些世俗情趣,充分表现出对生命与自然的挚爱。
他的一幅画《倘使羊识字》关系到生命与死亡的悲悯,让我感动了很久。画面上两只羊被人牵着,进入店铺,等待它们的是死亡结局。羊抬起头望着招牌上“羊肉大面”几个大字,没有伤痛的神情。画旁有弘一法师的题诗,“倘使羊识字,泪珠落如雨。口虽不能言,心中暗叫苦。”画上的羊不识字,读画的我识字,现在是识字的我替它们在心里叫苦。
还有一幅画《统一思想》,不知画于哪一年,但可以确定是画在统一思想的年代。统一思想意味着对人们思想的剪裁,合则留不合则去。丰子恺画了一排站立的人,有一把大剪刀伸过去,从头剪去,有的剪去半个头部,有的剪到脖子,被剪过的人都留了一样的高度。我在世界各国的漫画里,在中国漫画诞生后的百年作品中,还没有看过这样鲜明生动、寓意较深的反专制反极权的作品。
丰子恺有他独特的地位,是一位有骨头的画家,这在美术界极为稀少。你平时看到的都是一身傲气的画家,但是没有傲骨。比如,谁会像丰子恺那样,宁可画一千多幅画,送给来信索取的不相识的百姓,却不想画一幅画,送给当朝天子和官员。
我们欣赏丰子恺,顺便记住了他说的话:有些动物主要是皮值钱,譬如狐狸;有些动物主要是肉值钱,譬如牛;有些动物主要是骨头值钱,譬如人。
丰子恺还说,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中国古典文人的境界,在于聪慧,在于觉悟。他们会看淡一切,面临大难也不动声色。
1966年,丰子恺六十八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丰子恺成了上海十个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之一,被押到十万人的斗争大会上斗争。他家原本住整幢房子,被勒令搬到楼上,楼下住进了好几户人家。他画于前一朝代的画作,被攻击为当朝的反动作品。他的女儿第一次看到白发苍苍的父亲委屈地流泪。“在这之后,父亲似乎横下了一条心,冷眼旁观,泰然处之。无论多么无情的批斗,都不再触动他的心灵。”
那一年,作家老舍被革命青年毒打之后投湖而死,丰子恺淡淡地说,死就死了吧。第二年,学者马一浮被革命运动羞辱后病死,丰子恺还是淡淡地说,为何不早死一年呢。——早死一年,就不必受这份屈辱了。
1967年底的一天,丰子恺最小的儿子结婚。那一天丰子恺被拉去开斗争大会。全家人都等着父亲回来吃团圆饭,他却到晚上九点多才冒雨而归,一进门气喘吁吁喊着“我来迟了”,还笑嘻嘻地将揣在怀里的一对小镜子分送给新人,还送他们两句诗“月黑灯弥皎,风狂草自香”。
这是丰子恺对生死荣辱的态度,面临大难不动声色,不惜生命被乱世夺走,但不会像老舍选择自杀,不会像马一浮羞愤而死。《金刚经》上佛说,“一切法得成於忍”,讲的是忍耐,但在有些佛经里翻译为忍辱,是考虑到了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社会,一直有自己特殊的国情。
辱都能忍了,还有什么不能忍的?丰子恺比他们多活了八九年,1975年因肺癌去世。
进入二十一世纪,他被人想起来的时候不多,甚至想也想不起来了。重庆有人因为网络言论判刑三年之前,审问者看到他QQ空间中有幅名为《统一思想》的漫画,作者丰子恺。审问者确实不知道丰子恺是谁,于是问被审问者:“你与丰子恺是何时联系的?此人现在在哪?”
——以首场广东喉管·唢呐独奏音乐会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