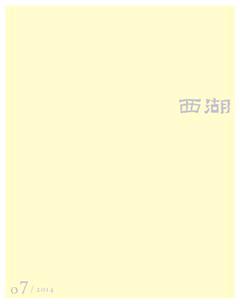个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想象之“重”
徐勇
“80后”作家中,有“玉女”之称的张悦然非常有代表性且十分独特。说其有代表性,是因为张悦然的小说创作代表了“80后”写作中耽于想象、成长与爱的主题的重要倾向;说其独特,是指她的写作是为数不多的刻意回避自己人生经验的青春写作的代表。张悦然的写作虽有所谓“生冷怪酷”的评价,其中弥漫着杀戮、幽灵与病态,但也是这些作品,同时显示出极为浓郁的抒情格调与浪漫气质。张悦然的小说虽然称不上气象恢弘,但也充沛淋漓,其文字简洁流畅,叙述纡徐舒缓,即使常有稚气流露,亦并不掩盖她在文学写作方面的巨大潜力。张悦然的小说充分表明了“80后”写作所能有的深度和限度;优势所在,往往也是困境所在。张悦然虽有反省和自觉,但也常常进退失据或顾此失彼。
一
在张悦然的小说创作中,长篇《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和《樱桃之远》占有重要位置。虽说她的写作常因经验的缺失而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但她能在飞扬的奇想中自我突破,努力向各个方向发展,这三部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张悦然写作的三种倾向。
一是爱与恐惧的辩证故事。《樱桃之远》在张悦然的创作中有其象征意义。这是一部表达对人生孤独处境的大恐惧和大渴望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杜宛宛从小就感觉到耳边不断有神秘的声音存在,使她不得安生。她困惑、恐惧,以为是魔鬼寄居附体,后来偶然发现,原来这些都是因为一个名叫段小沐的陌生小女孩,是她的声音她的心跳她的一切一直纠缠着她。小说讲述的就是杜宛宛如何挣脱段小沐而最终两人合二为一的故事。她仇视段小沐,潜意识里还因为她能窥视到她的内心,使她的弱点无处隐藏无所遁形。表面看来,杜宛宛是一个很孤傲的女孩,但她其实非常孤独;她把自己封闭起来,用孤傲做武器,虽看似强大,但其实十分脆弱。这部小说虽然讲述的是三个女孩和三个男孩间多角恋爱的纠葛,但其实关切点仍在个人的孤独与爱这一主题上。这是“80后”写作的一大特点,表面看来塑造表现了一大堆人物,其实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内心感受。所谓“繁华背后的苍凉”即此。小说中的三个女孩,杜宛宛、段小沐以及唐晓,其实是一个人的不同侧面:一个孤傲、残忍而偏执,一个热烈、单纯而执着,一个宽恕、坚忍而圣洁,她们互为镜像,彼此看到曾经的自己。同样,三个男孩,纪言、管道工和小杰子,也是一个人的不同侧面,与三个女孩的性格恰相对照。杜宛宛因爱(段小沐)而牺牲自己,管道工无私的奉献的爱,段小沐以爱化解恨,等等,都一再表明爱的宽恕与救赎仍旧是这部小说的情感诉求。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关于人生对称性和“双生”的故事。在小说的附录《我的回顾》中,作者表达了对“双生”的渴求和困惑,“生命应当是对称的……它绝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也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相信生命是安全的,在另一处,有另外一个人与你一起奋力支撑坍塌的天空”,“它(指生命的对称性——引注)诞生于生命最初的时刻,是一种隐形的深层对称”。虽然很难说张悦然就此表达了什么深刻的哲学思想,但仍能从中看出先验唯心的倾向。这是以想象的方式完成的先验唯心主义哲学命题。人生而孤独,因为她是残缺的,故而总在寻找另一半;她有另一半,她的一生的经历,就在于寻求这另一半;寻到了,她就圆满了,幸福了,未寻到,她就是不幸。张悦然小说的主人公段小沐和杜宛宛间从对抗到最终合二为一,从“隐形”的潜在的“对称”,回归显在的对称;张悦然以小说形象地诠释了柏拉图的理念说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说。最初的自我是统一的,后来分裂了,在经过了人生的历练后复归统一,这就是所谓的人生的辩证法。人的一生的意义也就在于,找回另一半,回归自我。如有些批评家所言,这确乎是一种“意念和情绪”下的产物(邵燕君:《张悦然:生冷怪酷的“玉女作家”》,《“美女文学”现象研究》),但从另一方面看其实也比较符合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人的经验:一方面是生活在爱的包围中,一方面是内心的荒芜、寂寞和恐惧,两者常常奇怪地统一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矫情造作,但对他们而言这却是实实在在;他们生活在这种自我想象的分裂中,渴求回归与统一。《樱桃之远》中女主人公宛宛的形象的意义正在于写出了这一悖论和隐秘。
二是成长叙事中的写作、爱与救赎三位一体的故事。成长固然是“80后”作家们念兹在兹的话题,但把成长与写作、爱、救赎放在一起的,却要首推张悦然了。对于大多数“80后”作家(典型如七堇年、颜歌和张怡微)而言,成长往往同时意味着创伤、疼痛和遗忘;张悦然亦然,但对她来说,疼痛往往并非仅仅“他为”,疼痛常常源于自身,这是自我施与的疼痛。正是这种自虐式的疼痛,写作与爱就成为他们走向自我救赎的必经之路。从这个角度看,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的意义就在于道出了“写作”(书写或叙述)之于“80后”的重大意义。这是以倒叙的方式讲述的一个名叫陆一璟的青年女作家的成长故事。成长与写作,是很多“80后”作家共同的小说主题,但对于张悦然的主人公陆一璟而言,却似有另一层含义。在笛安、春树、颜歌、七堇年和李晁们的主人公那里,写作是处于成长阶段的主人公面对孤独时自我疗伤的武器和自我想象圆满的方法;但对陆一璟来说,写作则包含有双重意义,这既是职业之一种,是自我确证的方法,更是自我救赎的方式。陆一璟的形象,很容易让人想起颜歌《声音乐团》中的小说家刘蓉蓉,这都是孤独的青少年主人公形象,童年失爱使她们的青少年时期笼罩在残缺之中。虽然说,她们都通过写作来传达内心隐秘的感情,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静,但不同的是,写作让刘蓉蓉深陷其中,却让陆一璟从中最终获得一种人生的提升与救赎。写作让陆一璟大获成功,声名大振,却最终使刘蓉蓉作茧自缚,香消玉殒。
《水仙已乘鲤鱼去》之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塑造了一个有暴食症倾向的抑郁症青少年的形象。作者写出了成长中的青少年主人公如何反抗自己的抑郁倾向的故事,一方面是孤独少爱,一方面又是对爱的渴望。爱、回忆和写作构成了主人公自我救赎的三部曲,这当中,爱才是真正具有救赎力量的东西。张悦然小说中的青少年主人公很少有叛逆的表现,但却普遍具有自闭或幽闭的倾向。她的主人公孤独少爱,沉静自持,但另一方面又富于幻想,想象力发达。写作就成为他们自我救赎和自我确证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张悦然之不同于大多数“80后”作者的地方。虽然说孤独与疼痛是“80后”作者普遍的写作主题,爱的缺失也一度成为他们的中心议题,但真正写出爱的救赎面向的,却非张悦然莫属。少爱的一面是孤独自闭,但另一方面也是对缺失的爱做填充的渴望。虽然这多少令张悦然显得浅薄,张悦然的作品很少有存在主义式的深刻内涵,但她写出了爱的向上向善的一面。这于“80后”作家之刻意渲染孤独和疼痛的倾向,无疑是一种补充。
三是基于经验不足上的进入历史写作的浪漫奇想。在“80后”作家中,经验不足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青春和成长似乎就成为他们永恒的话题;张悦然当然也不能免俗,但她能突破经验的限制,进入历史叙事的想象世界,《誓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这是一部构思奇巧的小说。小说中,作者构筑了一个发生在南洋的古代故事。南洋而古代,可见作者的想象力之丰富。对于“80后”而言,塑造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形象或许并非他们的所长,事实上,很多“80后”作者也无意于此(春树是个例外)。小说之于他们,更多是一种想象世界构筑梦幻的方式方法,历史书写往往能提供这种便利;它能有效地摆脱经验的束缚,进入历史,也就进入了想象驰骋的空间,恣肆纵横。
颜歌也有过想象历史的尝试,但其《关河》更多地是一种寓言式的演绎,历史被高度象征化。相较而言,张悦然则能在对历史的想象中凸显青春文学的精神特质,而《关河》的思想的象征中则看不出多少“80后”的影子。这也是张悦然不同于颜歌的地方。虽然说,她们的历史写作都非写实,但一个是在想象的开掘上,一个是在象征的表征上展开,其面相终究不同。《誓鸟》采用的是故事套故事的结构,先后讲述了春迟、淙淙和宵行的故事,情感的纠葛、成长,仍是这部小说所欲表达的主题。而所谓青春文学的精神特质,尤其体现在小说中文字的稚美、想象的葱郁、主人公们的执拗及渴望爱的救赎上。这不是一部写实作品,当然不能要求主人公们按照现实的逻辑行事,这使得她的主人公大都显示出偏执的一面来——春迟为找回记忆弄瞎自己的眼睛,宵行对春迟没有理由的依恋,淙淙对春迟由爱而恨,钟师傅几十年如一日的坚贞,等等。但这都是对爱的坚守,她们因爱而生、因爱而亡。历史小说的写作有很多种,有刘震云式的解构历史,苏童式的个人视角,姚雪垠式的史诗追求,但像张悦然这种进入历史而只写爱和爱的救赎,确乎显现出青春文学的精神特质。
二
或许正如张悦然所说,我们的文学需要“一个从集体到个人、从宏大叙事到个人化表达的转变”(《我们能够带着理想走多远》)。在她这里,借助想象而非个人经历就成为这样一种“个人化表达”的方式方法。她的小说沉浸在想象的空间,我们从她的作品中很少可以看到个人经验的影子,这与其他很多“80后”作家不太一样。很多“8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大都立足于有限的人生经历,对其反复书写与渲染;虽然很多也极富想象力和才情,但总给人一种自我反复与重复的感觉。相比之下,张悦然之有意回避个人经验的反复书写,确能带来某种飞翔;事实上,张悦然的突出之处正在于,她能突破已有经验的束缚,通过想象而不断再造经验。她的小说体现了幻想写作的典型特征。说其是幻想写作,是因为张悦然的写作建立在想象而非经验的基础上,这使得她的小说创作充满一种浪漫的基调。个人经验之外,张悦然偏向于从构思奇巧和想象上用工夫,她的小说也常常摇曳多姿,“色”彩斑斓(如《红鞋》)。
但另一方面,张悦然其实又并不能脱离时尚大众文化的限制。她一方面努力突破已有经验的限制,沉浸于想象和幻想的空间,但终究还是有点落入类型文学的窠臼。她的小说尽是一些鬼魂、自杀(或杀戮)、虐恋、阴谋、伤害与多角恋爱等大众文化的陈旧话题。这一倾向,集中体现在她的《十爱》和《葵花走失在1890》这两部中短篇集中。《十爱》讲述的是十个有关爱的主题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集中,张悦然写出了爱的救赎,同时也写出了爱的毁灭性的一面:爱是禁锢,具有排他性。其中如《昼如夜房间》,两姐妹之间爱与被爱的纠缠和战争令人心颤。或许,正因为爱是一场战争,死亡才让爱得以飞翔,从这个意义上说,《葵花走失在1890》(小说集)讲述的正是爱的毁灭与死亡的故事。《纵身》中的“我”,被欺骗和谎言包裹,在决定“纵身”之前,仍在精心计算着“纵身”的速度和落地之前获救的可能。《葵花走失在1890》和《红鞋》中,爱则成为灾难、毁灭与一厢情愿。
一方面是“个人化表达”的诉求,一方面却又是有意回避个人经验,这是否意味着张悦然的自相矛盾或自欺欺人?这似乎正是张悦然的独特之处。张悦然深知,个人经验的反复书写虽然带有个人色彩,但这样的经验其实并不必然“个人化”,因为显然,作为一代人的个体之一,个人的很多经验往往是一代人所共有的,而对张悦然这样并不具备更多独特经历的“80后”而言,要想写出“个人化”的经验,似乎惟有想象的再造一途,别无他法。为此,张悦然努力追求一种“魔幻和童话色彩浓重”的“情感纯粹而极致”的表达,虽然其“尚未得到经验的补给, 仅仅是靠情感驱动, 运用蓬勃的想象力, 它们纯粹、强烈, 而且趋向极致”(《“80后”的文学对话——霍艳访谈张悦然》)。这样一种写作的好处是,它毋需经验也不必倚靠经验就能飞翔,而那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则会因为经验的匮乏导致叙述过于简单, 或者故事过于虚假”(《“80后”的文学对话——霍艳访谈张悦然》)。其结果,她的主人公大都带有一种执着(或偏执)的性格特征,像暴食、自虐(自杀)、幽闭、内倾和固执等等皆为偏执的明显表征。“极致”而偏执,张悦然借助想象所建构的,并非脱离现实的自足而完美的化外之界;她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极致”化表达,呈现出来的毋宁说是对现实世界的独有理解和感悟。这仍是一种面对现实的发言。可见,张悦然以一种远离经验的“极致”化想象方式,完成的其实是对经验世界的重铸和再造。
这些偏执性格虽说有病态之嫌,却并非变态。病态而不变态,典型地体现在《红鞋》里的杀手身上。杀手虽然冷酷无情,杀人无数,但最终却栽在一个小女孩身上。他从小女孩身上看到自身的影子,他渴望用爱和关心唤醒自己,最终却发现原来一切都只是枉然。相比世界每天发生的背叛与杀戮,爱的力量微乎其微。张悦然在这篇小说中写出了爱的拯救的微茫之于世界的荒谬的困惑。病态常能让人产生怜悯并给人以美感,变态则只能带来恐惧和不安,张悦然很好地把握了这中间的尺度。病态而不变态,这也是张悦然的小说虽然诡异、“生冷怪酷”却仍十分浪漫的原因。对她的主人公而言,偏执是一种内心状态,它只针对自身,他们宁愿自残自虐,而无意于报复社会伤害他人;偏执使得她的主人公们内心普遍匮乏而焦灼,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力求回归和渴望圆满的等待中。这样一种充满张力的平衡,从中不难看出张悦然的内心弥漫着对这个世界的怕和爱。她和她的主人公们沉浸在个人的小叙事里,看不到宏大叙事,但不意味着对世界的漠然和无视。事实上,世界令人不安的一面,如杀戮、背叛和变态等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世界冷漠而无助,她们不能理解,理解不了,但又渴望理解,这样一种拒绝(宏大叙事)而渴望(认识世界)的矛盾心理,某种程度上正是张悦然的小说沉浸于想象世界的原因。这一通过想象再造的经验,表达的正是她对现实世界隐秘的理解、恐惧和希望。可见,在张悦然以及她的主人公这里,想象并非仅仅逃避并远离现实世界的工具,毋宁说更是重新介入世界的方式方法(方法论)。这就有点像康德意义上的先验世界,先验虽在经验世界之外,但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引导并介入经验世界。张悦然在现实世界之外构筑想象的世界,想象之于她和她的主人公们,其意义并不在于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而在于回归和接续,它以一种表面上的挣脱完成的其实是对现实世界的发言和重新介入。
三
可以说,张悦然是“80后”作家中比较清醒的有代际意识且具有反省精神的作家,她曾把他们一代人的文学称之为“形容词文学”:“我们这一代的文学更多的是形容词文学,我们对于繁华世界的描写,其实就仅仅体现在比上一代人多了这么几百上千个形容词上。但是,我们的动词萎缩得很厉害,我们的小说缺少了行动,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空虚的描述。”(《我们能够带着理想走多远》)“形容词文学”即所谓夸饰性文学、不及物文学。它是一种注重修饰和表达的文学,而对于表达什么,抑或现实生活中真正发生的事情却很少关注。或者可以说,“形容词文学”是一种抒情性文学,与之相对的,则是一种叙事(故事)性文学。这确乎是“80后”写作中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一倾向在七堇年、颜歌和春树等作家那里十分明显,而事实上张悦然自己也不能免俗。但这样一种意识对她也并非没有影响。张悦然的文字纯净、简练而富有抒情色彩(“抒情性”),这与七堇年繁复华美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也与春树直接少修饰的语式迥异。
即使如此,张悦然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必然和过渡,“我们的文学必须先完成从集体到个人的演变,才能考虑故事的复兴”(《我们能够带着理想走多远》)。夸饰性写作——幻想写作是其中一种——无疑是他们拒绝宏大叙事的策略之一;但问题是,一旦文学经由个人小叙事而回到“故事的复兴”,这样的“故事”其实已难称为“故事”,而毋宁说是生活碎片化的个人呈现,纵使聚拢也不再显现其总体化的面相,更不用说给人以慰藉和想象的可能。“80后”作家们并非不知道这点,“个人化表达”往往只是他们抗拒宏大叙事的方式,而不是目标。从这个角度看,张悦然的《湖》(2011年)正是这一悖论的隐喻。这是一部张悦然意义上可称为“故事的复兴”的现实题材小说,小说写得细致深沉曲径通幽,足见作者的笔力。主人公程琤远赴重洋来到纽约,正可以看成跟原有的“象征”人生的断裂。迷茫、沉重、执着而又决绝的内心,使得她进退失据如履薄冰,冬日结冰不厚的“湖”的意象恰是对这一人生困境的表达。
这一迷茫与决绝的人生困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正是“80后”文学写作的困境。耽于成长主题的想象和“个人化表达”,是他们的所长,也是他们之所以作为“青春写作”的标志。他们一旦回到坚硬的现实人生层面的叙事,虽显示出成熟老练的一面,但也可能会失去自我的风格特征而不复是他们自己了。莫言曾在《葵花走失在1890》一书序言的结尾写道:“伟大的文学,从不单纯停留在梦幻的层面上,它要涵盖历史,涵盖广阔的现实与责任,涵盖琐碎、艰难而具体的现实人生。”(《飞扬的想象与透明的忧伤》)这当然是对张悦然的忠告。张悦然自己其实也很清楚,她之所以很少写现实题材,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中篇小说《湖》的出现,确乎让人看到一个成熟大气且有潜力的作家的形象,但这样的作品,却很难与张悦然惯常的风格联系在一起。
成熟也可能意味着迷失,对于“80后”作家们,这似乎是一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