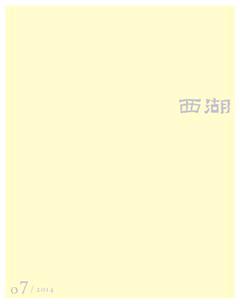汉字动物园:麒麟·羔羊·喜鹊·乌鸦
朱孟仪
本文诞生于《春秋》的最后一个字。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在《春秋》纵贯242年的时间幅度中,“麟”在整部书里只现身一次,而且是在最后一条经文中。据《左传》记载,当年鲁国叔孙氏的仆从射杀了一头鹿身、牛尾、马蹄、头上有肉角的动物,大伙儿都疑为怪兽,认为是不祥之兆。孔子获知后老泪纵横地说:“仁兽,麟也,孰为来哉。”意思是世所罕见的仁兽麟呵,你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在这个时候来了!次日,孔子在竹简上写下“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依孔子的理解,麟是瑞兽,“非其时而至”,不禁悲从中来,从此绝笔不再著述。
“获麟绝笔”的故事,为想象力丰富的文人墨客留下一串悬念。为此,韩愈写下了《获麟解》,试图设置一个返回经典的对话场,探寻其中的奥秘。“麟之为灵,昭昭也”,弦外似有不以为然的意味——韩愈说,麟与“灵”音同,这妇孺皆知的灵兽,无非是马、狗、猪、豺、狼、麋、鹿这类形象的集结整合而已。
麟,金文写作“ ”,由 (鹿)、 (粦)会意组合而成。其中,“ (粦,顶层是两火,下层为双足)”暗示出先人造字的意图:粦是跳动的磷火(俗称鬼火)或闪烁的粼光(波光粼粼),意味着幽冥、灵动,暗含“活在他世界”的意思。史书上说,麟的复数形式是“麒麟”,“毛虫三百六,麒麟为之长”。在中国,凤是羽虫之首,麟是毛虫之长;麟凤与龟龙向来是吉祥的象征,合称“四灵”。按“六书”的说法,“麟”以“鹿”为类旁,又因其身披鱼鳞而得名,属于会意兼形声字。不难想象,古人造这个字的时候,似乎是说麟由鹿演化而来,但它又决不是鹿,比鹿多了一些装备和配件:它只是体形像鹿(麋),身上布鳞,圆顶上还有一只角,角端有肉、黄色。从造型上看,鹿(麋)身、牛尾、马蹄、鳞皮,这无疑是对那些备受人们喜爱的动物所具特征的分解与重组。我们之所以无意于侦破其中分解与拼合的痕迹,是因为它是在幻想中建构的,体现了中国人“集美”的思想,这与龙凤的营造法式并无二致。所以说,麒麟是依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复合虚构的动物。在中国文学诗意喷发的唐期,韩愈的《获麟解》试图走出神秘主义的泥沼,见解非同凡响。
可是,《获麟解》全文只有186字,不可能为我们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是韩愈惜墨如金,还是不屑着墨,已不得而知。沿着韩老师授业解惑的线索向上追溯,晋人杜预的解读令人眼前一亮。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杜预说:“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意思是,你看到的这个文本缘起于最末所陈述的事实,“获麟”触动了孔子奋而起笔,而你看到的最后一个字才涉及到这起笔的由来。这是个令人欣喜若狂的发现:《春秋》阅读的终点,恰恰是作者写作的起点。按照杜预的说法,《春秋》收笔于“麟”绝非偶然,一定是孔子殚精竭虑、蓄谋已久的铺排。
暂释这份喜悦,折回《春秋》这部肃穆的经书。众所周知,孔子笔削后的《春秋》已不是一部单纯的鲁国史书,或可称为孔子意欲整肃天下的经典。孔子说:“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一向被后世推崇。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按时下流行的说法理解,即于沧海横流之时,孔子著“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撇开《春秋》政治层面的文化、舆论的力量不谈,仅从技术上看,我个人认为《春秋》当是凝聚了孔子一生的心血和智慧,不可能是随意应景之作。或许,胸有块垒的孔子在构思《春秋》之前,心中早有麒麟左右冲突、上下翻腾。他以“麟”为“灵感”的触媒,化“麟”为文学意象,使其贯穿《春秋》始终,并试图设置一个首尾开放的文本结构,启发后人作开放式的思考。这对于知天命、“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子来说,不是难事。
孔子为什么选择“麟”作为《春秋》的文学意象呢?可否从苏童的《米》、莫言的《蛙》分别选择“米”和“蛙”作为文学意象的现代手法去揣测古人?“获麟绝笔”两年后,孔子追随那头神兽西去,时年73岁。孔子之死,想必是轰动了朝野,“获麟绝笔”的故事也随之流传。李白在《古风诗》中就有“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诗句。
蹊跷的是,孔子的肉身和命运居然是按照麟的营造法式合成的。据《韩诗外传》记载,姑布子卿曾对子贡说:“孔子额头像尧,眼睛像舜,脖子像大禹,嘴巴像皋陶。从前面观看,相貌过人,有王者气象。但从身后观察,却是肩高耸,背瘦弱,这样的不足与缺陷比不上四圣,将会让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无坐朝堂之富贵。”这难道又是巧合吗?如果是,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巧合。
更蹊跷的事发生在73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51年(鲁襄公22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颜徵在)去尼丘山祈祷,途中遇一麒麟而生孔子,这就是“麒麟送子”的神话。孔子生来头顶上凸起一个小山包(与麟相似的肉角),所以得名孔丘,字仲尼。传说孔子降生的当晚,有麒麟降临孔府阙里人家,并口吐玉书,上有“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徵在贤明”的字样。意思是说,孔子乃自然造化之子孙,非凡人也;虽未居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堪称“素王”。
遇麟而生,又遇麟而死——看来孔子他老人家真把自己当成麒麟转世的化身了,“不知生焉知死”,竟然自由操纵了自个儿的生死大限,这与鲁智深听钱塘江潮信而圆寂的故事好有一比。“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向来敬鬼神而远之。在孔子的灵魂深处,是否藏有身世以外的玄机?梳理相关史料,一条清晰的脉络赫然在目:遇麟而生,感麟而书,文成获麟,泣麟而死,这是一条解读《春秋》乃至孔子思想的线索。沿着这条线索不难发现,孔子的思想与“麟”冥冥感应、息息相关。
“孔仁孟义周礼乐”,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可说是儒家学说最高的、根本的道德准则,主旨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具有“仁爱之心”,并以“爱人”与否为道德标准,以确定人们是否应该受到尊敬和重用。
统御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其脉络竟与一头神兽有关!长期生活在我苏北老家的农学专家胡淼先生,在《〈诗经〉的科学解读》一书中,引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说麒麟实际上是现在仅存于中部非洲一带的麋羚。麋羚古时曾遍布于东亚到西亚及非洲的广大地区,直到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山东半岛最后消失。这个说法与“孔子厄而作《春秋》”的时间大体上吻合。但在科学尚未昌明的中国古代,麒麟在传说中被赋予了“仁”的品质,比如说其“性温善,不覆生虫,不折生草,头上有角,角上有肉,设武备而不用”,因而被称为“仁兽”。西凉武昭王《麒麟颂》:“一角圆蹄,行中规矩,游必择地。”《宋书·符瑞志》:“含仁而戴义,不饮池,不入坑阱,不行罗网。”《说苑》:“含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后践,位平然而后处,不群居,不旅行,纷兮其质文也,幽问循循如也。”……说法纷纭,其中闪烁着麒麟仁厚君子的谦谦风度。麒麟崇拜之所以在人文传承中被广为接纳,正是因为“仁兽”所具备的秉赋契合了传统礼教和儒家风范。
麒麟往往在太平盛世伴随着“圣王”出现,于瑞气祥云缭绕中,在香音飘缈中,款款而来。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传说麒麟现于郊野,为人所贱,标志着世界的日暮途穷和贤人的困厄,故孔子厄而作《春秋》,获麟而绝笔,《春秋》也因此被称为“麟史”、“麟经”。孔子认为,麒麟之死是个不祥之兆,据传他挥笔为麒麟写下挽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这正是孔子遇麟而泣、悲极而殁的原因吧。
动物是谜语,是密码,也是揭密解码的线索。从动物出发,突破层层阅读的障碍,可以与书写者从容对话。从结构主义的角度看,《春秋》最末一条有关“获麟”的书写、文本与阅读的模式,冥冥中被罗兰·巴特“文本开放理论”所印证,证明了书写结束是阅读之始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春秋》时其实已在打开孔子原本就蕴藏其中的“未来”。我读台湾学者李纪祥关于《春秋》开放式文本的文章,深受启发。李纪祥认为,卡尔维诺的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而这种实践在时空上也与杜预“文起于所止亦终于所起”的思想遥相呼应。
尼采说,上帝死了。罗兰·巴特说,作者死了。
羔羊
麒麟是仁兽,羔羊是义兽。
羔羊是羊群里的XO,“鲜美”两字中就含有这么一只“羊”,“义(義)”字里也隐藏了这么一只羊。这是一只守身如玉、含苞待放的羊,其“鲜美”成色大致相当于政商大佬们津津乐道的嫩模。所以,名儒董仲舒干脆撇开羊群中泛泛的“俗物”,专门讨论心目中的极品羊。《春秋繁露》说:“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啼,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在董仲舒眼里,羔羊知仁、知义、知礼,集儒家的道德原则于一身,正如《诗·召南》中所说,“德如羔羊也”。“德如羔羊”,是人对羔羊“人格化”品质的感悟和高度概括。正是在这种感悟和概括中,羔羊被称为“义兽。
最早见于甲骨文的羔( )是个指事字。在羊( )身上加四点( )作为指事符号,指点人们去想象一只小羊( )一生下地就四肢站立、欢快跳跃的物象场景。甲骨文中另有一只羔羊( ),小身子骨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这状况看起来很残酷,但也很眼熟,这正是今天存活的汉字“羔”的雏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依蜀人黄奇逸的解读,“羔”的造字本义应与祭祀祖先神灵有关(黄奇逸:《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国古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描述的是以羊“火祭”的情形,而不是吃货们想象中吱吱冒油的烤全羊。
羔羊不屑于迎合、适应、培育人类的多重欲望,所以,始终没能像狗那样成为宠物而得以与人朝夕相伴,甚至爬上主人的床榻;也没有像鸡那样被用作暗喻、影射的素材,顺手拿来杀之儆猴;更没有像马那样,听任阿谀者把马屁拍遍。在六畜中,羔羊代表羊群执着于仁义孝道,与牛猪一道走上祭坛(三者全备称为“太牢”),化为殒身不恤的“牺牲”。这使我们不禁如见中世纪那威猛的烈焰,以及罗马鲜花广场上的火刑场面。
在今天,所谓“牺牲”是指像布鲁诺那样为某类人群或科学以身献祭、殉道的义举,常作动词;在古代,所谓“牺牲”是牛、羊、豕(猪)三牲的合称,说到底都是些人文化了的畜牲,属于名词。牺(犧)的篆文“ ”是由“ ”和“ ”合成的会意兼形声字,指的是祭典现场宰杀的猪牛羊。其中,“羲”既是声旁也参与表义,再现了杀羊宰牛、奏乐起舞的娱神的场景。甲骨文“牲”写作“ ”,文字学者认为左边的“ ”(羊),是弯角羊头加上表示母羊生殖器的三角符号;右边“ ”(生)则是小草生长之形,含有生机勃勃的春意。左右两形会意,表示母羊顺产活蹦乱跳、充满生机的小羊羔。汉字发展到隶楷阶段,“ ”左边的“羊”被“牛”取代(变成汉字“牲”)。这可能是对牛在农耕文明时期地位上升的奖赏,也可能是汉字对羊的一次盛大安慰——貌似以牛代羊做了“牺牲”的材料——事实上,牛不曾为羊做出任何“牺牲”,相反羊却为牛做过一次“替身”。
孟子曾提到过这只倒霉的“替死鬼”。某一天,齐宣王坐于堂上,堂下有人牵牛走过,宣王问牵牛何为?那人答曰杀牛祭钟(杀牲取血涂抹新铸成的钟)。宣王说:“牛本无罪,却要白白送死,看它吓得哆嗦的样子,真不忍心。放了它吧!”牵牛的人说:“大王慈悲,那么就不祭钟了吧?”宣王回答:“怎么可以不祭钟呢?换一头羊不就得了?”
对齐宣王来说,牛可废(以羊代之)而“祭钟之礼”万不可废。你可以同情眼前的牛,却不必同情那不在眼前的羊。比孟子早些时候,孔子曾率先对“礼”与“羊”的轻重问题发表过意见。据《论语·八佾》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的意思是:“子贡你脑残呵,你想在朔日祭祀(告朔)的仪式上省去活羊,首先就不合周礼。我一生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图个啥?还不是为了恢复周礼嘛。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礼重于善也哉。你爱惜羊我爱惜礼,小子你看着办吧。”子贡没有借用亚里士多德回敬柏拉图的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顺从的子贡们成不了亚里士多德。
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读《论语》时,发现“告朔之饩羊”与汉字“美”中的“羊”,都是“牺牲”的象征。在美的本质问题上,他认为“真”是存在的意义,“善”是存在的机能,“美”是存在的恩惠。在《关于美》一书中,他说:“美比作为道德最高概念的善还要高一级,美相当于宗教里所说的圣,美是与圣具有同等高度的概念,甚至是作为宗教里的道德而存在的最高概念。”可见,“美”是羊这种“牺牲”的外化衍生,正因为羊常常作为祭品出现,富有牺牲精神,超越了善的范畴,因而具有更丰富的宗教意蕴。
当羔羊作为宗教圣物出现时,实际上已被先民赋予了图腾意义。在川西2000米以上的海拔高度,羔羊悲悯的目光垂直向下,俯瞰大地。这种场景,很容易令我等不得不放任思绪穿越数千年时光,在岷江上游回溯到一个古老民族的上游。《说文解字》:“羌,西戎牧羊人也。”许慎认为,“男羌为羌,女羌为姜。”顾颉刚也认为:“姜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古文字学家董作宾、孙诒让等,对“羌”字也有类似解读。赵诚则说得更直白些,他认为“羌”、“姜”分别像男子、女子头上佩有羊角之形。这种戴羊角的习俗,反映了羌人的“羊”图腾信仰,他们相信通过这种象征性的模仿,可以使图腾的神力交感传播到自己身上。
汉字中,羊、姜、羌都与“戕”韵同音近,造字者似乎暗示着羊以及以羊为图腾的古老民族的命运。果不其然,在甲骨卜辞里,有许多戕害、杀戮、活埋、焚烧、肢解羌人充当祭品的记载,情形等同于罹难的羔羊,令人触目惊心。诗人流沙河感慨说:“异体字羌字犹有捆系残余,使人不安。2008年四川大地震又损我羌胞,伤哉。”
李宗吾从历史的转角旮旯中看到了“厚黑”二字,鲁迅从历史的通天彻地中看到了“吃人”两字。两位先生各执其词,我个人更倾向于调和:中国历史是人吃羊的厚黑史,中国的传统礼教是人吃羊的礼教。取象于人、羊相依的小篆“佯”字就是明证。汉字佯“人羊相伴”的结体昭示人们:不管是羊通人性,还是人扮羊样,总之汉字“佯”就是“装模作样”的意思。一切文化都是“佯”教化,一切礼仪都是“佯”斯文,一切道德都是“佯”善行,一切赞美都是“佯”说辞,只要你长得美白鲜嫩且性情温顺、宅心仁厚、知义懂礼,你就沐浴更衣准备摆上道德的餐桌或礼祭的供桌吧。在中国人的逻辑体系中——假如有逻辑且成体系的话——羔羊“其美德可以任人景仰”与“其生命可以任人宰割”是同位语。当子贡试图为羊开脱的时候,众生也许不禁感叹:再也没有比羔羊的嫩肉更美味可口的了。羔羊知仁而死于不仁,知义而死于不义,知礼而死于非礼,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不错,羊是合群动物,有前赴后继之勇。据流沙河观察,假如以竹竿设栏,领头羊一跃而过,羊群则相继跳跃而过。流沙河说,“此时纵然收去竹竿,后面的羊照样跳跃一次。”好比我们小时候排队跳山羊,仿佛有意识地为双脚装上了发条,多米诺骨牌似地倒向前面摔倒的小伙伴。相信名字取象于羊的刘翔同学也可能装有这样的条件反射系统。然而,如果一只领头羊带着大伙朝火坑里跳,你也跟着跳么?事实上羔羊们真的跳了,他们顺从了领头羊的意志,免去了思考和选择的苦恼,浩浩荡荡义无反顾地走上祭坛、走向屠场,至死不发出半声悲鸣。
这难道是出于羊性的自觉?无独于中国,西方的羊也曾代人受过。在西方,历史上第一只“替罪羊”死于公元前2000年。创世之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杀了你的长子祭神!在人性考验的最后一刻,这道刻薄的命令,幸好改为用一只羊来执行(上帝呵,不兴这样的)。文明演进了2000年,终于到了公元元年,新鲜出世的救世主认为,犹太人是一群“迷途的羔羊”。为了替犹太人赎罪,无罪的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上十字架,做了有罪的犹太人的“替罪羊”。在“狼图腾”时代,强权淫威下,面对数千年难免“牺牲”的命运,羔羊们做了沉默的大多数。生存权是基本人权,生命权是基本羊权。不曾想,在所谓尊重人权的西方,羔羊的命运好像也没好到哪里。
拜信息多元化所赐,时下再也没有谁能垄断资讯之沟渠。所以,相信羔羊迟早会颠覆性地读到鲁迅先生的警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喜鹊
所以,她决定筑一个巢。
在凤凰的嘲笑中,喜鹊完成了这个伟大的计划。“鹊”金文写作“舄( )”,上为鸟窝( ),下为“鸟”的省变( )。小篆 (鹊)承袭了金文形制,同样是上下结构,突出了鹊筑巢的本能。从金文和篆文的字形可以窥见,这位将“巢”高高举于头顶顶礼膜拜、以巢作为族群徽标的鸟类,与高傲的凤和贪婪的鸠相比,的确有先见之明。时至21世纪才大彻大悟的屌丝们终于活明白了:在今天的中国,房子高于一切,房子是一切的一切!
凤凰耽于作秀而疏于筑巢,令后世瞻仰者只能在神话世界(据说现实的大地上凤凰因无巢而“绝后”)捕风捉影,想象“凤凰于飞”的曼妙风情。北京以全球最大的“鸟巢”诏告天下:“更快、更高、更强”的逻辑起点是房子!种群繁衍、文明传承、文化递延,还是房子!总之,筑巢是必须的。
传说远古时代,不可一世的凤凰每天无忧无虑地啄理她漂亮的羽毛,还不时起舞弄清影,向百鸟展示王者风范。而喜鹊不知疲倦地穿梭于旷野林间,衔来树枝搭建自己的巢穴。凤凰嘲笑喜鹊不懂生活,没情调,更不会调情。喜鹊听罢,只是用嘻嘻的笑声回敬凤凰,用更加勤奋的创造,享受着自己的生活。很快,产卵的季节来到了,凤凰整日作乐却没有自己的房子,只能把卵胡乱产在山坡上、草地上,随即被蛇、鼠、狼享用一空,于是鸟之王者在地球上永远消失了,现实的大地上只留下凤凰栖居的遗迹——梧桐。喜鹊用自己的努力,创造了生命的赞歌。历史与现实的天空,每天都回响着它的声音。
背着房子炫富的蜗牛不需要筑巢;生来披一身毛皮的动物,对居所的要求也没那么饥渴。即使是兔子、旱獭、河狸这一类天才建筑师,也只是基于遗传基因,将打洞做窝当成生活的唯一娱乐,犹如老鼠的啃噬,压根儿就不是为了胃。“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国风》)《诗》三百篇中第一个出场的动物鸠,也是不筑巢的鸟。《禽经》将鸠不筑巢归因于它的愚笨和懒惰(“拙者莫如鸠,不能为巢”),而《诗经》则把它的不筑巢归因于蛮横与霸道。“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诗经·召南》),意思是说,鸠惯于占人茅房,只有智慧的鹊类才懂得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喳喳鹊叫着海子的诗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礼记·月令》中说,“鹊始巢”。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说:“巢,乃是爱情的产物。”于是,为爱情筑巢的发明家鹊鸟,有了一个悦耳的名字——喜鹊,这是中国人赐予鸟类的爱情最高项奖(喜蛛也有此殊荣,但它不算什么鸟)。所以,《格物总论·鹊》概括地指出了喜鹊的色彩、形貌与发声的象征意义:“鹊,一名飞驳,形类于鸦而小嘴,尖足爪黑,颈项背绿色,白翮,尾毛黑白相间,善为巢,其声喳喳,鹊声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鹊。”在青海湟水北岸,曾出土一件彩陶喜鹊图,这说明喜鹊文化最早起飞于新石器时期的高原部落。随后,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从黄土高坡飞来的吉祥鸟大度地选择了我们,做了我们的邻居;同时也选择了一棵大树,深入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基层,立足于剪纸、绘画、诗歌、散文、小说、歌曲、戏曲、影视桥段以及风俗习惯等,大尺度地表现爱情主题,唧喳喳地渲染喜庆场面。好大喜功的中国人也大尺度地接受了喜鹊报喜不报忧的公开献媚。最让中国人开心的画面是《鹊登梅枝报喜图》,人称“喜上眉梢”。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文化里的另一位超级明星——梅。相传梅是喜鹊从王母娘娘那里偷来人间的。梅虽然不比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实惠管用,但她却增加了喜鹊在国人心目中的分量,尤其是解决了林和靖们的单身苦恼,满足了“隐者”的恋物情结。
中国人把报丧的职权分配给了乌鸦,把报喜的任务布置给了喜鹊。《周易统卦》曰:“鹊者,阳鸟,先物而动,先事而应。”师旷在《禽经》中说:“灵鹊,灵鹊兆喜,鹊噪则喜生。”可见,喜鹊具有感应自然的功能,能够为人类先一步感应和预报喜事。喜鹊的一言一行不仅为中国大众带来一天的好心情,还为公共权力提供源源不断的政治智慧。在中国乡村的天空,可以没有“超级女声”,但一天也不能没有“花喜子”(我老家把喜鹊称为花喜子)的唧喳喳。据说,只有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才难得听到喜鹊的噪叫。这一天,喜鹊倾巢“鹊起”,离开它们依恋的村庄、大树和巢。传说,除了“隐者”需要爱情以外,还有一对苦命鸳鸯也正在饱尝别离之苦,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家族宇航员”集团——牛郎、织女及其孩子们(嫦娥充其量属于个体宇般员,而且也没能超越太阳系)。《古诗十九首》的《迢迢牵牛星》里有这样的诗句:“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首诗以质朴、清丽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天茫茫,路迢迢,银河两岸的饥渴青年望穿秋水,他们每日只能用“火星文”、“流星体”,狂写《两地书》打发时间。这一点也许你没看到,但喜鹊看到了。虽然你没看到,但你一定听说了:冒着被牛郎踩落天河的风险,喜鹊在天河上搭起一座十分壮观的“鹊桥”。
筑巢是为了自己的爱情,盗梅和搭桥是为了别人的爱情。喜鹊不负众望,人们自然皆大欢喜。可是,我认为喜鹊筑巢是打着爱情的旗号去孵卵。因为爱情起于卵而终于卵,它是世界的摇篮。非卵生的动物不会“蛋疼”,他们打洞只是个体的偏好;筑巢的喜鹊是心疼她的蛋。所以,孵卵才是喜鹊筑巢的真正动机。
这一点你可能没看到,但造字的先贤们看到了。古人用“舄”( ,表示鸟的房子)作为基本构件,加上“宀”( ,表示人的房子)做字头,发明了会意字“寫”(金文写作“ ”,简化字是“写”);以卵巢为字象,借以表达文明传承和生命延续的意义。我们没法回到初民从动物到人的“奇点”,也无法还原由“舄( )”到“寫(写)”的造字的第一现场,但我们却能想象到“写(寫)”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文化与词》一书中说:“动物依靠自身的体气或撒下的便溺来辨认自己的来路,人却用语言来辨识自己的来路。”作为手书的视觉符号,文字的诞生就是为了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朽力量,将稍纵即逝的语言(口语)以及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绵延不息的人类文明的万古长河。德国汉字学者雷德侯在《万物:中国艺术的模件和规模化生产》一书中说:“文字的目的即在于将话语转换为图形从而将其记录下来。因此,语言也就变为诉诸视觉而非诉诸听觉的媒介,较之于口语,更能流传久远。”因之,汉字“写”的大意是:人类走出树栖时代,住进象征文明的房子(宀)里,把转瞬即逝的思想记录下来,像筑巢孵卵(舄)的鹊鸟一样,一代代繁衍生命、传递薪火;文字的书写,是一种保存和传播人类文明的最好方式,它使文明传承能够在历史长河中获得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破壳而出的人类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书写的历史,这也是小学生背着代表文明累积的沉重的书包,终日忙于写字的缘由。
这一点你虽然没有看到,但你一定看到过喜鹊的黑白艺术照:身穿“白领子”、“黑礼服”的喜鹊,不正是“白纸黑字”的大写意么?近距离与喜鹊相处、心里揣着阴阳太极图的中国人,惯于在黑、白之间洞悉绚丽多彩的世界,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道至简。当我们从熊猫身上领悟“知白守黑”的哲学智慧时,不由得惊讶于“鹊体”行为艺术——原来,一切都是那么玄奥,一切又都是那么直白。
乌鸦
喜鹊承袭小篆时期文化专制的遗传基因,顺当地钳制了动物界舆论之后,我老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致认为:喜鹊叫喜,乌鸦叫丧。
从此,动物界百鸟朝凤,每日朝闻莺歌晚播燕舞,充耳皆是凤鸣喈喈、凰鸣啾啾、鸾鸣噰噰、鹊鸣唶唶……独不闻乌鸣哑哑;林间皆以莺之喜啭为标准,评选动物好声音,于是,“汉字动物园”里鹤不长唳,枭不凶叫,鸱不哀啸,鸦不悲啼……这还不够,造物主唯恐乌鸦多嘴,特地遣它去了“子虚乌有”、“黑不溜秋”的世界,罚它躲在黑夜的一角背诵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可是,乌鸦离“光明”毕竟有些远。在汉字的书写体系里,造字者借鉴“减法原理”,只挥一挥手就抹掉了“鸟”字里代表眼睛的那一“点”,与“奥卡玛剃刀定律(简单有效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埤雅》云:“(乌)全象鸟形,但不注其目睛,万类目睛皆黑,乌体全黑,远而不分别其睛也。”意即乌鸦一身缁衣,泼墨一般胡乱涂鸦世界,是一种看不到黑眼睛的鸟( )——我看不见你,你也看不见我——如此观照审视一番之后,就有了小篆中的“ (乌)”字:少了一个“看”点,多了一分世故。
支起世故的耳朵,乌鸦的歌声果不如喜鹊喳喳顺耳、莺啼婉转遂意,更不像鹦鹉八哥那样嘴甜会说人话;而且乌鸦老不识趣,专挑人类心情不好的时候吊嗓子,好像是吊丧。然而,缺乏功利意识的诗人并不理会这一套。十九世纪美国浪漫主义诗人爱伦·坡就把乌鸦的歌声当成了忘忧药。爱伦·坡深信,自己的前世一准是一只神秘的乌鸦。所以,在《乌鸦》一诗中,他把哀伤唱到了绝望的地步,幸好这时候乌鸦真的来了。那是1844年的冬天,一只乌鸦从敞开的窗子里降落在文艺女神的雕像上。这个时候,坡正沉浸在小爱人死去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它是安慰他而来的,坡这么想。因此,他把这只乌鸦称为“充满悲伤的幽灵”,一会儿又说它的名字叫做“永不复还”,身上还散发出熏香的气味。这与中国人通常嗅到的乌鸦的口臭,截然相反。
世上终有并不世故的人。一位不乏功利意识的犹太商人竟然格外钟爱乌鸦,他不仅用乌鸦做了店徽,而且还为这个世界奉献了一个名叫“寒鸦”的儿子。寒鸦性格内向,关起宇宙的大门与世隔绝,把写作当成唯一的精神寄托。在支离破碎、荒诞不经的暗夜里,寒鸦悲啼着,曲调曲折晦涩,旋律跌宕不羁,言此意彼的现代派象征手法常常让阅读者抓不住文字驾驭的缰绳,但阅读的困惑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的理解和敬重。为纪念这位独一无二的表现主义作家,1983年,在“寒鸦”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人们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卡夫卡”。在捷克语中,“卡夫卡”就是“寒鸦”。这是一只传说中“黑得不顾一切的鸟”,他刺破黑夜的遮蔽和惶恐,穿越扭曲变形的世相,试图找回公平做鸟的名义和权利。直到今天,他一直卑微地歌唱。
这歌声,恍恍惚惚飘落自成一统的“小楼”。在古老的寓言里,乌鸦的鸟嘴既然能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容器里取水,说明乌鸦的智商在禽类中相当高,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公平的待遇。但遗憾的是成也鸟嘴败也鸟嘴,由于天生的使命感和卓越的智慧,乌鸦总想把自己对灾难的感知预警给人类,可谁愿听那些鸟语呢?但凡应验之后,却又得背负不祥的恶名,总之挨骂是肯定的。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太愿意“跟着课本游绍兴”了——鲁迅,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他认为乌鸦凄厉刺耳的歌唱委实不合时宜;在黑暗如磐的世界,他偏偏要用这不合时宜的乌鸦嘴给旧制度唱挽歌。在小说《药》的结尾处,鲁迅说: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上个世纪初,不管是否有过面对面的“卡式”交谈,年龄相差仅两岁的鲁迅与卡夫卡,两位超级大师的灵魂一脉相承,想必神交已久。
在我记忆深处依然存活的老家门口那两棵老槐树的顶端,鹊巢和乌巢同时存在,它们是大树的两颗高端果实,仿佛是文明的两个侧面,一面是生和良好的愿望,一面是死和灰暗的咒语。如今,树毁鸟亡,卡夫卡、鲁迅、爱伦·坡也相约去了人生背光的那一面;我们作为生生不息的集体中的一分子,依然痛苦地留守在这貌似光鲜的这一面。在卡夫卡、鲁迅、爱伦·坡遗留给我们的荒诞、刻薄、惊悚的文学世界里,黑夜遮蔽了太阳,灰暗羁留了乌鸦;乌鸦成了黑暗的“使者”、光明的“他者”、天空的“黑客”、麻醉的“鸦片”……可是,想象力丰富的先民,偏偏从太阳身上找到了乌鸦的影子,从乌鸦身上找到了太阳的光斑。在神话中,日母(太阳女神)羲和每天要在“甘渊”给她十个长得不太干净利落的太阳儿子洗澡,可见古人在羿射九日之前,就发现了太阳身上有污点。在甘肃临洮出土的一只彩陶罐上,太阳纹的圆圈中明显绘有一个黑点,这证明青铜时代人们已观察到太阳黑子。俗语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在鸟类家族中,乌鸦黑得那么执着,正好用来表现太阳黑子,日中金乌的神话由此流传。也因此,古人认为,太阳就是一只大鸟,三足乌。人们发现,一些古代画家总要天真地在太阳上画一只蹲踞的乌鸦。“乌飞兔走”,说的就是月亮里的兔和太阳里的三足乌周而复始的运动状态。
世故和遮蔽,是喜鹊政治的主题思想。当科学遮蔽了神话,我们或许应该嘲笑古人的无知;而古人想必也会笑话我们非要用科学的态度去校正人文初始的呓语,譬如成人用“像”与“不像”批评儿童画,反而显得“成熟的浅薄”。一旦太阳与乌鸦建立起关联,崇拜太阳静穆的古代粉丝们自然会“爱屋及乌”,喜欢上乌鸦。据说在秦汉以前,中国人就没那么世故,认为乌鸦和喜鹊一样都是好鸟,而且乌鸦还是一只能预言吉祥的好鸟。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引《尚书传》说:“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董仲舒提到的“大赤乌”指的就是乌鸦。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乌鸦的恶名始于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山海经》。《山海经》预言,玄丹山上的乌鸦,飞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要灭亡。我个人认为,至少在“轴心时代”,由于多元价值观造就了“百家争鸣”的人文气象,乌鸦还没有被喜鹊之类遮蔽在主流声音之外(其时,“儒术”幸好也没“独尊”)。据说,当年听惯了声音各异的鸟鸣,主张“有教无类”、充满仁爱之心的孔子,曾与乌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回,孔子发现一只被射杀的乌鸦倒毙路边,便挖了个坑安葬了这只可怜的小鸟。孔子的义举感动了沉浸在悲痛中的鸦群。不久,孔子在从尼山回曲阜的路上遭遇歹徒袭击。危难之时,知恩图报的乌鸦上演了“格里菲斯式”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大群的乌鸦从天而降,勇猛地将歹人啄逃,护送孔子安全回府。这些神勇的乌鸦,被后人称为“素王”孔子的“三千乌鸦兵”。人可以世故,乌鸦并不世故。孔子去世后,这些“乌鸦兵”仍然不肯离开一生不得志的孔子,它们世世代代地守护在孔庙,形成“孔庙乌鸦成群,孔林乌鸦不栖”的怪异现象。
孔子厚爱乌鸦,当然不仅仅是出于交互式的感恩。学者们从儒学思想核心与乌鸦的慈孝形象中找到了内在联系。儒家认为,乌鸦是孝鸟、慈鸟,慈乌反哺是尽孝报本、感恩戴义,颇具道德价值,因此乌鸦又称德鸟。“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是儒家以动物教化人伦的一贯主张。《本草纲目》称:“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乌鸦是否真有反哺习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在“乌”与“孝”意义的接壤地带,却有现实的地名遗留随时备查。比如,浙江义乌的地名演变就封存了这个秘密。传说,义乌一带有一位叫颜乌的孝子,用双手挖土葬父,感动了乌鸦,乌鸦群起以嘴啄土相助,以致鸟嘴受伤,于是秦代就把这个地方叫作“乌伤”。汉代根据这一传说,改“乌伤”为“乌孝”。唐代以后干脆直呼其为“义乌”,以表彰慈孝义勇的乌鸦。在儒家看来,“百善孝为先”,孝是支撑国家道德大厦的核心。孔子说:“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句话,后来被收入蒙学教材《弟子规》,意思是说要先学会做人,然后才有余力学文。童话大王郑渊洁说:如今这个朴素的道理被弄反了,学了知识,考完试,已无余力慈孝、诚信和博爱了。
学识与慈孝,与诚信、博爱本应并行不悖,甚或相得益彰,就像金钱不应排斥良知,良知理应赢得富足一样;只因当今世界知识太多学不完,获取知识的渠道又太多,所以我们可以原谅现行教育体制缺失的关于个人德行的一环,这是个解不开的圈套。“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钱钟书:《论快乐》)乌鸦作为慈孝、诚信与博爱的符号,在中国一向与悲情、悲伤、悲痛相联系,喜鹊顾名思义便是可喜、可贺、可乐的代表,所以趋乐避苦的人们,讨厌、憎恶乌鸦也在情理之中。钱钟书说:“譬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以快乐与欢喜的名义张开的所有的翅膀,都如蜻蜓点水或惊鸿一瞥,只图轻浮地存留于片刻的感官满足,它们拒绝签收深沉的悲情、绵久的伤痛和莫名的诗愁,把这些劳什子都转发给了爱伦·坡、鲁迅、卡夫卡,以及张继、马致远们了,哪管得了乌鸦的鸦原本写作《尔雅》的“雅”(鸟同隹,古人云“长尾为鸟,短尾为隹”),或者“雅典”的雅和“典雅”的雅呢?这怨不得谁谁,一群“乌合之众”!——有宗庙没信仰,有组织没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