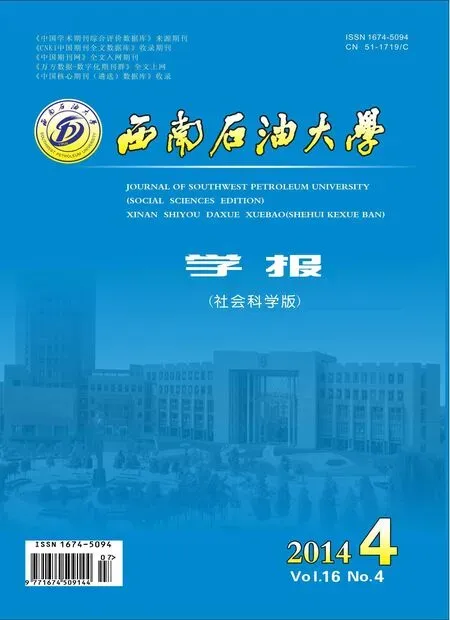论宗教教诲在罪犯改造中的效果及启示
——以中西方监狱宗教教诲比较为视角*
仲崇森
(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部,上海 201701)
论宗教教诲在罪犯改造中的效果及启示
——以中西方监狱宗教教诲比较为视角*
仲崇森
(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部,上海 201701)
在当今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背景下,有必要引进多种有价值的改造手段。宗教教诲因其蕴含的丰富改造资源和独特的改造视角,亟须得到挖掘。为弥补宗教积极因素在罪犯改造实务和理论上的空白,要以中西方宗教教诲历史演变的比较为视角,发掘我国近现代监狱存在的宗教教诲传统,并在了解西方监狱宗教教诲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将宗教教诲纳入到监狱管理制度中。
监狱;刑罚执行;宗教教诲;感化教育;罪犯改造
仲崇森.论宗教教诲在罪犯改造中的效果及启示——以中西方监狱宗教教诲比较为视角[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4):80-85.
监狱行刑是刑罚执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监狱法》开宗明义地指出:监狱行刑目的在于“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就目前来说,“我国监狱学界所达成的共识是:狱政管理、教育和劳动是中国监狱罪犯改造的三大基本手段”[1]。其中,教育改造方面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监狱改造方法发展、影响改造效果的一大因素,特别是思想道德教育层面的不完善,导致服刑人员出现外在满足、内在缺陷,宏观一致、微观失衡的局面①这里的外在、宏观指受刑人表面上的矫正成功、改造质量评估良好,内在、微观则指罪犯隐性上的、内在人格缺陷未弥补、罪恶感未消除、世界观未得以重建。,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构建多元化的人格改造体系问题。因为内在、微观始终属于人的精神世界改造领域,而宗教作为抽象观念的聚合体,更因其独特的终极理念和情感体验在人类精神领域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如今宗教研究也早已不是学术禁区,所以,在研究监狱行刑中的罪犯改造问题时,宗教教诲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视角。
1 感化、教育与宗教教诲
感化一词意义与教化相似,是指在罪犯改造过程中,通过对罪犯心灵施以影响,矫正其自身恶性和危险性,从而塑造全新的行为模式,实现改造的目标,即所谓的“教诲感化”。而宗教教诲则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德育范畴,其与教育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通过渐进的方式更新国民的思想境界、道德层次,而后者着重对受教育者灌输知识和训练生存技能。由此可见,在罪犯感化教育中,教诲居于优先地位,宗教教诲更因其蕴含的众多改造思想而处在优先地位,如果把感化比喻为“竖立在黑暗海洋上的一个灯塔”[2],那么宗教教诲就是灯塔上一道耀眼的光芒。
2 近现代中国监狱宗教教诲的概况
2.1 监狱宗教教诲的法律渊源
通过考察清末狱制改良到“中华民国”时期的监狱,不难发现宗教教诲在罪犯感化教育中的强势地位,具有代表性的立法规定包括以下几条:
首先,成文法典层面。由日本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主持起草的《大清监狱律草案》规定:“在监人若请就其所信宗派之教职者,受教礼或行宗教仪式,斟酌情形得许之。”这是第一次用法典形式对宗教教诲地位的肯定。“中华民国”二年司法部公布的《监狱规则》第6章第48条规定:“在监者一律施教诲。”另外,国民政府1935年颁布的《监狱法草案》和1946年颁布的《监狱行刑法》中也出现了类似规定。
其次,中央司法部的规章、指令层面。1915年,当时的司法部下令允许基督教在监狱布道。1917年司法部针对有教会函拟在京师第一监狱乘囚人休息之际敦请会员做德育演说等情形,指令认为“事属可行,应准照办,仍仰将嗣于讲演一切与该会随时商定,务臻完善,俾收实益”[3]。此外,1936年1月31日,司法行政部进一步发布新监训令,认可了监狱在周末邀请佛教团体或法师入监演讲的做法,但对演讲内容做了限定,并要求典狱长和教诲师在宗教活动时均应在场。
最后,在地方监狱章程和细则中,也出现了强调宗教教诲的现象。如《上海英国监狱章程》第39款规定:“于礼拜日、耶稣圣诞日、耶稣受难日、及大斋日、或感谢日,犯人惟用于作监狱内所必须之事。”[4]第42款至58款更是详细规定了教士、监狱牧师的资历、职责和任务。
2.2 监狱宗教教诲的实践及推行
在狱政中推行宗教教诲的实践承袭于清末狱制改良,得益于行刑理念从报复主义逐步向感化主义的过渡。在当时监狱改良运动的影响下,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些推行宗教教诲的新式监狱、模范监狱。
早在1912年,山东省浸礼教传教团就举行关于“西方国家的监狱和处罚方式”的布道,在他们的济南分会准备培训山东新的模范监狱的看守。1917年6月,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自愿向监狱管理方请求在罪犯作业的闲暇时间进行德育教诲,该请求得到批准并准许其每星期讲演一次。1920年,一名英国医学院的院长受司法部的推荐抵达沈阳,他已经在京师第一监狱进行了演讲,检察官坚信感化的作用,他允许英国人在奉天第一监狱中传播福音。在江苏省,20世纪20年代江苏监狱感化会派遣了和尚在监狱和县监中演讲。
监狱宗教教诲的地位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得到更大的提升。1935年7月,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监狱司注重宗教感化的效果,要求各新旧监狱查明“有无佛教团体到监演讲”,并考察其感化的效果。1935年又向各法院和监所发布训令,要求保障罪犯接受宗教生活的权利,比如,按期向其施行宗教教诲,即使罪犯要求延请牧师入监,监狱管理当局也不能拒绝其请求。当时学者郑耀焜在其《监狱改革声中论教化》一文中列举出入监演讲的群体分类,从中不难窥探宗教教诲的兴盛之状(见表1)。

表1:民国时期入监演讲邀请群体分类[5]
2.3 关于宗教教诲发展历程的简要评析
宗教教诲发端于西方,我国古代狱讼并无宗教文化的基因,之所以在近现代中国监狱出现推崇宗教教诲的现象,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是西学东渐的影响,来华的西方人和出洋中国人带来了西方的先进学术思想和理念,其中自然包括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历史渊源的宗教教诲;另一方面,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权确立之初便纷纷吸收西方国家的诸多现代化理论成果,藉此显示出与国际接轨的潮流,反映在监狱教诲上的一个特征即是:仿效西方监狱中的宗教计划或宗教服务,在国内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推行宗教教诲。
虽然教诲的效果尚存争议,但作为罪犯培育情感、慰藉精神的一种方式,它也显示出诸多积极因素:对于外籍犯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护,如严景耀在《北平监狱教诲与教育》一书中提到,自1922年4月7日京师第一监狱开始收押俄国罪犯,为保证其树立坚定的宗教信仰,监狱当局专门邀请北京东正教宗会司负责该类罪犯的宗教事务。对宗教教诲内容和范围的管制,如当时司法部对监狱道德教育教材的严格控制,监狱官员对宗教教诲方法和材料的要求,在狱政管理实践中,凡是涉及政治、危害监管秩序以及影响罪犯情绪的煽情式布道等,在当时均是被监狱管理方所禁止的。监狱作为矫正罪犯犯罪思想、心理和人格缺陷的场所,教诲的方式和内容必须经过监狱方的许可,否则改造效果在不规范的条件下将适得其反。
然而,我国毕竟缺乏西方原罪观和救赎观的宗教文化土壤,国人内心也未形成西方式的坚定的宗教信仰,这种“照葫芦画瓢”式的单纯模仿在实践中也显示出一些不足:第一,推行宗教教诲改造方法的监狱大都局限于新式监狱和省级监狱,比如京师第一监狱、河北第一监狱、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等,而地方监狱特别是县监仍未摆脱旧式监狱的陋习。第二,宗教教诲的形式主义倾向严重。表面上看,宗教教诲在感化教育理念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实际功效如何、罪犯是否实现了精神世界的更新、内心是否实现了真正的顿悟都无从得知,宗教教诲偏向于一种运动型的活动而缺乏长久性规划。第三,宗教教诲中以基督教和佛教教诲为主,其他宗教或教派,如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则涉及甚少。因此,如若在我国监狱改造手段中采纳宗教视角的罪犯改造方法,就必须对西方监狱宗教服务起源和现状有所了解。
3 西方监狱宗教教诲的起源和现状
宗教教诲在西方监狱被视为罪犯改造方法的一个基本途径,监狱牧师和教士向罪犯提供的宗教服务,也被看做是道德感化的核心。与中国缺乏宗教信仰的文化遗传不同的是,西方监狱宗教教诲的起源和发展始终根植于宗教伦理的环境中,并与社会大众的宗教情感相互印证,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监狱立法中尤为突出。
3.1 监狱宗教教诲的起源
原罪教义是基督教的重要基础教义,指人天生即是有罪的,这种原始和本源意义上的罪来自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的行为。正是因为人生而有罪,所以一生需要不断赎罪以实现最终的悔悟和自新。这种“原罪观”和“救赎观”使宗教的感化和忏悔具备合理性,普通人因为人性恶而必须不断救赎,更何况罪人,更需要在宗教教诲过程中进行罪恶的消除、灵魂的洗涤,最终实现“因信得救”的目的,否则就要受到神的审判,即“经过这种审判,善人将进入天堂享乐,恶人则堕入地狱受惩罚”[6]。既然监狱宗教教诲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亦是监狱发展的应有之义,“从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代开始,早期的基督教会(Christian Church)就同意为那些在其他情况下会被肢解或者杀死的犯罪人提供庇护。早在公元539年,教会的成员就认识到,会见监狱中的犯人是一种义务”[7]。
3.2 监狱宗教教诲的现状
综上所述,宗教是认识西方监狱发展的一条主线,监狱宗教教诲深深植根于宗教所蕴含的庞大的灵魂拯救、心灵自由的理论体系,即使在当今现代化程度发达的西方监狱中,“宗教教诲仍是狱内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监狱规定有专门接受宗教教诲的时间,并设有进行宗教教诲的专门设施”[8]。笔者主要阐述在宗教教诲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立法例。
首先,在人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法国监狱,宗教教诲被界定为对罪犯的精神帮助,《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五卷)在执行程序中甚至单设一节来规范罪犯的狱内宗教活动。一方面,罪犯参加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权利不容侵犯;另一方面,法律详细规定了神甫(教诲师)的职责和任务,如神甫可以自由确定工作时间,认为有必要时可随时同本教派的犯人谈话,甚至规定神甫和犯人的谈话不设看守且可以自由通信。
其次,在英国,监狱教诲师往往由牧师担任,法律将其归入监狱官员一章中,并且规定每个监狱必须任命监狱牧师,在适当的时候,牧师还可以帮助监狱长维护监内纪律和秩序。另外,“牧师必须每天在狱内布道一次。每逢礼拜日、耶稣受难日及圣诞节里得布道两次,他必须每天到医务室布道并且探望那些受到惩罚的犯人。牧师必须看望、劝诫那些刚入狱或将被释放的犯人,必须在他服刑期间经常探望每个犯人”[9]。英国1999年的《监狱规则》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监狱牧师提供宗教服务的具体内容。
最后,在矫正制度独具特色的加拿大,根据1992年的《矫正与有条件释放法》(CCRA)第101条的规定,加拿大矫正局向罪犯:(1)根据罪犯宗教信仰的不同,提供所需要的监狱牧师服务;(2)提供表达宗教虔诚的设施;(3)向罪犯提供宗教饮食;(4)提供与罪犯的宗教仪式有关的必需品。当然,犯人并不是被动接受这些宗教服务,在不妨碍矫正机关工作和其他人员安全的前提下,他们也享有佩戴宗教标志、订阅宗教书籍等权利。
由是而论,西方国家监狱宗教教诲不仅有丰厚的本土文化资源,而且宗教实践往往通过立法确定下来,在监狱牧师提供宗教服务、罪犯接受教诲的过程中,犯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格和精神层面的矫正,并且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恰好也内含在宗教导人向善的宗旨中。通过比较中西方监狱宗教教诲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西方宗教感化在监狱行刑中的独特功效。
4 监狱宗教教诲的矫正效果
在监狱服刑的罪犯类型多样,他们的犯罪原因、犯罪心理和行为方式表现各异,因此在改造实践中提出了个别化的改造方法。另外,罪犯的宗教信仰也存在差别,有的罪犯是无神论者,有的则建立了坚定的宗教信仰,有的则只是具有朴素的宗教情感。宗教教诲之所以在西方监狱备受尊崇,这与罪犯从小经受的宗教理念熏陶不无关系。因此,在罪犯误入监狱这一“歧途”后,宗教发挥的感化作用之大不言而喻。与之相反,我国素来存在政治上、文化上“大一统”的局面,宗教多而不一,有宗教而宗教信仰缺失,所以宗教教诲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在此讨论的矫正效果主要针对罪犯中的宗教信徒。
其一,通过建立和强化宗教信仰升华罪犯人格。对于新入监的罪犯而言,由于自身突然受到强制和隔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内心的痛苦和不安,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罪犯适应监管环境,甚至会造成罪犯精神崩溃、改造流于形式;而对罪犯实施宗教教诲,既能帮助罪犯调适心灵上的压抑和受挫感,确立人生希望,也有利于加强对改造工作的认同感。另外,“在宗教伦理中,爱往往被看成善的集中表现。这里的爱有着双重意义。它首先是对神或神圣的道的爱,其次是对他人的爱”[10]。罪犯之所以犯罪,原因之一就是主观上缺乏对他人之爱,缺乏对他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尊重,缺乏责任和关爱意识。而宗教强调的大爱表面看来遥不可及,其实与我们生活中的世俗之爱不谋而合,人人都可以形成“我爱人人、人人爱我”这一思想,对罪犯的宗教教诲,更能激发他们本身作为宗教信仰者爱人的潜意识,从而有助于培育罪犯的道德情感,促使他们努力向善,进而积极地接受改造。
其二,改造罪犯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基本需要包括生理、安全、社会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由于罪犯普遍追求物质享受或者精神上一时的刺激而排斥自我价值、人生目标狭隘,所以他们的需要层次低下。与之相反,宗教偏重于灵魂上的苦修,更多地强调精神上的磨炼,这与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是相互吻合的。宗教教诲对于罪犯改造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矫正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缺陷。
其三,有助于罪犯改造工作的顺利开展,保障监管秩序的规范稳定。宗教活动是神圣和严肃的,它一方面要求罪犯实现内心自律,另一方面要求他们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参加宗教活动。这样在向罪犯提供归属感的同时,增强了罪犯抵制冲动、控制自身需要的能力,因而能够保障罪犯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5 在我国监狱中推行宗教教诲的启示
马克思关于宗教有一著名论断:“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声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长久以来,宗教都与“精神麻痹”“迷信”“愚昧”等词眼联系在一起,监狱学理论和改造实践在此领域也是一片空白,遑论在罪犯感化中推行宗教教诲。然而,马克思在当时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强调宗教的欺骗性,而且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宗教有其复杂的、深层次的原因。作为一种在我国近现代和西方监狱中已被证明有价值和意义的改造方法,将宗教教诲纳入罪犯改造视角是我国建设文明化、人道化监狱的必然要求。在监狱中推行宗教教诲的实践,可以尝试从以下几点入手。
5.1 在立法层面保障罪犯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早在1955年的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就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其中第41条第1款规定:“如果监狱囚禁的信仰同一宗教囚犯达到一定人数,应指派或批准该宗教的合格代表一人。如果就囚犯人数而言,在条件恰当而又得到监狱当局许可的前提下,该代表应为专任。”第3款进而规定:“不得拒绝囚犯往访任一宗教的合格代表的权利。但如果囚犯不希望任何宗教代表前来实施教诲,此种态度亦应得到充分尊重。”第42条规定:“在可行范围之内,囚犯应准许参加监狱举行的宗教仪式并持有所属教派宗教、戒律和教义的书籍,从而满足其宗教生活的需要。”我国宪法也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然而,作为刑事执行法的主要组成部分,《监狱法》却未对罪犯的宗教信仰处遇作任何规定,罪犯的宗教信仰自由停留在抽象和理论层面。罪犯由于被国家强制隔离于社会之外,本来宗教信仰权利的行使就处于真空状态,再加上监狱法或行刑法的缺失,在罪犯中开展宗教活动更是空谈。所以,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在监狱法中规定专门保障服刑人员宗教信仰自由的措施,并且考虑将其纳入到教育改造一章中,从而保证对罪犯进行宗教教诲的合法性,这也是依法治监的时代要求。
5.2 将宗教教诲纳入到监狱管理制度中
现阶段罪犯教育改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教育改造方法单调、缺乏创新,长期以来的思想、文化、生产科技“三课”教育处在单一说教的模式中,监狱干警强制灌输而罪犯被动接受,双方关系更多体现出命令和服从。罪犯主动改造的积极性不高、参与性不强,这就必然导致教育改造质量的低下。实践需要我们探索新时期教育改造的新机制、引入新方法,对于监狱内有宗教信仰的罪犯而言,无疑可以将宗教教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矫治手段加以引进。第一,将宗教教诲纳入监狱矫正计划。学界一直呼吁实现监狱教育的社会化和人文化,“监狱教育只有实行社会化,才能充分利用和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提高教育改造的质量”[11],所以,应将宗教教诲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改造手段看待,具体指:采取“引进来”的方法,与社会团体(自然包括宗教组织)、高校学者、宗教人员建立“教育协作网”,招募宗教志愿人员进监提供宗教帮助,且定期进行帮教服务。然而,监管部门始终应审慎地看待宗教感化方法的作用,宗教教诲时间、地点、对象必须由监管部门规定,宗教教诲的教义也应经过监狱方的事先审查。第二,监狱要对新入监罪犯进行宗教登记。主要由罪犯主动报告其宗教信仰、表明其宗教身份并由监狱登记在册,宗教信仰一经登记不能轻易更改,如果以后罪犯想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应交由当地宗教教职人员和监狱共同审查。另外,允许登记的宗教应仅限于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合法性宗教。第三,在监狱图书馆资料中补充宗教经典书籍或以监狱宗教教诲为主题的文化著作。监狱图书馆作为供狱内警察和罪犯学习的固定场所,在监狱这一封闭式的、与外界思想文化交流存在障碍的空间内,发挥着仅有的“鼓舞智慧和心灵”的教育改造功能。为满足狱内有宗教信仰罪犯的需求,监狱图书馆馆藏文献应增加心理类、宗教类等文献资料。此外,可以考虑将图书馆作为狱内宗教活动的开展场所,即在不影响监狱正常秩序的前提下,根据监狱管理部门的安排,在图书馆举行宗教仪式、进行宗教辅导等。第四,侧重用宗教教诲改造外籍犯和少数民族犯。在“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过程中,一批外国人因触犯我国刑法而被依法判刑投入监狱进行改造,由于在思维习惯、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存在差异,对外籍犯的管理教育也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结合外籍犯普遍具有宗教信仰的特点,可以考虑在教育改造中对其进行宗教教诲,如可以将上海市青浦监狱外籍犯监区对信奉伊斯兰教罪犯人性化的改造方法作为参考,“监狱里发给每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囚犯一只专用的饭盒……监狱当局每当开斋节来临的前几日,就特地通知大伙房,为这些囚禁中的伊斯兰教徒提供方便”[12],可以说青浦监狱在尊重罪犯宗教饮食法律权方面做出了表率。而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由于信教人数所占的绝对比例远大于汉族,在少数民族犯改造中运用宗教教诲疏导罪犯心理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赞同陈士涵的观点,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监狱采取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教诲,比如,在具有悠久历史的藏传佛教传统下的藏区监狱,在矫正实践中可以考虑运用藏传佛教的教义和仪式对罪犯进行宗教教诲。第五,监管人员的人文精神的培育也是教育改造工作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监管人员一向被冠以“改造灵魂的工程师”的美誉,这就要求监狱干警树立尊重罪犯尊严、价值的人文关怀理念,要用富有人情味的改造手段去矫治在押人员的心理,最起码怀着一颗把服刑人当普通人看待的同情心。
6 结 语
我们引入一项新制度应通盘考虑该制度的由来、历史及功效,所以,监狱主管部门应先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先由该机构考察当前我国监狱内在押罪犯的宗教信仰分布、构成和保护状况,然后再进一步论证宗教教诲作为我国监狱改造方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最后才能考虑试点和推广的问题。进而言之,“罪犯宗教信仰处遇不可一蹴而就,宗教教诲应先在少数民族犯、宗教信仰者比较集中的监狱进行试点,待积累到一定经验后再逐步推广”[13]。对于宗教教诲而言,我们不能过多地纠缠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而忽视它在罪犯改造中的丰富资源,我国近现代监狱的宗教教诲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而且西方国家监狱宗教教诲的实践也已证明了这一改造方法的有效性,在当前教育改造手段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现实情况下,宗教教诲以其独特的人格和情感视角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和谐社会下“以人为本”的监狱管理理念在罪犯改造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1] 贾洛川. 监狱学基础理论[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47.
[2] 金兆銮. 感化录[M].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
[3] 张东平,胡建国. 论民国时期监狱的宗教教诲[J].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3):88.
[4] 麦林华. 上海监狱志[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783-784.
[5] 张东平. 近代中国监狱的感化教育研究[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22.
[6] 陈士涵.人格改造论[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754.
[7] 吴宗宪. 当代西方监狱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723.
[8] 邵明正,王云海. 第二十讲:西方国家的监狱制度[J].国外法学,1988(6):58.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外国监狱法规汇编: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109.
[10] 罗竹风. 宗教学概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32.
[11] 王斌. 对新时期监狱教育的思考[J]. 辽宁警专学报,2004(4):59.
[12] 耕才. 狱中洋囚——来自上海青浦监狱外籍犯监区的报告[J]. 检察风云,2000(12):69.
[13] 耿光明,李百超. 罪犯的宗教信仰处遇论略[J]. 现代法学,2000(4):53.
The Effects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Criminal Reforming——A Comparison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Prisons
ZHONG Chong-sen
(Graduate Depart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In today’s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ng modern civilized prisons,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a variety of effective educating and reforming methods. Religious education needs to be used in educating and reforming criminals because of its rich reformation resources and unique perspective of reformation. To make up for the inadequacy in both pracit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bout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religion in educating and reforming prisoners, we should explore the tradition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prison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y comparing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studies on the history and status quo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western prisons, we should finally bring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into China’s prison management system.
prison;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religious education; reformatory education; reformation of criminals
10.11885/j.issn.1674-5094.20137480
1674-5094(2014)04-00080-85
DF87
A
编 辑:余少成
编辑部网址:http://pxsy.cbpt.cnki.net/WKC/
2014-03-05
仲崇森(1990-),男(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监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