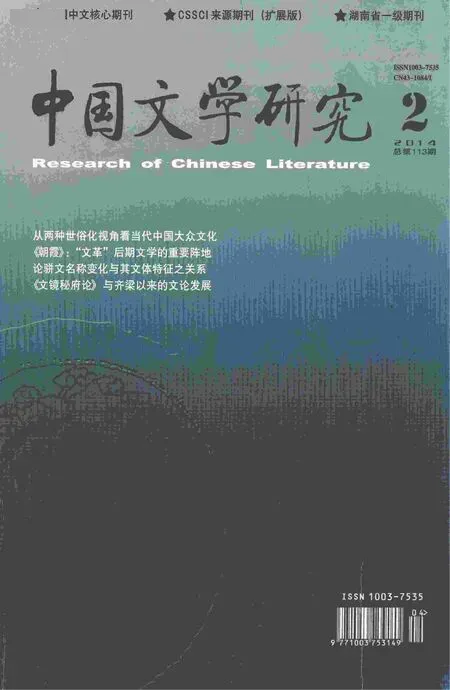王士祯“神韵”说时空蕴藉形成的历史脉络
刘新敖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8)
一、“神韵”说时空蕴藉的源起
“神韵”作为一个批评范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和理论积累过程,由人及画,由画及诗。从内涵来说,则经历了由指涉具体形象,到着重空间想象和时间蕴藉的过程。
神韵一词最早用来论人,《宋书·王敬弘传》中以“神韵冲淡,识宇标峻”形容王敬弘,本转引自宋顺帝诏书中语。作为艺术批评术语,“神韵”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我国六朝画论中,谢赫《古画品录》中即谓“神韵气力,不及前贤;精微谨细,有往过哲”。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也用“须神韵而后全”之语论画。如果说在谢赫的说明中,“神韵”与“气力”对应并举,还偏重于指艺术形象的神态、神情的话,宋元以后的南宗画派在讲神韵时则已经慢慢开始接近于由眼前的艺术形象所衍生的具有空间意蕴和时间蕴藉的艺术境界。所以,其画论强调应有含蓄深远,意余笔外的超妙意蕴。如苏轼论书,讲究“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远”与“外”,即发展成以空间思维来评价艺术创作、以空间形态来喻状艺术审美境界的一种方式。王世贞论画,推崇“契妙自然”的“逸品”均是例证。
以“韵”论诗,一般认为以北宋范温为最早。范温曰:“有余意谓之韵”,“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有“余意”才能“远”,“远”非具象所能指,而是诗歌的寓言蕴藉及其所表现的张力结构,是以空间想象的形式所彰显的审美内涵。较早将“神韵”一词作为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则见于明胡应麟《诗薮》。在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中,神韵作为诗歌内在品格的一项标准被使用:“诗之筋骨,犹木之根干也;肌肉,犹枝叶也;色泽神韵,犹花蕊也。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显然,在字意的使用上,胡应麟所云神韵与其后王士祯所言者并无本质区别。
“神韵”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古代传统批评理论的精华,逐渐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哲学基础,以空间的玄远和时间的蕴藉为特征,有其独特审美内涵的批评理论。“神韵”批评论的最早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钟嵘所著的《诗品》。王渔洋曾说:“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钟嵘《诗品》对“神韵”说的影响莫过于“滋味说”,钟嵘云:
五言句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钟嵘论诗,有破有立,以“味”论诗,正是其立之处。“滋味”说是中国古代辨味批评理论的典型代表,它认为诗歌的目的在于抒情,诗歌的审美风格在于有余味。“兴”就是一种“余味”,追求的乃是言外之旨,韵外之致的境界,所以,“兴”大大突破了“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传统观点,诗论从语言、形象的层面,突破到了“象”和“物”之外。诗歌以“兴”为主,加之以形式的创造手法,诸如健朗的风格、质朴有力的语言、美丽的辞藻,“味之者”便能达到“无极”之境,营造一种空间的玄远之境,“闻之者”在其中体味时间的沉淀,岁月静好和万宇有灵的审美境界便一一呈现。其中的时空蕴藉,以“直寻”的创作方式体现。《诗品序》开篇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对诗歌源于情,钟氏有更进一步的论述: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时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观,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横骨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意?非长歌何以聘其情?
在此,钟嵘详细列举了触发作者诗情的两类事物:自然界四时变化和社会的兴、衰、祸、福。其实,自然之物又何尝不是带有情感偏见的诗人眼中之物?钟氏强调诗之余味,“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将“兴”从一种写作手法转变为诗歌的一种基本特征:意在诗外。这种从诗外言诗,在诗歌的空间感觉和时间感中寻求美感的讲究“余味曲包”的审美风格被钟嵘加以强化,对中国的抒情诗创作和批评理论的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钟氏认为,有“滋味”的诗歌缘于“直寻”式的创作,他在《诗品序》里这样描述“直寻”:
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钟氏列举大量“古今胜语”,标举“直寻”之说。“直寻”即不假思索,不经理性推敲,凭心中涌出的感受自然吐露出来,不事人工雕饰,直寻所产生的作品往往朴实无华,却又不失其真,滋味无穷。通过审美直观构建的审美形象,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也更容易吸引读者参与其中。“直寻”的这种特征和“神韵”所言的“伫兴而就”不无密切关系。
二、“神韵”说时空蕴藉的确立
唐代是神韵诗创作的繁荣时期,这在历代批评家的文论里得到充分反映。中唐诗人皎然无疑在“神韵”理论的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皎然在批评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首先是其“文外之旨”之说:
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观文字,盖诗道之极也。
所谓“文外之旨”,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高手”之诗,能于朴素的语言之外见出作者之意,这种作者之意往往并不直接由于语言文字体现,“不观文字”即是使具象淡化,而成为一种充满生机的空间想象画面的过程,当然,如此诗作,只有“高手”才能完成。这正是司空图“象外之象”的先声。皎然以十九字来概括文章风味,“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体风味尽矣。”其中与神韵有关的有:
情:缘境不尽曰情。
意:立意磐泊曰意。
静:非如松风未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
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
由钟嵘的“兴”到皎然的“情”意味着“神韵”理论的长足发展。钟氏认为“文有尽而意有余,曰兴”,而皎然更进一步,在文与意之间,有一种或现实或虚构的“境”作为审美的中介而存在,诗人围绕“境”而“立意磐泊”,于是能生“意”。至于“静”与“远”,则是意中之静与远,是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一种“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与物相契合,物我两忘的超远境界。所以皎然之“境”,正是以创造空间和时间感为目的的。王渔洋于顺治十三年提出的“谈艺四言”,即典、远、偕、丽便深受皎然的影响。而对于这种时空感的创造方法,皎然则说:“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友,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自然”的诗,情性应真,而且最好不要于词彩之中见出人工雕饰的痕迹。王渔洋其后推崇自然、清远的山水诗可以说和皎然的理论一脉相承。
“神韵”批评发展史上,唐代司空图可谓集大成者之一。他对其后的严羽和王士祯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味外之味的论调始终贯穿于司空图的全部诗论中。不妨将他的著名论著引之如下:
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醋,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盐,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既知味外之旨矣。
味外之旨并非司空图首创,钟嵘即曾有“文有尽而意有余曰兴”之说,皎然《诗式》亦有“文外之旨”的说法。但司空图却有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味”是和“象外之象”联系在一起的。《与极蒲书》中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实际上是对味外之味的补充。《诗品》二十四则诚然不拘一格,但都未脱离味外之味,味外之味并非来自眼前的景和象,而是在主体情思和眼前景象交融,形成的亦真亦幻的艺术境界。“象外之象”之说,进一步明确了具体形象到想象的空间形象的构建的路径。可见,司空图味外之味关键在于诗境中“景”与“象”的处理,也即在于空间感的营造,及其中对于人生时光之境体味的深度。
在诗境中,司空图注意捕捉景物中的静趣和细微现象,并将其总结为“冲淡”,作为一品列入《诗品》中。“应该说,《诗品》的美学范畴是多样的,具见作者能博采兼收;然而在多样范畴中,基本内容,亦即诗人的美学思想,仍自可见:突出雄浑、冲淡二品。”《诗品》雄浑与冲淡代表着不同的两种审美类型,雄浑是元气于中而发之于外,冲淡则是在于守素持静的朴素之美,且看司空图的描述: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冲淡的妙处是能于无形之中默识宇宙之妙,其核心在静默淡泊,得意而忘形。“冲淡”是对于人生的领悟,对时间的参透,将人生之“动”与时间之“静”的结合,从而在诗的空间之境中,使时间停滞,使读诗者在这种玄远之境中,体味静默之美,得到人生之思。
《诗品》中,涉及“冲淡”的地方颇多,《典雅》中“人淡如菊”,《冼炼》中“体素储洁”,《清奇》中“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均道出司空图对冲淡的偏爱。这对王士祯的影响非同小可:
司空表圣作诗品,凡二十四品,有谓“冲淡”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希。”有谓“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者,曰:“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是品之上者。
司空图谓冲淡一类品格,都是超越现实,在隐逸旷达的时空感之中追求“至味”,这种审美风格无不渗透时代风格,这正是神韵派的特点所在。尽管司空图的论述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但它以时空感觉喻诗的理论方法,无不和中国传统的哲学和审美方式息息相关,对以后神韵批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明理学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神韵批评理论的发展,直到严羽《沧浪诗话》的问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严羽为了批评宋诗学古的弊端而提出自己的理论。严沧浪认为,学古应重在形貌风格上,故创以禅喻诗之说,而以禅喻诗的诀窍在于“妙悟”: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惟悟乃当行,乃为本色。
参禅重在妙悟,作诗亦如此。“悟”是一种创作心态,更是通达时空之感的路径。作者灵感突发,超越严密的逻辑思维状态,瞬间领悟诗之要旨。严沧浪借妙悟批评过去人们吟诗总是喜好堆砌学问,阐发哲理,而忽略诗歌本质。孟浩然作诗出于韩退之之上,根源在于孟襄阳作诗是“伫兴而就”,故“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也即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妙悟呢?严羽说: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兴趣是妙悟的途径。所谓兴趣,即指诗人由于受到自然事物的触发,而情感生动,诗兴勃发,这正是妙悟前期准备阶段的特征。而后,“无迹可求”,突破形式局限,营造“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时空之境,严沧浪以“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形容在诗境空间中的形象感,脱离了眼前具象而与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触手可及却又难以捉摸,因此,让人流连忘返,有余音绕梁之感。严羽认为,诗的风格可以分为两类:“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对二者,王小舒说:“‘沉着痛快’相当于司空图的‘雄浑’,‘优游不迫’则相当于司空氏的‘冲淡’,二者都可以从兴趣导入。”沧浪论诗,人和自然和谐一致,含蓄淡远,空间形式和时空蕴藉结合、自饶韵味的审美风格仍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不仅继承了唐代以来的‘神韵’理论,也和王士祯的‘神韵’论更加接近了一步。正如吴调公所说:“严羽的《沧浪诗话》有看中司空图的可能”,“严羽《诗话》是司空图诗论的后劲。”其后王士祯对严羽兴趣之说推崇备至:“严沧浪论诗,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又‘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云云,皆发前人未发之秘。”严羽对“神韵”批评论的贡献可见一斑。
三、王士祯“神韵”说时空蕴藉的形成
王士祯言诗标举“神韵”。“神韵”要求诗歌含蓄悠远、富于空间感,充满时间蕴藉,使形象脱离具象层面,消融于意蕴之中,难以指实,而又能令人涵咏不尽。王士祯的“神韵”说,从理论渊源来讲,是对钟嵘、司空图诸人诗论的继承和发展。
“神韵”批评的雏形最初见于王渔洋步入诗坛初期,于顺治十三年提出的“典、远、谐、丽”,即“谈艺四言”。王士祯在《丙申诗序》中说:

诗歌要“典”,强调广泛地向传统典籍学习,文举六经廿一史,诗则三百篇以下,兼容包蓄,不拘一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字“远”,它不仅是对传统神韵理论的继承,而且传达出新的理论信息。从字面看渔洋的解释,他推崇的是言在意外的表达方式,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韵味,但如果结合王渔洋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远”字的真正内涵在于和实际生活保持一定距离。所以,远既是一种艺术手法,更主要地体现为一种审美态度,通过“远”的艺术手法,可以既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受,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生活的超越,这标示着一种新的审美态度、创作方向,值得玩味。“远”是渔洋的生活态度,是诗意的生存方式,是与实际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如此,诗人足以反观自我,体验人生。
体现在艺术中,则是一种将人的思绪引向遥远时间和空间画面之外的深长含蓄的意味。
“远”字原则的提出,开启了王士祯神韵批评的先声,也奠定了其“神韵”论时空蕴藉的基础。
于创作而言,王士祯亦如前贤,强调“神韵”应“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乃是与传统诗论的时空意识一致,追求诗歌之“空”与“韵”。王士祯钟爱山水诗,即是例证,其所标举“神韵”之诗,也大多是山水诗。他在《东渚诗集序》中说:“夫诗之为物,恒与山泽近,与市朝远。观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大约得江山之助,写田园之趣者什居六七。”因此这些诗皆清词丽句,韵味悠长。王士祯推崇山水诗,因在山水自然境界之中,能保持人和情之“远”,在空间和时间距离中,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来思考、体味一切。于此,诗人需会思考,因此,学诗乃是前提。王士祯认为,学诗应从名家入手,做诗应该讲究根底和兴会。在这里王士祯无疑深受神韵理论的前辈影响。诗歌固然要“无迹可求”,但如果要达到大家的境界,却最好要有丰富的积累,从名家开始学诗。王士祯云:学古人勿袭形橅,正当寻其文外独绝处。学古人名句并非字句照搬,而是能“寻其文外独绝处”,将古人之“韵”化为自己之“味”,在其中揣摩古人空间想象和时间蕴藉的创作技巧。对诗法的追求不是对诗歌的约束,相反是诗有“神韵”之妙的必然途径。没有诗法,又如何能来王士祯所描绘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时空之境呢?只有对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法”已经内化为诗人的能力素质,才谈得上毫无碍滞地传达出内心的审美体验,才能使具象虚化为想象空间,达到”入神“的境界。
王士祯不仅讲究作诗要有诗法,同时认为根底和兴会不可偏废。根底源于学问,是学力,兴会则和性情有关,二者皆不可偏废:
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底也。根底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於斯二者兼之,又翰以风骨,润以丹青,谐以金石,故能衔华佩宝,大放厥词,自成一家。
所以,诗之“虚空”并非无根之稽谈,而来自于诗人深厚的功底,对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所以,由眼前之景而外旋的形成的空间形象之感和其中的时间蕴藉,既是“兴会”所至,归根结底,乃是诗人思想情感之精华,所以“空”而不“虚”,历久而弥新。
于审美风格而言,王士祯追求清远冲淡的时空之境。在审美风格论上,渔洋山人受中国传统批评理论的影响同样突出,在他的论著中,常能见出钟嵘、皎然、司空图、严羽等人的影子。他在《唐贤三昧集序》中说:
严沧浪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味在咸酸之外。”康熙戊辰(二十七年)春杪,目取开元、天宝篇什读之,于二家之言别有会心,承其尤隽永超旨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厘为三卷。
王士祯对严沧浪、司空图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将“其尤隽永超旨者”作为选取诗集的标准,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总结发展了前人的理论。王士祯还说:“表圣论诗,有二十四诗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境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他又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选出“冲淡”、“自然”、“清奇”三品,认为三者“是品之最上”。诸此种种,王士祯在将传统诗论的虚空感和时间感传承得恰当好处。
王士祯亦以味论诗,“味”是“神韵”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初看未见,愈久不忘”的审美风格,这和他一直所标举的“古淡”风格是一致的。是由空间形式感和时间蕴藉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意义空间。
从钟嵘“滋味”经司空图“味外之味”再到王士祯之“味”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审美风格论中,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文外之旨”,超越之态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主线,突出的不外乎是诗歌在外旋的时空机制中的审美韵味。
〔1〕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清)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7〕郭绍虞.诗品集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吴调公.神韵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9〕(唐)司空图.诗品[M〕.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清)王士祯撰,袁世硕主编.王士祯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
〔11〕(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2〕王小舒.神韵诗学论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3〕(清)王士祯著,李毓芙选注.王渔洋诗文选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