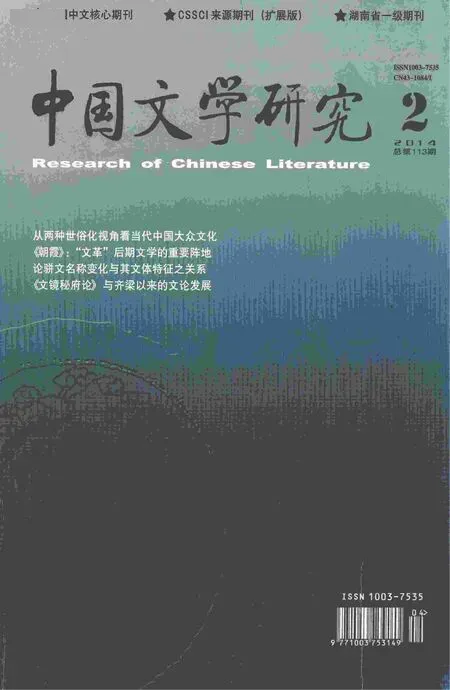袁可嘉与新诗现代化
蒋洪新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著名诗人、评论家袁可嘉先生在1988年8月写下《茫茫》一首诗,诗中写道:“生也茫茫,死也茫茫,宇宙洪荒,我将何往?我将何往?地狱?天堂?我将何往?火化?水葬?何处我来,何处我往,青山绿水,皆我故乡。”这首二十年前写的诗如今似乎在冥冥之中变为谶语。他晚年与家人团聚美国,于2008年11月8日在美国去世,但他的诗文没有国界,所谓“青山绿水,皆我故乡”也。
大凡与袁可嘉先生同时代的许多前辈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他们早岁因战争而颠沛流离,解放后经历多次政治运动而受到创伤。袁先生在七十岁时整理出版了文集《半个世纪的脚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其中回忆自己大半生涯时写道“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也进入了古稀之年,回顾一步步走过来的脚印,心情是酸甜苦辣,四味俱全的。”他一生的确命运多舛、困珂屯蹇,但他对诗歌的热爱和学术的探索终生不止。
袁可嘉先生于1921年9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六塘头袁家村(现为慈溪市崇寿镇大袁家村),幼时受其兄影响,爱好文学。在中学阶段他爱好语文和英语,与同学办壁报练习创作。他的第一首习作《死》发表在1941年7月重庆的《中央日报》,悼念重庆大轰炸中的死难者。1941年秋天,考入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在这里有一批著名诗人、作家和教授如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叶公超、冯至和李广田等。那时他的人生道路已经明确,他要以他们为楷模,立志做一位作家兼学者。入大学后他与爱好文学的同学一起办名为《耕耘》(双周刊)壁报,丰富校园生活和练习写作。他的诗歌《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被冯至看中登载在《生活周报》副刊,后来被香港大公报1943年7月7日转载。这首诗可看出初出茅庐青年诗人袁可嘉的锐气和才华,诗中有云:
我们——新中国的轻骑兵
沉重地驮载着世纪的灾难
曾久久抑郁在霉烂的叹息里
在惨白的默默里
罪恶的黑手,娇纵地
为我们增订一页页痛楚的记忆
多少年,我们躁急地等待第一声出击。
终于有一天
(那在历史上嵌稳了不朽的日子)
一支复仇的火令闪过北国七月的蓝空
我们狂笑中噙着眼泪
向风暴,催动我们骁勇的桃花骑。
如同该首诗所说,年轻的袁可嘉的确像“新中国的轻骑兵”,当时家国灾难深重,但他在这些痛楚的记忆里顽强出击,就像当年的英国诗人济慈那样在诗王国里纵马驰骋。大学期间,他的诗歌兴趣逐步从浪漫派转向现代派,他评述说:“我最初喜爱英国浪漫主义和徐志摩的诗,1942年以后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卞之琳的《十年诗抄》和冯至的《十四行集》,觉得现代派诗另有天地,更切近现代人的生活,兴趣就逐渐转移。我学习他们的象征手法和机智笔触,力求把现实、象征和机智三种因素结合起来,使诗篇带上硬朗的理性色彩。”与此同时,他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T.S.艾略特、叶芝、奥登、里尔克等人作品,感觉到现代派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为口语化,更有现代味。因此,他说:“从此,我就一头扎进现代派文学中去了。”
在1946至1948年,袁可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任助教,在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和冯至等主编的报刊上,发表了新诗20余首和以论新诗现代化为总标题的一系列评论文字,介绍西方现代派,批评当时新诗存在的弊病,倡导新诗走“现实、象征和玄学(指幽默机智)相综合的道路”。他的系统诗学观点后来成为“九叶派”主要主张。
这一系列的文章后来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虽然是针对当时中国诗坛争论的问题,但于今看来对我们的文艺建设仍有启发意义。首先,他厘清新诗“现代化”的意义,许多人开始以为新诗“现代化”等同于新诗“西洋化”。袁可嘉指出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但决无理由把“现代化”与“西洋化”混而为一。从最表面的意义说,“现代化”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指空间上的变易;新诗之不必或不可能“西洋化”正如这个空间不是也不可能变为那个空间,而新诗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鉴于此,他提出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依据。
诗歌必须“返回本体”。袁可嘉提出这个观点与当时在国统区文艺界所流行的文学观相左,那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文学被视为阶级斗争工具、文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他毫不避讳提出“人民文学”是“人的文学”一部分的观点,认为当时文学主潮逐渐脱离文学本身价值和独特传统,有沦为政治斗争和宣传的工具。因此,他提出:“当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人的作业相对照时,‘人的文学’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他这样说的理由是:文学活动有别于他种活动,因为他有着先天赋予的艺术性质和特性。文学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关系并非隶属关系,而是部分与部分的平行关系。文学完成作者所想使它完成的使命或作用必须通过艺术。他在《我的文学观》一文中写道:“再就文学作品是一种文字艺术说,文学第一是艺术,第二是艺术,第三还是艺术。”在《诗底道路》一文用诗意的语言来描述诗与现实的关系:“把心抛出去,交给风,交给雨,却永远不让风雨漂白去自己的标记,它面向现实,深入现实,但不粘于现实,现实真象一条清浊交混的大河流,我们不能想象跳得进去而跳不出来的游泳者。”这里可以清楚发现,袁可嘉所主张的诗歌“本体论”,并不是躲进艺术的象牙塔,与现实绝缘,而是深入现实,但不局限于现实,通过艺术的手段从中升华。
新诗戏剧化。中国新诗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师法英美浪漫诗,后来由于许多出现诗的情绪感伤和政治感伤,诗显得浮浅乏力,袁可嘉在《新诗戏剧化》一文指出新诗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方面的毛病:“由于这个转化过程的欠缺,新诗的毛病表现为平行的两种: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表现情感的则沦为感伤的,两者都只是自我描写,都不足以说服读者或感动他人。”那么,如何使这些意志和情感转化为诗的经验,袁可嘉借鉴英美现代诗的表现手法,提出他的新诗戏剧化观点:其一,尽量避免直截了当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感,戏剧效果的第一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表现在现代诗里,第三人称的单数复数有普遍地代替第一人称单数复数的倾向。其二,比较内向的作者往往努力探索自己的内心,把思想感觉的波动借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而得到表现的。比较外向的作者通过心理的了解把诗作的对象搬上纸面,利用诗人的机智,聪明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而诗人对处理对象的同情、厌恶、仇恨、讽刺都只从语气及比喻得部分表现,而从不坦然裸露。前种类型的诗往往沉潜深厚,具有静止的雕像美,以德国诗人里尔克为代表;后种类型的诗活泼广泛,具有机动的流体美,以英国诗人奥顿为代表。
新传统的探询。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诗人倡导融过去与现代为一体的诗歌道路,这些思想无疑对青年袁可嘉的诗学观颇有影响。袁可嘉在《新诗现代化》一文中指出现代诗歌都显出高度综合的性质。这种综合性质与他所主张新综合传统是密切相关的,“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为此,现代诗人就是要把握现代诗的综合传统。他提醒人们注意综合概念的内在含义,他在《综合与混合――真假艺术底分野》一文中分析说:“这儿所谓‘综合’显然包含两重意义:一是通常对于某一特定作品形成过程的描写;二是泛指突出于许多可能倾向中的有代表性的趋势”。他区分“综合”和“混合”在传统继承中的差异,综合是内生的,混合却是外附的;在现代性综合性的极丰富的含义里有一种是社会意义;综合的作品(不问是西洋的或中国的,古代的或现代的)重在诸种意义的融合无间中把社会意义突出来,从有机配合取得雄浑力量;综合是有机的统一的,混合则是支离的,破碎的;综合所求是最大量的意识活动,混合的目的在它最小量的获得。这些话对目前的诗歌创作仍有借鉴意义。袁可嘉对他四十年代所提出的“新诗现代化”后来在九十年代所出版的《半个世纪的脚印》自序中有很好的概括:“这种‘现代化’的实质,说得简单一点,无非是两条。第一,在思想倾向上,既坚持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主张,又保留书写个人心绪的自由,而且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强调社会性与个人性、反映论与表现论的有机统一;这就使我们与西方现代派和旧式学院派有区别,与单纯强调社会功能的流派也有区别。第二,在诗艺上,要求发挥形象思维的特点,追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注重象征和联想,让幻想与现实交织渗透,强调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的结合。”这里可以看出,袁可嘉所主张的“新诗现代化”是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艺术主张,同时更重要的是结合了中国的现实与传统,也就是他提倡的“中国现代主义”的诗学道路。
进入新时期以后,袁可嘉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随后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对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研究与译介工作,他辛勤耕耘,撰写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评论和译介西方现代派的最丰硕的成果,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主编(与董衡巽、郑克鲁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5);《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下)主编(与叶廷芳等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主编(与绿原等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这在中国封闭那么多年之后,从袁可嘉译介的作品里,中国文艺界第一次认识到西方现代派的多种表现手法如“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有些作家借鉴这些技巧用于自己的创作中去。
从理论上对西方现代主义给予了总体认识和把握于我们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建国以后,我国文艺界与学术界由于受左倾思潮影响一直将西方现代派视为毒草,列为批判的对象,更没有人对它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认识。袁可嘉自1978年以来,在中国勇敢地向这一学术禁区发起挑战,并对中西方关于这一领域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有根据的看法。首先,关于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边界线问题。由于现代主义主义思潮影响广泛,内容复杂,对它的起迄期限的界定学术界聚讼纷纭,袁可嘉避免给它下简洁的定义,而是从它的起迄期限、思想和艺术特征、它与其他近似的文艺思潮的比较来勾勒它的边界线。他把现代主义文学的起迄期在1890-1950年间,即从法国象征派(1886)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50年以后的新流派划入后现代主义文学,以便与正统的现代主义相区别,虽说这两者之间又有相当密切的联系。现代主义和其他相近的文艺思潮(如先锋派、颓废派、象征派、广义的现代文学、唯美派等)相比较,以求明确现代派在整个现代文学中的位置。他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孕育期(1840-1890),从唯美主义到早期象征主义,即从爱伦·坡和波德莱尔到兰波、马拉美;肇始期(1890-1910),即后象征主义在欧美扩散的时期;鼎盛期(1910-1930),各种流派纷呈的年代,如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都崛起于这一期间,20年代则是颠峰,衰退期(1930-1950),由于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欧美出现左倾文学,现代主义阵营开始分化,逐渐走向衰退,到40年代为存在主义文学所代替。袁可嘉这种分析与划分虽不说精确到位,但至少是饱读西方现代派许多著作与评论,经过自己思考得来的看法。其次,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局限和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碰到西方现代派这一敏感话题往往闭若寒蝉,更不敢肯定其成就。袁可嘉经过全面细致的清理与分析之后,对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它所暴露的严重局限以及它所带来的复杂问题,进行客观的梳理和比较。他认为现代派文学的主要成就首先是它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危机意识,这对我们认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益的。“所谓危机意识不仅包括经济危机、信仰危机、价值危机等等,更根本的是在人类四个基本关系方面—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产生的脱节和扭曲;所谓变革意识是指在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剧烈变化。”对现代主义的表现人类四个基本关系的深刻分析,西方学术界还没有如此展开论证,这是袁可嘉在理论上一大重要贡献,他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为指导,经过自己理论提炼而得出的结论。袁可嘉的分析是以辨正法的观点来看现代派的局限,“现代派作家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使他们看不到出路,只能提出反传统、反理性的主张,散布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情绪。在意识变革方面也有作过了头的地方。在一个具体作品里,这种成就和局限往往是混淆在一起的,我们只能肯定其成就,批判其局限,而不能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何况具体作家和作品的情况又千差万别,需要区别对待。”他除了理论上进行很好梳理和把握之外,他还深入到现代主义每个流派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进行阐释,将这些流派的文本的代表作组织人进行翻译或者节译,让国人了解现代主义文学的风貌,给中国文坛注入新鲜气息。再次,袁可嘉不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分析和解读,而且还讨论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的关系,总结七十五来我国译介和借鉴现代派文学的成绩与教训。他概括分析了:“五四前后(1915-1924)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和胡适等作家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和意象主义的译介评论;30年代(1925-1937)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引进,施蛰存、刘呐鸥等对日本新感觉小说的仿效,曹禺、洪深等对奥尼尔戏剧手法的吸收;40年代西南联大师生,主要是冯至、卞之琳、燕卜荪以及后来所谓九叶诗人等对里尔克、瓦雷里、叶芝、奥登、纪德等翻译和述评及其所受的影响;60年代对现代派的猛烈批判和全盘否定,70、80年代对现代派的重新引进和在创作界、理论界产生的影响。”例如他在《西方现代派与九叶诗人》一文中指出九叶诗人在中国新诗发展的独特色彩,其独特的地方在他看来:“独特在他们既坚持了三十年代新诗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主张,又保留了抒写个人心绪波澜的自由,而且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既继承了民族诗歌(包括新诗本身)的优秀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现代诗艺,努力尝试走新旧贯通、中西结合的道路,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在九叶诗人中间,既有共同的创作倾向,又有各人鲜明风格。简言之,一向被许多人认为水火不容的事物——反映论与表现论,社会性与个人性,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他们那里得到了较好的虽然远不是完美的结合。”经过袁可嘉这些有根有据、辩证客观的分析,九叶派诗人在中国诗坛得到了应有的地位。
袁可嘉对中国新诗的贡献不仅表现在自己的新诗创作、对西方现代新诗评述,而且还翻译了大量英美的诗歌。他出版的翻译诗集英译中有:《天真之歌·布莱克诗选》(与查良铮等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米列诗选》(新文艺出版社,1957),《彭斯诗抄》(新文艺出版社,1959;上海译文出版社增订版,1986),《英国宪章派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60;修订版,1984),《美国歌谣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将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有:陈其通的《万水千山》(外文出版社,1957),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外文出版社,1957)。他还将英美作家的文论翻译成中文:《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上、下)(主编)(作家出版社,1961),《试论独创性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袁可嘉是诗人与评论家,他的许多译诗可谓形神皆备,手下别有炉锤。我们以他翻译的美国现代著名诗人威廉斯的一首短诗为例:

诗人威廉斯自称这首诗有欢快的节奏,原诗交替使用两个重音和一个重音。译诗充分迻译了原诗不胜惊喜的口吻“那么多东西/依仗/一辆红色/手推车……”同时再现色彩明丽的画面:以红色的车为中心,配以晶亮的雨水和白色的小鸡。译诗以汉诗的两顿和一顿的交替来对应原诗中两个重音和一个重音。袁可嘉在大量翻译实践基础上,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译诗理论。例如,他在《关于英诗汉译的几点随想》一文中提醒译者在采用“顿”的方法来译格律诗时,要防止绝对化,切勿胶柱鼓瑟。他说:“我以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宽严有度,不作绝对化的追求,在影响译文流畅或风格表现时,宁可在形式上做点让步。”他告诫译诗者要避免两种作法:一是语言一般化,即“以平板的语言追踪原诗的字面,既不考虑一般诗歌语言的应有特点,也不照顾个别诗人的语言特色,结果既不能保护原诗的真正面貌,更谈不上传出原诗的神味。”二是语言的“民族化”,把外国诗歌汉译成整齐划一的中国五言、七言或者中国民歌,这样虽有诗意,但经常导致削足适履,矛盾重重。他举例说,“译的是美国歌谣,那又怎样把美国的民族性‘民族化’过来呢?如果硬要民族化,便是改成中国化的东西了,结果作品不伦不类,甚至庸俗。经过自己多年的译诗实践,袁可嘉先生深有体会地说:“文学翻译是一种很特殊的行业。就语言说,它要求熟谙本国语(母语)和外国语(外语)以及它们背后的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涉及广泛的文化修养;在文学内部,翻译又居于创作与研究之间,既要有创作家的创造性,又不可离开原作;既要有研究家的深入理解,又不能故弄玄虚。它经常处于创造与模仿,本能与规律的张力之间。要在这些矛盾之间保持平衡,掌握分寸,是相当困难的事。有些译者做得较好,全仗他们的悟性与功夫。悟性部分是天生的,同样需要通过治学来培养,功夫则全赖勤奋刻苦。一个好的文学翻译家应当是通晓母语和外语,熟悉中外历史文化,有较高创造才能和研究功夫的作家兼学者。”袁可嘉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位集诗人、学者和翻译家为一体,故他翻译的选材、译文的艺术以及相关的研究都是非同凡响的。可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算是一个业余译者。”
1946年青年诗人袁可嘉发表《沉钟》,诗中写道“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把波浪掷给大海,/把无垠还诸苍穹,/我是沉寂的洪钟,/沉寂如蓝色凝冻;/生命脱蒂于苦痛,/苦痛任死寂煎烘,/我是锈绿的洪钟,/收容八方的野风。”这首诗抒发了当时年仅25岁青年诗人的历史沧桑感,他将自己喻为沉寂的洪钟,置于横穿亘古的时空之中。如今老诗人仙逝于美国,我们阅读他的诗文,缅怀他为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贡献,依然感到他如同洪钟,永恒长鸣,令我们奋发前进。
〔注释〕
①袁可嘉:“关于英诗汉译的几点随想”,见《中国翻译》1989年第5期。
〔1〕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3〕袁可嘉.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4〕袁可嘉.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袁可嘉卷 驶向拜占庭〔M〕.北京:工人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