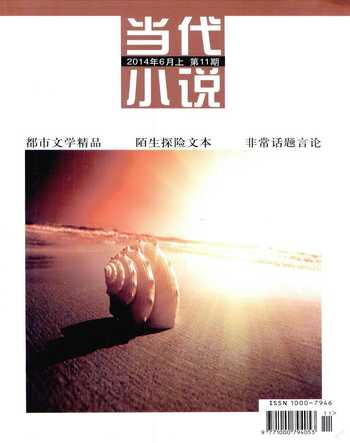追寻
符浩勇
傍晚,连阴天终于放晴了。要紧的是,他的心情已经变好。窗外,地面上似乎不那么泥泞了。
为什么昨天傍晚没有在公共汽车上看见那一张动人的脸呢?好像失去了一张珍爱的画。那么,今天能不能在汽车上碰到她?那个年纪已经不轻、脸子也不俏丽的陌生女人。
一年多了,他几乎天天在公交车上和她碰面。
那真是一张耐人寻味的脸,它沉思,它微笑,它忧伤……永远活跃着生命。关键在她的神采,神采常会使平庸的相貌变得美丽和动人。这是一种只有艺术大师才能捕捉到的美。
他不是大师,他甚至不能有一顶名正言顺的画家的帽子。他本来应该而且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才气的画家。他得天独厚地具有一般人所不容易具有的眼睛的记忆。凭着眼睛的记忆,他已经画了无数张她韵素描。她。这陌生而又亲切的女人。在他那斗室的墙壁上:带着各种神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望着他,观察着他。
他是学绘画的,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弄到气象站来工作。的确,他会干什么?又能干什么!除了要出黑板报,或是逢年过节要在机关门口装饰“元旦”、“国庆”、“春节”几个美术字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他这个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可那机会那么少。又那么的短暂,没等人们留下什么印象就被忘记了。
一年多来,欣赏她、揣摩她、描摹她。无声地用心和她交谈,已经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可是,昨天傍晚,他没有在这趟汽车上看见她。他的心情变得那么坏,整整一个晚上显得那么暗淡。
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呆呆地出了好半天的神,然后,他忽然发现她的每一张素描。都是那么的不能传神。他越看越别扭,是那支彩笔不好用了。他光着脚板跳下床,把那些素描从墙上扯下来。一张也不剩,撕得粉碎,弄得满地的纸屑碎片。
应该买一对彩笔,他走进了那家日夜营业的百货商店。
卖彩笔的姑娘正在和别人聊天。
“小姐,我买彩笔!”没人搭理。
他提高了声音。再次说道:“我买彩笔!”
她爱理不理地走了过来。斜着身子,胳膊肘往玻璃柜台上一靠,然后翻着眼睛问他:“要哪一种?”
“深蓝色的!”
柜台后面有人叫了:“小王。你的电话!”
“啪”,扔过来一双:红色的。他苦笑了。
要不要等她接完电话,换成蓝色的?已经六点三十分。再等就会错过那趟汽车了。他不等了,转身去候车亭。
她在那儿。夹着一把浅绿色的塑料伞。浅红色的衬衣外面,是一件银灰色的外衣。拎着的网兜里最上面的是五个扎在一起印有某某中药店字样的纸包。有人病了,不知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孩子。她一定累坏了,一脸的倦容和烦恼,微微地拱着身子,靠在候车亭的铁栏杆上。
公共汽车来了。永远是那么不顾死活的拥挤。她一定会急着回家。他冲到她的身边,尽力推开拥挤的人群,让她能挤上汽车。
她跟前的乘客下车了,位子空了下来,她重重地跌在座位上。伞,却从她的腋下掉了下来。他忙为她捡起。他害怕得连心也缩紧了,生怕听到像在买彩笔时听到的和那营业员姑娘一样的银铃般的嗓音。那样,他在想象中已经习惯了的形象就会被那银铃般的声音砸得粉碎。
他听见一句低沉的、甚至是略带嘶哑的话:“谢谢!”
他感激地望了望她。有好一阵不能从那莫名其妙的快乐里清醒过来。有什么声音在他的心里响着。是了,是那句话:“不,该是我谢谢你,你没有让我失望!”
她瞥了他一眼。那是一双除了她自己的世界。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当然也没有看见他。用不着,他并不想认识她,也并不想爱她。他只是想画这张动人的脸,并且把她的画像挂满他的墙壁。
几乎所有的收藏家都会喜欢向人们炫耀自己的收藏,高兴的时候,也还会转送给自己的朋友。可绝对没有哪一个人愿意自己的女人被人欣赏。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或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发生兴趣便是想要爱之,占有之。他想,既然人是自然界里最杰出的艺术品,到什么时候男人才不把女人或是女人才不把男人仅仅是当做求偶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件艺术品来欣赏。
回家进门了,他试着在心里重复摹仿她说话的语气、语调。他从那声音里好像又更多地捕捉到了一些感觉。他神经质地搓着自己的手指头,准备重新为她画一张素描。
他走进自己逼仄的房间,顺手关上了房门,空气一下子显得那么温暖,就像他今天晚上的心情。他在画架前面坐下,凝思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