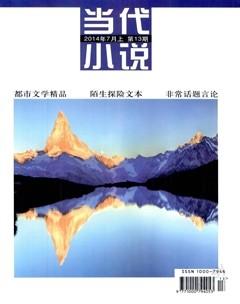截杀
王健 王菡
解放前。从内蒙古包头市经过鄂尔多斯、乌审旗到宁夏的陶乐、平罗一带有一条商旅大道,叫做“蒙边道”;中间经过内蒙、陕北和宁夏三省交界的地方,叫三段地。这里往东80里是内蒙的鄂托克前旗。往西50里就进了内长城,到了宁夏地界,往南60里又到了著名的陕北三边之一靖边县。前清年间。康熙皇帝亲征葛尔丹叛乱。三次打仗,两次从这里出兵,出镇二里有余,大路旁坐落着当时清军的粮草场,号称老营盘:当年康熙爷御笔亲题“一骑踏三省,王师镇九边”指的就是这里,别看地方不大,可确实是个要害地段。咱们要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949年1月,我在绥宁工委保卫部担任侦察科长,一个寒冷的夜晚,保卫部首长紧急召集我和侦察队长马三喜开会。部长和政委向我们交代:刚接到边区保卫部通知,随着平津战役结束,敌人正在做失败前的最后挣扎,派出一批高级特务,陆续向西北各省渗透。根据内线情报,一个叫王冬的军统中校,带着电台和密码,五天前已化装从包头出发前往宁夏,准备长期潜伏,伺机破坏。上级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中途活捉他,缴获电台和密码。但我们除了他一个名字,其它都不知道,更没人见过他。怎么查找?怎么捉拿?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经过大半夜商议,保卫部决定派出一个精干的侦察小组。化装前往三段地,在这个宁蒙之间的必经之路截杀他。
第二天上午,朔风凛冽,天冷得能把人耳朵冻掉:一支驼队出现在荒漠里,驼铃丁当丁当地响着。我和马三喜、刘黑娃骑着马走在前头,我变身成一个富商,高筒皮帽黑墨镜,身穿价格不菲的二毛皮袍。马三喜是驼队头,小刘是小伙计,后面三个都是驼驼客(驼夫)装束。我们每人一支短枪,一把匕首,再就是人人一身好功夫。我和马三喜都是自幼习武,经历多年的战火熏陶,格斗中三四条大汉近不了身。刘黑娃虽才17岁,却有一身好轻功,随身还带上了一根两头包铁的打狗棍。后面拉驼的白音宝格图和巴特尔是两个蒙古壮汉,是保卫部最棒的摔跤手。金盛财则是个出色的“刀客”,一把宰羊刀耍得出神入化。我们一边走一边商量。按我们的推算,当时的蒙边道上不是戈壁就是草滩,荒无人烟,这时节天寒地冻寸草不生,土匪刀客出没无常。那个特务王冬只有沿这条大道走才比较安全,还能住店吃饭得到接济。按他出发的时间,明天就应该到三段地了,一旦碰面必是一场生死相搏。我们必须提前赶到,在那“恭候”他。
暮云四合,我们赶到了三段地,穿过热闹的集镇,直奔“老营盘”。“老营盘”历经沧桑,早就破败了,后被人购得修成了客栈。成了这一带最大的“豪华酒家”,大号三义盛客栈。这客栈还真是名不虚传。高高的土墙围了个足有三十几亩地的大院子,院中是一个高大的中庭,康熙爷御笔亲题的金字牌匾就挂在正堂上,周边是一排排大房子。客房、仓库、厨房、牲口棚、草料场一应俱全,都是厚重的大土坯垒成的平房,还保留着当年那威风凛凛的军营气势。我们被两个伙计让进了中庭,刚收拾停当。一阵丁丁当当的驼铃由远而近,又是一队驼队走进了大院,为首的是一个肥壮的黑大汉,体重足有200斤,光秃秃的脑袋,趴鼻子,颌下一副络腮胡子,满面煞气。另一个是个黄脸汉子,寡皮精瘦,一脸烟容,两只三角眼滴溜溜乱转。后边也跟着一个伙计三个驼驼客。这伙人刚进中庭坐定,后面一阵响动,紧跟着一个公鸭嗓子娇嗲嗲的传了过来。“哎哟哟,我说怎么一大早就听着喜鹊叫,原来是来了老客亲爷们……”话音未落,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妪冒了出来,此人头肥身短没脖子,一个硕大的脑袋直接栽到了肉球似的身子上。两条胳膊比水桶还要粗些,满头乱发直竖,脸上抹得像个白面团,上嘴前突,下嘴缩进,活像一只狐狸,嘴旁两道深深的纹路更凸显出她的泼悍。蒙边道上口口相传的三义盛大掌柜孙佩花“孙寡妇”。竟然是这样一个又老又丑的怪物,不禁让人哑然失笑。
吃罢晚饭。我西他东。两伙人被伙计送往中庭两侧的客房安歇。那客房是一溜五大间,,屋里是连铺大炕,炕前摆着条桌长凳,墙上是上下开合的木格子大窗。一灯如豆,我们紧张地商议着。一是我们选在这里守株待兔对不对?--是今晚来的是伙什么人?正小声议论着,突然,门边放哨的小刘做了个噤声手势,一指窗外,马三喜噗的一声吹灭灯火,老白和老巴滑下炕去,悄无声息掀起上窗探出身去,一个伸出两只大手捂嘴掐脖子,另一个抓住来人衣服,“嗨”的一声,竟把那个猫着腰躲在窗外偷听的人,硬生生提了进来。老金的刀子紧紧跟上。在他脖子上不轻不重比划了一下。一见血那人立时瘫了。
“饶……饶……饶命。”
“说!”
“说,说,我全说,别……别杀我。”
我打着火一看,原来是酒店的大伙计……
经过审讯,我们弄清了情况,一是孙寡妇开的是个黑店,这里就是蒙边道上走私贩毒、销赃赎票、拐卖人口的交易场所和中转站。二是今天来的是伙歹徒。那黑大汉就是盘踞在麻黄山的大土匪张武,江湖道上有名的贼武子。跟随的伙计就是他的保镖。那黄脸汉和他的同伙是道上有名的一群“土客”(大烟贩子)。这次是黑大汉带着抢来的财物到包头,通过黄脸汉四处销赃,换成了烟土、枪支和红伤药,护送他们返回匪巢。三是这伙毒贩看着我们马好驼肥,货物沉重,竟起了歹心,想趁夜深人静把我们“做了”(暗杀),再干个肥票。晚饭后黄脸汉去找老窝主孙寡妇商议。于是孙寡妇派这个笨蛋来偷听我们谈话,要摸清我们底细。
情势险恶,只能先下手为强。我们略作布置,押着那伙计,悄悄摸出房去……
到了“土客”房前,刀子一顶,那伙计哆嗦着叫开门。我们一拥而进。“都别动!谁敢动我崩了他!”马三喜举起了手枪。屋里烟雾缭绕,臭气熏得人一个跟头,炕头上,黑大汉和黄脸汉正躺着吞云吐雾烧大烟,剩下四个人正脱了光膀子,围着地下一个小火盆捉虱子烤裹脚布。见我们冲入,虽惊不乱,显然早就见识过这等场面。黄脸汉一骨碌跳下炕,瘦脸硬挤出一丝丝笑纹,“别误会,兄弟是包头蔡云记老板蔡生礼,有话好说。好说。”“蔡虫子,你卖大烟都从河东卖到我们河西来了?”一揭了他韵老底,他顿时愣住了,“长官,你们是……?”我掏出缴获的国民党证件一晃,“说出来吓你一哆嗦,老子是河西保安司令部侦缉队的。今天撞上了,算咱兄弟们有缘,现在各位的安全就由我们负责。当然,各位的货也都交给我们。”黄脸汉顿时急了,“使不得,这可使不得,这货都是……”他顿了顿,斜眼看着黑大汉。我作势一拱手,“武子哥,幸会。”那土匪头恶狠狠盯着我,脸色越发狰狞。我挥挥手,“把那俩摁住,带其他人起货。”几个人一声答应,上前就要动手。“慢着,你们真是侦缉队的?”角落里突地站出一个驼驼客来,三十六七年纪,精悍健壮,目光阴冷。我故作轻蔑:“嗬,谁他妈的裤裆破了,咋冒出这么个(song)货?”那汉子勃然大怒,“混蛋,他妈的见了长官还敢放肆……”他突然意识到失言,立时住嘴。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这“猎物”居然自露马脚,我们不由心头一阵狂喜。“长官,我们就是来接你的,”小刘一跃而出,窜向那汉子,那汉子骤然脸色大变,抬腿猛一蹬,他面前一张厚重的条桌斜飞过来。小刘一个旱地拔葱,跳上桌面,顺势一棍砸下,那汉子一闪躲过,抄起条长凳横抡在小刘腿上,小刘大叫一声,栽在地下。我一声怒吼,抓起一个沉重的铜脸盆砸了过去,那汉子躲闪不及,霎时头破血流。我顺势一撑桌子,一个侧空翻跳了过去,落地刹那双腿齐出,把他狠狠蹬倒在地,就势拧住他一条胳膊。身后忽地一阵劲风,一条硬物狠狠砸在我后背上,我眼前一黑,“噗”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接着头顶一声沉闷的枪响,一个壮硕的躯体重重砸倒在我身上……原来刚才是那黑大汉抄起长凳想要结果我,被马三喜一枪打爆了脑袋。同时黑大汉的保镖也扑过来,一刀扎进了马三喜的右臂,鲜血喷涌而出。那保镖举刀又扎,被倒在地上的小刘一棍打碎脚踝骨,两个断腿的人又倒在地下扭成一团。这边厢那黄脸汉抄起马鞭,对着老白迎头一鞭,老白双手一抄,举起那个被抓住的客栈伙计迎了上去,一鞭竟把那伙计打得惨叫一声背过气去。与此同时,金盛财的刀子也捅进了黄脸汉的后腰。黄脸汉那几个同伙这会儿也回过味来,冲上来和巴特尔厮打;几分钟时间,屋里所有能动的东西都飞了起来,所有能砸烂的东西都砸了个稀烂,连结实的房门也被硬撞下来一扇。
屋里敌人拼命挣扎,要说那特务的中校肩章还真不是塞钱塞出来的,他精通格斗,身手了得,又急于脱身突围。所以拳脚齐出,招招致命,以一对二,像疯狗一样和我们玩了命,我和马三喜都带着伤,力不从心,一时间根本制服不了他,危机关头,只能舍命一搏;趁那特务往前猛扑,我往后一挫身子,借着劲一下跳起来,整个人在空中横过来向那特务猛撞过去,把他撞得连翻几个跟斗。马三喜大步跟进,伸手就抓他的咽喉;没承想那家伙忽地一个鲤鱼打挺又蹦了起来,手里还多了一支“掌心雷”(短管左轮枪)对着马三喜就是一枪。“嗖”的一声,赶过来的金盛财把刀子猛掷过来,正砸在枪上,子弹砰的一声射上房顶。我们紧跟着一人一脚,把他踹倒在炕上。他就地一滚,一个鱼跃前滚翻,竞撞烂大木窗。滚落到院里爬起来跑了。我刚要跟着跳下,被老巴一把拉住,“别追,他跑不了。”果然,院里立刻传来群狗狂吠撕咬和救命的惨叫。原来蒙地的大狗晚上都散在院里防贼防狼,只要发现陌生人,一群狗立刻扑上去乱撕乱咬。那特务不知蒙地的习俗,只想着跳窗逃命,没承想一下落到了恶狗嘴里。老巴和老白抄起打狗棍冲了出去,不一会儿就把那个浑身是血被咬得半死的家伙拖了进来。
后来的事情就有些戏剧性。天还没亮,孙寡妇就溜过来打探消息。看到那一地狼藉和尸体,立刻呼天抢地大闹起来,口口声声让我们赔偿她的损失。还嚷嚷着要去报官。我们告诉她,如果她把“土客”存放的货物交出来,就留给她千斤重的一驮货做补偿。原以为这个老江湖还要讲点黑道上的义气死不开口呢,没想到她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带着我们去了她的地窖。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大烟、枪支和藏在药品里的电台,但怎么也找不到密码本……
天色大亮,我们知道这里还是敌占区,不宜久留;准备留下老白继续查找,其余押着捆好的俘虏先撤。孙寡妇又奔过来了,口口声声要求我们把她儿子留下。“你儿子?”这会儿我们可真蒙了,孙寡妇一指王冬,“我昨天晚上才认得干儿子,他还答应送我30块大洋呢,你把他抓走了,我找谁要钱去?”孙寡妇两手拉住我的马缰,往地下一倒,两腿乱蹬。一脸鼻涕眼泪的放声干嚎。面对这个“滚刀肉”,我突然意识到什么,怒喝道:“孙寡妇,他给你钱,是让你给他藏东西吧?”孙寡妇的干嚎戛然而止,翻着两只肉泡眼一声不吭。老白往地下狠狠抽了一鞭,“说!”她吞吞吐吐。“就……就给……了一个……小包。”在我们的“威逼”下,她终于从腰里掏出一个裹得严严的油布包,打开一看。里边正是一个小巧精致的皮面本……趁我们全神贯注地翻看密码本,旁边的孙寡妇竟偷偷拉上我们一峰最壮的骆驼悄然不见了踪影……
后来,王冬交代了前后经过。他出发时,包头的军统通过关系找到了那群“土客”,把他假扮成驼夫塞了进去,那群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到了客栈。他很快就看出我们是群假扮的商人。为防万一,他许以重金,把最要紧的密码本转移给孙寡妇保管一夜。后来我们那一番“黑吃黑”的表演让他信以为真,正要出来“认亲”,却猛然意识到不对,他潜伏的任务是绝密的,并没通知宁夏的军统,对方怎么会派人出来接他?小刘一说话,就更证实了他的判断,于是只好跟我们拼个鱼死网破……他哀叹道,在军统闯荡了20年从未失过手,没想到机关算尽,却栽在我们这几个土八路的手里……
责任编辑:李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