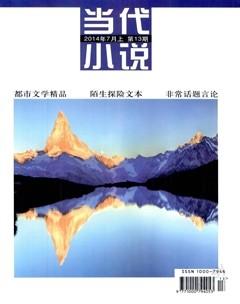谷满仓的秘密
项中立
那天,我居然想起了胡小豆。这虽是百无聊赖中的一个闪念,可我仍然觉得好笑——胡小豆与我,就像槐树和梨,没一点关系。他是个中学生,而我,是一个厨师。
好像也是那一天,谷满仓来后厨找我。他说打算退掉他租住的房子,搬来和我一起住。他每天可以补贴我五毛钱。“一个月下来,你就额外收入十五元呢!”他很自信地望着我。他相信我会被这个数字打动。
“十五元,数目不小呢!”他又说。
“可是,你也同样省下了十五元吧?”我知道谷满仓每月房租是三十元。
他的黄白的脸皮不自然地皱了一下,像是有点尴尬。“唉,没有办法。丫头在北京念大学,花费大,眼下,浴池里营生又淡,挣不了多少,能省点就省点……项师傅,如果你能让我免费住在你那里,我可以免费为你搓澡的……”
我的房子是饭店老板花钱租的。房子大得很,再安一张床不成问题。我只是对谷满仓这个人有点看法,确切地说。是不太喜欢他。要是换成胡小豆——我怎么又想起胡小豆了呢?我好像有些时日没见胡小豆了。近几个星期天,总是小豆的爷爷独自用一辆旧三轮车,把后厨外面的废纸盒、废易拉罐和空酒瓶拉走。胡小豆的爷爷说,小豆这些时日忙着准备高考,所以,这件工作只能他自己来做了。胡小豆的爷爷患过脑中风,身子不太灵便,这工作做起来明显有点困难。我闲着的时候,喜欢帮他一把。我是个热情的人。我帮小豆的爷爷装好车,然后,看着他吃力地推着车渐渐远去。他的汗碱弥漫的后背,像一块锈迹斑驳的旧铁瓦,在我眼中摇着的时候,我真心希望胡小豆考上一所好大学。
——还是接着说谷满仓吧。安徽人谷满仓在西水镇一家浴池给人搓澡。他好像是半年前来了西水镇的。那时候,天气还冷些,还是有人乐意到浴池里泡澡的。泡泡搓搓,谷满仓每天能有个三十二十的收入。这就把安徽人谷满仓留在了西水镇。我喜欢到浴池里洗掉满身的油烟味,所以跟谷满仓不陌生。
谷满仓搓澡的手艺只能算个三流。他惟一的好处是不藏奸。他不用搓泥宝,也不打盐和奶,更不会拔罐和按摩。他只会用蛮力气,像褪猪毛一样,拿澡巾蛮力地搓。他搓过的地方,一层枣色的红,像淤了血的猪肉皮。人家忍不住了,说,谷满仓,你轻一点不行吗?谷满仓就怯怯地住了手,红着脸说,我弄疼你了吗?要不,你少付我两毛钱吧。付小费时,人家真就少给他两毛钱,谷满仓惋惜得要抽自己嘴巴。西水镇的人虽然吝啬,却也没有人刻意地为难他。只是当谷满仓又跟人家讲起他丫头在北京上大学这件事时,人家会显出极其厌烦的表情来。
几乎所有来浴池泡澡的人,都知道谷满仓有个在北京念大学的闺女。
“北京,那可不是个平常的地方!”
说这话的时候,谷满仓眼睛发亮,好像他就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站在颐和园门口,站在鸟巢和水立方前面,站在摩天大楼的脚跟下——“我的丫头就在那里念大学。她是去年考中的。到今年麦收,她该念大学二年级了……”
接下来。谷满仓会说。他的丫头是他们山村飞出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金凤凰。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跪在先祖坟前,把头一下一下地磕在墓碑上,磕得头破血流。他们家连续半月没断过贺喜的人。光大叶子烟,他就碾了满满一箩筐,饱满的葵花籽备下了两口袋。村长还卖了一口袋高粱。请一个唱书的瞎子唱了三晚书。那书叫《寒门闺秀》,说的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子,勤学苦读,最后成了官家千金的故事。那段日子里,他的丫头就像腰带山尖上飘拂的一朵美丽的祥云,被众人仰望和爱戴着……
谷满仓喜欢一边蛮力地给人家搓着澡,一边轻松而熟络地讲述这些事情。换一个人,又从头讲一遍。起初,人家是乐意听的,也真心地为谷满仓有个出息的丫头高兴。后来,听厌了,就烦了。他再要讲时,人家就说,谷满仓,你还会说别的不?
谷满仓一直用着蛮力的手,这时候会短暂地停留一小会儿。然后,他会像不小心得罪了客人一样,讨好地点着头,赔着笑脸说:“那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腰带山的卧龙崖吧,”
谷满仓在讲述卧龙崖的时候,脸色逐渐变得晦暗,眼神里显现出一股极力掩饰着的哀伤。他说,腰带山的北坡有一面陡峭的断崖。崖深百尺。终年不见阳光。冬天积下的雪,直到来年夏秋,才得融化。断崖的石缝中,偶尔生长着一种数百年不枯的老藤。据先人传讲,这老藤的根,经数百年的阴光历练,已成名贵药材。将其切割成薄片,放于陈年旧瓦上,阴火焙干,再碾成粉,用烈酒拌成糊状,敷于骨断处,三日痊愈。明时宁王朱濠宸率兵十万,与安庆督军杨锐大战,遭了杨锐滚木礌石袭击,朱军伤者甚重,骨断筋折。朱濠宸命军士从崖缝中搜挖老藤根,治愈了数千将士,但也有无数的军士因挖老藤根葬身崖底。崖底间白骨散落,夜晚时磷火烁烁,像一条蜿蜒逶迤的长龙,静卧崖底。“卧龙崖”因此得名。饥荒年代,为了生计,腰带山先人也有豁出性命攀断崖挖老藤的,十有八九都摔死在了崖底,成了卧龙身上新生的一枚鳞片。有侥幸活着回来的,也是空手而归,说是因了当年朱濠宸的搜挖,老藤已经十分罕见。也正是因了罕见,老藤便成了一个传说。传说中的老藤便愈加珍贵。近几年。有南方药贩子来腰带山收购老藤根。几万元一斤的价格。是个不小的诱惑。但腰带山的人,但能活下去,谁去卧龙崖呢?他们是宁愿想象着几万元一捆的票子流口水,也不肯去卧龙崖送命的。
“一九六零年闹粮荒。我爹禁不住饿,瞒着我娘去了卧龙崖。结果一去就没回来……但我爹,他不是最后一个死在卧龙崖的人……”
说到这里,谷满仓就突然打住了。他嘴唇紧紧地闭着,像是把很多的话都极力地关到了嘴里边,不让它冒出来。他手下不自觉地用了力道,那个趴在澡床上的人,背上的皮肤,霎时变得枣色的暗红,便怒道:“谷满仓,你下手轻点儿!”谷满仓先是慌张着愣一下,然后,脸上挂起层歉意的笑纹,小心翼翼地说:“对不起,我弄疼你了吗?你少付我两毛钱吧……”
进了初夏,西水镇渐渐炎热起来。槐树花开始谢了,遍地的矢车菊却茂盛地绽放了黑蓝的花朵。几乎是一夜间的事。西水镇很多人家的屋顶上,都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人们可以在家里冲冲澡,免得去浴池花钱。中午或晚上的时段,西水镇很多人家的院里,就有了哗哗的水龙头放水的声音,然后,就有灰脏的污水从门底下的水道口泻出来,涓涓地,千百条细流一路漫延,汇聚到西水镇街两侧的阴沟里。苍蝇蚊子们,便把这里做了理想的乐园。偶有流浪的野狗渴了。想喝几口阴沟里的脏水,结果总是被蚊蝇们叮咬得落荒而逃。
浴池的生意一下子淡下来。这直接危及到了谷满仓。有时候,他在浴池里守上一天,所得小费,还不够他一天的房租钱。我想,精明的安徽人谷满仓。因此才退掉了每月三十块钱的租住屋,然后。花十五块钱跟我同租一室。他大概以为,十五块钱,完全可以打动我。
大概是看出了我漾在脸上的不屑,他开始慌乱起来。他把一只手伸进他的口袋里,不停地摸索,但最终,什么也没掏出来。他就那样可怜兮兮地望着我,几近哀求地说:“项师傅,您就算积德行善吧,帮帮我的丫头,她在北京念大学,麦收就要升二年级,我得尽快攒足她一个学期的学费呀……”
我最终答应了他。我说过,我是个热情的人。但我得承认,我这样做,完全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我也说不清我是不是真的出于热情。反正我答应了他。直到这时候,谷满仓一直揣在兜里的手才抽出来。他手里竟然握着一盒香烟。那个海蓝色的烟盒,我一看就知道是全天下的屠户都拒绝的牌子——白沙(白杀)!湖南烟,八块钱一盒。,后来我想,倘若我不应他这件事,他一直揣在兜里的手,会不会把这盒八块钱的烟拎出来呢?其实。我不喜欢抽湖南烟,湖南烟有点软塌塌的,我更喜欢烈一些的云南烟。但是,谷满仓坚决把烟塞给了我。他说他不抽烟,他有点肺病(还煞有介事地咳嗽了一下)。这香烟既已买了,就请项师傅凑合着抽了,不然白瞎了八块钱呢。我接烟的时候,留意了一下他的脸色,真是有些苍白。但我想,那可能是整日守在浴池里,给水汽蚀的。连那声咳嗽也是装出来的可怜相儿。
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谷满仓总是深夜才从浴池回来。这严重影响了我休息,好梦也被他开门关门的声音碾碎了。他的永远也抬不高的鞋底,嚓嚓地蹭着地面,像用砂纸粗鲁地打磨我的耳膜一样,叫我烦躁得难以忍受。我几乎忍不住要怒斥他,可想想他可怜巴巴的样子,还有那盒湖南“白沙”,我又强忍住了。强忍着愤怒的我。很难再入梦境。第二天炒菜时,头就昏昏沉沉,错把盐面当成了味精,结果,客人就咸得咧着嘴,把菜给我退回后厨来,搞得老板对我极不满意。
更叫我难以忍受的是,半夜回来的谷满仓并不急着睡觉。他每天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他身上所有的口袋都翻个底朝天。翻出来的角票硬币,乱茅草一样摊在床铺上。他很有耐心地将这些零钱捋顺整齐,抚平纸票上的皱纹。然后,借了昏暗的灯光,一遍又一遍地数起来。我觉得这是他一天中最辛苦的工作。那把散碎的钱票攥在他手里,总也数不完的样子。他数钱的时候,眼睛眯起来,嘴唇半张着,叠满褶子的脸皮,神经质的一下一下抽搐不止。那目光看似深邃,实则呆板,有时会有泪花从眼睛深处开出来。绽放到眼角上,最终败落成硕大一滴。摇摇欲坠的样子。数到他自己也感觉腻了的时候。他才肯把那点钱小心翼翼地放进一只旧鞋盒,然后,再把旧鞋盒锁进床底下的一只旧木箱里,而钥匙用细绳拴了,牢牢系在手腕上,万无一失的。做完这一切,他还会朝我这边觑一眼,探查我睡熟没有。这明摆着是防备我的意思嘛!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见钱眼开的小人?我好歹也算西水镇上有个名号的大厨,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在乎你那点散碎银子?这不是黑我么?
后来,谷满仓跟我说起他来西水镇之前,曾被同室的河南人偷了两个月小费。那个河南人跟谷满仓在同一个浴池搓澡,偷了他的钱就销声匿迹,不知去了哪里。“有一千多元呢!”谷满仓说,“差不多是我丫头半个学期的学费!”
鬼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这个安徽人,我是愈来愈不喜欢他了,总想着找茬黑一黑他。
安徽人谷满仓似乎患着严重的失眠症。很多时候,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折腾,最后,只得起身下床,蹑手蹑脚地溜出屋,到院里待上一阵。院里有一个石墩,我听见他像是坐在石墩上,咳嗽了一阵又一阵。
谷满仓每天挨不到天亮就要去浴池,往那大池子里注水,然后,撒上消毒粉。那种粉让一池清水变得莹蓝诱人;而我,要在被窝里赖到八九点钟才起床。我起床的头一件事,是拿把条帚扫屋地上的烟头。谷满仓是不抽烟的。我烟瘾极大,一个晚上,要抽掉多半盒云烟。带着长长滤嘴的烟头,像硕大的潮虫的尸体,横七竖八躺满屋地。我扫着烟头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地上只有寥寥几个秃滤嘴,更多的烟头哪去了?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甚至满怀恶意地去了倒垃圾的地方找过,也不见更多的烟头。后来,我蓄意翻了下谷满仓的褥子下面。哈哈,一把焦黄的、或多或少都遗了些烟丝的云烟烟头,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觉得,到了我黑一黑他的时候了。
又一天夜里,安徽人谷满仓坐在石墩上咳着的时候,我悄然站在了他的背后。我看见他一面咳着,一面将一支点燃的烟头放到唇间,狠抽几口,扔掉。又换上另一支烟头。我说:“谷师傅,抽不惯云南烟吧?”
谷满仓骇得一跳,差点从石墩上滑下来。月光浅浅的,我看不清他的脸色,但我估计。那张苍白的脸,一定变得红晕弥漫。
院里的葫芦花夸张地绽放着。那花香像潮湿的雾,极有质感。这样的花香到底叫人生不起气来。我突然间就不想黑他了。我说过我是个热情的人。我的热情,常常叫我突然间做出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情。那夜,我甚至友好地递了根云烟给他。谷满仓感激地接了,熟练地点燃,狠吸了几口,然后,毫不掩饰地摆出一副极受用的样子。
“我老婆走之前,我是从不吸烟的。”他说。
谷满仓的老婆几年前出去打工,再没回来。从谷满仓平时不经意的话语中,我听出他老婆是因为厌烦了山里清苦的日子,才绝然而去的,我想,她断然不会再回山里。但谷满仓坚决不同意我的看法。
“她会回来的!只要我找到她。告诉她丫头考中了北京的大学府,她就会回来的。”
谷满仓说。他从安徽的西部城市六安起步,一路向西,至四川雅安,在折向南。循着安徽人出外打工惯常的路向。一直寻到了云南的乡云小镇。那地方靠近中缅边界,毒贩神出鬼没。有毒贩的地方钱厚。在那里打工的外地人多是女子。她们在宾馆饭店浴池里做服务员。或小姐。谷满仓说,他女人虽是山里人,却一点都不比城里女人差。他女人心灵手巧,模样俊俏,做服务员不在话下,就是做小姐,也够格的。谷满仓原想,他女人有可能流落到乡云小镇,但一路寻下来,至今不知花落何处。
乡云小镇有浴池数十家。谷满仓在那里学会了搓澡和抽烟。
“那时候,我抽烟抽得很凶。”谷满仓说,“一天两包春耕牌香烟都不够!那个牌子的香烟不贵,才五毛钱一包。可细算起来,一个月要抽掉三四十块。多吓人的数目啊!丫头在北京念大学,费用那么高,我哪能这样糟蹋钱呢?我得替她省着点儿。”
谷满仓把已经燃尽的烟头从唇间拿下来,举到眼前看了看,又吝惜地放到唇间狠吸了两口,确信那只剩一截光秃秃的滤嘴了,才优雅地用手指将烟头弹向夜空。然后,他长久地仰着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好像那漫天亮晶晶的星星里,有一颗是他的丫头。
那天夜里,谷满仓告诉我。西水镇也不是他久留之地。过几天,天气热起来,他就要离开西水镇。他已经想好,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唐山。他知道有很多安徽人在那个城市打工。也许城市的钱要比西水镇的钱容易挣些,他决定去城市里闯闯。
“也说不准。在唐山能找到我老婆呢。”
谷满仓又咳嗽了一阵。这一阵,好像比往常咳得要厉害一点儿。
“看来,这烟真的要戒了。”谷满仓擦着咳出的眼泪说。
胡小豆的爷爷来收废品的时候,我正坐在后厨外面的椅子上发呆。我发呆的原因是因为我又想起了胡小豆。这一段日子,我常常在不经意间想起和我毫不相干的胡小豆。我为什么总是想起他呢?我扯不出原因。扯不出原因的我就显出了呆相。
五月的阳光有些滞重。蔷薇和栀子花都开了,油桐花也开了,雪一样的白。小豆爷爷照例把他的旧三轮车停在后厨旁边。通常,他会立即投入他的工作——从车上拿下几条粗质的编织袋,然后,把铝质的易拉罐和玻璃酒瓶,分类装进袋子;再把旧纸盒用脚踏平,码起来,用旧铁丝或麻绳捆成捆,这样,装车就方便一些……小豆爷爷做着这些工作的时候。专心致志,从不理睬任何人。但是这一次,小豆爷爷例外地没有立即开始他的工作,而是径直朝我走过来。他的脚有点跛,但他走得并不慢。
“小豆考中了!”他说。他的眼睛亮着晶光。让我想起安徽人谷满仓说着他丫头考中北京大学府时的目光。
“昨天下的通知书。”小豆爷爷从兜里掏出半盒云烟,抽一支递给我,剩下的又揣回兜里。“喜烟,抽一支吧。”
然后,小豆爷爷冲我笑了一下——其实。我实在拿不准他是不是笑了一下。患过脑中风的小豆爷爷,本就嘴眼移位,笑和不笑没有多大差异。
我好像有些时日没有见着胡小豆了。以前。碰到不上课的星期天,胡小豆偶尔随他爷爷来店里收拾废品。我喜欢站在后厨门口,沉默着,看他们爷俩工蜂一样地忙碌着。这时候的胡小豆,完全不像一个中学生。他的衣服是肮脏和凌乱的,他的脸上扑满灰尘。他的头发上,粘着几片从槐树上败落下来的花瓣,或者一角罐头盒上脱落的商标纸。他像个十分敬业的废品分拣员,小心谨慎地分拣着废品的种类。把铝质和铁质的易拉罐分别装进两个袋子。把纸片和塑料布分别打成两个捆……有时候,突然想起装着铁质易拉罐的袋子里,误装了一个铝质的易拉罐,他会毫不犹豫地将整袋易拉罐倒掉,重新开始分拣;或者为了鉴别一个易拉罐是铝质还是铁质,他要使用很多种办法进行识别,用指头弹,甚至用牙齿咬,就像耐心地演算一道费解的数学题一样。这时候,我的心情常常被一层薄薄的忧伤覆盖。这种忧伤,引导我躲开老板的视线,从饭店冰箱里拿一瓶红茶,或两瓶矿泉水,塞给他。胡小豆总是腼腆地笑笑,轻轻地道声谢谢。只有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胡小豆不光是个优秀的废品分拣员。他还是一个有文化的中学生。
关于胡小豆,差不多整个西水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孤儿。
发生在十几年前的那场车祸,在西水镇,肯定还有不少人记着:一对赶西水镇早市卖菜的农村夫妇,被一辆重型卡车碾成肉酱,而肇事车辆逃逸。那血腥的场面,我是有幸目睹了的——鲜血和肉泥覆盖了一大片路面,黄的白的黑的器官碎渣,被轧断的骨头,还有染血的手指头,散布其中;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坐在翠绿的蔬菜上,满眼惶恐地注视着他面前的两具半截尸体,和四周围着他的人。男孩就是胡小豆。他命大,没死。后来,没死的胡小豆就被西水镇手套厂看传达室的老光棍收养。老光棍就是现在胡小豆的爷爷。胡小豆的爷爷几年前突发脑中风,虽没死,却落下嘴歪眼斜,腿脚不灵的后遗症。留下后遗症的小豆爷爷自然就被手套厂解雇了。被解雇的胡小豆爷爷买了辆二手三轮,每天吃力地推着它,出没在西水镇每一个可能找到废品的地方。
其实,胡小豆是有个亲叔的,他完全有义务把胡小豆留在老家。但胡小豆的叔是个出色的赌徒,他哥嫂出事那阵,他大概正输塌了锅。他开出的条件是,只要手套厂看传达室的老光棍拿出两千块钱,他就可以把胡小豆领走。当时的情景,胡小豆的爷爷后来不止一次地跟西水镇人叙述过。那是个晚上。因为交不上电费,村里的电工把电给掐断了,屋里没有灯光。但那晚的月光很好,彼此能够辨清或站或坐的姿势。胡小豆是蹲在一条板凳上的。他像个城府很深的大人,整个晚上都沉默不语,静听着看传达室的老光棍和他叔讨价还价。叔强调,少于两千块钱,别想把小豆领走;看传达室的老光棍说他全部积蓄只有八百块钱,可他非常希望领走胡小豆。讨去还来,因为数目悬殊,很难达成共识。眼看双方要谈崩的时候。只见胡小豆灵巧地从长凳上跳下来,紧紧拉住了老光棍的手,说:“爷爷,你去借上二百块钱,给他凑足一千,我跟你走。”就这样,老光棍花一千块钱,买断了胡小豆和他叔的一脉血缘。
后来,胡小豆跟我讲,接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天,爷爷嘱咐他去老家给爹娘坟上烧些香纸,顺便去给他亲叔报个喜。聪明的胡小豆一下子就猜到,爷爷是拿不出足够他上大学的学费,才叫他去看望他叔的,他叔断然不会叫亲侄子空手而归的。爷爷的预料非常准确,叔看见小豆果然非常高兴,问他这些年在西水镇过得好不好?小豆说我们过得还不错。只不过我爷爷前几年得过脑中风,被手套厂解雇了,现在,他每天推着三轮车收废品。但我们过得很开心。叔说叔现在有钱了,小豆你回家住吧。小豆说叔你发财了,你的钱留着你自己花吧。我不会离开我爷爷,我要给他老人家尽孝呢。他拾废品供我念完小学念中学,现在我又考上了大学。“你考上大学了吗?”叔的眼睛亮着晶光,“我们胡家可出了人物了!”叔就举着一把票子往小豆怀里塞。小豆像掸衣服上的尘土一样,把那些票子哗一下掸掉在地上,摔得满屋地都是。叔像根枯木桩一样瓷在那里。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一阵黄,像盏诡异莫测的霓虹灯……
“小豆这孩子很倔。”小豆爷爷说。
这个星期天,我发现小豆爷爷对他的工作一点都不着急。他不停地跟我夸着胡小豆的优点。同时。不失时机地跟我套着近乎,虽是生硬些,却是极用心的。我怀疑他另有图谋。果然不错,后来他说:“兄弟,你得帮我两千块钱,小豆的学费还不够……”
我是个热情的人。我当然不会拒绝他。我说这不成问题,只是要等几天,因为老板还没有给我发工资呢。
“来得及,来得及。”
小豆爷爷又掏出那半盒云烟,抽出一支往我唇上递。我谢绝了。其实我已经品出那烟是正宗货。我又特别喜欢抽这种牌子,我只是想到,说不定胡小豆的爷爷还要用这半盒烟去套别人的近乎。在西水镇来讲。这个牌子的香烟,还算是拿得出手的。我得给他省下一根。
胡小豆来找谷满仓时,他刚刚咳过一阵。我愈来愈觉得,谷满仓的咳,跟抽烟没有一点关系——他已经好些天不再抽烟,一来西水镇没有“春耕”这种牌子的便宜香烟卖,二来我抽烟时,刻意抽得彻底。不留一根烟丝在丢掉的滤嘴上,让它没有一点二次利用的价值。有时候,我听见谷满仓躺在床上辗转不停,我就知道他又想烟抽了。但他宁愿那样艰苦地忍受着,或者孤独地坐在院里的石墩上无聊地看星星,也不肯伸手向我讨一枝烟来抽。这出乎我的意料。
胡小豆的到来,叫谷满仓不安起来。
“谷师傅,我想跟你学搓澡。”胡小豆说。
谷满仓的不安,体现在他的沉默上。谷满仓的沉默是真正的沉默,眼皮也不眨一下,像个瓷人。
“谷师傅,我给你点一枝烟吧。”
胡小豆掏出半盒云烟来。我一眼就认出是那天他爷爷手里那半盒云烟。里面好像还是那么几枝。这说明除我之外,小豆爷爷并没有找到几个可以套近乎的人,或者是找到了。只是人家不肯买他的帐。在西水镇,有几个像我这样热情的人呢?
“谷师傅,我爷爷一时拿不出供我上大学的学费,我得自己挣一点。”
谷满仓依然沉默着。
谷满仓的沉默,叫我忍不住愤怒起来——
“谷满仓,放个屁会难死你吗?”
“谷满仓,你怕小豆抢了你的饭碗吗?”
那夜,直到小豆无奈地离去。谷满仓都没说一句话。他安静地躺在床上。反常地没有辗转和咳嗽。这更说明了他心里的不平静。下弦月的光,脆弱得如同婴儿的目光,摇晃的树枝条,轻轻地就把它搅碎了。碎糟糟的月光散落在人的眼睛里,人的心情也变得碎糟起来。
后半夜,谷满仓突然从床上爬起来,说:“项师傅,给我枝烟抽吧。”
也不容我答应,伸手就把半盒云烟拿将过去。然后。抽掉一枝又一枝,像是发狠地打发着多日积下的烟瘾。早晨起床时,我看见屋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烟头。而谷满仓早已去了浴池。
这天下午,我去西水镇超市买了盒云烟,回来时,看到了满面愁容的胡小豆。他守在后厨门口等我。
“项师傅,你得帮帮我……”
“你一定要学搓澡吗?”
“在西水镇,只有搓澡比拾废品来得快一些……”
罢了!我的不值钱的热情,就在这一刻。突然地泛滥起来。我去饭店前台拿了两瓶白酒和一只刘美烧鸡,告诉老板从我工资里扣除。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塞给胡小豆,告诉他,晚上,磕头,拜师。
后来的事情,完全出人意料。
胡小豆拎着我提供的礼物站在谷满仓面前时,他正跟往常一样,耐心地数点着零星的钱票。那天,谷满仓几乎将他所有的钱票从旧鞋盒里倒出来,一堆一堆地摆在床铺上,像集市上卖八角和肉蔻的香料贩子。十五瓦的节能灯泡弥漫出薄雾一样的光线。这叫谷满仓不得不眯起眼睛,同时,把苍白的脸尽可能地贴近钱票。他把钱票数了一遍又一遍,后来,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了,就把那些钱票统统塞进鞋盒里。这才抬起眼睛,看着他面前的胡小豆。他的目光温柔得如同一只哺乳期的母狮子,爱怜地瞅着它的幼崽。
“小兄弟,把酒倒上。”谷满仓说。
胡小豆慌乱着动起来。他居然在窗台上找到一只落满灰尘的杯子。酒倒进去的时候,有几只蚊虫的干尸浮现上来。谷满仓一下子就喝干了那杯酒。他说:“祝贺小兄弟考中大学。”谷满仓的脸。开始有鲜嫩的潮红涌动。他说,他丫头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可没有拿酒来祝贺她。他只给她买了一条红纱巾。丫头很早就喜欢过的那种红纱巾。丫头围着红纱巾走在山村里,真像一只美丽而高贵的凤凰。
谷满仓又喝了第二杯酒。他说:“小兄弟,你是个倔孩子。”谷满仓说,他的丫头和胡小豆一样地倔。丫头考上北京大学府的时候,他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的学费,求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没凑足学费的一半。为此,他愁出了一场大病。丫头服侍在他床前,端汤喂药。丫头说,爹你不用为那点学费发愁了,我有办法搞到我上大学的学费。丫头真倔,她真的自己去弄钱了。那条红纱巾证明了这一点……
谷满仓的眼睛,已经变得红艳而忧伤,仿佛有一条忧伤的红纱巾在他眼睛里肆意飘扬。
第三杯酒,谷满仓久久地端在手里。他像是犹豫着,将要做出最后的重大决定。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暗暗捅了一下胡小豆:“磕头,拜师。”就在胡小豆将要跪下磕头时,谷满仓毅然地喝下了那杯酒。然后,他把那个装满钱票的旧鞋盒塞给了胡小豆:“不多,三千块钱,算份心意吧。”
“老谷!”我几乎要去阻止谷满仓了。“你好好想一想,那可是你丫头的学费呀!”多年以后。我回想起当时不经意间冒出的这句话时,总是禁不住脸上发烧。
“对不起,”谷满仓平静地说,“我一直瞒着你们,其实,我的丫头,她已经死了。”
谷满仓执意要离开西水镇。他说,他要去唐山闯一闯。他的老婆很可能也在那个城市,或许。他能够在那里找到他老婆。我想,除了这些,谷满仓执意离开西水镇的原因,是我们洞悉了他藏在心里的秘密。用不了多久,整个西水镇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安徽人并没有一个在北京念大学的丫头。所以,他要换一个地方。就像这几年,他不断更换新地方一样。在一个新的地方,他完全可以守护着心中的秘密,说他有一个在北京念大学的丫头,今年麦收就要升大学二年级了。她是他们那个山村飞出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金凤凰,甚至,他可以像说有个河南人偷走了他一千多元小费那样,说有一个叫胡小豆的河北人,偷走了他半年的小费……这个安徽人,谁知道他呢?
我和胡小豆送谷满仓坐上了西水镇开往唐山的长途汽车。那是个飘着雨丝的清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有几只流浪猫出现在街旁阴沟边,冲着忧郁的天空喵叫几声。汽车启动之前,安徽人谷满仓从车窗里伸出手,拍了拍胡小豆的头说,念大学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用功些,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该升大学二年级了。我丫头要是还活着,过了麦收就要升大学二年级了……谁会料到,她会背着我去卧龙崖挖老藤呢?那是个尸骨无还的去处呀!若不是我亲眼看见那条红纱巾挂在崖石上飘扬,我死也不信的……
汽车缓缓启动之后,安徽人谷满仓突然想起了什么,从车窗里探着头,朝我喊:“项师傅。有件东西我忘在床下的木箱里了,你去找找,把它烧了。”
回来后,我在那只木箱里找到了一张“安徽省六安市人民医院”的诊断书,患者的姓名是谷满仓。病症是肺癌晚期。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