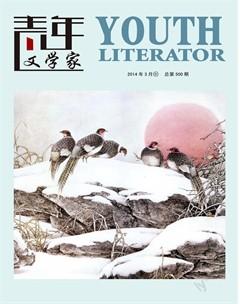论新世纪小说中农民形象塑造的“伪现代化”倾向
摘 要:农民一直是中国现当代作家最热衷的母题,在现当代的小说中塑造最成功的形象就是农民形象。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和工业的现代化,作家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也体现了渴望现代化的情绪,出现了一系列“新农民”典型。然而,从深层来分析,作家笔下的所谓的当代农民的骨子里更多甚至全部还是传统的质素,只是一种“伪现代化”,当代农民形象的真正出现还需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关键词:新世纪小说;农民形象;塑造;伪现代化
作者简介:马平野,男,1985年生,汉族,辽宁朝阳人,文学硕士,阜新高等专科学校财经系,助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8-0-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城市化和都市现代文明都得了全面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明显松动,在城市文明日益渗透到乡村的每个角落的同时,大批农民走向城市,以城市为蓝本,寻找自己的现代化方向。随着21世纪主流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号召更为农村的现代化转变提供了理所当然的依据,文学作为社会的神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一变化。传统的农村农民生活已不适合今天现代化的要求,打破传统的农民形象,关注农村农民对现代化、城市化的追求,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把握当下文学审美经验的多样性就显露出特别的意义。
事实上,“现代性”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90年代中期以来已引起了广泛的论争。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的、文化的概念,包含着“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维度,杨春时、宋剑华、逄增玉、陈晓明等对此都有经典的论述。现代化则是社会学的概念,它所强调的是“世俗现代性”,具体表现为与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相关的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如启蒙主义、意识形态和工具理性等等,也就是对现代性的理性上的认同、肯定。杨春时在《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指出:“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指对传统社会的根本变革,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相应的文化变革。”[1]逄增玉在《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对“现代化”概念剖析得更明确:“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它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在人类社会各个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巨大的、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物质经济、制度规范、价值取向、思想意识、精神心理等所有领域,并使那种合理化的科学和工业主义精神渗透、体现在这所有领域中”。[2]孙津在《打开视域——比较现代化研究》中这样界定“现代化”的定义:世界性的穷国追赶富国的过程。[3]虽然人们对“现代化”问题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但大体上可以形成共识的是“‘现代化是以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普遍参与等为内涵的。”新世纪以来小说中作家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体现了农民渴望现代化的情绪,农民形象较之以往更加丰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农民人物画廊,在整个农民形象发展史上具有转折的意义。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农民较之以往有了很大进步,不再是传统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中默不作声的服从者,甚至部分先进的农民已跨入现代化的门槛,但就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而言,其基本的传统特征并未彻底改变,中国以农业社会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的地位和中国农民的传统特征也没有彻底改变,尚未出现真正的当代农民形象典型。
新世纪小说所塑造出的当代农民形象也反映出了这一现实问题,体现了农民对现代化的渴求和自身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矛盾。孙惠芬的《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何顿的《蒙娜丽莎的笑》、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尤凤伟的《泥鳅》、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艾伟的《小姐们》、荆歌的《爱你有多深》、李肇正的《女佣》、项小米的《二的》等明显的“农民进城”小说无须多说,即使是那些一辈子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也在分享着现代化的成果。如夏天智(《秦腔》)从儿子那里感受到城市的气息;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中的悲剧产生的原因等等。“乡村关注,乡村人的生态关注,已经更其具备超越‘族而体现出‘类的性质。乡村的发展或沉沦业已跟城市息息相關,乡村的隐忧业已跟城市的隐忧形影相随,城市与乡村已经越来越无法规避那些共同的担当,城市和乡村物质和精神文明,在人类生存发展的前程中已经越来越成为相互制约、生死缠绵的共同体。”[4]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现实中,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根本问题,他们在追寻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已受到了作家的关注并体现在创作中,当代中国农民的新形象得到了展现。农民是现代化主体的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实行现代化的需要,更深层的也是他们自我的内在需要,对贫困生活的焦虑逼迫着他们急切地要摆脱这种生存的状况。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打破了传统的界限,他们认识到要想改变这种落后的情形绝不能再仅仅死守着土地,如果被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他们就很难接近以“工业化、知识化、都市化”为表征的现代化本质,也就难以真正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诉求。
然而,现代化的场域里并没有同等地考虑到占社会多数的广大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他们没有充足的资源和便利的条件可以凭借,政治、经济、文化上先天的不足使得他们很难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同时也就注定了他们必然的悲剧命运。然而这种种悲剧是被忽略的小人物的,甚至在某些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可笑的,就像人们对引生(《秦腔》)、程买子(《歇马山庄》)们的嘲笑一样。当悲剧在人们眼中失去了悲剧色彩并以喜剧的面貌出现时,正说明了底层农民的不被重视和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膜,这恰恰是最大的悲剧所在,也急需整个社会的关注。作家们意识到了农民的这一处境,也试图表现它,但是由于作家对中国当前农村、农民的变化和现状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所以作品更多地是以想象的方式和同情的态度对待农民,似乎只要表现出农民的艰难和对他们的同情就是真实的农民,并没有挖掘出造成这种苦难的真正内涵,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深度。
“农民,像是‘永远的,是常数,恒星,其沉默或笑意都像永恒。‘许多年了,他似乎总是一个模样,仿佛他不曾年轻过,也不能变是更老。(何士光《种包谷的老人》)这是一个已活了几千年且还将活下去的生命,仍然活着的‘历史,存活于现在的‘过去。”[5]作家们知道,比较起来,当代农民更或者说21世纪以来的农民较之传统无论是生存状况还是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死守土地,安于现状,他们在现代化、在城市的引导下有了现代化的追求,即使这种追求最终都几乎成为泡影,甚至追求到了还是同样无法得到平等的对待,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有了改变的要求和冲动。
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传统农民形象也许还依然栩栩如生,可是他们却再也站不稳脚跟,甚至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当现代化的成果和商品经济的思维主导了整个社会人们的头脑时,农村和农民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变化了的农民形象,放弃土地就成了他们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出外求学、进城务工、开办工厂,哪怕是采取非正常的甚至是极端的方式。夏风(《秦腔》)、程大种(《太平狗》)、王小蒙(《乡村爱情》)、国瑞(《泥鳅》)等是其代表。应该说,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的洗礼后,农民的头脑确实得到了开化,物质利益原则同样也受到了他们的吹捧,而这种吹捧的产生无疑是他们真正尝到了市场带来的甜头。 于是,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夏天义、夏天智、茅枝婆等传统农民被弃的无奈和必然,更看到了夏风、夏君亭、程买子、丁辉们的春风得意。
然而,从深层来分析,作家笔下的所谓的当代农民的骨子里更多甚至全部还是传统的质素,“新”只是表面上的、时间上的。比如,在小说中农民的根本地位并没有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依然传统、落后等等。所谓的当代农民是相对于传统的,其实他们并不现代、并不“新”,他们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也很少能够成功,即使成功了也很难被承认,就像王祈隆(邵丽《我的生活质量》)一样。
作品中这些当代农民形象的真实性问题同样值得人们关注,缺乏真正的农民立场是当代农民形象塑造很难有重大突破的罪魁。虽然,似乎新世纪以来这些所谓当代农民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产生了许多轰动性的效应,仿佛一夜之间中国进行了城市化的彻底变革,可当我们仔细思考时才发现这却是作家的功劳。政治注意到了农民地位的重要性,而农民又没有自己言说自己的能力,于是就给作家为其代言提供了可能。可是作家的代言常常是借助底层的声音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的不满;或者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的口吻来刻画乡村农民、审视农民,给予其怜悯。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精英意识促使他们来关注这一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然而,他们自己也找不到最终的出路,难以感受到历史发展的稳定逻辑和明晰的方向,这势必造成历史意识分裂的矛盾和惶惑,甚至常常异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被代言者。因此说,当代农民形象的真正出现还需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宋剑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2]宋劍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3]孙津:《打开视域——比较现代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4]黄毓璜:《文学与乡村》,《文艺评论》,2007年第1期,第50页。
[5]赵园:《地之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