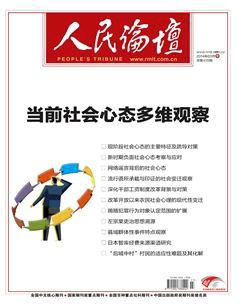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对流出地的影响—以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农村为例
王换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其发展快慢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我国要实现基本达到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城市化进程在所难免,这必然会引起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流动人口不仅给流入地带来众多影响,也给流出地带来了许多影响。因此,把握流动人口这把“双刃剑”,既要疏导流动人口缓解城市人口压力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又要合理管理以减少对农村人口流出地的不必要影响,这是城市化进程中迫切需要深刻思考并科学应对的问题。
流动人口对流出地的积极作用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地域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分工多样化,人口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其范围也越来越大。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不仅促进了流入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流出地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有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农民工占据着很大的比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流动人口改变了传统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春夏秋三季在地里干活,冬季赋闲在家的生活方式,更使得他们由原来的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的合理调配。外出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开阔了眼界,具有一定的市场敏感度,他们会告诉父辈们种植一些收益快的经济作物,改变了传统农业中只种植小麦、土豆、玉米等粗放型作物的做法,转而开始种植豆类、瓜类等经济型作物,使得农民收入大大提高。
缓解了农村贫困状况。全国各地农村到城市经商务工的人员大为增加,尤其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广大农村,由于缺乏矿产资源、土地贫瘠等原因,一直是典型的农村贫困地区,有一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城市,寻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经商务工所得收入,对改变他们原住地的贫困农村状况有所贡献。据调查,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除了靠老人或者妻子进行最基本的生产劳动维持基本生活支出以外,主要的经济来源都是依靠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收益。尤其是子女上学、盖房、婚丧嫁娶等费用支出,大多是依靠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收入支付的。在走访调查中有近30%的打工者,依靠自己在城市的收益,使生活在农村的家人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
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教厂滩村为例,全村大约有100户人家,人均土地占有量较少,土地收益不高,生活困难,很多家庭交不起学费致使孩子在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为改变贫困状况,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该村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包头市经商务工,男性往往学习一些技术,如泥瓦匠、装潢等;女性往往进入各大饭馆,做服务员或者厨师。这样,村中老人、妇女主要种地和养一些家禽等,年轻人在外地打工,这些家庭完全解决了温饱问题,经济上也比较宽裕,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以前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大都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自产自销,商品交换也大多是进行着简单的物物交换,物质生活极其贫乏。如今,在这些农村地区家庭液晶电视、冰箱、洗衣机、摩托车甚至汽车都成为日常用品,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由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大大改变了这里的贫困状况。
促进了流出地人口素质的提高。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初期,大多从事一些体力活,生活比较艰辛。然而,随着他们在城市生活与产业化劳动中眼界开阔了,见识增长了,总体素质提高了。特别是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许多人认为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乌兰察布农村地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学校规模小,设施也较简单,有的学校甚至只有一名老师。相对于流出地农村来说,城市教育设施、教育条件要强很多,打工人口的孩子往往能受到比当地更好的教育。所以,许多打工者家长宁可多花钱也愿意让孩子在城市读书,如今流动人口的子女在城市的中小学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在内蒙古包头市赵家营子小学,五个年级总共有24个班级,每个班级平均五十人,有的班竟有30多名学生来自外地农村,其中五年级特别的一个班,共有52人,有46人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这些在城市就读的孩子一般来说享受着比农村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流动人口对流出地的消极影响
诚然,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加速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为流出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但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我国广大农村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造成流出地农村的“萧条”。探讨刚兴起的打工潮对流出地的影响,形象一点就是农村成为“99、38、61”部队,即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近年来,农村流动人口的年龄越来越大,除了青壮年劳动力之外,只要能够在城市栖身,哪怕是扫大街、捡垃圾也不愿意务农的中老年人大有人在。这就导致广大农村呈现房屋破败、土地荒芜的局面,水利设施无人修缮,农村文化活动无法举办。以乌兰察布卓资县教场滩村为例,原本拥有100多户人家、400多人的村庄,如今只剩下76人,60多岁的村民在该村是最年轻的。中华民族传统的元宵节也组建不起曾经红火热闹的秧歌队,整个村庄呈现一片萧条之气。
流出地村民自治能力被削弱。村民自治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众的三个伟大创举之一。它在中国农村的实施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应,在农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由农民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新思路,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政治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可以说,拥有一定数量的素质较高的村民是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的良好运行离不开村民的积极参与。由于大量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年农民的外出,一方面村中可供民主选举的村委会成员候选人大大减少,这将直接导致村委会总体工作能力的下降,甚至有些地方村委会和党支部的负责人流动在外,村级组织陷于瘫痪;另一方面,留在村里的农民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有的甚至不会书写姓名,对民主程序和自治意义不太明白,容易导致民主程序流于形式,民主决策很容易异化为少数村干部的决策。对于大量的外出人口来说,所在村庄已经不再是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他们一年中很长时间都在城市里生活,他们与村庄及其村民之间的联系纽带越来越松弛了,而且往往不再具有原来的直接利益关联。利益关联是政治参与的根本和内在动力,外出村民对于和自己利益相关不大的村庄事务往往缺乏参与热情。流动人口在城市打工谋生,他们积累了能够在竞争环境中得以生存的经验。经济收入增加使流动农民感到自身价值的存在,在外务工经商的艰辛有时也让他们认识到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因此,相对来讲,他们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等也比流出地人口强。由于他们长期在外,村庄无法对其实行有效的控制,而他们回到村庄常常因为自己见过“大世面”或赚了钱而自视清高,不愿意接受村民自治组织管理,这使得村民自治成效受到一定挑战。
对流出地计划生育工作造成了困难。流动人口对流出地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超计划生育现象。当今农村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方法较为单一,普遍采取的方法是超生罚款,其结果就致使一些农村妇女怀孕后,为逃避罚款而加入流动人口行列。尤其是在某些农村,重男轻女现象还很严重,有的家庭不生男孩不罢休,在当地或是小城镇比较显眼,也容易被发现。因此,他们往往临时栖身于“三不管”地带,生下男孩后再返回原籍。这不仅增加了中国的人口压力,还使这些家庭日益贫困,孩子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这个问题也给城市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提出了挑战,重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利国利民。例如,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赵家营村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经过调查,该村专门设置了一个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统计育龄妇女的情况,每季度查一次,并建立了生育档案。他们耐心宣传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那些违反政策的夫妇,他们往往与其家乡联系,双方合力说服解决,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不利于流出地风俗习惯的传承。我国已经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物质及精神生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相对于城市空巢老人,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却另有心酸之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后,随之举家前往城市,他们忙于自己的生计,往往只是在春节才有时间看望老人,平常靠电话和老人保持联系,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孝文化以及养儿防老心理是格格不入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亲情疏远。近年来,出现了一种较反常的“隐形啃老”现象,那就是年轻人在城市过自己的小日子,留守老人在家里务农、饲养牲畜,等到秋收之后,辛苦的父母开始到城里给自家的孩子送农作物、猪牛羊肉等,短暂的团聚也只能是暂时排解他们的寂寞。如今我国大部分农村昔日的淳朴民风已不再,外出务工的年轻一代已基本适应了城市的生活节奏与习惯,他们一般已经不适应“寂寞”的乡村生活,甚至把生活在城市里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带回农村,有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全村赌博的局面,这也不利于新农村文化的建设。
城市化进程中流出地自身发展的路径
城市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表明城市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容纳力是有限度的,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况且对于流出地来说,也需要更多有能力、有文化的青壮年参与到当地的建设中来,以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双赢。
减免农业税政策的启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然而,近2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远低于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尤其是1998年以来,这一趋势表现的更加明显,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长7%左右,而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还不到2.5%,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免农业税是农民减负增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客观要求。减免农业税受社会大多数成员—农民的支持和欢迎,同时也有利于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减小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减免农业税,农民自然增收,立竿见影,一目了然,且给农民积极性以动力的作用也不可小瞧。
如前所述,乌兰察布地区农村是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口流动最多的地区。由于乌兰察布地区经济不发达,特别是农村和牧区全年的收入除了交纳农业税后,只能达到温饱,导致大多数青壮年流入城市打工。自从乌兰察布积极落实各项支农政策后,粮食直补、退耕还林现金和粮食折现补贴及时足额到位,切实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促进了农村牧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农业方面的优惠政策,也使一些在城市境遇较差的农村流动人口返乡务农。以该地区十八台乡为例,该地气候干旱,农业收成差,过去这里的农民种地扣除农业税后一般只能维持温饱,于是纷纷到城市打工赚钱,有的甚至举家搬至包头居住。减免农业税政策出台后,一部分在城市打工而且很难融入城市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开始怀念农村并不富裕但安逸的生活,不愿意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打拼,愿意回家乡务农。由于没有农业税负担,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他们除了耕种自己的责任田外,还租种别人的土地,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从这一惠民政策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外出打工很多都是出于无奈,政府只有真正关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结合实际,制定适合当地发展的政策、措施,才能有利于当地的发展。
大力发展流出地生产力是根本对策。流动人口用智慧和汗水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但在这些光鲜的背后,却是背井离乡的辛酸。实际上,流动人口内心难以真正融入其打工的城市,在现实和心理差距的刺激下,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对流动人口心理的调查中,笔者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流动人口不管在城市有无正式工作,他们都认为自己没有完全融入这个城市中,他们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怀念老家新鲜的空气、宽敞的住房。可以说,如果他们家乡的经济同样发达,他们宁愿返回故土,而不愿意生活在别人的城市中。而大量人口的流失,致使流出地青壮年劳动力急剧减少,对流出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经济越落后,人口流失越严重,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越小,经济更加落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流出地的生产力,增强对当地农民特别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吸引力。而且在外来务工人员流出地保有稳定的一定数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对于发展流出地农业生产,普遍提高当地农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城乡和谐发展之根本。
积极推进流出地新农村、小城镇建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政界、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给农村提供了相对优惠的政策。新农村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只有积极推进流出地的新农村建设,才能尽快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才能不断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但是,缩小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真正实现农民在保险、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加快农村地区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流动的选择路径才可以更多一些,尤其是改变过去依靠外出务工成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状况,使得留在当地的人员也可以有比较好的经济收益,人口流出地会吸引更多的青壮年留在家乡,发展新农村,建设小城镇,为当地经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要想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引导人口的有序流动,必须大力发展流出地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吸引更多的本地区优秀人员投身于家乡生产建设。
综上所述,城市化进程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的过程。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并不是到处出现城市,而是要使全体国民享受现代城市的一切城市化成果并实现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文化教育素质等的转变,唯有此,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和农村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