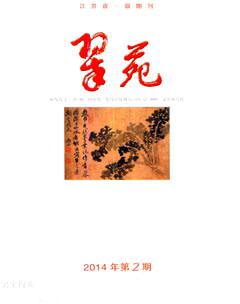第八站:伊朗
李一芾
“咣”的一声,酒店大堂的门被推开,走进来一个卷毛、一个冲锋衣、一个瘦高个。
正在上网的我抬起头,“おはよう!(早上好)”卷毛对我说。
“おはよう!(早上好)”我本能地复读。
“にほんじんですか?(你是日本人吗)”
“ちゅうごくじんです(不是,中国人)”
卷毛和冲锋衣齐刷刷看向瘦高个,“What? Korean? Japanese? Chinese?(怎么了?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瘦高个一脸茫然。
“Yes! Chinese!(没错!中国人!)”我说。
他笑了,“说中文!”
到达设拉子的第二天清晨,四人组合就这么诞生了。
瘦高个叫石头,内蒙小伙,在车站碰到这两个日本男生,就跟他们一起来找酒店。冲锋衣叫Tom,卷毛没有英文名,于是,我叫他们俩Tom and Jerry,猫和老鼠。
存了行李去景点,打了两次车之后发现设拉子地方不大,于是决定用脚丈量。
大家一路嚷嚷,伊朗南部就是比德黑兰暖和,石头突然说“哎?我们去玩那个吧!”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路边竟然有一座攀岩壁!三个男生兴奋得大叫,边跑边脱鞋,直接冲了上去,爬到一半被一位穿制服的大叔叫了下来,说没有安全绳你们爬太高危险。
三人悻悻地回到地面,大叔笑呵呵的:“你们赶时间吗?要不要来喝杯茶?”
跟着大叔穿过停车场进屋,才发现这里是个消防局!一楼是办公室、工具间、厨房和客厅,二楼是值班宿舍。大叔去烧水煮茶,一个叫默罕默德的年轻人招呼我们到火炉旁边坐下。默罕默德说,伊朗的消防局除了救火,还负责紧急救援,外面的攀岩壁是他们用来训练的。他问我们是不是第一次来伊朗,都走过了哪些地方。于是我听到了伙伴的旅行故事。
石头是辞职后出来游荡的,在东南亚和非洲度过了大半年,因为签证问题无法继续穿越中亚,伊朗是他此行的最后一站。我问他为什么要放弃在央企的稳定工作?他说,不想在20岁的时候,体验50岁的生活,没悬念没过程。我说真佩服你的勇气,我这趟春节假期结束就得回去上班,乖乖赚下一笔旅费。Tom和Jerry是搞舞台音乐的,从东京出发,走过了韩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一路到了伊朗,此后将经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返回日本。Tom很得意地跟我说,我还学了一句中国话哦,“兵马俑”,用来哄女孩子会不会很感动?我心想这是怎么个感动法?Tom说这是我爱你的意思对吧?我和石头瞬间笑趴:“啊哈哈哈哈哈!哪个坑爹的教你的?”
回到酒店已是晚上,我开着房门透气,行李扔得乱七八糟,住我对门的客人回来了,朝我这儿望了一眼“呵呵”地笑。“Sorry for the mess!(抱歉我这里一团糟)”我很囧。“Never mind, Im worse.(没关系,我的更乱)”他安慰我。
这位邻居是伊朗人,说他去过中国,但是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容易招揍:“你叫什么名字?”“尼玛!”没错,他的名字就叫Nima。
Nima毕业于设拉子大学,现在为某个代理机构工作,喜欢旅行,喜欢摄影。这人用中国话说是个自来熟,认识不过30秒,我就被他拉去拍屋顶的日落。等他专心拍完,低头一看穿着夹脚拖的我在寒风中搓着手上蹿下跳,心生愧疚,于是一脸狡黠地问:“我有威士忌,你要不要喝?”我说伊斯兰教不是禁酒么?他说他偷偷藏的。聊天中,他又告诉我,其实他的本名叫霍梅尼,因为不喜欢与那位发动伊斯兰革命的领袖同名,才改叫Nima的。我问为什么,他说霍梅尼的宗教治国,让年轻人们丧失了发展的机会,也生活得更压抑。
二战后,巴列维国王强力打开了封闭千年的国门,让妇女摘掉头巾、拥有选举权、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也让年轻人们看到了外面的天空。而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又让伊朗回到了神权,在西方列强30多年的经济制裁之下顽强地生存。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权,在伊朗人心中的评价褒贬不一。虔诚的宗教徒认为,伊斯兰教法就是伊朗一切法律的基础,妇女必须包裹头巾、衣服长度必须盖过臀部,禁止饮酒,禁止同性恋,禁止与异教徒通婚,不承认多神教徒、异端信徒和无神论者的基本人权;而和Nima一样的年轻人,却都渴望自由的生活,希望能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一样,有机会看看多彩的世界。我提醒Nima,“听说伊朗有很多便衣间谍,公开场合说这些话你不怕么?”他笑着看看我说,“希望你不是。”
当然不是。我只是游客,只需享受伊朗最有趣的一面。
包车去波斯波利斯的路上,剃了个鸡冠头的年轻司机把车窗都打开,音乐开到最大声,我们就这样一路飞驰,听着嗨歌、看路边走过的黑袍飘飘……这种保守与开放共存的和谐感,没到过伊朗的人是绝对体验不到的!
鸡冠头给我们的“惊喜”可不止这么简单。
设拉子的郊外,我们瞻仰完波斯帝国的遗址,爬到旁边的山头上等看日落。风很大,穿了棉衣还是哆嗦,鸡冠头就穿了件短袖,一路跟着我们。他不会说英语,我们就比划着示意他可以回车里等,我甚至还画了图给他看,他坚决不肯,表示自己不冷。我们心想真是个怪人,也就没理他,四个人开始摆各种Pose搞怪合影,一晃就是三个小时。
回到设拉子,结账,原先谈好的80万里尔一车,变成了80万一个人,320万一车。我们恍然大悟,这小子宁愿冻死也要盯紧我们,敢情是怕我们跑路了没得宰啊!Tom和Jerry没搞清楚状况已经在掏钱,被我制止,跟石头并肩开启战斗模式和鸡冠头理论,当然是英语VS波斯语的鸡同鸭讲。僵持不下,石头往椅背上一靠: “Go police(报警)!”
警察是个腼腆的小年轻,讲句英语要翻半天白眼,最后无奈地两手一摊:“双方都让步一点吧?”。鸡冠头转过头说那就300万,“No!”280万,“No!”250万,“No!”他做出了一脸“我都这么吃亏了你们还不愿意”的表情。我们不愿意再和他耗下去,四人一使眼色,“我们知道市场行情,喏,这里是100万,要就收下,不要我们就一分钱也不给了!”甩门走人。
在街上绕了一圈,确信鸡冠头没跟着我们,这才安心地去找地方犒劳肚子。石头很得意,“在伊朗天天跟他们China good, USA not good,今天居然能迸出impossible这种高级单词了!紧急状况下果然智商会爆发啊!”引来大伙的无限鄙视。
吃完最后一顿四人晚餐,Tom和Jerry坐夜巴士去伊斯法罕,石头去卡尚,我在设拉子多待一天。互相留了联系方式,约定回国后分享照片。很不舍,但终究要各奔东西,旅行中的别离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回到酒店,正想着明天一个人去哪里晃晃,手机响了:“菲菲你还在设拉子吗?我们来啦!”是和我同一班飞机来伊朗的小K和大叔。哈,送走一拨又来一拨,热闹!
第二天跟小K和大叔碰头,他们听说我很闲,就怂恿我跟他们再去一趟波斯波利斯,我居然脑袋一热答应了。在山脚下休整时,碰到三个伊朗女生,要求跟我们合影。其中一个金发的姑娘蹦到我面前:“你觉得我好看吗?”我说“嗯,你很漂亮啊”。她很受用地继续说:“我要找男朋友,中国男朋友!”我笑出了声,指着小K和大叔说,“那你挑吧!”大叔说我儿子都上学了,剩下小K吓得往角落撤退,“伊朗不是很保守的嘛?现在这个是什么情况?”大叔掐指一算,说估计是平时教法太严,物极必反了,今天碰上你这个有缘人,定要把握机会!最终金发姑娘还是要到了小K的手机号码,满意地跟我们挥手再见。
回城的路上开始飘起鹅毛大雪。小K收到一条短信:“How are you my love?(亲爱的你好吗)”哇,一段异国情缘要开始了吗?
当天晚上我去了伊斯法罕,小K和大叔去卡尚,他们在那里遇见了石头,据说当大叔掏出西湖龙井和20包榨菜的时候,石头热泪盈眶。
巴士停靠在伊斯法罕车站的时候,满城银装,新闻里播报,伊朗50年来首遇大雪。这么有情调的日子,不如去看场伊朗电影吧!
影院门口贴着波斯文放映表,我指着最近的一个时间对售票员说,我要看这本!拿着票进门,茫然地东张西望,工作人员走过来示意我在大厅耐心等待。
原来,整个影院只有一个放映厅,一场电影轮回放。等到前面一场散了,他们立即带我进去,给了我最好的座位。
伊朗的艺术造诣很深,巨幅街头壁画,屡屡感动世界的电影……可惜,我看的这一部,走了韩剧路线,俩人相爱后女主车祸,好不容易救回来了,男主又病死,真是很狗血、很苦情。唯一的亮点是观众,每当出现男主角的特写镜头时,他们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口哨,并在背景音乐响起时整齐地打拍子。我想印度人民一定能理解这种投入的娱乐精神,他们甚至会在坏蛋死掉的时候全场起立欢呼。人比电影有趣!
……
10天后,回家的飞机上,旅行中的美好片段像幻灯片一样从脑海中清晰闪过:
德黑兰夏宫,背着行囊爬坡累到虚脱,递给我一颗糖的拐杖爷爷。
德黑兰机场,一个人候机飞往设拉子,给我苹果当夜宵的朝圣大家族。
设拉子车站,大雪封路大巴延误,陪我在寒风中等待发车通知的眼镜小妹。
伊斯法罕街头,寻找三十三孔桥迷路,把我送上公交车并交代司机提醒我到站下车的姑娘。
伊斯法罕四十柱宫,想再一次进去欣赏,记得我昨天来过免了门票的工作人员。
德黑兰地铁,没有英文报站,提醒我去机场要中途换乘的女大学生。
还有一路上遇见的其它中国旅友,和我携手闯荡德黑兰街头的四季、带着小兔玩偶一起旅行的伶伶、每天买菜做饭的Judy和大厨姐姐、拄着双拐周游世界的林家大叔……
谢谢你们,因为你们,我的伊朗之行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