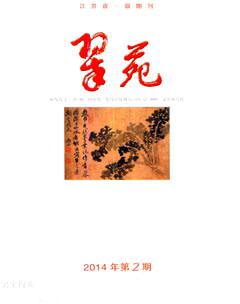空心
惊 蛰
母亲包饺子的姿势很特别,她是先把饺子皮垒好,形成了饺子的初步轮廓,然后再灌进饺馅,这倒有点像建筑工地上的灌桩,先用钢筋扎好模子,而后灌进水泥混凝土,等到收浆后再拆去外面的模子,也就完成了整个浇筑过程。当然,饺子跟灌桩是有本质区别的,饺子“拆模子”的过程先是在人的嘴里,而后再蔓延到食管、肠胃。
母亲她老人家认为,包饺子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其实苏中里下河一带,并不像北方那样流行吃饺子,主餐还是以米食为主,包一次饺子,那也是打牙祭式的尝尝鲜。可这个鲜也不是常常尝到的,当然,我的这句话可能说得有点语病,你也许会问:能经常尝到那还是鲜吗?
至少,在我小时候,母亲一年也许只能包上一回饺子。只要家里包铰子,那可热闹了,包饺子的前一天,母亲总要亲自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回娘家一趟,很郑重地向娘家人发出邀请:明天我们家包饺子,你们来吃饺子吧。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当然,亲戚家包铰子,我们一家也能收到邀请。这么说吧,要是哪家包饺子,就像家里娶媳妇一样,能请来的亲戚都会请来。
我就是在一场饺子盛宴上认识小芳的。那天,村里的李大海家包铰子,向我发出了邀请。其实,这么说有点抬高了我自己,准确地说是这样的:李大海向母亲发出了邀请,母亲附带着我去蹭上一顿。
我兴高采烈地去李大海家吃饺子的时候碰上了一件更加兴高采烈的事,那就是遇见了小芳。小芳那年也不过十二三岁,那天梳了两个羊角辫,还插上一个缀着蝴蝶的发卡,穿着一条白底红花的连衣裙,仰脸一笑,露出一对迷人的小酒窝。要是走在花丛中,她就真像一只花蝴蝶,能煽动着翅膀飞起来。
我正想走过去跟“花蝴蝶”打招呼的时候,不想一只脏兮兮的手伸过来,抢走了“花蝴蝶”。我很生气,但定睛一看,气又消了。跟我争抢“花蝴蝶”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大海的儿子李小虎。李小虎长我两岁,在村里却是个小霸王,他的老子李大海是队长,他也像是队长似的,总对着我们大呼小叫,我呢,跟他碰在一起,算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干脆躲着他走。
李小虎拉走了“花蝴蝶”,我也只能干瞪眼。不过我也挺机灵的,通过窥听大人们的谈话,呵呵,在此处用“窥听”两个字显得有点高深莫测,大人的谈话哪会避嫌我这个小屁孩呢。不过那时我刚刚看完了一本没有封面,里面还被撕去N张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我经常把自己幻化成福尔摩斯,我那时用“窥听”两个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把四处窥听到的话语串连起来,终于知道了“花蝴蝶”的来龙去脉:“花蝴蝶”的名字叫小芳,是李大海老丈人家邻居的孩子,李大海请老丈人来吃饺子时,顺便也把小芳的父母请来,小芳也就跟着来了。
我走到李小虎和小芳的背后,李小虎正绘声绘色地讲着什么,小芳“咯咯咯”地笑,她的笑声像极了我家刚孵出不久的一只小母鸡,富有挑战意味。我趁他们不备,猛地叫了声:小芳。
小芳不防备,“哎”地应了一声,还转过头来看我。小芳的眼睛像春花绽放,看得我心都醉了,那个时候,我还没学会喝酒,也不知道醉是啥滋味,但我没办法用别的词来形容彼时我的心情,我权且借用了大人们的醉来形容。李小虎也倏地回了头,他的眼睛里能蹿出火苗,如果我是干柴,我能当场就烧起来。可我不是干柴,烧不起来,自然也不必理会李小虎。
小芳,你真像只“花蝴蝶”。我痴傻般地看着她,把对小芳的形容脱口而出。
小芳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她还站起了身子,张开了双臂,挥动着连衣裙一扇一扇的,得意地说:对,我就是“花蝴蝶”。
这本来是一个如诗如画的气氛,冷不防被李小虎放了一把野火,他粗声粗气地说:酸,我酸得牙都要掉了。说着,还作势俯下身子作找牙状。牙当然没找到,因为牙还长在他的嘴里,并且下面的牙床咬住了上面的嘴唇,我知道那是李小虎发狠时的模样,他冲我们发狠时都是这副模样,像极了他的老子李大海。他接下来的动作,就是冲我们挥拳头,果然,他就真地把拳头扬在空中冲我挥了两挥。
我罕见地没有屈服,这让李小虎十分不爽。不过,小芳似乎知道尊重李小虎这个东道主,毕竟她吃的是李小虎家的饺子。这丫头,也知道吃人家的嘴软。她朝我又“咯咯咯”三声,就又转头对小虎说:小虎,你刚才说到哪儿了,接着往下说。
李小虎狠瞪了我一眼后,又绘声绘色地讲起来,我听得出来,他讲的是《西游记》里的一段,“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那一段,还是我讲给李小虎听的,他狗日的活学活用,竟勾起了小芳的兴致。我多么想对小芳说,小虎讲得不对,让我来讲给你听。但我还是没讲,那个时候,我不是怕李小虎的拳头,他的拳头也硬不到哪里去,我领教过,打到我身上也就疼一会儿的工夫,又打不死人。可我还惦念着他家锅里的饺子呢。“花蝴蝶”与饺子比起来,我还是偏向选择了饺子,孔子云:食色性也。虽然我后来才知道孔老夫子的这句话,但我早就实践过了,深有感触。
那天,从李大海家吃完饺子回来的路上,我跟母亲说:咱们家也要包饺子,也把“花蝴蝶”请过来。母亲吃惊,哪个“花蝴蝶”?我说是小芳。母亲又问:哪个是小芳?我说:小芳就是小芳呗。母亲可能真地记不得是哪个小芳了。在李大海家吃饺子的人很多,小芳只是众多孩子中的一个。母亲实在想不起来,她就不理我了。她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今天是惊蛰,过些天要到清明了,清明那天你爸回来我们就包饺子。
对清明我没在意,我牢牢地记住了惊蛰,因为我认识小芳的那天就是惊蛰,很有纪念意义。
芒 种
在县城见到小芳的时候,如果不是她叫我,我真差点与她擦肩而过。
小芳那天穿着一件浅黄色条纹的连衣裙,两只羊角辫不见了,改成了大波浪式的卷发,嘴唇红得像一团火,涂的是那种红得令人眩晕的唇膏。耳朵里还塞着耳机,她见我盯着她的耳机看,就不好意思地从小坤包里掏出一个随身听。
她说,她正在听邓丽君的歌,一曲《甜蜜蜜》她反反复复地听了好多遍。
看着眼前的小芳,我才惊觉距离我们吃饺子的那些日子已经是七八年了。我进了县城读了中专,又很快毕业分配进一家国有企业。偶尔回老家时,也装着无意地打听小芳的一些消息,母亲说,小芳高中一毕业,就到上海去学美容去了。
那次见到小芳,她匆匆地从上海回家,过了两天,又匆匆地从县城搭车回上海。我本来想请她吃顿饭的,但她抬手看了看腕表,说算了,时间不多了,我还要赶车呢,下次吧。
看着小芳袅袅婷婷地走进汽车站,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我还有些恍惚,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也许就是一次梦游吧,眼前的小芳怎么不像多年前的那只“花蝴蝶”呢?
周日,我回了老家一趟。在村头的小桥上正好遇上了李小虎。李小虎长得高大彪悍,留着寸头,开着一辆异形拖拉机,正帮镇上的水泥厂送货。“每天就挣几十块钱吧,你一个月拿多少钱工资?”李小虎拦下了我,一直追问着我的工资收入,似乎有比试一番的样子。我不说,确实也不好意思说,我的月工资也就相当于李小虎干几天的活儿挣的钱吧。
李小虎仍不甘罢休,还在紧咬不放。他的拖拉机像个庞然怪物,就堵在村头的小桥上,来来往往的人被这么一堵,排起了长龙,叫骂声响成一片。看来我不妥协一下,李小虎就会这么一直堵下去。我只得告诉他实情,他听后一笑,在我的肩头上狠狠地拍了两下。“不错,多多少少也算城里人了。”我听出了李小虎话中的揶揄之意,我不禁有些脸红,后悔自己照实说了。
李小虎终于将庞然怪物挪到了桥下,让出了一条道给那排成一行的“长龙”,“长龙”依次穿过我和李小虎身边时,他们有的朝李小虎瞪瞪眼,有的还指桑骂槐地说上几句:这桥也造得太窄了!有的则朝李小虎的庞然怪物看看,摇摇头叹着气走开。
我也要急着离开,李小虎却依然拉着不放,还故作高深地说:小芳前些天回来了。我淡然回答:回就回来呗,这儿本来就是她的娘家。
李小虎不满意了,他叼起一根烟来,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没接。李小虎眼睛瞪大了,怎么,做上城里人就嫌烟差?我赶忙解释,你的烟档次不低了,我们厂长也就抽你这样烟吧,但我确实欠学,不会。
我这么一说,似乎又满足了一回李小虎的虚荣心。在接不接烟的问题上,他不再坚持了。他话头一荡,依然回到了小芳身上:小芳打扮得像个妖精。想起在县城车站偶然遇上的小芳,我不得不承认李小虎的描述是正确的。
你见过小芳?李小虎冷不丁地兜头一问,吓了我一跳。我赶紧摇头否认,还加了一句旁白:进城后,我就没见过她。
我为什么成心在李小虎面前撒谎?我自己也搞不清理由。我感觉这次的桥头相遇,我已经被李小虎说不出来的气场给震住了,除了妥协和迁就外,我竟然找不到一招制敌的法宝。
李小虎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会儿,深重地呼出一口气,那烟雾就从鼻腔里喷薄而出,要不是我扭了扭头避开,烟雾就能直射我的脸上。他低声说:小芳变了,不是以前的小芳了。还没等我搭腔,李小虎突然一拍脑袋,光顾跟你说话,差点忘了送货的大事,改日我请你吃饭。
说完,李小虎扭身跳进了他的庞然怪物,“突突突”地扬长而去,我站在后面看着他开着庞然怪物走远,若有所思抑或若无所思地出了会儿神。
那天下午,母亲一脸阴沉地回到家。劈头就问我:你是不是见过李小虎?我茫然地点头:怎么了?母亲脸色更阴了,你是不是告诉他你工资的实话。我依然点头,不明白母亲话中的含义。
母亲说,李小虎那家伙四处说,说你白读了几年书,进城了,工资还没他干几天的活儿多。我心里一紧,坏事了!母亲的心劲一向很高,自从我进城读书、工作后,母亲在村里走路的姿势明显轻快了许多,说话的腔调也调高了八度。我后悔得要死,真不该对李小虎实话实说,害得母亲估计好一段时间不能昂首挺胸了。
时过不久,我接到李小虎打到厂办的电话,他先东拉西扯地闲聊了一会儿天气,而后见火候差不多了,单刀直入:小芳又回来了,这次是一个看上去有四十岁的老男人陪她一起回来的,还开了一辆小汽车。
我心里也是一紧,老男人?小汽车?这些跟小芳挂上了钩,潜意识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李小虎不屑地说:我以为小芳出去能找个比我强得多的城里人,哪知道却找了个老男人。
你是不是仍在打小芳的主意?这句话说出来我就后悔了,我担心李小虎受不了我的言语刺激。但李小虎的抗击打能力却出人意料地强,他在电话那端豪爽地哈哈大笑,小芳就是个妖精,我对她留恋?可能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有个对象,比小芳不知道漂亮多少呢,你就等着吃我的喜糖吧。
果然,到了第二年夏季,我记得那天是芒种。李小虎真个请我吃了喜糖,而且还拉着我去吃了喜酒,不过说真的,李小虎的新娘并不如他所描述的那般漂亮,看上去很一般,我把她跟小芳做了个对比,根本没有可比性。直到此前,我才算彻底明白了李小虎说小芳是妖精的话来,挺有哲学味的,嗯,李小虎看来真算得上一个乡村哲学家。
我听说李小虎结婚前,也请过小芳的,但小芳没回来。那么多人中,我四处没寻觅到小芳的身影,有点怅然若失。
白 露
小芳是在那年秋季出的事。小芳出事的消息还是李小虎告诉我的。那天李小虎专门开了他换了的大货车“呼隆隆”地拐进了我的单位,守门的保安还以为是给厂里送水泥的呢,也没查问,直接就放他进来了。
李小虎就如他的大货车一样冲进了我的办公室,也顾不上办公室还有人,就咋咋呼呼地嚷开来:小芳……小芳出事了。
我一惊,从椅子上“呼”地站起来,引得同事对我侧目相看。我又下意识地坐回了椅子,压抑着内心的激动不安,故意用平淡的语气问:小芳出啥事了?你慢慢说嘛。说着,我还是起了身,给李小虎倒了杯茶。但李小虎没要我递过来的一次性纸杯,他掏出一个不锈钢的杯子,说,我自己有。他自己转身给杯子续了水,然后,拉了张椅子,跟我挨近着坐。
李小虎放低了声音: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你这个秀才白当了,村里的事都不知道,还天下事呢!
我惭愧地将笔在手中不停地翻转,我不是惭愧我这个所谓的秀才不知村里事,我是惭愧,我怎么从小到大,都被李小虎身上的那股气场所震慑呢?论文化,李小虎才混了个初中毕业,论经历,我在厂里都做到办公室主任了,而李小虎仍只是一个厂子的送货工,但他凭啥就那么强的气场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氛围中已经退居其次了。我当时最迫切的就是想知道小芳,那只我眼中的“花蝴蝶”,李小虎眼中的“小妖精”究竟出了啥事。李小虎喝了一口茶,还呷出了很响亮的声音,再次引得同事们的惊诧。
李小虎卖完了所有的关子,似乎看把我的胃口调得差不多了,这才像个说书艺人般地讲开了。他说小芳在上海傍了一个老板,做了小三,后来那个老板的老婆知道了,就找人把小芳痛打了一顿,把一条腿给砸断了,现正在家里养伤哩。
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又喝了一口茶,那茶很烫,但李小虎却牛饮一样,竟然一口就让他的杯子见了底。喝了茶,他又续着上一段的“下回分解”,神秘地说,小芳给她老子的钱,盖起了楼房。你瞧她老子,盖了个破楼房就张狂得不行,到处说他的闺女有本事,赚了钱给家里盖楼房。其实,赚个屁,不还是靠她的妖精本领,让那个老板花的钱!
李小虎说到这儿开始咬牙切齿。我喜欢看李小虎气急败坏的样子,因为他的气急败坏,我把本想要说的话咽回心里,笑着问李小虎:这么多年了,你儿子都快打酱油了吧,怎么还对小芳放不下?
屁,我放不下她?她就是一个妖精,能勾引别的男人,却勾引不上我。李小虎更显得气急败坏,我很享受他的失态,还想继续用话题挑逗他的失态,但李小虎却站起了身,说是要送货了,转身告辞。我要送他下楼,却被他摁坐进椅子,坚决不让我送。在我还没起身的时候,李小虎已经风风火火地走了。
送走了李小虎,我想我该回一趟老家了。我随便找了个借口,跟妻子说要回一趟老家。妻子也闹着要跟我回去。她总是埋怨城里的蔬菜太贵,害怕超市卖的大米农药残留过多,每次回去,她都像个下乡扫荡的鬼子兵,不手提着肩扛着老家的大米、蔬菜进城绝不罢休。对于她的扫荡手段,我也责怪过几句,要考虑到父母劳作的艰辛,怎么能把他们的劳动果实大运动般地说往城里搬就往城里搬呢。妻子振振有词:我又没有实行“三光”政策,他们两个老人在家,吃得了那么多吗?妻子的反驳,我并不是无理由可对,但是我不能讲理由,因为越讲理由越说不清理由。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说,沉默的人有三种状态,其一是没水平说,其二是有难言之隐不便说,其三见怪不怪不想说。我想我属于第三种状态吧。
我还是孤身一人悄悄地回了老家。从母亲的口中,我却听到了另一个关于小芳的不同版本:小芳与人合伙在上海开了家美容店,有个男客去店里洗头,那个男客却不老实,对洗头的小妹动手动脚,小芳就说了那男客几句。那男客大怒,打手机叫来了几个混混,把美容店给砸了,还将小芳的腿打出了粉碎性骨折。
我问母亲这话是听谁说的,她说是小芳亲口说的。到底哪个版本是事实真相,我无法求证。我说我要去看看小芳,母亲一怔,她知道吗?母亲所说的她就是我的妻子,我摇摇头,这事哪能让她知道,知道了还不发生家庭战争啊。母亲点头说也是,你要去就去吧,小芳这孩子也挺可怜的。
我去的时候,站在病房门口,里面有好几个病人。我探头探脑地看到了病床上的小芳。她倚在床头,脚上打着石膏,在看着窗户外的一棵树发呆。小芳,我讪讪地叫了一声。见到我,脸色有些苍白的小芳咧开嘴笑了,一笑起来,两个明显的酒窝依旧那么让我心里一紧。
我局促地站在病床边,竟然把反复打好的腹稿全忘了,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倒是小芳笑吟吟地示意我坐下。我就中规中矩地坐到了她的床边,眼神从小芳姣好的脸容上扫一眼就看向了别处。
小芳说,时间过得真快,我还记得到你家吃饺子时的情景呢。那次,你盛的第一碗饺子就端给了我,还悄悄地跟我说,这碗饺子是你自己包的。但我实在不敢恭维你包饺子的水平,饺馅包得太厚了,都没熟透,吃一口,一嘴的青涩味。
小芳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但小芳那时却吃得津津有味,并没有表现任何不适状态。要不是小芳今天说出来,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她对你好吗?小芳问。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道怎么回答。为了摆脱这尴尬的氛围,我问小芳,这么多年了,怎么不找个人嫁了,一个女人在外面闯荡,不容易啊。
我以为我的话会让小芳唏嘘一场的,其实她并没有,她依然带着笑说,我中意的,人家并不中意我,人家中意我的,我又不中意人家。一切随缘吧。说完这些,我们竟无语了。
小芳裹了裹了薄被:到深秋了,天气真有点儿凉。我掏出手机看看时间,应了声,是啊,今天正好是白露哩。
大 雪
李小虎犯事了,他酒驾撞了人,撞人后还跑了。交警的警车追上了他,他还仗着酒劲跟交警耍横。这一下,麻烦越闹越大。李小虎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那辆大货车也被卖了,赔偿了医药费。但伤者的家人还不罢休,三天两头就跑到李小虎家闹。
李小虎的老爹李大海英雄了一世,没想到老来却得了这个下场,一气之下,中了风,李小虎的老婆既要照顾病倒的公公,又要照顾上学的儿子,还要应付上门闹的伤者家属,她终于厌烦了,干脆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说是外出打工,但一去就沓无音信,纵使李小虎出狱了,我估计她也不会回来了。
李小虎出事的那个冬天,小芳终于找到了一个上海男人把自己嫁了。小芳的婚礼是在老家举办的,30多岁的小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不少。而那个上海来的新郎,小芳说只比他大几岁,但是看上去却长得比较急,有四五十岁的样子。我母亲吃完喜酒后回来的路上还跟我探讨,说那个男人一定比小芳大好多,肯定结过婚的。我却平淡地回应着母亲,这年头,只要真心相爱,年龄,是否有过婚史都不重要了。
母亲很认真地问:年龄相差那么大,就不怕有代沟?我很惊讶地看着母亲,母亲大字识不了几个,却能说出“代沟”这样的话。不过,我很快找到了答案,母亲一定是活学活用的,我儿子也就是我母亲的孙子,她一直很喜欢带着,但我老婆却不让她带,说虽然隔代亲,胜似命,但老人带孩子,那么大的年龄差距会有很大的代沟。我反驳她:我们不也比儿子大两轮吗?难道就没有代沟?
这番话一定是被母亲听到了,母亲一定也很刻意地记进了心里。
小芳结婚的动静很大,小芳离婚的动静同样很大。离婚是那个上海老男人折腾出来的,离婚是在第二年冬天,小芳生下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后提出来的。那个上海老男人说这个女儿不是他的血脉,非要去做亲子鉴定不可。小芳不同意,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吵得凶了,小芳就抱着女儿回了娘家。我在老家遇到过小芳。不到两年,她看上去气质没那么好了,虽然仍衣着时尚,漂亮依旧。但是脸上的笑容却几乎没有了。一见到我,小芳显得有些絮絮叨叨,她说,那个男人对她不好,把她的手机、QQ密码都要过去了,时不时地就查,一查就得闹出点动静……
小芳同样的话其实不光对我一个人说过,她对村里的小姐妹说过。可巴掌大的村子,一时间,关于小芳的花边新闻就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小芳是个苦命人,人到大龄找了个男人还对她不好;也有人说小芳太过于放荡……冬闲,闲得没事,打打牌,串串门的时候就议论起小芳,越议论气氛越热烈,有时因为某个观点而争执,由争执又上升到争吵。那年冬天,咱村里就因为小芳而空前地热闹起来。
大寒的那一天,小芳终于离了婚。办理完所有的离婚手续,小芳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离了。对于这条短信,我想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回复。没办法回复,只能给她打了个电话。电话中,小芳又问我:你跟她过得好吗?我回答:说不清,就这么混一天是一天吧。
我们活在世上能有多久啊?为什么要混?小芳语气急促,对我模糊的回答很是不满意。她机关枪一般扫射后,我才插上话,可能没有遇到真心相爱的人吧,如果有真心相爱的人,我也会走你那一条路的。
小芳默然。过了片刻,她说她又一次听了《甜蜜蜜》的那首歌,这些年,她一直喜欢听,她希望她的生活能如歌中所唱的甜蜜蜜,可是却一直往相反的方向行走。我说,傻瓜,歌是唱给人听的,是专门安抚人们躁动不安的心情的,如果这世界这人生都活得比歌中唱的还好,还有人去听歌吗?小芳说,也是,也许你说得很对。
隔了几天,小芳又打电话给我,问我李小虎关在哪所监狱。李小虎服刑后,我还一直没去看过,我打听了一番,找到了李小虎服刑的监狱,告诉了小芳,小芳说,我们一起去看看李小虎吧。
小芳第二天就开车来到县城,拉着我去看李小虎。李小虎仍是活得虎头虎脑的,他没想小芳来看他,他显得很激动。李小虎呵呵乐着说,监狱里的生活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坏,我还活得很有滋味哩。
李小虎一直和我说着话,小芳并没有插话,很安静地坐在一边。直到探视时间结束时,小芳自始至末都没说一句话。当然,李小虎也没有刻意地与她说话。
开车回来的路上,小芳说,等小虎出来,我要嫁给他。这样的决定毫无征兆,我岂止大吃一惊,大吃十惊都不能形容出我当时的惊愕。小芳吁了一口气说:我还想变回从前的“花蝴蝶”,小虎依然是当年的小虎,而你却不是当年的你了,只有他,才能让我再次做回“花蝴蝶”。
我无语,侧过身看着车窗外的农田与旷野,不知何时,农田与旷野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素装。
哦,下雪了。苏北平原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
作者简介:
徐向林,江苏省作协会员,江苏省盐城市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编辑。从事小说、纪实文学创作十余年,先后在《当代小说》《作家天地》《微型小说选刊》等发表作品,6部中篇小说被《华西都市报》等十余家报纸连载。先后获得《中国作家》杂志社全国征文二等奖,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奖原创文学大赛一等奖、江苏省报纸副刊好作品报告文学一等奖等30余个文学、纪实、新闻奖项。出版有长篇畅销纪实小说《欲望红颜》,中短篇小说集《空心》及纪实作品集《天天向上》《闯荡好莱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