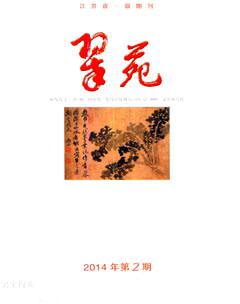绿的怀乡病(七章)
绿的怀乡病
怀念森林。
一种对于绿的怀念。
明净的空气将污秽的灵魂洗涤,
即使混杂发酵的腐果和萎谢的花叶,
那味道也似中酒的恣醉。
怀念森林。
一种对于美的怀念。
想起守林人海青额克(老爹)和他的小孙女玛露霞。
谁的眼睛像玛露霞那般单纯、无邪?
谁的笑靥像海青额克那般如明艳的阳光映射?
我随玛露霞到林中采摘,
我茫无所知,她边采边洗:
“看!东方草莓,如今叫蓝莓,酸甜酸甜的……”
“这叫悬勾子,这叫羊奶子,都能吃……”
“这飞蓬草可香啦!野蜜蜂爱盯着它哩……”
老海青额克啥也不说,只有“北大仓”酒才能撬开他的嘴。
咄!黑熊说不出稠李子就是都柿,一嘟噜一嘟噜准不会抓错。
岁月像树木—样。
老海青额头的年轮是一首时间的诗,
容易理解也难于理解。
谜一般的单纯呵!
如今,我在城里日渐衰老,他们是不老的,森林的绿在,他们就在。
怀乡病,我对于绿的怀乡病。
落 叶
落叶,覆盖了林中小径。
落叶似花,我愿采掇,
行将死去或已经死去的落叶也是收获物,它们慎重地告诉我另一个世界的消息。
落叶是金黄的,是温暖的,即使被虫蛀过玲珑多孔,即使遭扭曲后蜷缩而呈衰颓。
思想的火焰之本质功效乃“点燃”和“照亮”,不在于它的外观是盛绽还是凋萎,是飞花还是落叶。
它轻轻地诉说,你或许听不见,在你的脚下发出爱的警告,因为那终结是歌的止息。
落叶,一片又一片。
北方森林中的落叶积累千年的腐殖土。我愿采掇。
随意地拾取思想,
赤裸的思想没有形式,
赤裸的语言便是思想。
将独白的纸片收集起来,会听到出人意料的呐喊,瞬间完成了“我”。
绵延的世界和短暂的瞬间并没有区别,
如晨起吸纳清新的空气又吐出;
如风吹树叶颤动而悄吟;
阳光将整个森林镀金然后又洗尽铅华。
最后一爿叶子被暴风雨摧离枝头,满身挂着雨滴泪珠,依依不舍地告别母体、回归大地,如神话中的安泰,死而复生。
落叶,一片又一片。
兴安岭点彩
北方森林安眠的时间显得很长。
当她从呵欠中醒来。兴安杜鹃漫坡晚霞般斑斓。
初春的朱冠,给岭上白雪女神加冕。
接着,野芍药的蓓蕾绽露先声夺人的红。
紫蓝的鸢尾和铬黄的野罂粟造成色彩的戏剧冲突,
仿佛听得蜂群和棕熊的一片呐喊厮杀。
山百合像一个长着雀斑的俏皮姑娘袅袅婷婷,
白的铃兰挂着小铃铛是姑娘的裙饰。
还有离离芊芊的
漏竹、山扁豆、大蓟、玉竹、渥丹……
矶踟躅使空气里满是香水精的浓味儿,
地榆却有一股黄瓜的淡淡的清香。
百里香和暴马丁香招蜂惹蝶。
飞行神速的针尾雨燕误以为来到梦想世界,
愿意在这次长途旅行中作永久的憩息。
白背啄木鸟和灰山椒鸟的家就在附近的混交林里,它们相安无事,各自忙着觅食和生育。
一群细嘴松鸡,从阿库特岭的白桦林里迁徙。
北噪鸦的鸣啼夕暮召唤兴安岭黑色的静谧。
于是,雪鹗——白猫头鹰,终于在月光下出现……
黎 明
在冻土苔原,寻找三叶草上露珠一样闪亮的诗,语言落了霜。
树冠上空渐渐透露银箔。
继续喘吁的夜终于死亡。
倒翻转来的大鱼,上端鱼肚白,黑沉沉的脊背压向树根。
于是林中的虫鸟多声部啁啾。
响一阵,静,又响,又静……
赞美黎明前初生的新月。
腐殖土堆积松针、柞叶和白苔,散发出发酵了的醇酒的浓香。
树墩长满了蘑菇菌,便是发酵、变异、孕育的短暂的生命群体。
雾舔湿了纵横交叉的枝桠。
柞树林变黑了,亮出间杂的小白桦的朦胧。
呵,我和你邂逅林中——黎明。
白天鹅
在我独自伫立的荒原上空,天鹅悲唳着,飞去了。
我少年时代,曾有一匹白马,一个姐姐。
天鹅之歌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白马想起姐姐。
白马仿佛天鹅的地上之魂,或失落的伴侣。
姐姐骑着的马来了!在湖畔,那倒影是月晕和迷离的树影。那是我童话里的公主!
带我去吧!白马插翅便变成天鹅。铜号响了!地平线接着地平线。
年复一年。姐姐什么时候再来呢?我希冀之白马又在何方?
车过嫩江
——车过嫩江。
我醒来。卧铺车窗外远远近近散落些灯火,影影绰绰仿佛有一条泛亮的大河。
嫩江四月,冰河还没有开。
说是夜半必有轰隆隆的响动。江畔的老婆婆唸叨:龙叫了!
清早起来,嫩江几十里的冰面划开一道口子。
晶白晶白的世界出现齐崭崭的裂缝,翻起黑沉黑沉的江水。
传说是独角龙“秃尾巴老李”连夜顶开的。
你肉眼不可见,但能听到:热流冲击冰块连续崩进的交响!
轰隆隆!牢固的冰河即时瓦解。
列车胜利地冲过了冬天。
曙光映照着霜花的车窗,我呵气,用手指画出一小幅透明的玻璃画——“老李”不发威时。
——车过嫩江了。
在一个小站下车。
残雪消融。浅灰的天空雷鸣电闪,疯了一阵,抢出一个“雷电闪”。
接着,喷射一年中最初的雨丝。
霏微春雨,仅仅润泽了你的头发。
家乡的老婆婆不多嘴,只在窗台上放一把剪刀,说是用来镇雷的。独角龙和雷公是把兄弟。
他俩喝醉了春酒,摇摇晃晃地走远了。
于是重重叠叠的山岭,被乳汁般的银雾缭绕。
经冬不凋的苍翠的樟子松林,掩蔽了多少岩穴?
一冬舐手掌的黑瞎子该饿醒了。
……
四月,嫩江的四月。
森林肖像
那头颅,那额角,不是隐蔽着北极狐的突兀的岩崖么?
那乱发,那鬓髭,不是丛莽的荆榛和蟠结的根须么?
那箭簇一般尖削的鼻子;那弓也似的有力的唇;那洞悉大自然的忧郁的眼睛;
不正是你也是北方大森林的象徽么?
(涉过一片塔头甸子,跨越了激流河的倒木桥,在神秘的绿色的恐惧中忍受了三个小时以后见到你的,那里有一片疏朗的白桦林,你的撮罗子在白桦林边缘的开阔地带。)
我闻到了替驯鹿薰蚊蚋的香艾的烟味,
我听到了铃铛发出金属撞击的清脆;
我先发现一群多茸的驯鹿然后才看见你的,
你独自在森林里。你有喝泉水的树勺,你有肉干,你有驯鹿奶;你有自烤的面包和蔬菜罐头;你有火以及随时可点着火的日本进口打火机。你有猎枪、精致的桦皮鞘猎刀、望远镜和手电筒;你有树皮鞋、其哈密软靴;你有桦皮篓和皮革手提箱;你有铝壶、铁锅、烤肉叉……你还有用灰鼠皮绑制的山神……还要有什么呢?应该有的你都有,不需要的绝不让身外物成为累赘。
森林起了哨音。
像暴雨前骚扰的风那样的,
像礁屿间的洄流急潮那样的,
像湍湍漱石的涧水那样的,
像夕照将树梢毕剥燃烧了那样的,
像如泣似诉的口弦琴那样的,
像啄木鸟和红鸫的歌吟那样的
……
(你说:你的儿子在北京民族学院是画画的……你说:你的老伴就在前面的三棵落叶松树枝上风葬的……你的唯一的儿子,正在画《森林小屋》, 画《鄂温克的回忆》。他再不愿进寂寞的山林,他再不愿喝驯鹿奶,他饮苦而黑的咖啡。他画《回忆》,那“回忆”的土角,便是你……)
根河市郊有你漂亮的新居,
一屋子的家具,淡漆的木床,无法躺置你黧黑的骨骼。
对你无用的东西便是你的累赘。
你不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你儿子空白的“回忆”。
只需要不打上时间烙印的面包、盐、酒、水和篝火,以及猎刀、皮绳……你需要这年轮只印制在树身上而自己越活越强健。
你的肖像就是枝叶间露青的一角,森林迷瞬的姿容。
作者简介:
许淇,1937年出生于上海市。早年学画于苏州美专,后师从沪上大师学画(见文《我与绘画》)。1956年“支边”到内蒙古包头市工作至今。在内蒙古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表和出版散文诗集、散文随笔集、短篇小说集等300余万字,为我国著名散文诗人。被评选为中国90年散文诗重大贡献者;任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他一生献身艺术,写作与绘画并进,从油画创作开始,继而上溯传统中国画,追摹青藤、八大,于宣纸上泼墨重彩,创“东方表现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