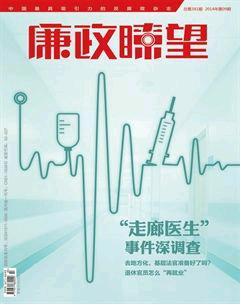“116名公务员骗低保”背后的权力链
韩永等
因仅有审批权,县一级的受人所托者,自然无法独享收益。下一级也拥有了向上级讨价还价的余地,比如多要几个指标。
116,一个看似吉利的数字,在周至县一度变得颇为敏感。
2014年春,陕西省纪委公布了去年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情况,周至县成为唯一一个被两次点名的地方。该县116名公职人员骗取低保,出现在网站醒目的标题中,这个以盛产猕猴桃著称的县,贡献了两个搜索热词——“116”和“低保”,政府公信力也受到质疑。
在乡镇,“违规吃低保”不算新鲜事。但在重重监督、审核之下,一些公职人员是如何轻易办到的,许多体制内人士也不明就里。记者在该县乡镇,对骗取低保的整个过程及各级干部的小算盘进行了“刨根究底”。
村支书分到名额仍“失落”
周至县农民周光辛,曾目睹过低保指标是如何被“瓜分”的。
2007 年左右,低保刚开始在中国农村铺开。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年7月,国务院下发通知,农村低保保障的对象,是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民。其中的重点,是因病残、年老多病、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民。
此间,周光辛所在的村开了一次“两委会”(村委会、村支委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低保指标分配。作为曾连任的前村支部书记,周获邀列席。
参会时,周光辛发现,会议的重点并非低保指标在村民之间如何分配,而是放在了这些指标在村“两委”成员间如何分配。争执的焦点,是如何在保证村“两委”成员都能分到指标的前提下,向村书记和主任适当倾斜。
最终达成的方案,是除按贫困程度分配大部分外,将少部分名额总体上平均,村书记、主任只比其余人多一两个名额。村书记似乎有一种“被分权”的失落感。
这些手握指标的村“两委”成员,开始为指标寻找合适人选。周光辛发现,最终拿到指标的,与上文提到的低保标准关系不大。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与村“两委”成员之间,都有或亲戚、或朋友的关系。
而村上那些真正贫困的人,却可能被排除在名单之外。除了村民口耳相传外,村“两委”没有通告,村上的公示栏上也看不到,于是,村民之间杜撰出各种各样的版本。
近两年,随着村务公开和监督的推进,大多数村“两委”在指标上的操作空间已大大缩小。
每次调查前都有“财产转移”
村里确定了名单,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两步,乡里的审核,县里的审批。
乡里的审核主要包括两个环节:一是入户调查,二是民主评议,旨在核对申请者所报资料是否属实。前者用事实说话,后者让群众说话。
这两个环节由乡镇主持,实际上村里拥有很大的话语权。比如入户调查,由于乡镇对申请者的情况不甚熟悉,入户调查时规定由村干部陪同。调查人员或基于完成任务的需要,或受限于了解情况的难度,其调查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村干部的介绍。有的调查人员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听介绍上,而将入户环节一笔带过。
由于村干部与被调查对象间可能有种种关系,村干部通常会在这一过程中暗渡陈仓。翻开一些入户调查报告,会发现其内容与村上申报的内容几无二致,却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一些参与虚报的村干部,还会将乡镇来人审核的信息告诉被调查对象,让他们提前做些准备。周光辛等人反映,每次入户调查前,村里都会有一些财产转移的行为。
入户调查的遭遇,会在接下来的民主评议环节中重演。这一环节通常由一名乡镇干部主持,参加者包括村“两委”成员及部分村民代表,但村民代表的选择权,仍在村“两委”手里。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农村低保的申请流程中,村级政权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控制力。它不仅让村级的初审权高度集中,还事实上分享了乡镇的审核权。周至县一名副乡级官员称,自己亲戚拥有低保的村干部,在该县村干部中占比不低于80%。
经“两委会”成员的拉拢,一些“民主评议”场合变成了“睁眼说瞎话”,有时会将某户原本家境尚可,说成饱受饥寒之苦。
这两个环节通过后,主要的“险滩”均已涉过。接下来是最后一道关——县里的审批。
县里与乡里的权力有一字之差:乡里叫“审核”,县里叫“审批”。“核”主要是对内容负责,“批”则是一种程序上的权力。
审批前,县里还有一个抽查的环节。按规定比例不少于30%。由于县村之间距离遥远,这种抽查更有赖于乡村两级,事实上又落在了村“两委”手里。
周至县一名副乡级官员称,“县上最终审下来的名单,与村上申报的名单大同小异。”
谁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就在上述程序中间,闪烁着116名公职人员的身影。
这116名公职人员,以村、乡和县为中心形成了3个权力场,权力场的圆心,是村“两委会”、乡镇民政所和县民政局。而其中的手握重权者,是村书记和村主任、乡镇民政所长以及县民政局局长、副局长和低保办主任。
而在这个圆心周围,围绕着好几圈分食利益的人。这群人包括县级领导、乡镇领导、退休领导、工作上下游部门官员、有监督权的部门官员及利益输送者。
上述副乡级官员称,虽然提出名单、入户调查和民主评议有时陷入形式主义,但基于保险考虑,村干部通常在受人所托后,拿出一部分收益拉拢乡民政所长。
乡镇虽然内容的审核权在握,但县里的形式审查与30%的抽查率也不容小觑。周至县一名纪检官员透露,抽查可以做虚,也可以做实,虚实之间的自由裁量权,存在难以琢磨的风险。若乡镇受人所托,也通常会将其中的一部分钱财送给县上。
而县一级的受人所托者,亦无法独享收益。由于其只是拥有审批权,审核权和初审权还掌握在乡村两级,他得给这两级打招呼,说把某个人报上来,不占用你们的指标。三级政权在这一过程中心知肚明,下一级也因此拥有了向上级讨价还价的余地,比如多要几个指标。
相比县和村,乡镇操作的余地更大一些。一方面,村一级的初审权是受乡镇委托,乡镇也可以直接接受低保申请。另外,乡镇将名单报到县里后,被后者审批掉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基于此,乡镇民政所长的位置,正成为乡级职位中的香饽饽。
乡镇民政所的上级——乡镇党政领导在低保问题上发言权亦很大。周至县金融系统一名官员,讲述其为侄子办低保的经历:他坐在村支部书记的家里,给乡党委书记打了个电话,说侄子生活困难,给他办个低保吧。乡书记说行,到时候再说。“我说别再说,我現在就跟村书记在一块,你给他安排就行了。乡里书记说行,这个事就成了。”
近两年,中央在治理违规吃低保问题上措施频出,地方上的低保乱象正在收敛。2013年全国“两会”,民政部长李立国公布了5项正在和即将实施的措施,如低保申请者可以跳过村级,直接向乡镇和街道提出申请;对低保经办人员和村“两委”干部近亲属实行备案,单独进行审核;推动建立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严格公示等,被认为颇具“杀伤力”。
不过,周至县一名副县级退休官员认为,从制度设计上看,中国村、乡、县结合的三级低保申请制度,是一个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的设计:村里最知道谁需要低保,认定成本低,且高效准确;乡与县的入户调查与抽查,则有望形成一种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的监督。而问题在于,这个制度如何真正实行,执行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