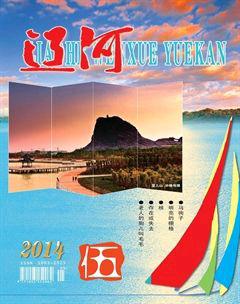一张会跳舞的字据
孙德明
半年前,相老太的二儿媳为她添了个孙子天宝。相老太自从有了孙子,高兴得整天合不拢嘴,就是在梦中也常常笑醒。大儿媳五年前给她添了个孙女,着实伤了她的心!
就像光棍盼媳妇,如今相老太终于盼到了孙子。她整日烧香拜佛求童子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怎不令她心花怒放呢?相老太每天一起床,第一件事便是看她的宝贝孙子天宝,雷打不动。当小天宝睁开一双天真明亮的眸子的瞬间,相老太四方形的脸上像绽开的一朵灿烂的菊花,双目生辉!日子便这样在祖孙俩的笑声里尽情地流淌着……
这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天空阴沉沉的,飘着毛毛雨。相老太的大儿子相柱来给她报喜说,又给她添了个孙女,请她过去伺候大儿媳几天。老人闻听“嗯”了一声。尔后便再也没有吱声。她下意识地将怀中的孙子搂得更紧了,生怕有人抢走似的。
无奈,相老太只好到相柱家伺候了大儿媳桂萍两天的月子。等亲家母一到,自然便替下了她。如今她整天乐滋滋的,因为她又有足够的时间看护她的宝贝孙子了。只要一抱着她的孙子,她的心灵也仿佛寻到了最好的归宿,有一种欣慰、踏实的感觉,这时,她的脸上时时泛起一种昔日少有的红晕,写满了激动。就在她的大儿媳刚出满月的第二天,大儿子相柱来找她了:“娘,我丈母娘明天就回去了,你就先去我家住上几个月吧。”相老太看了一眼儿子说:“你媳妇光在家里看个孩子做个饭,累不着。再说天保妈才到塑编厂找了个活干,我,我实在分不开身呀。”
相柱闻听,面露不悦:“娘,我那口子体质本来就差点,这您是知道的。我今天来就是……”
“就是想把我喊过去?”相老太闻听疾言厉色地打断了他的话,将床上的天宝一把抱在了怀中,像头护犊的老牛。
“娘,想来您老也是明理人。您已经在我兄弟家住了近一年了。您老可要公平待人呀。”相柱铁青着脸道。
此刻,只听门声一响,相老太的二儿子相栓走了进来。相栓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可谓娇生惯养。虽生性有些懦弱,行事鲁莽,但却自尊心强。兄弟俩会面,点了一下头。相栓从口袋里掏出一对小巧的玩具狮子狗,逗着母亲怀里的儿子。相老太一边忙着将天宝含在口中的玩具往外取,一边嗔怪道:“以后再要买这些小猫小狗的,可要买些个大一点的。小心让我天宝生吞了它。以后可得注意了!”
兄弟俩谁也没接母亲的话。相柱看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直言不讳地道:“老弟,明天我想让咱娘再去我那住些日子。我丈母娘明天要回了。”
“实话告诉你,这个月我恐怕去不成了。下个月再说吧。”相老太未等二儿子开口,自己先把话封住了。于是相柱便抡个风悻悻而去。
“哥,你听我说。”相栓言罢急急地追出去,解释说,“哥,是这样的,你弟妹近些日子才找个活干,等过些天我自然会让咱娘过去的。”相栓茫然地望着哥的背影,惆怅地叹息了一声。
翌日,天刚放亮,相柱两口便叩开了相栓家的门。桂萍唾星四溅,指着相柱的脑门道:“丑话说在前头,你老娘一碗水端平了正好。否则,要是不识抬举,我可活不养死不葬。”桂萍这几句话像导火线引燃了相栓的火爆,“好好好!大哥大嫂,这话可是红口白牙从你们嘴里说出来的。这娘只是我相栓的,从此以后,由我自己赡养,与你们无关了。权当咱娘只生养了我一个总可以了吧。”
“好小子,真行啊。有种的你敢跟我们立个字据?”桂萍双手卡腰,步步紧逼。相栓一拍胸膛,眼一瞪道:“男子汉大丈夫,吐口唾沫砸个坑,你们等着。”言罢,他刚要进屋去找纸和笔,被大哥相柱喊住了。相栓心一横,冲到大街上吆喝道:“乡亲们听着,我娘只生了我相栓一个儿子。我大哥已经出了五服了!”言罢蹲下身,将纸垫在自己的膝上,提笔写道—— 大哥大嫂,娘是我相栓一个人的。今后赡养老人的责任,由我自己承担,与你们无关。
立据为证 永不反悔
立据人:相栓
当相栓将字据交到大嫂手中的一瞬,小两口的脸上顿时阴转晴,遂说说笑笑地走了。相栓呆呆地站在那里,像尊雕像。直到老婆秀芹上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才如梦方醒。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错得无以复加了;又像是被人抽走了什么筋,抽得全身软塌塌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当初的自信像飘飞在空中的肥皂泡,毫无声息地破灭了。他后悔不已,恨自己不该一时冲动,上了大哥两口的当。唉,后悔药没买的,我就权当没有这个哥罢了。
相栓的老婆得知实情后,气得浑身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抡起巴掌击向他的面部。相栓捂着脸,转身回屋,迎面正碰上母亲严厉的目光。相老太仰天长叹了一声道:“你这个糊涂的小栓子。你一张小小的白纸就让为娘痛失了一个儿子呀,你,太伤我的心了。”相老太言罢,两滴浑浊的老泪,从眼框里溢了出来。
“娘,您老别伤心。”相栓安慰母亲说,“以后你就权当生了我一个儿子。放心,我会赡养你一辈子的。”相栓言罢“扑嗵”一声,双膝跪地,接连给老娘磕了几个响头。一旁的秀芹见状,猛地一转身,抡个风去了……
时光如流,一转眼,五年过去了。如今,相老太的脸像核桃皮,背也驼了,已是暮气沉沉。
近些日子,她时常在儿子相栓面前唠叨:“自己吃的喝的倒是不少,可就是浑身没劲,也不上膘。”相栓闻听哈哈一笑,说:“娘,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嘛。我看你呀是福相。”他嘴上虽这么说,可看着老娘一天天衰弱的身体,心里也着实不是滋味。他暗暗下了决心,抽空一定得陪母亲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可当他将想法同秀芹商量时,却遇到了麻烦。纵然他说出了不少母亲的“丰功伟绩”,可老婆仍旧是满脸的冰霜。秀芹说:“这一进医院,恐怕这三百五百的不够。依我之见,你还是干脆去同你哥商量一下吧。当年你写字据那事,他身为老大,不可能当真,宰相肚里能撑船嘛!”
相栓闻听,立马像吃了八个苦瓜似的,身子一蹲,挠着头皮道:“唉,这事难了。再怎么说这些年多亏了咱娘帮着咱。我就是再傻,也不能挥着巴掌打自己的嘴巴。”
“好你个相栓,我问你,你娘是不是有两个儿子?”秀芹双目喷火,忿忿地道:“攒金子不如看孙子,这是她份内的事。再说这几年孩子也大些了,她也没出那么多劲儿,操那么多心嘛。可她在我们家一住就是五年。我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不信你去外面说说,像我这样通情达理的儿媳,她打着灯笼也没处找。敢情现在生病了,还让我们出钱出力陪她去医院检查,这也未免太过分了吧﹗”
相栓在老婆秀芹面前碰了个钉子,哑口无言,越想越窝囊,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禁不住泪水模糊了视线。他冷静下来之后心想:现在别无他法,只得去求母亲了。只要她肯答应从中周旋,此事肯定会有转机。
晚饭之后,相栓便默默地来到母亲房里。尽管他一副乞怜的嘴脸,可当他将此事向母亲说罢,相老太的肺都气炸了,二话没说,顺手抄起门后的笤帚疙瘩,猛地朝相栓身上击去。相栓也来了脾气,索性身子一蹲,任母亲在其身上拼命抽打。相老太打累了,那气喘嘘嘘的样子,像秋风落叶,一缕的惆怅和委屈在其心头荡起,她将笤帚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在上面,放声哭起来。霎时,浑浊的老泪在她的脸上汹涌着。
相栓陪着母亲哭了近半个小时之后,忽然灵机一动,似乎想出了一个规劝母亲的法儿。于是他便擦干了眼泪,将嘴凑到娘的耳边道:“娘,咱不哭。你老权当养了我一个儿。过几天,我陪你去医院检查去。”
此法果然灵验,相老太渐渐止住了哭声。
眼下,母亲只等我同他去医院了。可这钱在老婆秀芹的手上,咋办?借?!就索性先向厂里借1000块应应急吧!对了,还得请一天假。反正这厂里的情况老婆又不知,我只要让母亲守口如瓶,此事定能过关,想至此,相栓得意地笑了。
对了,还有个挠头事。儿子天宝眼下最依赖他奶奶。得向母亲说,这几天不要招惹他了,否则将如何脱身?下个礼拜四是岳母的生日。我得事先向秀芹说明,这几天厂里赶任务,加班加点。对!就选这一天和母亲去医院。但愿天助我也。
相栓终于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整个人仿佛精神了许多。
几天后,他的计划得到了顺利实施。诊断结果,母亲竟患上了可怕的糖尿病!听说这病不好治,属于不死的癌症;每天必须药物陪伴,饮食上还要节制。为此,相栓冥思苦想了很久,他想让母亲独立生活,可让他挠头的是,这事又不能同妻子正面相商。于是,他便开动了脑筋,思忖良久之后,打算把家中的两间西屋腾出来,让母亲住进去。当相老太得知自己的病情后,竟痛快地顺从了儿子的安排。
当日下午,当秀芹和天宝到家之时,相栓已将母亲所需用的东西全部搬进了西屋里。相老太戴着老花镜坐在门前,正在缝补着什么东西。
“奶奶,我姥姥给我好多好吃的东西。”孙子天宝刚从车上下来,便一蹦一跳地过来,将一包蜜食送到她的手中,“奶奶吃,可甜了。”
“好天宝!奶奶倒是很想吃,可奶奶没这口福喽!”相老太言罢又转身对儿媳说:“今个我去检查了一下,大夫说我得了糖尿病,给了我几瓶药。这不相栓下班后,我让他把咱这西屋收拾了一下,我就搬进来了。”
秀芹闻听,脸色腾地涨红了,她刚要发作,可此时的相老太已经领着天宝出门逛街去了。
“相栓!”秀芹满腹的火气没处发泄,就急火火地高喊。相栓满面春风地从屋里迎出来:“哟!你回来了。咱儿子呢?”秀芹见状二话没说,一巴掌打在相栓的脸上。相栓如遭蛇咬般的后退一步。
“你娘看病买药是不是你掏的腰包?她搬进西屋是不是你的鬼主意?”秀芹怒气冲天,双手卡腰,像怒目金刚。相栓倒是不急不恼地道:“看美的你!发的哪门子邪火!实话告诉你,咱娘手里还有俩钱,还用不着咱特殊照顾。再说了娘搬到西屋里住,可是她自己的主意,想来她年纪大了,又患了那病,还是分开过的好,你说是不是?”
“不行!”秀芹忿忿地道:“你告诉她,这两间屋,我还打算养鸡用呢。”
“那你想让她老住在哪里?”相栓问。
“愿住哪住哪去。反正已在我们家住了五年多了。吃了辣椒不觉辣,什么玩意!”秀芹言罢抡个风去了。
相栓目瞪口呆!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相栓迫于秀芹的压力,便来到了母亲的房里,对母亲说:“娘,五年前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一时冲动,把您老害苦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娘权当就生了你一个儿子就是了。”相老太言罢眼泪便模糊了视线。
“娘,你老就别难过了。说一千道一万,我的错,可这铁的事实总归不容否定吧。只要你老肯出马,去找一下书记或村长,保证能说动我哥让他回心转意,并收回我立的那张字据。到时,我一定加倍孝顺你!”
“相栓,你咋这么糊涂?当初可是你将娘争取过来的。是你惹出的是非。俗话说,铃铛还要系的人去解不是?这事还是你自己出面为好。”
“这……娘,你是长辈,又是当事人,好说话。若是我去了,领导那倒好说,可他们俩口子一句话还不堵住了我的嘴!”
“好好!娘老了,不中用了,该死。那你们今后谁也甭管我了,行吧?”相老太双目喷火地道。
就这样,娘俩不欢而散。秀芹听了丈夫的“工作汇报”之后,大为恼火:“天底下也难找像这样的老娘。她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咱干脆不管她了!反正咱已经管她这么多年了。真理在我们这边,大不了挨一顿训罢了。”
相栓听罢秀芹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初这事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且不说,可归根结底,这些年母亲是为了看护儿子天宝,为了给秀芹腾出时间多挣几个钱才答应留下来的。母亲功不可没呀!可如今,天宝去了幼儿园,秀芹又没了工作可干,整天待在家中,母亲也就成了多余的人,没啥利用价值了且不说,每天还要花钱,难道就这样不要母亲了吗?卸磨杀驴可够残忍的。老天爷呀,她可是我的亲老娘呀!这样做天理不容呀!
相栓深知,自己就是将这些话都说出来,秀芹也绝不会买帐的。说又不能说,只能深埋于心底。于是委屈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汩汩而下。
“哭!你哭的什么丧?还是个男人吗?哼!”秀芹见状抡个风悻悻而去。
说啥也不能难为我老娘了。我得找村长去。相栓心里想着,便脚下生风地来到了村长的家中。
相村长听了相栓的汇报,笑嘻嘻地道:“大兄弟,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千不该万不该,五年前写给他们的字据。这字据可是白纸黑字的‘硬家伙,就怕他们连我的面子也不给呀。这样吧,我给你出出头,试试看吧,尽力而为。甭管这事成败如何,兄弟你记住了,欠我一个人情是一定了。我呢,也不求什么回报,过了年就要重新选举了。到时候选我一票就行了。”
“行!只是这事全仰仗大哥您了。放心,大哥的恩情小弟铭记在心,知恩必报嘛!”相栓道。
“好了兄弟,两天后听信。”相村长乐滋滋地道。
“拜托您了大哥,留步!”相栓言罢,下意识地朝村长鞠了一躬去了。
两天后的傍晚,相栓又叩开了相村长家的门。
相村长的老婆忙着给他泡茶水,相村长清了清嗓门道:“昨天傍晚我去你哥家了。你大嫂在家,她说这事没商量的余地,她尽说你们两口子的不是。唉,可怜我道理讲了有千条,好话说了一大车,可你嫂子死牛蹄子不分丫。兄弟,都怪当初你把事情做绝了。现在可倒好,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兄弟呀,一失足成千古恨,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相栓吃了闭门羹,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又被秀芹骂了个摸门不着。他像被人当头一棍,脑子里就像一池被搅得“嗖嗖”旋转的污水,又像一只受到惊吓而被迫无奈的鸟,只想找个清净的栖息之地了。于是,他神使鬼差似的走出了家门,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一阵神经质的狂奔之后,一头扎进了路旁的玉米地里。玉米刚没过头顶,随着耳畔的沙沙声,他忽然觉得身子一震,睁眼一看,原来撞到了一棵梧桐树上。这树是学大寨那年栽种的,有近两人粗。该树半边生机勃勃,然而,另半边却早已干枯。相栓仿佛遇到了久别的亲人似的,下意识地紧紧地抱住树干,一阵悲悯从胸中涌起,禁不住嚎啕大哭。哭声里充满了委屈与无奈的悲凉,被夏风无限放大。他想用哭声来麻醉自己,得到一时半会的解脱。可是,他错了。当他的眼泪流干、嗓子哭哑之后,脑子里仿佛更清醒了。随之而来的烦恼与痛苦,像一支支无情的利箭向他袭来,让他无从招架。他双膝跪倒,昂首叩问苍天:“老天爷呀,请您老人家告诉我,我相栓上辈子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呀?让我此生遭受如此的折磨!可怜我儿子还小……老天爷,你不公平呀,我,我相栓要到哪里去告你啊!”他的心被悲凉浸透着。他下意识地擦了一把迷离的双眼,蓦地,他发现不远处的头顶上向西伸展着一条矮矮的树杈。那树杈在风中微微颤动着,冥冥之中依稀在向他昭示着什么。他心里一动,站起身,伸出手,仿佛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棵救命的稻草,那树枝正被他捞在手中,若是再高一点,就望尘莫及了。他认为这事是老天冥冥中的安排,是他的命运。命该如此。于是乎,他便三下五除二地松开皮带,将裤子脱下来,系在树干上,那裤子就像一面灰色的旗帜,在晚风中摇摆起伏,呼呼作响!他抓住裤筒,系成了一个人们用来套狼的扣子,将自己的脑袋套了进去。而后,他一咬牙,身子猛地往下一沉,只听 “咔嚓”一声脆响,连人带树枝一起跌在了地上。原来那树枝是枯的,根本承受不住他的重量。
“好你个相栓,竟敢在我的地里寻死上吊!滚!别玷污了我的田土,呸!”相栓听着声音耳熟,睁眼一看,原来竟是大嫂桂萍!他仿佛被毒蛇咬了一口,心里一惊,头脑立时清醒了许多,便三下五除二地穿上衣裳,在大嫂恶毒的咒骂和嘲笑声中,提着裤子,跌跌撞撞,趔趔趄趄,边走边骂着自己:“我他娘的真是混蛋。我干嘛跑到她家地里寻死呢!混蛋透顶的东西!”
当相栓急急地来到自家门前时,一屁股坐在了门墩上!他气喘嘘嘘,精神萎靡,蜡黄的面皮闪着病态的光亮。他下意识地倚着门框长叹了一声,这真是兔子转山坡,转来转去回老窝儿。可眼下他实在没勇气再进这个家门了。他刚要起身而去,只听门声一响,相老太走了出来,用爱抚的目光打量着他说:“栓,你这是咋了?脸色咋这么难看?娘知道你日子不好过。”相栓闻听,心头一热,一头扑进了母亲的怀中,呜呜的哭泣声像开了闸的洪水呼啸而出。
突然,他猛地昂起头,对母亲说:“我这就去向秀芹表明心态,大不了离婚!”
相老太擦了一把老泪道:“栓,听娘的话,这事咱还是等以后慢慢说吧,咱得把心放宽些。”
“娘,我,我听你的话。”相栓带着哭腔道。
这日晚饭后,秀芹对他说:“既然村长那没戏了,下一步你打算咋办?光这样靠下去总不是个事吧。”
“那你想咋办?我可是没辙了。”相栓往床上一躺道。
“我看,还得动员你娘自己行动。”秀芹眉毛一挑,轻叹了一声。
“这条道咱行不通,我不是早已试过了。”相栓愁眉苦脸。
“你行不通,我出马。我就不信,这牛角总是弯的。”秀芹疾言厉色。
“好!行行!不过有一条,希望你、你别惹她老人家生气为好。只要她老人家不生气,让我相栓咋着都成。”
“精彩。不愧是大孝子。”
两天后的傍晚,当相栓给母亲送面之时,母亲没好气地冲他道:“还送啥面呀。你娘还不知道是否能活过这十天半月去哩。”
“你,你咋了娘?”相栓说着伸手就去抚摸母亲的额头。相老太头一偏,眼泪汪汪地道:“你们小两口要是不想养活我,就直说,可不要再难为我这老婆子。”
“娘,秀芹又跟你说啥来着?她又让你生气了。我回去好好说说她。娘你千万别生气,该吃吃该喝喝。”
“栓,回去在你媳妇面前说话要掌握分寸。千万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你们夫妻的和气。”相老太凝视着自己儿子的面孔嘱咐。
原来,秀芹早就找过婆婆了。她说自己这些日子又没找着工作,一家四口仅靠相栓微薄的工资生活,日子不太好过。而后,她便话锋一转,遂又提到了大哥家,说他给人开汽车,跑长途,工资确实要比相栓高几倍。大嫂种的个小菜园也有收入。相老太深知秀芹今天特此过来,向她说这些话的真正用意所在。因此她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听着,没插半句嘴,也压根不想插嘴。
当秀芹提出让她动员一下大儿子时,相老太的脸上便失去了往日的和蔼。可她的那张嘴巴。却是一直闭得紧紧的。
渐渐地,秀芹终于忍不住火山爆发了。她先是声色俱厉地发了一通牢骚,尔后竟直言不讳地要求老人半月后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否则竟让她无条件的搬出去!
尽管秀芹如此的对她,但相老太在儿子面前,依旧是守口如瓶。尽管儿子再三追问,但为了这个家,相老太咬牙忍了,兀自将苦水咽进自己的肚子里,也只有如此,相老太觉得值,她甚至内心深处感到了几分欣慰。
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混一天算一天吧。相老太心想,我倒要看看凭你朱秀芹能把我怎么样?
转眼,离秀芹规定的期限还有一天时间,这天晚饭后,秀芹直言不讳地问相栓:“你娘到底打算咋办?我建议她去做一下你哥的工作,可她执意不听。你今个干脆去西屋问问她,到底想打算咋办?”
“行!”相栓竟然痛快地答应一声,去了天井内启动了摩托车。秀芹一听不对劲,便急急地追出门,叱道:“你这私孩子,要上哪争命去?”
“去厂里了,今晚我替人值班。”相栓的话音在夜空中回荡。
翌晨,天气阴沉沉的。
吃罢早饭,秀芹送天宝去幼儿园后,悄悄来到了婆婆的门前,见老人正在洗脸,便重重地咳嗽了一声:“今儿个半月的期限可就到了,你那个事办得如何可心中有数?”
相老太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依旧在忙她的事。
秀芹见她的话未起任何作用,心里的火“腾”地一下就起来了。她脸色一沉,横眉立目地道:“你住的这两间屋,我今天要拆了。搬与不搬,你自己看着办吧。”言罢,急急地去给他弟弟打电话,说家中有要紧事,要他过来帮忙。秀芹要拆屋的事,像蛇一样在西屋里每一寸空气里游动着,叮当有声。相老太依旧坦然地坐在那里,那始终板着的脸,透出一股冰冷的坚硬,毫无通融的余地。约二十分钟之后,随着一声摩托车的刹车声,一个留着长头发的小伙子,出现在秀芹的面前。
“弟弟,先歇歇脚吧。”秀芹言罢进了屋,倒了杯水,递到了他手中,“姐今天叫你来,是让你和我拆屋的。”
“好好的,拆什么屋啊?”弟弟大惑不解。
“这两间西屋碍事!”秀芹顺手一指道。
“这屋是你们结婚前才盖的吧,才几年?”
“弟弟,你别多问。咱准备干吧。换上你姐夫的工作服。”秀芹言罢将衣裳扔到了他的手中。弟弟微微一笑,三下五除二换上了工作服,姐弟俩来到了西屋前。
“上去先把瓦揭下来再说。”秀芹言罢将一个梯子搭到了西屋上。其弟便三下五除二爬上了屋顶:姐,咱人手少,这瓦咋往下递?”
秀芹说:“今天这活人多了还怕不行哩。你等会儿,姐给你找一个提篮去。”
秀芹将一个系着绳子的提篮,扔给了弟弟。于是,弟弟便将揭下的瓦,顺手放到了提篮里。待放进了八九片之后,便绷紧绳索,顺着屋檐将提篮放下来。秀芹将瓦从提篮内一一取出,放到了西屋的门前,并故意弄出较大的声响。
一会儿工夫,相老太的门前便被半人多高的红瓦墙堵住了。相老太见状猛地推开房门,只听“哗啦”一声,瓦墙被推倒的同时,秀芹猛地一闪身,愠怒地道:“你这老不死的东西,没长眼睛呀!”
相老太悻悻地走出来,朝街上去了。
屋顶上的弟弟见状惊得目瞪口呆。
“你小子发什么愣呀,干!”秀芹吩咐。
“姐,我,我不干了。这房子大娘住着好好的。看来这事你没同她商量就要拆了。”弟弟言罢,顺梯子下来了。
秀芹抹着眼泪,忿忿地冲弟弟道:“你这熊种,咋不看事?你不看这老东西刚才要砸死你姐嘛。要不是我躲得快,你姐这条腿就保不住了。”
“姐,这活我说啥也不能帮你干了。还是等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吧。”弟弟说完,去屋内换上衣服后便去了。傍晚,相栓竟没有回家。相老太惟一的希望落空了。她胡乱地吃了点东西后便下意识地抬头望了一眼天,但见阴沉沉的天空没有阳光,心也像灰色的天空,沉甸甸的。想去街上坐坐,又实在没有心情,便进屋躺了下来。不一会,便沉沉地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屋内的相老太忽然感到头皮上凉凉的。她下意识地用手一摸,泥水便流进了她的眼里口里。她一阵咳嗽,猛地醒来,只听外面雨声“哗哗”,屋内“滴滴嗒嗒”地响个不停。她顺手拉亮了灯,可就在灯亮的瞬间,但见灯口上“哧哧”地爆起一团蓝色的火花后,又陷入了黑暗。相老太战战兢兢地摸索着坐在床上,胡乱地披上被子蜷缩在墙角,恐惧加上不时扑进来的凉气,使她瑟瑟发抖,呻吟不止。渐渐地,她将自己的身体蜷缩成圆圆的一团,像一只遭受袭击的龟。雨一直下到天亮。相老太在极度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了一个有生以来最可怕、最难忘的雨夜。
翌晨,相栓回来了。当他看到母亲门前的红瓦和绳上晾的衣裳时,一种不祥的预感,雾一样弥漫开来。他走到西屋一看,便一切都明白了。他胸中“腾”地燃起了一股怒火,像一头发疯的野牛,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屋里,挥起巴掌,“啪”地一声打在了正在吃饭的秀芹的脸上。秀芹自从与相栓相识以来,还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更从未挨过打,扔掉干粮,二话没说跑入里屋,收拾东西便回了娘家。
昨夜,相老太几近地狱般的感觉,使她大病一场,相栓索性请了假,送母亲到医院里治病,整日守候着母亲。这些日子,母亲那被病魔折磨得痛苦的模样,使他整个身心受控于这份隐痛。他精心伺候着母亲,仿佛捧着一件极易打碎的器皿,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怠慢。
在此期间,相柱曾来看望过老人。可惜是半夜来的,母亲正在睡梦中。相柱呆呆地在母亲床前坐了近半个小时。只希望母亲早日康复!他从口袋里掏出1000块钱放到了桌上。相栓瞥了一眼,说有钱,让他拿回去,可相柱执意不肯,末了眼泪流了下来。相栓知他是背着大嫂来的。见他可怜兮兮的样子,心一软,便收了下来。毕竟是亲兄弟。相柱临走之时,含着泪紧紧握住弟弟的手说,五年来,兄弟你以实际行动告诫我:对母亲最深沉的爱,莫过于不辜负她的希望,去尽儿子的责任,然而,哥哥却是背道而驰。自己身为老大,对母亲应尽孝心才是,可难办的是你大嫂从中作梗。言罢,相柱的眼里闪动着坚毅的光芒。
两个礼拜之后,相老太出院了。
相栓想,母亲只住在我家,天长日久了,也总不是个办法,还是听大哥的话再努力一下,去找找村领导吧。此事既然村长又办不了,这次我干脆去找书记去。
书记姓张,个子不高,“国”字脸,一双眼睛倒是挺有神的。他认真听取了相栓的诉说后,说:“你家这事我已有耳闻。这样吧,三天之后,礼拜六上午十点,你们一家全都到村办公室来,给你们一次性解决。”
“好!全凭张书记做主了。”相栓下意识地向张书记深鞠一躬后离去了。
礼拜六一眨眼就到了。相栓同母亲九点半就已赶到了村办公室,但见书记村长端坐在办公椅上。相柱也早早地过来了。张书记起身忙搀相老太落座,给老人倒上杯茶水,相柱忙接杯在手,递到了母亲的手中,略带尴尬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娘,这些年儿子我对不住您老。请您原谅我吧。昨天我没有来得及同您商量,就去跟桂萍办了离婚手续。”言罢双膝跪倒在相老太的面前,取出离婚证打开,递到她的手中。相老太惊得目瞪口呆!少时,眯缝起眼,仔细地瞅了几眼证书,两行浑浊的老泪,顺着核桃皮一样的脸颊流了下来。老人指点着他的额头颤声道:“相柱啊,咱家给你娶上媳妇不容易,你咋就说离就离了!”
“娘,我也要和朱秀芹离婚。我今天请求您老答应我吧。”相栓言罢也跪倒在相老太的面前。
“甭离了!这不,秀芹回来认错了么?”村长话音刚落,只听门声一响,秀芹走了进来。相栓气愤地将脸扭向了一边。秀芹的心被一种难言的羞愧啃噬着,“扑嗵”跪倒在相老太的面前:“娘,都是俺的错,俺做得很不对!”
“亲家,您就狠下心来,狠狠揍她一顿吧!这孩子太不通情达理了。”随着洪亮的声音,随后进来两位老人。相栓定睛一看,正是自己的岳父岳母。张书记含笑相迎,热情地同两位握手,并请到了贵宾位上坐下。村长忙着给他们递烟递水,寒暄着。
此刻,跪在相老太面前的相柱,用颤抖的手取出一张纸条,递到相栓手中。相栓定睛一看,正是五年前他亲笔写下的那张赡养母亲的字据,他顿感面上泛热,相对无言,只有泪两行。
相柱顺手把字据从相栓手中拿过去,用膝盖当脚走,挪到母亲的面前:“娘,我相柱不是人!这些年来我没有赡养您老一天,让您老受苦了,遭了不少罪。请您老惩罚我吧。”言罢,“砰砰砰”给老人磕了三个响头。而后,将手中的字据双手呈到母亲面前。相老太没有去接,只是望了一眼,摇了摇头,眼泪无声地滴落下来。
相柱顺手掏出火机,随着“啪”的一声脆响,喷出一股蓝色的火舌,那白纸黑字的字据,霎时幻化成一股黄色的火焰,闪展跳跃,欢乐地舞蹈!张书记见状,带头鼓起了掌。这掌声如迎春的鞭炮,充满了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希望,在人们的心头回荡着。
“秀芹你起来吧!”相老太站起身说:“相柱,你也站起来吧,过去的事,咱就让它过去吧。”言罢双手拉起秀芹,并不时给她拍打了几下身上的尘土。
相老太在这一刻,满是皱纹的脸露出笑意,几乎胜于她在往昔生活中遇到的所有温暖与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