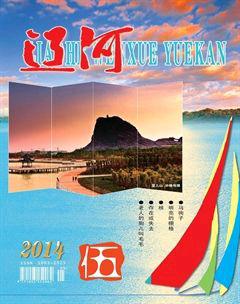把柄
卢佩恒
村民姓郝名大胆,可胆子比谁都小,遇事没个准主意,连他老婆都不如。村里人喊他郝大胆,多是嘲讽他。
这几天郝大胆跟村长大老黑怄上气了,说起来都是因为那块地的事儿。
在以前,那块地就算撂荒都没人稀罕。村里人常调侃:外出打工给现钱,窝在村里种地不得闲;外出打工好风光,留在家里最窝囊。想想也对,祖坟都哭不过来,哪还有闲心哭乱葬岗子?承包它,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也挤不出多少油水,图啥呀?可这阵子不同了,村里几乎闹翻了天。村长大老黑家的门槛子都快给踢破了,进进出出找上门来,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都是为了承包那块地。现在这农业税一免,补助款一拿,那个滋润,就跟白捡钱一样,难怪人人都眼红了!
可这便宜事儿,郝大胆愣没得着,他憋屈呀!五年了,那块机动地一直由郝大胆承包着。当初郝大胆不想承包,是大老黑拎两瓶酒来求他,最后象征性地只收他一点点承包款,几乎白让他种,他才勉强接手。郝大胆接手那地后,真没得到半点油水,是白种了。他舍不得投入,侍弄不上去,加上连续几年春旱,种子、化肥一路飙升,农业税居高不下……他常常抱怨是大老黑把他坑苦了。现在风水轮流转,郝大胆等到好光景了,可他的承包期也到了年头。他本以为村里还能跟他续约,谁知大老黑把脸一黑,以他经营不善为由,重新洗牌,愣是把那块人人看着眼红的机动地抖手给了别人,煮熟的鸭子飞了,郝大胆他能不窝火吗?
还有更窝火的。郝大胆的宝贝闺女在镇上读高中,去年高考失利,今年复读。不知那妮子心里咋想的,放着好好的书不念,悄悄留下一封信,面也不露,招呼也不打,就自作主张外出打工去了。打工显然不是她一个人的主意,而是两个人的决定。那个与她合谋的不是别人,正是村长的宝贝儿子铁蛋儿。
晚上,郝大胆磕磕巴巴看完闺女的信,他的肺都气炸了。他一边喝酒、一边自言自语地唠叨:“这不等于私奔嘛!咋办呢?这咋办呢?”
老婆翠英一见就气不打一处来,她没好气地磕碜他:“咋办你个头啊!老的欺负你不说,现在轮到小的也骑在你脖子上拉屎。闺女都让人家拐跑了,你还有心在家里人模狗样地灌你那尿水子?还不快去找村长算账,你的脑袋是不是让驴给踢了?”
老婆这一通连讽刺带打击,郝大胆这才如梦方醒。他一拍脑壳,心想:“对呀,通过这一闹,没准承包地的事还有转机,事不宜迟!”酒也顾不上再喝,腋下夹着把镰刀,便气咻咻地来到村长家,找大老黑理论。
大老黑见他怒气冲天,竟一点儿也不生气,反倒很热情,一会儿敬烟、一会儿留吃饭。大老黑以为郝大胆主要是为承包那块地的事来家里兴师问罪,连忙解释,好言安抚,最后非常严肃地把郝大胆不能承包的理由一一罗列出来。
郝大胆见大老黑脸还黑着,看来局面轻易不可挽回,就使出“撒手锏”——也是最后一招。把他闺女与村长儿子双双离家出走这件事抖了出来。
大老黑听罢笑容更加可掬。他说:“铁蛋儿也给我留话了,那信我不看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孩子们既然不愿念书,换句话说不是读书的料儿,出去闯一闯也不是啥坏事,年轻人,见见世面也好,那可是人生的财富啊……”
郝大胆犹犹豫豫地说:“老黑,不提你我这么些年的交情,就是看在两个孩子处对象的份儿上,那块机动地也该最先考虑我不是?你不把我放在眼里,那孩子们的事儿就趁早歇菜!我坚决不同意!”
大老黑机智地反问:“他们说处对象了吗?记得他们只说是一道去打工,也没说别的呀。如果是处对象,那我倒要考虑考虑。不过那块地你就别打主意了,承包合同已经签字盖章备了案了。板上钉钉的事,神仙来了也没辙。况且这公是公私是私,一码是一码,怎么能拿承包地的事要挟呢?我考虑的是孩子们的前程。你家妮子是不错,我家铁蛋儿也很优秀嘛,不是吗?”
郝大胆理论不过大老黑,又无功而返,心里更加憋气。
郝大胆从村长家昏头涨脑地走出来,黑灯瞎火地被大老黑家院门的高门坎子给绊了个跟头。他爬起来索性大骂一句:“混账王八蛋,想娶我闺女,想得美!”还不解恨,照着村长家的院门咣咣猛踹两脚。
不知什么时候,起风了。小北风呼呼地刮得挺来劲。
郝大胆缩脖抱膀从村长家院里出来,一扭头,可就一愣。他发现村长家的柴草垛边上有一处发亮。仔细一瞧,分明是一处火星儿。郝大胆连忙走过去,那火星越来越大,已经烧了起来。这时,如果他一脚踩下去,连踩几脚,那火很容易控制,也根本不会兴风作浪。但他没有踩灭。不但没踩,反倒踢上两脚。这一踢不要紧,火借着风势可就旺旺地着了起来。
郝大胆望着熊熊大火发了一通呆。嘴巴里不由自主地说:“真解气!烧吧,烧吧,把他狗日的统统烧了,烧它个精光……”
这时背后窜过来一人,上前二话不说,一把揪住他的袄领子,把郝大胆拖到村街拐角的暗处。
那个人这才开腔说话:“郝大胆,你真好大的胆子啊,敢给村长家放火?”
郝大胆冲着火光细看,这才看清原来是村里无人敢惹的刺头赖义巴。村里人都习惯叫他“赖一把”。
“我没放火,那火不是我放的。”郝大胆此刻见着赖一把,胆小如鼠了,他连连为自己愚蠢的行为辩解着。
“你敢说你没放?我可都亲眼看着了,也亲耳听着了。现在,你又被我抓了个正着。你挑吧,咋个解决?是报官呢,还是私了?”
郝大胆一见这阵势,吓得腿都哆嗦了,连忙讨饶说:“千万别声张,我愿私了,我愿私了。”
私了的结果,郝大胆出钱买烟。
郝大胆哆哆嗦嗦老半天才摸索出皱巴巴两块钱来。赖一把看了大发脾气,大声嚷道:“你打发要饭的呢?两块钱,能买个鸟?老子抽烟从来都是两块钱以上的。今天也该你出点血,少说也得二十五,买一条!”
郝大胆万般无奈又抠抠搜搜极不情愿地摸出两张十元的,一张五元的票子。他本想让赖一把将那两元钱找给他,哪知赖一把上来就是一把收,说:“找啥找?都是我的了。”赖一把拿到钱乐颠颠随着纷纷赶来的村民,忙着救火去了。
此刻村长家的柴草垛火光冲天,跟个火焰山似的。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霎时村长家院子里烧成一片火海。柴草垛紧挨着猪圈,连猪圈四周为保暖而堆放的玉米瓤子都着了,烤得圈里的几头肥猪嗞哇乱叫,一股股烧焦的猪毛味儿时不时就传过来,看来村长家快要烤全猪了。
郝大胆没有去救火,他正为那二十七块钱顿足捶胸呢。那钱显然不是大风刮来的,现在倒让大风给卷了去,你说他能不揪心吗?但细想想也没办法,谁让你多事,盼着村长家着大火,还说那样的鬼话?谁让你多事,见人家着火不救,反倒火上浇油踢上两脚,还让人逮了个正着?你说让谁逮到不好,偏偏又是他刺头赖一把?要说这人呢,一不走运连喝口凉水都塞牙!
第二天一大早,村长就差人来请郝大胆了。害得郝大胆心里直打鼓:“是不是昨晚的事东窗事发了?难道是他赖一把不地道,拿了我的钱又去告了我的黑状?”郝大胆硬着头皮慢悠悠往村长家走,一路走一路忐忑不安。
他正合计着怎么对付大老黑的盘问,远远地就见赖一把在村长家的院门前转来转去,丢了魂似的踅摸啥。姓赖的见他来了,招呼也不打,就做贼一样走开了。郝大胆心里犯疑:“那小子是不是真想告状?或者,已经把我给告了?”这样一来,他心里就更不安了。尤其看着村长家被烧得黑黢燎光的柴草垛和猪圈,甚至不敢多想,甚至不敢走进村长家的院门……
大老黑见了他,对昨晚着火的事只字不提,仿佛那是别人家的事儿,仿佛压根儿就没有那事儿。大老黑依旧满面春风,笑容堆得满脸,反倒比昨日更热情地招待他。
大老黑说:“铁蛋儿那小子昨晚来电话了,两个孩子找到工作了,他们现在很好,叫我们不用担心。听两个孩子说话的口气,他们是在处朋友。这样也好,两个孩子离家在外,人生地不熟的彼此也能有个照应。别说,前几天铁蛋儿患了重感冒,高烧都直说胡话,又是打针又是抓药的,多亏有妮子那孩子围前围后照顾,我家铁蛋儿才转危为安。既然孩子们情投意合,彼此真心喜欢,我家是没啥意见,我希望你们两口子也能重新考虑考虑,孩子们的事儿,最好还是听孩子们的吧,你看呢,亲家?”
郝大胆给弄得蒙了头了,一句“亲家”叫得他云里雾里,像是在做梦。他现在所担心的是昨晚故意纵火的事儿,真是挥之不去,仿佛绿头苍蝇找到了带缝儿的鸡蛋,一盯上就赶不走了。对孩子们的事儿他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也是,火燎眉毛的时候,他哪还有那份闲心?因此听得有些心不在焉。他心里本来就发虚,底气不足,生怕村长提着火那茬儿,更害怕赖一把悄悄告他的黑状。只要一闭眼睛,昨晚的大火就会熊熊燃烧着扑面而来。他此时只想及早逃出去,远远地逃离村长家的院门。
村长见郝大胆听完没反应,以为他也想通了,默许了,就更加热情地留他喝酒。
郝大胆这才回过神来,连忙说:“不了,不了,家里还有事儿……”一边说一边就逃也似地往外走,害得村长两口子趿了个拖鞋把他送出了院门老远。
当天晚上,郝大胆已经躺下睡觉了,这时就听赖一把在外面狠劲儿敲他家窗户,让他出去。
郝大胆万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出来了。没好气地问:“你还来干啥?”
赖一把嬉皮笑脸地说:“嘴馋了,想酒喝了。想让你赏点钱拿去喝一顿。”
郝大胆壮着胆子说:“你真无赖,昨天不是给过你了吗?”
赖一把忙说:“别提了,越提我越上火,都怪你,咋不提醒我呢?你给我钱之后我不是救火去了吗,结果那钱我就揣这个兜儿里啦,你说咋能没了呢,真真活见鬼了?这不,今天一大早儿我就去村长家门口儿找,踅摸几个来回也没找到,我这个后悔呀……”
赖一把一脸沮丧,又接着说:“郝大胆,昨天那钱我没花着,是不能算数的,所以,今天的钱,你必须给!”
“到底有完没完?”郝大胆有些急啦,又说,“我要是不给呢?”
赖一把索性也抓破脸,说:“我就是一个无赖,天底下最大的无赖。不过呢,对纵火犯来讲,是花点酒钱摆平值得,还是把事情闹大蹲笆篱子值得?这半斤八两哪头重哪头轻你可整准了!”
郝大胆毫不示弱,说:“你要告就去告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成为亲家了,随便你告。”
赖一把冷冷地说:“原来这样啊,看来是有村长给撑腰了,胆儿肥了?好啊,你以为成为亲家就没事了吗?老子打儿子,按理说属于天经地义吧?但是,如果老子拿刀砍儿子,那性质可就完全不同了。能说是儿子就可以随便动刀吗?一旦出了人命,看有没有人来管?同样,纵火犯就是纵火犯,成了亲家也逃不了,反正把柄在我手里,你掂量着办?”
郝大胆生性胆小,听赖一把这么一说,被吓得又有些底气不足了,想想赖一把说得在理,忙讨饶说:“要多少?”
赖一把见了,忙转怒为喜,说:“去镇里喝酒,少说也得一百。”郝大胆一听,声都变了,连连赔不是,赔笑脸,说:“求求你,少点吧,我没那么多了,兜里只有五十。”
赖一把将脸一扭,脖一仰,道:“那就照顾你,先拿五十。”
这几天郝大胆被赖一把搞得焦头烂额,放火的把柄在那小子手里攥着。郝大胆这个后悔呀,真是哑巴吃黄连,赔钱的事还得瞒着老婆,要让那婆娘知道了,非河东狮吼与他玩命不可。郝大胆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合计:“那混蛋哪是赖一把呀,是不是把我这当成他家银行了,简直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等着吧,说不准那家伙还将耍什么花样呢?”
果不其然,消停了两天,只消停了两天,赖一把尝到甜头又来了。
郝大胆见了他吓得头皮发麻,简直要给他下跪了。直嚷:“你可饶了我吧,你是爹,你是爷,你是我的活祖宗,还不行吗?”
赖一把一听,扑哧一声乐了。说:“没人愿意当你的祖宗,折寿。你看怎么办吧?兄弟我三十出头,至今还光棍一条。还是饭店老板说得对,我白活了我。到现在连女人的滋味都没尝过,我亏呀我。你也就可怜可怜我,还是拿钱吧,我好到镇上找个小姐耍耍,也尝尝女人到底是啥滋味。”
郝大胆莫名其妙地胆子大起来,回答得干脆:“没钱!要钱没钱,要命一条!”
赖一把呵呵一笑,笑得十分骇人。他说:“少来那一套,老子二十年前用过的招数,现在反倒用来应付老子,不好使!给你一天时间,明天晚上这时候,还在这见面,记住,把钱凑足了,一百元。好像不够,镇上歌舞厅的小姐听说睡一次就得一百,还得交台费酒费杂七杂八。要不就拿一百吧,我去村东头杨寡妇家看看,睡那娘们便宜,对付一宿得了。”见郝大胆傻了似的半天没反应,赖一把又说:“怎么,到底行不行?哑巴啦?行不行?——你若心疼钱,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只要你舍得把老婆让出来——本来你老婆岁数有些大,我不是很满意。但是,为了照顾你这舍命不舍财的主儿,看来也只好委屈委屈我自己,就让她陪我睡一晚上算了,老女人也是女人么。好,就这么敲定了,要么拿钱,要么让老婆,你看着办……”赖一把说罢,扬长而去。
“你,你,你不是人!”郝大胆气得浑身哆嗦,差点昏死过去。
回到家里,郝大胆越想越不对劲,心里甭提多别扭了。“你说这是什么事儿?要钱也就算了,现在倒好,又打起我老婆的主意,钱和老婆,我一样也不能给他,大不了,就与那王八羔子拼了,不然,真是没完了呢。”这样想着,郝大胆就着手准备,他悄悄把剁猪食的菜刀藏在了挎包里。
郝大胆的反常举动,机灵的翠英看得一清二楚。其实他们两个男人的最后谈话,她也都在暗中听到了。她只是盘问男人兜里的钱哪去了,还半开玩笑地逗他,是不是背着她都塞进了村东头杨寡妇的腰包。
半夜,趁男人睡熟之际,翠英把菜刀从挎包里拿出来,悄悄把两块一样大的木板塞进去。她又准备了一瓶柴油和两件破衣服,另外,还把她们家的鸡毛掸子也翻了出来。
第二天天刚擦黑,赖一把就准时进得门来。见面就问:“昨天和老婆商量没,考虑得怎么样了?”
郝大胆一见,忍无可忍,随手操起一空酒瓶子扔过去,吓得赖一把赶紧往外窜。郝大胆借着冲劲拎着挎包就撵了出来。一边撵一边破口大骂:“赖一把,我考虑你奶奶个腿儿。你真是欺人太甚,老子今天和你拼了,我先用菜刀骟了你,看你还往哪儿跑骚……”
两个人说着骂着便真要动手。郝大胆从挎包里往外就掏家伙,掏了半天竟是两块木板,傻眼了。再看赖一把,光棍不吃眼前亏,顺手从栅栏上扯下半截儿木棍,左右挥动两下,拉开了决斗的架势。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郝大胆家的柴草垛莫名其妙着了火。没有风的天气里一股浓烟直冲云霄。然后红彤彤的大火便趁势烧了起来。
两个要打架的男人都非常奇怪,这火咋烧起来的?真是活见鬼了。
这工夫翠英披头散发哭哭啼啼地从柴草垛后面跑出来,一口咬定是赖一把放的火。赖一把真是有口难辩,最后说:“不就一堆破柴草垛嘛,有啥大惊小怪的?又没死人。”
翠英哭天抹泪地反驳:“谁说只是柴草垛,还有我那窝鸡,柴草垛连着鸡窝,我那三十多只下蛋的母鸡呀,这回全报销了。你赔,你赔我的鸡啊!那可是三十多只下蛋的鸡啊……”翠英哭着说着,拎把铁锹直奔赖一把而来,似乎真要玩命。吓得姓赖的连连后退,最终落荒而逃。
村里人都赶来救火。邻居们一边泼水一边直嘀咕,这是怎么了,三天两头地着火,是不是犯邪了?人们紧张地忙活着,只有郝大胆两口子站在原地不动。
郝大胆问:“老婆,怎么失火了?”
翠英嘿嘿一笑,说:“我故意放的。”
郝大胆不解地问:“没有风,怎么就着了起来,还那么旺?”
翠英说:“我浇了柴油,还有两件沾满柴油的破衣裳,能不旺吗?”
郝大胆接着问:“咱家的鸡鸭鹅赶在禽流感之前不都处理掉了吗,哪来的三十只鸡?还下蛋鸡?”
翠英答:“这叫兵不厌诈。我不这么说,姓赖的能这么乖乖地就此罢休?”
郝大胆打破沙锅问到底:“那闻起来怎么真有一股烧焦的鸡毛味儿?”
翠英一听也忍不住呵呵笑,一边笑一边说:“那是我把咱家的鸡毛掸子找出来,给扔火堆里烧了。明白啦?”
郝大胆还有些不明白,最后又问:“我的菜刀怎么变木板了?”
翠英佯装生气地答:“看你那点儿出息!你们俩背地里的那点儿猫腻还能瞒得了我?菜刀变木板,那是我给调的包。我怕你一时犯虎,出了人命,可不是好玩的哟……”
面对熊熊燃烧的大火,两口子肩并肩地站着,望着,仿佛在观西洋景。偶尔互相看对方一眼,笑了。
“烧吧,去去晦气,火烧旺运!”翠英说。
“火烧旺运!”郝大胆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