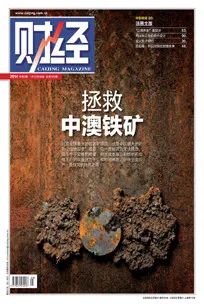剑与法
1572年8月24日午夜的巴黎,热闹了一天的人们沉沉睡去,等待着第二天圣巴托罗缪狂欢节日的喜庆。一群戴着白臂章和画有白十字帽子的人悄悄出动了,这是隐掌朝政的大贵族吉斯公爵领导的天主教保卫团,他们的目标是酣睡的新教徒(在法国又称胡格诺教徒)。
新教徒们来参加其首领纳瓦尔的亨利与当朝公主玛戈的婚礼,满心希望新教借此机会在法国获得合法地位。未料风云突变,天主教极端派大开杀戒。纳瓦尔的亨利侥幸逃出巴黎,回到自己的领地,誓要复仇,法国遂爆发了又一次宗教战争。这只不过是从1562年到1594年间,法国先后爆发的八次宗教战争中的一次而已。长期的内战对国家带来了严重破坏,也极大地败坏了国家的政治德性。
此前的法兰西,政治正当性基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政治观念。国王的善治需要两样东西:剑与法。这两者不可偏废。国王的政权来源于法律,是法律(lex)使国王成其为国王(rex),一旦他只用剑来统治,则不再成其为国王。至于法的来源,则不是出于国王的意志,而是源于历史上国王、贵族、教会、城市、第三等级等各种复杂的群体经年累月的互动博弈而成的行为惯例,亦即习惯法。
种种习惯法基于各群体间的现实力量结构关系磨合而成,从而有执行力;又由于无人可自外于这个磨合过程,从而习惯法又超越于所有人——包括国王——之上。人们依法行事,不仅是因为良善,更是因为支撑着习惯法的具体的力量结构关系,使得人们无法不依从它。
然而,地理大发现之后,远洋贸易展开,一种不依托于土地的新财富形式出现了。国王和大贵族都发现这种新财富的妙处,他们可以从中借款,以扩大战争的规模,压服对手。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力量结构关系逐渐被销蚀,习惯法失去了其有效性的根基,传统自由不再被尊重,政治德性日渐败坏。法律无法再约束住人们的行动,暴力开始成为说话的本钱。君主的剑不再带来正义与秩序,而只带来杀戮。法国的历次宗教战争便是例证,它们只是以宗教为名,行争权夺利之实。
如何摆脱这种可悲局面?回到过去的旧时光显然不行,因为新财富的出现是个不可逆的事实,不可能走回头路。推翻那个执掌暴力的暴君吗?同样不行。因为能够推翻暴君的,一定比暴君更强大,他将成为新的更坏的暴君。于是,要驯化暴力,便不能依靠暴力,而只能依靠理论。要用这个理论来重新定义暴力,重新定义暴君,使人们从“所有人皆不自由”进入到“所有人皆得自由”。能成此功的理论便不是抽象的空谈,而是现实的一部分,是它将暴政驯化和升华为政治。
这是时代的现实问题对于新理论的呼唤,让·博丹出版于1576年的《国家学六书》,开创性地提出主权理论,完成了这一工作。博丹坦然接受了暴力不再是分布于各个阶层,而是会被一个不尊重传统的强人所垄断这一事实。但是他对于这个强人的身份进行了拆解,将其拆解为主权者和最高行政长官两个法律身份。
主权者的职能在于颁布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其手中的暴力则是法律有效性的担保;最高行政长官处理具体的日常行政事务,要依照主权者制定的法律行事,不得违背。这样一种身份拆解,使得“国王陛下忠诚的反对派”的概念可以成立了。暴力被理论驯化,又回到剑和法,使国王成为国王的逻辑,所有人皆得自由。只不过此时的剑、法、自由都是重新定义过的。
主权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对全体国民普遍适用。如果它只适用于部分国民,而把其他部分国民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则对这后一部分人而言,暴力仍是笼罩其头上的利剑,则前一部分人又将成为暴力的奴隶。
内战中的吉斯公爵本可以类似地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张,让自己的战争努力获得全体国民支持,但是他的极端宗教思想遮蔽了政治智慧。反倒是纳瓦尔的亨利,以新教徒的身份征战,一直打到巴黎城下。天主教徒担心他的获胜会让自己陷入不利境地,便提出要亨利转信天主教,巴黎将开门迎接他登基。
亨利沉思后说道,“为了巴黎,值得改信”,遂登基成为亨利四世,开创了波旁王朝。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了宗教自由,主权者的法律具有了普遍性,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国王。从此法国走上称霸欧洲之路。
作者为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