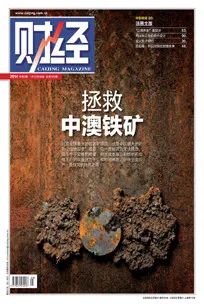阿多诺圈
由于没有言论自由,前东欧的思想市场始终处在地下。志同道合的朋友结成小圈子,定期讨论禁书,成就前东欧一段特殊的阅读史。在前东德,就曾存在这样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读书圈。
这个圈子开始于1977年秋天,成员在每月一个周三聚会,直到1981年。第一次聚会讨论霍克海默、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涉及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于是大家将自己的圈子称为“阿多诺圈”。聚会地点在各家轮流,有时离开柏林,一起去外地过周末。圈子有12名成员,9男3女,全都是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来自文学、神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和经济学等各个专业。
一开始,“阿多诺圈”的读书兴趣主要是文化,不是政治。1968年,捷克发生“布拉格之春”运动,要求实现人道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华约军队干预,东德军队最初也加入了入侵,后来担心西方抗议,很快就撤出。这次事件给“阿多诺圈”的年轻人带来很大冲击,他们开始对东德的现状产生怀疑,渴望为国家寻求另外的出路。1976年,沃尔夫·比尔曼事件促使他们第一次参与实际政治。
比尔曼是一位诗人和歌词作者,他信服布莱希特的创作原则,即“在充满活力的冲突中思考与写作”。他与政府的首次冲突就是在音乐剧中涉及了柏林墙,为此他的小剧院被迫关闭。此后,他的抒情诗越来越尖锐地批评当局,也越来越遭到干涉。在他首次出访西德时,开始公开批评东德政府,并在西德出版了自己的唱片和诗集。1976年,他再度获准前往西德演出,东德当局借机取消了他的国籍。
此次事件在东德知识界引起广泛抗议,最负盛名的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带头发起请愿,“阿多诺圈”的一位成员也参加了签名。平日里,圈子的话题是多种多样的,全是根据各自的兴趣,相互介绍自己读过的书。从回忆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广泛兴趣,如尼采的哲学,荷尔德林的诗歌,西柏林的现代画展,先锋派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等等。
政治和经济话题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有人在聚会时介绍了苏联上世纪20年代工业化的情况,以及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之间的会谈;有人介绍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研究;甚至还有人介绍了国外“增长的极限”的经济理论。当时,东德著名体制内改革者鲁道夫·巴赫罗出版了《抉择》一书,指出斯大林体制建立在一个落后国家的基础上,并希望东德领导层进行改革。巴赫罗为此遭到审判,但这本书却通过地下渠道在东德广为流传,成为各个读书圈讨论的热点。“阿多诺圈”也由一位物理学家主持阅读了此书,并讨论了有关此书的几篇研究文章。
禁书的传播是通过复印、抄写,其中大部分来自国外,有的是西德人来看亲戚留下的,有的是从东欧邻国匈牙利、捷克带入境。偷运的方法五花八门,各显神通,有人将书装在塑料袋里,挂在火车厕所里的钩子上,以躲过海关人员的检查。
阿伦特曾认为,极权制度不可能产生自发社会,但她的判断并不全对,当西方人来到东德,听到这里的人竟能谈论奥威尔的《1984》、科斯勒的《正午的黑暗》时,全都惊愕不已。
除了家庭聚会,“阿多诺圈”的成员还相约去教堂等公共场所,参加那里举行的诗歌朗诵会。这种读书会同时也产生了友谊。文学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组成,来此相聚的人均来自截然不同的生活领域。这算得上一种微型的公共领域。其中的成员终于觉得不再孤单一人,终于进一步击退了渗透于人们所接触到的社会各个角落的专制。
这些年轻人的读书会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想要了解各种不同的意见。这种欲求是再正当不过的,但对于当局来说,读禁书就是思想犯罪,国家安全部一直监控着他们的活动,并记录进秘密档案。当时克里斯塔·沃尔夫的《无处容身》似乎代表了他们的时代感受,小说中两位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为了体验失败而自杀,作家由此探讨了“社会绝望与文学失败之间的联系”。
“阿多诺圈”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会,对于后来历史的剧变,他们也许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但其中一位成员在回忆文章中,却想到混沌理论中的初始条件:蝴蝶扇动翅膀,改变了气候。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