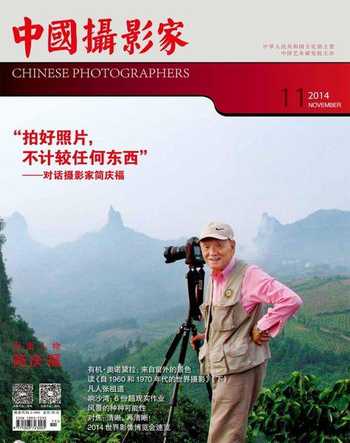遥祭张祖道叔叔


9月4日,我像往常一样,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办公室里习惯性地打开电脑看新闻,无意中看到一条消息:摄影家张祖道先生8月6日逝世。我心里一惊,忙打电话跟夫人说:“不好,张叔叔去世了。”
这天晚上,看着床前张叔叔给我们拍摄的结婚照,我久久不能入睡,想起了很多事情……
许多人称呼张祖道“老道”、“张老师”……我一直叫他张叔叔,因为他是我父母(吴祖光和新凤霞——编辑注)的好朋友,我很小就认识他,因此张叔叔的称呼一直没有改口。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家属于“黑五类”,张叔叔不避嫌疑,继续与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时学校不上课,有大把空闲时间,我开始对摄影产生了兴趣。正如后来父亲在他的文章中所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里一架质量一般的照相机已成为吴钢专用的了。……吴钢用那架相机学习摄影,到了着迷的程度。我叫他去拜了个高级师傅,就是戏剧舞台摄影大家张祖道。他是我四十年的老朋友,如今成了儿子的老师与密友。一起拍照,一起钻研,一起在暗房里放照片到深夜而乐此不倦。”(吴祖光:《笨儿吴钢学艺记》)
按照戏曲界的规矩,拜师是件大事,像结婚一样要举行拜师仪式的,所谓“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在是文革期间,一切从简。但是张叔叔受好友之托,且遵从戏曲界的习惯,从此就像慈父一样呵护我、提携我。
正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跟张叔叔学摄影。他给我讲述了摄影的基本知识,我们用木板制作简易的印相箱、放大机。那时候北京大栅栏国华摄影器材商店常有相纸的纸边卖,是制作照片时裁下来的下脚料。利用这些下脚料,张叔叔教会了我印相、放大的基本知识。用这些纸边放大出来的照片都是竖着或横着的窄条,尽管如此,我摄影的兴趣仍然越来越高,还想办法买了一台海鸥4B的120双镜头反光相机,可以加装135胶卷。张叔叔用这台相机告诉我,加装135胶卷后,120相机上80毫米焦距的标准镜头,会呈现出中焦距镜头的结像效果。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没有单反相机、没有长焦距镜头、更没有变焦镜头的文革时期,这是我唯一能够体验中长焦的设备。正是在张叔叔的启发和教导下,我平生第一次在双反相机的磨砂玻璃上观看了标准镜头与中焦镜头的差异,也第一次用中焦距镜头拍摄了半身人像摄影作品。当时我是高中生,如此奇特的学摄影经历,不是现在用手机都可以变焦的孩子们能够体会到的。
文革结束后,张叔叔到刚刚恢复的文化部“五刊物”编辑部(《大众电影》《人民戏剧》《人民音乐》《美术》和《音乐》杂志)任摄影记者,此时文艺界百废待兴,急需专业人才。张叔叔介绍我到“五刊物”编辑部应聘,我也是凭借张叔叔指导下拍摄的几张摄影作品,正式调到编辑部做了摄影记者,和张叔叔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记得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没有摄影设备。张叔叔用自己的一台蔡司120皮腔折叠相机拍照,这台相机的快门在皮腔前面的镜头上有一个小拨杆。目测估计距离对焦后,眼睛靠近取景窗,手指要伸到皮腔的前面按快门。
我们采访的第一位演员是侯宝林先生。那时他家住在什刹海附近的大杂院里,南房终日不见阳光。侯先生在院子里的树上拴了面镜子,可以反射一点阳光到屋内。为了拍照,侯先生特意穿了件黑色的中山装。这是我第一次摄影采访,就像年轻演员第一次上台面,既激动又忐忑不安,幸亏有张叔叔带领,他就像沙场上的老兵一样从容不迫,跟侯先生谈天说地,直到都放松下来,才开始拍。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我跟着张叔叔学会了如何通过聊天完成采访、如何取景、如何用光……
后来,我们可以订购进口器材了。张叔叔骑着自行车到处跑,申请外汇指标,要资料、订器材。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照相店里最高级的相机是80多元的海鸥皮腔折叠相机。海鸥DF单镜头反光相机是高档产品,要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才能买到,而友谊商店是要凭护照才能进大门的。于是张叔叔的桌子上堆满了花花绿绿的国外摄影器材介绍,精通英文的张叔叔先选出适用的器材,再填表、写申请、报批等。记得那时张叔叔的家离单位很近,狭小的房间里到处堆满了照片、资料、报纸杂志等,没有下脚的地方,唯一的空间就是桌子上和椅子上,他的两个男孩儿就在桌子上和椅子上玩。那时需要订摄影器材的单位很多,不少摄影师都是下班后来请经验多、英文好、脾气又好的张叔叔帮忙,他总是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提供帮助。正是在张叔叔的努力下,经过无数的表格、审批、盖章、公文旅行,我们终于拿到了全新的两套哈苏和两套尼康相机。张叔叔把最新型的哈苏2000型相机交给我专用,他用的是普通型的哈苏500型。两者的区别是,2000型是最新型的电子幕帘快门,由于去掉了镜间快门,标准、广角和中焦镜头,都是f/2.8的大光圈。
张叔叔经常带着我到外面拍照,拍摄戏剧舞台照片。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我们知道,文革是中国摄影历史上摆拍、假新闻照登峰造极的时代。而摆拍的导演就是摄影师自己,当时很多摄影师还遗留着文革时期的拍摄作风,喜欢在拍摄现场指手画脚、主观摆布,甚至大呼小叫,弄得被摄者十分紧张,手足无措。张叔叔绝对不这样。他常常对我说,你摆布被摄者,他只摆一个僵持的动作,我们不摆布他、不要求他,他会做出很多自然的、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动作。张叔叔的经验之谈,指引了我后来一生的摄影方向。
其实摄影师就应该处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度,才能够拍摄出真实自然的照片,正如国外的专业摄影师总是把相机的牌号用黑色胶布粘上,也是为了尽量不引起被摄者的注意。张叔叔告诉我,摄影师不是导演,永远是配角,有时候像是戏曲舞台上的龙套。而龙套是最能够近距离、不被人察觉地观察主演的一举一动,很多好演员正是从站龙套开始,偷师学艺,而后成为大家。摄影家张祖道叔叔就是一位手持相机的龙套,不多嘴、不张扬、不炫耀,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抓拍了众多大艺术家的照片,成为纪实摄影的艺术大家。
后来我父母家搬到了东大桥,张叔叔也搬到了农丰里,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一箭之遥。于是张叔叔又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他带来了多年前为爸爸妈妈拍摄的照片,看他的照片就像看一部小说或者一部纪录片一样。譬如他在1950年代为母亲拍摄的《杨三姐告状》的剧照,相机从侧后方取景,母亲的目光向后看,一条大辫子从脑后甩过来,非常形象地表现了杨三姐的倔犟性格,照片刊登在当年的《新观察》杂志封面上。同时他还跟随着父亲母亲,一起去访问了当年还健在的杨三姐本人。于是我们看到了父亲母亲坐在马拉的大车上,颠簸在乡间土路上的照片,车上还坐着老报人龚之方先生。这些几十年前的老照片,给受文革摧残而半身不遂的母亲带来极大安慰。
现在看张叔叔的作品,我可以明显看出他的创作风格。他不是为领导拍摄,也不是为评委拍摄,他是为了观众而挖掘和刻画出最真实、最自然的瞬间。他的作品,可能当时看起来很普通、很平常,但是时间越久远,越能显现出生命力与亲和力,越能体现作品的人文价值,这就是他的个人艺术风格。这也正是当下一些年轻的摄影家所没有意识到的,好的作品,好的摄影家,要耐得住寂寞。真正的艺术品的价值,往往是在艺术家身后才能体现出来,美术作品如此,摄影作品也是如此。
回首我一生中与张叔叔的交往,我在摄影艺术上有一点成绩,离不开张叔叔的教诲和帮助。1988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自己的第一次个人戏曲摄影展览,父母的老朋友都来提携后人,吴作人伯伯题写展名,曹禺伯伯写前言,黄永玉叔叔画作者像,曹欣之叔叔设计请帖,赵忠祥兄和姜昆兄担任主持,张祖道叔叔拍摄开幕式照片——都是一时之选,顶尖的艺术大家,张叔叔作为著名摄影家位列其中,丝毫也不逊色。2004年,我出版《美丽的京剧》摄影画册,也是张叔叔为我拍摄了首发式上的活动照片。我出国之后,每次回来,总是抽空去看看他;有一些理论上的想法和问题,也是打电话第一个向他请教。
张叔叔一生在新闻界工作,门生故旧遍布各大媒体,而他去世的消息竟然在一个月后才传出,可见他的为人与他的作品一样,低调、朴实、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