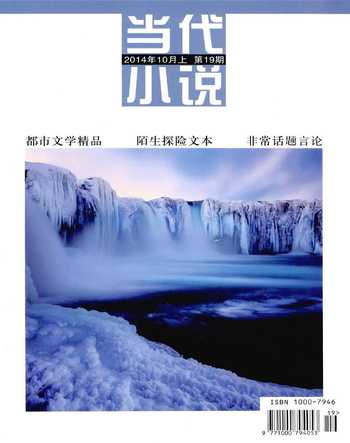我平凡的故事你在听吗?
张丽军 等
秋季主持:张丽军
秋日的忧伤
乔宏智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夏末秋初,暑热退却,早晚已觉凉爽的秋风带着拂过正拔节生长的庄稼的沙沙声,吹上人们的心头,带给我们丰收的希望和对丰收后喜悦心情的希冀。综观夏末秋初的文坛大刊,正如这时节即将收获的庄稼,让我们看到了文坛新的生长力量和累累硕果。一方面,文坛新生代青年作家汇报创作成果,《收获》2014年第4期开辟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栏目,集中呈现70后、80后青年作家的作品,与池莉、王蒙、叶兆言等文坛前辈同台竞技。另一方面,中、短篇小说创作占据了各大文学期刊版面相当大的比重。《清明》2014年第3期推出了《中篇小说专号》栏目,《十月》(2014年第3期)和《天涯》(2014年第4期)杂志也刊登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其中不乏优秀的篇目。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同样也有《人民警察》等作品可圈可点。
当我们畅快阅读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品尝秋日收获果实甜美的时候,却在舌尖喉头体味到了一丝丝的苦涩,感受到了阵阵弥散在心口的忧伤。那一抹秋日的忧伤,销声于岁月,匿迹在韶华,遁形于爱恨,却在不经意间带给生命一次次悸动的阵痛。
少年不识愁滋味。告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初识愁苦的少男少女们面对成人世界里的种种规则,往往不解其味,难以理解。面对初开的情窦,也充满着干涩的少年忧伤。巴克的《残忍的季节》(《清明》2014年第3期)讲述了初中生张子川的少年愁滋味。张子川就读于民办贵族学校星光学校,他的母亲郭琳是工商局科长,父亲是装修公司老板,家庭条件可谓富裕。张子川的成绩在班里也很得班主任语文老师盛老师的赏识,在他周围也有一圈志同道合的同学和朋友。然而,这衣食无忧的生活并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给张子川带来无忧无虑的生活。一次和暗恋自己的女生许艺的聊天,使得张子川对父母的感情产生了怀疑。经过张子川的一系列“侦查”,他不得不接受一个残忍的事实:父亲有了小蜜,母亲也有了自己的情人。或许在成人们看来,这一切虽残酷却可以理解,但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既无法和父母沟通,又“不知该如何面对发生的一切”。最后只得怪罪到暗恋自己的、为自己提供情报的许艺身上,给他人带去了伤害。张运涛的《谁是米的爸爸》(《清明》2014年第3期)同样是一篇以少年为主角的中篇小说。尖子生杨罗倩和同桌淘气男生张周都对自己的家庭产生了好奇,这种共同的少年疑问让他们两个人成为朋友并互相出主意打探彼此父母的秘密和自己的身世。杨罗倩母亲不姓罗,为何自己要叫杨罗倩?张周是否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小妹妹叫小米?两人带着这些疑问共同找寻线索,原来杨罗倩生身父亲姓罗,一岁时罗姓父亲雨天闯红灯出车祸死去。而现在的父亲正是当时的肇事车主,杨姓父亲其实在父母婚前就和母亲相识了,是母亲带孕嫁给了罗姓父亲。杨罗倩还因此产生误会报警以为车祸是一场蓄意谋杀。而张周的父亲在外确实有了小三,还生了私生女。小说借用俏皮的脑筋急转弯:谁是米的妈妈?花生米;米的爸爸是谁?蝶恋花。充满童真的同时讲述了少年淡淡的忧伤。双雪涛的《跛人》(《收获》2014年第4期)则讲述了十七年前“我”与小女朋友刘一朵在高考结束后一次“私奔”去北京的经历,尽管最终我们半路折返,尽管多年后“我”定居在了北京也再未彼此相见,但那年花开时节少年懵懂的甜蜜和忧伤至今仍难以忘却。
青年是喷薄而出的东升旭日,青年是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生命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人生中最应该奋斗和最有奋斗压力的时候。事业、家庭、婚姻、爱情,在当下浮躁的社会中,青年人的无奈和忧伤显得格外扎眼。面对忧伤,有人选择隐忍挣扎,也有人选择逃离。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收获》2014年第4期)则讲述了一个青年人——可悲的“我”逃离忧伤的故事。“我”放弃了大城市的打拼生活,来到了越南边境一个叫拉丁的地方,在远房表叔老康的帮助下,我决定去到荒无人烟的热带原始森林里居住生活一段时间。尽管“我”选择了逃离,最终却仍然无法避免挣扎于忧伤湖畔的命运。“我”曾有过两个女朋友。前女友李蕾,曾为“我”流过两次产,无奈我们生活拮据,尽管彼此一起奋斗努力,但社会现实让我们逐渐明白即使再努力也无法实现梦想。第二个女朋友则是有些偏执的女孩子小乌,她甚至追寻“我”找到了“我”隐居的原始森林。“我”本以为在原始森林里投入全部资金的药材种植能够让“我”有能力给与小乌一个美好的未来,然而药材的绝产让这一切化为泡影。得知小乌怀孕的消息后,“我”却只能“像野马样狂奔狂笑,躺到雪地里,假装已死”。青年人的奋斗却保障不了生活,负担不了爱情,这甚至已超越了忧伤的程度。陈仓的《上海十日谈》(《清明》2013年第3期)则讲述了报社记者与化妆品公司销售主管米昔的一段旷世绝恋。年轻时我们相恋相爱,却没想到患有心脏病的米昔在“我”的失误下受到刺激心脏病发作离世,“我”在米昔的墓旁守护了四十三年后,终于在地下与心爱的人儿团聚了。“十天爱了一辈子,天使米昔之墓”,这是青年爱情忧伤的墓志铭。
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一直是当代文学对情感和社会责任的一个关注点。而女性的忧伤则往往与一辈子的悲惨命运相连。池莉的中篇小说《爱恨情仇》(《十月》2014年第3期)便讲述了顾命大这样一个命途多舛的乡村女性的爱恨情仇。顾命大出生的时候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婴,出生后就被父母扔到了便桶里打算溺死,没想到便桶冬天冻裂了液体全部流出,命大躲过一劫。后来命大又被扔到冬天的野外打算冻死,却又被救起又躲过一劫。因为村里神婆别春芳的预言帮助,命大才被父母接受养大。父母为了让命大陪着弟弟上学,便让命大也进了学校。这甚至让家里二姐因嫉妒喝农药自杀了。后来命大又因为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企图喝农药自杀,农药却早被大姐换成了水,目的就是让命大承受包办婚姻之苦。婚前为了反对全家人对自己是否是处女的身体检查,撞石碾子自杀又被救了过来。结婚后命大生下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丈夫却游手好闲,命大又屡次遭受公爹的侮辱,在怀上公爹的孩子后顾命大含恨跳河自杀,却又被打鱼的河南老九救起,转卖给了人贩子。后来几经辗转,最终嫁给了河南老九,生活在了无浪湖村。无奈无浪湖却是无风起浪,生活了十年之久,被多年来寻母的儿子陈富强找到,就在看似命运将要迎来安稳的当口,一辈子福不大命大的顾命大因为一场车祸死在了回家的路上。沈书枝的《三姐》(《青年作家》2014年第7期)同样讲述了“我”的三姐一生坎坷的命运遭际。家里一共五个姐妹,三姐因为排次居中从小得到的长辈关心就比其他姐妹要少。反而还要承担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三姐本想好好学习,却无奈中考一直不中。后来选择了就业,学过做皮鞋,外出饭店打过工,网吧当过网管,结婚后还和三姐夫一起开了小饭馆。就在生活充满转机的时候,三姐夫病逝,最终三姐选择了带着女儿园园再婚。生活还要继续,三姐的忧伤也将随着生活继续下去。麦邦盈的《地里的庄稼》(《天涯》2014年第4期)同样讲述了乡村女子石花受乡村封建思想和谣言的伤害,不得不一次次被迫选择爱情的忧伤故事。女性忧伤的背后体现的是隐忍、坚强的伟大母性。
时间是最忠实、最客观的裁判者,也往往是最无情的。岁月带给人们的忧伤往往最是令人唏嘘、感叹,充满历史的沧桑感。王方晨的《大马士革剃刀》(《天涯》2014年第4期)便讲述了发生在老济南老实街上一个有关老实人之间的老故事。被称为“济南第一大老实”的左门鼻生活在老实街三十五号莫家大院,开了一间小卖部,养了一只老猫叫瓜。后来隔壁刘家大院搬来了开理发铺的陈玉伋一家。陈玉伋因为手艺精湛,价格公道,很快得到了街坊四邻的认可。左门鼻原本自己剃头,拥有一把莫家大院早年间莫大律师留下的剃刀,后来左门鼻将剃刀送给了陈玉伋,并约定以后都让陈玉伋来剃头即可。没想到陈玉伋认出了左门鼻送的是一把绝版精钢的大马士革剃刀,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如此重礼,如此两人间三送三还,最终陈玉伋还是把剃刀还给了左门鼻。一天,不知是谁,将左门鼻的老猫瓜浑身的毛剃得一根不剩,致使瓜因为羞愧直奔大明湖投湖自尽。不久,陈玉伋拜托左门鼻给自己剃了个光头,便离开了老实街,回老家不久便病逝了。几年后老实街最终被拆迁,而那把大马士革剃刀,却带着猫毛被扔进了垃圾箱。历史也好,恩怨也罢,曾经的故事也带着岁月的忧伤沉没进了历史的尘埃中。
命运最是叫人难以捉摸。艾玛的小说《白鸭》(《当代》2014年第4期)便关注了花钱顶罪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忧伤。小说分上下两篇,上篇讲述古代的C城,贫者替富人抵死,收受罪者的钱财,以此来改变家境贫寒的故事。此种抵死的贫者被称为白鸭,甚至是被家族冠以孝子的名声。如果说古代封建社会狱吏黑暗、司法缺陷,然而小说下篇从古代回到现代,在法制健全、讲究人权的时代,仍然存在白鸭,甚至于现代版的白鸭情况较之于古代更加复杂纠结,远远超过了金钱利益的联系。除了以上介绍的几部作品外,杨小凡的中篇小说《总裁班》(《当代》2014年第4期)、叶子的《桃李赋》(《清明》2014年第3期)和张忌的《素人》(《收获》2014年第4期)等,将关注点放在大学教授、白领公务员、商人等社会成功阶层的身上,诉说了他们身上光环背后的隐秘和忧伤。
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方面,程琳的长篇连载作品《人民警察》值得一读。这是一部跨越了三十年时空的反映人民警察群体工作和生活的作品。小说分为三部,第一部早在2010年便发表在了当年第2期的《收获》上。时隔四年,《人民警察》第二部发表在了2014年第3期《收获》杂志,第三部发表在了2014年第4期的《收获》杂志。小说共分三部,以80年代、90年代和20世纪为三个时间段,以人民警察陈文一生的从警经历为线索,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人民警察职责和工作重点的不断转变,反映了基层人民警察个体的悲欢离合与警察群体法制工作建设的不断完善。这是一部向人民警察致敬的作品,作品中反映的许多历史性变革值得我们深思。
时间永是流逝,秋日的忧伤也终将被收获后的欣喜和寒冬的肃杀所终结。然而不变的是文学前进力量带动下向前走的步伐,期待着再次相约下一个金色年华!
最难的是活着
辛晓伟
夏季,是一个夹杂着焦躁和骚动的季节。气温的飙升在激活了体内细胞更加旺盛的活力之后并没有回歇,依旧在不遗余力的榨干人们的气血和精力。高温过后,于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看到了一群被大自然温度所灼伤的人们,我们更看到了被生活、时代所抛弃的失宠儿。那些曾经风光无限如今落寞惆怅的下岗工人。他们好像绽放一时的夏花,在经历一场霜打之后变得残败不堪。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文学作品从来都不是完全想象的产物,它是在捕捉时代的讯息和生活的缩影之后,对我们的生活做出的一种回应。生命是崇高令人生畏的,而生活是琐碎叫人心累的,但就在这岁月车轮的碾压中,我们在艰难地活着。
《北京文学》2014年第6期刊登的著名作家陈应松的小说《跳桥记》鲜活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体在时代巨变中的沉浮落寞。公胡子,一个爱唱歌、有着文艺范儿的下岗工人,在失业之后处处受到打击:在买断工龄之后与朋友合伙一起做生意,结果车、货被偷致使负债累累;妻子与其离婚并且企图抢走房子;儿子被抓进少管所后眼睛却被熏瞎。面对这一切,公胡子只能与酒为伴,在碰到债主讨债后,无力偿还想到去跳桥更以死作为了结。在“死本能”的驱动下,他甚至想到帮助别人一起死。就是这样一具被生活所摧毁的躯壳,灵魂已经腐朽只剩一副空皮囊,混迹于这个没有生活希望的社会。作者一方面在斥责这个时代和社会对他的不公,在历史的车轮滚滚中,他们只是被碾压而又被扬起的一粒微尘。时代与社会并没有直接吞噬掉他们,而是渐渐吸掉大部分的“氧气”,让这些下岗工人最后“窒息而亡”。曾经处在人人羡慕的“吃国库粮”的工作岗位,如今落得跟不上时代脚步的“扯后腿”,这些人所经历的不只是物质经济的落差,精神上的幻灭或许才是致命一击。下岗,一个在九十年代开始意味着被社会否定的代名词,公胡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存在感、认同感的缺失最终使他们选择自亡。因此,这些人的境遇是相似的。灰暗、艰涩、焦灼,《跳桥记》小说里弥漫着令人绝望的气息。无独有偶,《山东文学》2014年第6期嘉男的《一天与一生》也刻画了一个无处寻觅生的阳光、最终走向死亡的可怜人的形象。在《跳桥记》里面,其实,这只是一种表层的理解,小说里的公胡子的徒弟庞中华倒是一个带有鲜活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同样是下岗,但是他在学通卤菜技艺之后自开小店,活得有滋有味。这也是对公胡子形象的一种驳斥。当然,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下岗工人,就像一条条原本游得好好的鱼,突然被人从水里抓出来当街摔死。摔死的就死了,摔不死的,顺下水沟溜了。”同样第6期里面李其珠的《一抹阳光》这篇小说也恰恰涉及到这个问题。陆文虎作为一名下岗职工,用上面的话来说就是鱼没被摔死,而是坚韧的、挣扎着活了下来。由过去威风的采煤班长变成现如今垃圾站运送垃圾的运车工,陆文虎却认认真真地做了起来。每天拉着大平板车,顺路的时候会带上儿子,父子两个一路欢声笑语回家。活着,是靠一种心态,而非一些空而大的道理。儿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亲的乐观向上,对工作的本分、职责的尽守使得陆文虎有了生活的目标和方向。这种积极的心态就像一抹阳光,照亮的不只是一个人,更是周围的一个群体。因为阳光是温暖的,力量是强大的。
刊登在《鸭绿江》上2014年第7期徐岩的《老潘的油田》刻画了一位对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老技术工人形象。作为一名技术工,那就要靠技术说话,其工作就是为那些大大小小的磕头机检查和保养。“就是这些个不会说话的铁家伙,让老潘心里边觉得温暖,把他拴牢在这块荒蛮之地。”当然,这也让老潘乐亦在其中。小说着力塑造老潘的认真负责,那是一份不可言说的使命感,对这份工作的发自内心的热爱,“查看那些机器,对待宝贝似的亲自擦拭和检修。”然而一场意外把几十台磕头机全部报废,他也因此被“贬官”新采区。但是,工作地点的变迁丝毫没有减弱他工作的热情,他告诫徒弟“一定要脚踏实地,即便是拧个螺丝疙瘩也得做到认真细致,可别小瞧了那些个只会弯腰抽油的铁家伙,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呢。”把不会开口说话的铁疙瘩看做是有生命灵性的伙伴,这样的工作态度又怎能做不好呢?融入到生命里的工作在善良憨厚的老潘眼里,就是一辈子最大的乐趣。在老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上一辈人对工作的热忱和赤诚,这才是在今天我们心底的最大震颤。小说的发展顺应了我们当今社会的大流向,反映出来的贪污造假问题最终毁掉的不只是机器和人,更是一种精神与信仰的挫败。当杂质和劣质充斥在社会中而成为大多数时,难道我们只能痛心疾首、扼腕顿足!
而刊登在第6期《鸭绿江》上贾颖的《错位》这篇小说刻画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叱咤风云的大刑警,一个是“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管户口的小片儿警。小片儿警杨庆来一直在被儿子鄙视之后心里很窝火,一心想干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让儿子好好崇拜一把。孰料到在处理李德才的案子时还被李德才说到“你就会查户口”,就是这样一句略带轻蔑的话愈加刺激了杨庆来当一回英雄的欲望。当他看到风风光光的老同学卫凯后,才不得不发出这样一句感慨“自己的人生放在卫凯的人生面前,实在是说不出的单薄”。同样是警察,一个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一个在市井街巷里忙碌,表面上看起来不可同日而语,其实工作的本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活在这个社会中,自身的价值与存在感并不是取决于他人的眼光,而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可或缺。生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漫长而又艰难的,哪怕是在光鲜靓丽的背后也是一个个生命的隐忍过活。
生活有时候就像一片海,我们都漂在上面。尤其是对于那些之前设定好人生轨迹的人,巨浪过后,就会失去方向感产生一种虚无和幻灭。刊登在《延河·绿色文学》2014年第6期的吕虎平的《日历》,里面就写出了一位下岗工人的绝望。四处碰壁会磨灭一个人的精神劲头儿,在浑浑噩噩中结束后半余生。小说里面的木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依靠黄历过活的人。
我们说生活不易,且活且珍惜。当有一天,周围的一切在你眼中突然变得陌生起来,节奏变了,脚步也凌乱了。此时,不必怀疑也不必抱怨,这就是生活交给我们的无法去躲避的东西。正像刊登在《飞天》2014年第6期中雪归的《春尖尖》讲述了一位中年妇女的辛酸生活。上有老下有小,这一辈人肩上扛负的就是整个世界。周蕊是一位普通的洗车工,不像同事小祁那样可以依靠出色外貌就可以招揽很多顾客,她只是特别认真地洗好每一部车子,本本分分地做好手头上的工作。在李先生送给她一张健康体检卡后,她带着年迈的母亲来到大医院第一次为母亲做全身检查。母亲辛劳半辈子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周蕊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使得周蕊的心操碎了,她没有金钱和精力顾及这些“享受层面”的生活。但当第一次诊断出母亲患有癌病的时候,周蕊心里如针扎一般。“母亲罹患如此严重的恶疾,做女儿的,竟一直没有察觉,周蕊觉得自己真是大不孝。”生活这么困难,谁会没事来做检查呢?但当发现时,已经晚了。这就是生活在底层人的困境和悲哀。小说最后的结尾虽然是一种误诊,但作者是紧贴人物的灵魂走的,周蕊的一声哀叹“这下子,又该轮到哪一位儿女,为哪一个和自己母亲同名的老人揪心?那个母亲,会不会也和自己的母亲一样,说类似春尖尖一样古怪可笑,却妥帖又温软的话呢?”这句戳心窝子的话一下子拉近了人与人之间心的距离。所以,小说的结尾也变得意味深长。缪文宗《饭客老费》让我们看清了这个社会的真实面目,令人哭笑不得。
刊登在《延安文学》2014年第4期刘公的《游走在壶梯山下的魂灵》江大洪用二十年来偿还一份债,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第3期《延安文学》青疯的《地铁里的男女》以生活化的场景再现让我们感受到了真善美的存在。《西部作家》2014年第3期,清羽的《月亮湖彻夜不眠》读完之后,内心是一种隐隐的痛,却又哭不出来。
生活尽管是艰辛的,怎样把苦日子过得有滋味儿就是一种本事。生活是苦的,但回忆是甜的。就像《延河》2014年第6期马召平的《窗前明月光》就是一篇上好的佳作。作者的文字是那么的温暖,以月光来统领全文,读完之后我们没有生涩的苦,没有凌厉的痛,心好像找到了家。这就是文字温润心灵的力量。《北方文学·上旬》2014年第3期安世元的《关东猎人》也是一篇难得的佳作。作者笔力雄浑,小说也耐读,字里行间浸润着浓郁的关东气息。《辽河》2014年第6期秋泥的《旧照》以琐碎的生活为背景,刻画出仿佛近在眼前的人物形象,语言通俗直白,但却回味无穷。《时代文学》2014年第3期陈东亮的《回家》在乡野村头向我们传达生活的希望,只有好的心态,生活才不会觉得那么苦。
我平凡的故事你在听吗?
史胜英
回顾现当代中国的文坛,不乏对底层小人物的观照与叙写,从鲁迅笔下的阿Q到老舍笔下的祥子,再到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三仙姑,鲜活丰满的小人物形象在文学的舞台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辉煌印记。在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今天,对小人物的书写仍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小人物如地之精灵,以切身的生活与经历最深切地触摸时代的肌理,把握时代脉搏。小人物可能无法像英雄豪杰一样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创造历史,但他们在过自己的生活,零零碎碎,平平淡淡,不紧不缓,他们的喜怒哀乐可能牵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精神遭际最可能引起我们的情感共鸣,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正如朴树在那首新歌《平凡之路》里所唱的,“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在近几期的文学期刊上,作家们对小人物命运一如既往地进行思考和持续关注,一方面对小人物所面临的新的时代困境进行敏锐洞悉与艺术还原,另一方面对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与向度进行把握与观照,彰显了作家为时代、为社会立言的使命。
发表于《长江文艺》2014年第5期的中篇小说《芹的河岸》(王甜),以细腻温婉的笔触讲述了屠家三姐妹的故事,天生丽质的小妹水芹活泼、爱美,只是读书不用功,然而由于母亲冷漠至极的放任,大姐水英不问青红皂白的谩骂,行为不端的二麻婆的教唆,乡间可怕的流言以及学校不负责任地开除学籍,一切的一切,将一个原本自在美丽又可塑的生命一步一步逼向了堕落与毁灭。如此旖旎的水乡不禁让人联想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湘西的女子也如水一样纯净自由,《萧萧》里虽然描写的山民与外面世界的隔绝和愚昧无知,但在萧萧犯过“大罪”后,村里人给予了她宽恕与包容,体现了宽松的文化环境和对人的关怀。回看水芹,对于这个问题少女,周围人不是放任自流就是一味打击,并未真正去关注过她的内心世界。那么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中,为问题少女搭建一座怎样的精神河岸,成为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付秀莹的短篇小说《绣停针》(《长江文艺》2014年第6期)亦有着沈氏风骨,以散文化的文风记载了小人物的凡俗生活。心思细腻、绣得一手好针线活的小鸾嫁给老实巴交的占良,过着平淡的生活,然而二流子中树的介入如投入湖心的石子,给平淡的日子激起了涟漪,中树勾引小鸾并与她偷情,事后小鸾羞愧又愤怒,而中树发达后荣归故里的风光又使小鸾嫉恨交织。作者通过一桩桩平凡琐屑的小人物小事件如抖面筛子一般细细铺陈,淡淡地忧愁与微妙的感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没有大喜大悲的人物,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有的只是小人物的小烦恼与纠葛,以诗意化的语言和环境渲染,营造出古朴典雅的意境美,同时不乏现代意识的探索,其文风由此别具一格。
《作品》2014年第5期中的《拜访郑老师》(陈再见)和发表于《长江文艺》2014年第6期中的《师表》(赵卡)都是对乡村青年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拜访郑老师》中“我”陪哥哥一起去拜访郑老师,在这过程中所展现出了乡村风貌与世故人情:有着文学梦想的哥哥希望实现抱负,而将抱负的实现寄托在与郑老师的“关系”中,无奈受到现实的打压排挤,最后转投学医,郑老师去世后哥哥在村里当起了赤脚医生。小说最后独具匠心地描写了哥哥诊所的布置,地毯、沙发、报纸架,其风格以及哥哥的生活方式都是在模仿郑老师,那些文学和医术,悄然成为哥哥的敲门砖,哥哥真正梦想的,是城里知识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哥哥形象作何定夺我们暂且不论,作者对当下乡村知识青年的精神追求的把握与塑造深有内蕴。《师表》则是通过乡村代课老师的亲历亲见,让我们看到了基层教育的另一面真实。小说以幽默戏谑的叙事手法,开头交代了“我”这个代课老师实为待业青年的身份,从而解构了教师的崇高感,而在上任后有了自觉的使命感和转为正式教师的职业上进心。他的讲课方式也是独辟蹊径,教学生用英语骂人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班中的活跃分子打成一片,对漂亮女生产生萌动的感情,这一切都与传统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格格不入,这也使“我”最终被辞退的结局成为必然。作者所塑造的“我”却是符合人性的,真正关心学生、正直、负责的品质并未改变,以至于赵老师开学后又跑到学校去,浑然忘记自己已经被解聘的事实。
小人物的真实还体现在他们的恶的一面,这种恶是来自人性深处不易被察觉的却又是真实存在的,在小说创作方面不胜枚举。盛可以的《香烛先生》(《作品》2014年第7期)中傻子哥哥与聪明可人的弟弟在玩捉迷藏的时候将其摁进了棺材;罗门的《李探戈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作品》2014年第5期)中保姆李探戈利用主人家的家庭矛盾进行周旋而成为最大的赢家;曹明霞的《星期五浴室》(《钟山》2014第4期)以精妙的故事构架将亲妹杀哥的案件层层剥开真相;鲁敏的中篇《徐记鸭往事》(《长江文艺》2014年第5期)则以死者的口吻陈述鸭店老板生前的故事……这些怪异离奇的故事背后,透露着小说人物内心的真实和结构逻辑的合情合理,对人物内心的纹理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为我们认识思考人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迪。
黄荣才的创作一直很活跃,他的最近发表在《福建文学》2014第8期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和《四川文学》2014年第7期的短篇小说《车轮滚滚》中对鲜活的人物描写和具有强烈现实感的事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车轮滚滚》讲述了交通局长吴介义因一场于他并无责任的交通意外而产生种种连锁反应,最终失掉了局长的职位,现代社会人性的贪婪自私与失范的舆论,使得是非颠倒,展现了现实社会的滑稽与隐痛。《别人的城市》则将目光转向底层人物,观照一个农民进城的遭遇和房价飙升对普通民众痛彻心扉的磨难。农民王大伟来到县城谋生,渴望在县城拥有自己的房子,他卖掉农村的房子,忍受村主任林国民的欺压,甚至将女儿嫁给一个伤残者,而付出的种种努力都未能使他如愿买房。当他想放弃县城挣扎回到乡村的时候,猛然发现他的乡村也回不去了。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似乎又在今天复活了,恰似车子对于祥子的意义,房子对于王大伟,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容身之所,更是作为“城里人”的一种象征。
小人物的生存困境直指现实,小人物的精神困境则痛彻人心。冯慧的中篇小说《寻找余闲》(《长江文艺》2014年第6期)中的“凤凰男”余闲,受到婚姻家庭和工作上的双重挤压,致使他精神世界出现危机,小说通篇与其说是对一个失踪男人的寻找,不如说是余闲对其个体精神出口的寻找。第代着冬的短篇小说《那件事》(《四川文学》2014年第7期)记述了失业青年大表哥与妓女安小雪的纠葛,邮差出身的大表哥从恋上路到恋上人,认真执着的大表哥领养了派出所的一只叫匹夫的狗,共同守护不安分的安小雪。小说通过对乡村社会世态百相的书写,展现了基层权力的中空下,人们道德无处规约,精神焦虑无着的现状。作者架构小说的能力成熟老练,简短的篇幅为我们隐埋了许多象征和隐喻,几乎每个人物都是一个符号,如大表哥出走寻找匹夫,真正寻找的是文明与权力、秩序与公平。鬼金的中篇小说《多少悬在半空中》(《长江文艺》2014年第7期)记述了吊车司机杨怀为厂里编排话剧《天梯》的过程,以戏中戏的现代主义手法,写出了80后一代工人们的精神状态。“机器坏了还要保养修理,可我们人生病了,就要扣奖金或转岗”,80后一代没有老一辈的集体荣誉感,更多的被囚禁在制度中,对生活缺乏激情和热忱,生活如天梯般看不到尽头,人们在荒漠化的生活中,精神汹涌着无处诉说的焦虑。邓一光的短篇小说《深圳河里有没有鱼》(《作品》2014年第6期)通过寻访深圳河中有没有鱼,切入被遗忘的历史,通过对精神世界的不断追问,探寻我们灵魂的出路。“深圳河”与“鱼”都跳出了实指,成为形而上的象征,最后作者说“我是那条鱼了”,鱼象征自由的精神个体和人们信仰的一缕微光。
朱斌峰的《玻璃房》和刘永涛的《对面的女人》两篇带有意识流色彩的小说同时发表于《作品》2014年第7期,《玻璃房》中“我”与朱文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体现了现代社会中自我精神的迷失;《对面的女人》则从坐在对面的女人与记忆中的女人的双重线索展开,实则对面的女人也为臆想中的女人,作者在回忆与现实中心理的变化,为小说增添了几丝荒诞。90后新秀朱嫣然的《末路之旅》(《作品》2014年第5期)为情所困的年轻姑娘在旅行中进行精神创伤的治愈,行文清新而细腻。
小人物遍布地域的各个角落、各个行业、各个阶层,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矿藏,优秀的作家都是从表现小人物写起的。作家的笔像一面三棱镜,将小人物微观世界一经折射,便呈现出时代的千形万象。当下,对小人物进行日常化生活化的描写成为作家的自觉选择,体现了作家心态的日渐沉淀,对文学的现实感与艺术本质回归的认同,为尘埃漫布的文坛洒下清净的露滴。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