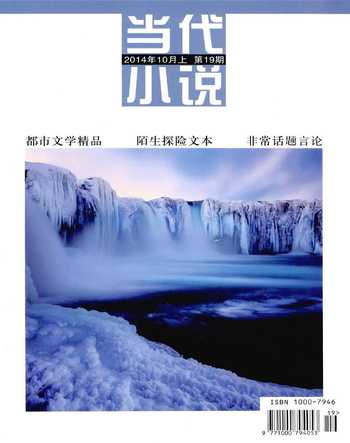松鼠们跑过山野
赵雨
六年级四班顾欣欣同学的爸爸这星期天邀请同学们去他家的别墅参观,中午在农家乐吃烧烤,班主任把这消息向全班公布时,要求想去的同学自己举手。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纷纷举起了手。顾欣欣的同桌李卫卫同学一开始没举手,他在桌下偷看一本漫画书,没听清班主任在讲什么。
“你不想去我家?”顾欣欣的手肘越过“三八线”,顶了顶李卫卫。
“去你家干什么?”李卫卫说。
“参观啊。”顾欣欣说。
“你家有什么好参观的。”
“你不去?”
“不去。”
“那我把你看漫画书告诉王老师,让她把你的书没收掉。”顾欣欣说。
李卫卫见识过顾欣欣的厉害,他上次就被她向王老师打过一次小报告,没收了他的一本漫画书,他不想得罪她,最后只能答应了。
去的那天,顾欣欣的爸爸派了一辆大巴车来学校接同学,李卫卫这天穿了一件白色小西服,一双黑色小皮鞋,是他妈让他穿的,就像童装海报上的小童星。
“你怎么穿成这样?”顾欣欣笑得肚子疼。
李卫卫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同学们排着队上车了,顾欣欣把李卫卫推上去,和他坐在一起。
车沿着省道往前开,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从省道拐上“衡山路”,就到了本地旅游景点——九峰山的地界。顾欣欣家的别墅就在九峰山下,名为九峰庄园,一大片掩映在绿树、茶园中的别墅群。顾欣欣的爸爸在停车场等,同学们一下车,他就和他们打了招呼,他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班主任来到他面前,说了声:“打扰了。”
“不打扰。”他笑着说。
他领着他们从树丛间过去,李卫卫已把衣服的事抛到一边,放眼望去,都是乡野的景色,不觉兴致盎然,因为顾欣欣在一旁,又不能表现得过于迎合她的意图,所以表面还是蛮不在乎。
到了顾欣欣家的别墅,偌大的屋子展现在他眼前,到了里面,大厅有近十米高,四面的扇形窗帘遮天蔽日,像走进了一座教堂。两个女人已在那里,准备了饮料,其中一个就是顾欣欣的妈妈,同学们落了座,王老师站出来说:“顾欣欣爸爸,你们这里真是大。”李卫卫觉得这话说得别扭,顾欣欣爸爸听了却很受用,“半年前刚搬进来的,有些地方还没打扫好。”他说。
同学们喝了饮料,顾欣欣爸爸带他们去参观了,顾欣欣待在李卫卫身旁,李卫卫觉得她今天有点怪。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头发梳成两个麻花辫,处处表现出小主人的礼仪,跟在爸爸身后,沿着回旋楼梯往上走。楼梯扶手雕龙画凤,通到二楼,几个房间的门开着,平台上摆着一张红木桌,可以俯瞰一楼。李卫卫在那里待了一会儿,不想跟随大众按指定的线路参观,便趁人不注意,溜到一旁,从偏门拐上另一道楼梯,到了三楼。那里有两个房间,一扇门开着,他便走了进去,里面坐着一个人,在玩电脑。
“这里也是参观的地方?”他说了句。
“对不起,我走错了。”李卫卫说,转身欲走。
“等等,”对方说,“你叫什么名字?”
李卫卫和他正面相视。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他说了,“对,我们肯定在哪里见过。”
“你是顾欣欣的哥哥!”李卫卫突然喊了声。
“对,”顾欣欣的哥哥说,“你是那捡球的小鬼!”
李卫卫想起他们曾经在学校组织的一场乒乓球赛上见过,顾欣欣请她哥哥来作裁判,李卫卫负责捡球。那次比赛,他捡了总有一百只球,顾欣欣的哥哥给了他一个绰号叫:捡球小鬼。那还是在李卫卫三年级的时候。
“快进来。”顾欣欣的哥哥这会儿向他招手。
李卫卫走了进去,这房间和别处不一样,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凳子和一个字纸篓,桌上放着个烟灰缸,里面全是烟头。
“你怎么穿成这样?”顾欣欣的哥哥说。
李卫卫摊了摊手,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顾欣欣的哥哥让他在凳子上坐,顺手抽出一支烟,“你抽吗?”他说,李卫卫摇摇头。
“很高兴再见到你。”李卫卫说,像大人一样。
“我也很高兴,”顾欣欣的哥哥说,“小鬼,你长得可真快。”
李卫卫耸了耸肩,“你怎么待在家?”他说。
“那我在哪里?”
“听顾欣欣说,你去了别的地方,去了……”
“兵营。”顾欣欣的哥哥说。
“对,兵营,”李卫卫说,“你去当兵了,那可真酷。”
“那可不是件酷的事,”顾欣欣的哥哥抽了口烟,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觉得去当兵是件很酷的事。”
“你不大乐意?”李卫卫说。
“你让四十多度的太阳晒过脑袋,在暴雨中坐过半把小时,就知道滋味了。”顾欣欣的哥哥把烟戳灭,又点上一根。
“我以后也要去当兵。”李卫卫说。
“行行,”顾欣欣的哥哥说着,站了起来,“但我们现在能不说这些吗?一说这些就让我头疼,你想喝点什么,小鬼?”
“别叫我小鬼,我六年级了。”李卫卫说。
“六年级的小鬼,”顾欣欣的哥哥笑道,“但你难道真不想喝点什么吗?”
“你这里有什么?”
“什么都有。”顾欣欣的哥哥走到床前,蹲下来,从床下拉出一箱饮料,真的什么都有。
“那就橙汁吧。”李卫卫说。
顾欣欣的哥哥拿了一瓶橙汁给他,自己开了瓶啤酒。
“你们家可真大,”李卫卫学刚才班主任的话说。
“大不大都一样。”
“你不觉得了不起?”
“你是说住在一幢别墅里是件他妈的了不起的事?”
“你不觉得吗?”
“就这样,”顾欣欣的哥哥说,“大不大不管我的事,我就住在这里。”他用手势把整个房间画了个圈。
“但你不出去吗?”李卫卫问。
“有什么好出去。”
“你干什么?”
“就待着,上上网。”顾欣欣的哥哥说。
李卫卫看了一眼他的电脑屏幕,上面是一堆手枪的图片。
“那些枪太酷了,”李卫卫说,“我喜欢枪。”
“枪可不是什么好东西,”顾欣欣的哥哥说,“但我也不讨厌它。”
“你拿过枪吗?”李卫卫问。
“拿枪?”顾欣欣的哥哥说,“当然,我还用枪杀过人。”
“不会吧?!”李卫卫说。
“我给你看。”顾欣欣的哥哥说着,顺手移开一旁的抽屉,李卫卫怀疑他会拿出一张杀人的照片,但结果取出了一枚弹壳,表面是黄铜色一层,染了几点暗红色。
“这就是我用来杀那个人的枪里射出的子弹。”顾欣欣的哥哥揉搓着子弹说。
“你上过战场?”李卫卫问。
“上过,”顾欣欣的哥哥说,“我在战场待了大半年,就是那种到处长满树,飞着蚊子的战场,你可以想想人猿泰山里那样。”他说。
“你怎么把那个人干掉的?”
“那天我受命巡逻,”顾欣欣的哥哥喝了一大口啤酒,“穿着迷彩服,扛着枪,戴着柳条编织的军帽,那感觉可他妈不大好,就像捉迷藏似的。而那混蛋就站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你猜他在干什么?”他说,看着李卫卫,李卫卫摇了摇头,“在撒尿!”他接着说,“那混蛋居然在撒尿!这他妈的可是在战场上最不要命的做法了,我敢保证,我当下就拎起枪给了他一枪。”
“他就死掉了?”李卫卫问。
“不,他只是倒下了,”顾欣欣的哥哥把啤酒喝完,又开了一瓶,“他张着嘴,像只河马那样呼吸,所以我就走过去给他补了几刀,他就死了。这可是我第一次杀人,我想留下点纪念什么的,就用刀割开了他的肉,把射进他体内的子弹给挖了出来。”
李卫卫倒吸一口凉气。
“这就是那颗子弹。”顾欣欣的哥哥把子弹摊在手掌心,摆在李卫卫面前,李卫卫用一种崇拜的眼神看看那枚带着暗红色的弹壳,又看了看顾欣欣的哥哥。
“你觉得怎样?”顾欣欣的哥哥说。
“太酷了。”李卫卫说。
“你喜欢吗?”
“喜欢。”
“那就送给你吧。”
“你把它送给我?”
“你不要?”
“要要,”李卫卫说,“但你怎么舍得送给我?”
“只是一颗子弹罢了,”顾欣欣的哥哥说,“我已经烦透这些该死的东西了,但我有个要求,”他说,“就是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一定。”李卫卫说,接过子弹,攥在手心。
这时,顾欣欣进来了,“我到处找你,”她对李卫卫说,“你怎么来这里了?”
“哟,我们的小公主来了。”顾欣欣的哥哥笑着说。
“我没跟你讲话。”顾欣欣瞥了他一眼,一副不屑的样子。
“你怎么每天像吞了火药似的。”顾欣欣的哥哥还在笑。
“请,你,不,要,跟,我,讲,话,”顾欣欣一字一顿说,“我们有约定的。”
“瞧,我们有一项该死的约定,”顾欣欣的哥哥对李卫卫说,“就是一星期不讲话。”
“现在你讲了,我们就要两星期不讲话了。”顾欣欣说。
“这是违约的惩罚。”顾欣欣的哥哥说。
“总之就这样,”顾欣欣说,拉了拉李卫卫的手说,“我们走吧。”
李卫卫看了看顾欣欣的哥哥,顾欣欣的哥哥对他扮了个鬼脸,“走吧,要不小公主要生气了。”他就跟着顾欣欣出去了。
“你怎么来这里了,”出了门,顾欣欣说,“你不该来的。”
“为什么?”
“爸爸会不高兴的。”
“为什么?”
“反正会不高兴,我也说不上来,”顾欣欣说,马上又好像把这事忘到了一边,问道,“你觉得我们家怎么样?”
“就这样。”李卫卫说。
“什么叫就这样?”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别墅的好话。”
“那就是不好。”顾欣欣说,李卫卫觉得抱歉,以为她会生气,想解释几句,但她转而说,“这样吧,”她说,“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去了就知道,这次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说着,顾欣欣便领着他从另一条楼梯下去,避开楼下的人,从别墅的后门出去,一条上山的路,两旁绿树成荫,耳边有鸟的鸣叫。李卫卫一下提起了兴致,跟在顾欣欣后面,不一会儿,山势开始变陡,李卫卫脱掉白西服,把两条袖子绑在腰间,作成裙子的模样,地上落叶满地,延绵数里,铺成一条毯子。树上站着几只花斑鸟,听到脚步声就“咕咕”飞进了枝叶,树后传来溪流的声音,但看不见,突然“噗通”一下,李卫卫觉得那是跳鱼的动静。
十来分钟后,他们到了一个岔口,左右各开着一丛叫不出名的花,如火如荼,像烧着一样。顾欣欣选了左边的道,李卫卫和她隔着一米的距离,又走了一会儿,顾欣欣说:“到了。”他便停下脚步,站在一块平地上,这里的树更加高大,把平地围成一面池塘大小,遮天蔽日,天空都望不见,不知何处飘来花的芳香。正前方,四根木柱支起一间小茅屋,离地三四米,一架楼梯挂在一旁。顾欣欣向李卫卫招了招手,他们便一前一后爬到上面,那里有一张木板床,盖着塑料布,地上铺着稻草。
“好了,就是这里。”顾欣欣说。
“这是什么地方?”
“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顾欣欣扬了扬嘴角,“谁都不知道。”
“你发现的?”李卫卫问。
“对,”顾欣欣说,“刚搬来这里时,有一次我一个人上山来逛,找到的。”
“这是别人搭建的?”
“应该是,”顾欣欣说,“但我发现时已经没人来了。”
“但那个人又来了怎么办呢?”
“你关心这些干嘛,”顾欣欣说,“究竟怎样?你还没说呢。”
“挺好的,”李卫卫说,“比你家别墅好多了。”
顾欣欣笑了笑,没搭话,“你过来,”她说,爬上了床,跪在床板上,推开上面的一扇草窗,用一根木棒撑起来,望出去,是一大片树林。
“看到没?”顾欣欣说。
“什么?”
顾欣欣用手指点着,“往那里看,那里,最大的那棵树,对对,再旁边一点,就是那里。”
“看到了,”李卫卫说,“一个大树洞。”
“对,”顾欣欣拍手说。
“大树洞怎么了?”
“那里是噜噜的家。”
“谁?”
“噜噜。”
“噜噜是谁?”
“噜噜不是谁,是一只大松鼠,那里住着噜噜和它一家,一窝松鼠。”
“你把一只松鼠叫噜噜?”李卫卫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是它们一家?”
“我看到过,”顾欣欣说,“晴天的时候它们会爬到树外,噜噜和它的几个孩子,但我就看到它们爬到树洞口,伸了伸脑袋,就进去了。我不知道怎么走到那里去,那里太远了,也没有路……”
“总可以找到吧。”李卫卫说。
顾欣欣笑了笑,放下支架,关上草窗,显然想换个话题了。
“我再给你看样东西。”她说,趴到床上,从下面抽出一个小木盒,打开盒盖,放着各种各样小玩意儿,头绳、手帕、橡皮筋、梳子……
她拿出一捆用橡皮筋扎起来的纸牌,“这是香烟牌,”她说,“你玩过香烟牌吗?可以叠起来拍,我和我哥以前玩过的。”
“你哥也玩?”李卫卫有点意外。
“对,还有这个,”顾欣欣又拿出一包玻璃弹珠,“这是放在石板上打的,也是我们玩过的。”
“你怎么把它们放在这里?”
“我哥现在不跟我玩这些了,我舍不得丢,就带来了。”
“他才不会跟你玩这种东西,”李卫卫说,“他现在干的都是大事。”
“他能干什么大事?”
“说出来会吓你一跳。”李卫卫说着,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颗子弹,他想起和顾欣欣的哥哥的约定,但现在他想让顾欣欣吓一跳的念头战胜了一切,所以他把子弹拿了出来。
“你看。”他说。
“一颗子弹?”
“对,子弹,”李卫卫兴奋得手心在出汗,“你哥用这颗子弹杀了一个人。”
“什么时候?”
“战场上,”李卫卫说,“他为了留作纪念,把这颗子弹从那死人身上挖了出来。”
顾欣欣大笑起来,“他跟你说的?”她说。
“怎么了?”
“你上当了,傻瓜,他的话你也能信?”
“你才是傻瓜,”李卫卫说,“你凭什么说他撒谎?”
“因为他根本没上过战场。”
“他去当兵了,你告诉过我。”
“我是告诉过你,”顾欣欣说,“但当兵了不一定要上战场啊,他当了半年兵就回来了,他可受不了那里的日子,假如他真上了战场,也是个逃兵。”
“你骗人。”李卫卫坚持说。
“他才不敢杀人,他这样的胆小鬼敢杀人我把头割给你,他连杀条虫都不敢。”顾欣欣说。
“那这颗子弹是怎么来的?”李卫卫把子弹凑近顾欣欣面前,试图用他最后的证据说服她,“上面还有红红的血迹。”
“那才不是血迹,是油漆,”顾欣欣说,“这颗子弹壳是他从部队回来后在旧货市场花十块钱买的,他还有一大盒呢。”
李卫卫觉得受了委屈,真想拿拳头打人出出气。
“总之他的话你一句都不要相信,他现在就是个骗人精,一个胆小鬼骗人精,”顾欣欣说着,看了看手表,把盒子盖上,塞进床底,拍了拍裤子,跳下床说,“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李卫卫跟她下了木梯,把子弹攥在手心,然后放进口袋。
但顾欣欣没带他按原路返回,而是走上了另一条道,比先前那条通畅多了。
“我们去哪里?”李卫卫说。
“去看看我奶奶。”顾欣欣说。
“你奶奶?”
“对。”
“她住在山上?”
“她不愿意住别墅,说山上的空气好,我爸就在这附近给她建了间小木屋,里面可好了,待会儿你就会知道。”
他们便往前走,不一会儿来到了另一块平地,那里有棵大榕树,腰身粗壮,枝繁叶茂,远远看到一位老奶奶坐在榕树下的矮凳上绣针线,顾欣欣喊了声:“奶奶。”
顾欣欣的奶奶抬起头,站起来,她满头白发,但脸色红润。
“这是我的同学李卫卫。”到了跟前,顾欣欣说。
“奶奶好。”李卫卫打了声招呼。
“你好,”顾欣欣的奶奶说,“今天怎么来了?”
“我爸请同学们来家里参观,我们上山来玩。”顾欣欣说。
“进去坐吧。”顾欣欣的奶奶对李卫卫说。
他便进了那间小木屋,里面放的都是老农具,墙上挂着蓑衣和斗笠,墙角摆着个石磨。顾欣欣的奶奶让他在窗前坐,窗户是木格窗,上面吊着碎花帘子。
“你想喝什么?”奶奶问。
“不用了,”李卫卫说,想起在顾欣欣的哥哥房里喝过的橙汁。
“我想喝桔子水。”顾欣欣说。
顾欣欣的奶奶点头笑笑,给他们泡了两杯桔子水,“你哥呢?”她问。
“待在家里,”顾欣欣说,“他能去哪里?”
“还没找工作?”
“他才不会去找工作呢。”
“你爸前段日子不是带他去公司干过?”
“是去干过,但没两天他就不干了。”顾欣欣说。
“为什么?”
“没劲,他说没劲,”顾欣欣说,“现在这就是他的口头禅了,爸爸说你就死在家里算了,”顾欣欣模仿着她爸的口气,“他说,就让我死在家里好了。”
李卫卫忍不住想笑,顾欣欣的奶奶叹了口气。
“他以前可不是这样。”她说。
“奶奶,你跟李卫卫讲讲他小时候的那件事。”顾欣欣说。
“你听了好几遍了。”
“但李卫卫没听过,”顾欣欣说,“奶奶你讲。”
李卫卫觉得好奇,奶奶倒是开始讲了。
“就是在他七岁的时候。”奶奶说。
“哦七岁,”顾欣欣说,“我还没出生呢。”
“那时,你们爸妈在外面做生意,他跟着我住,”奶奶说,“他和别的男孩子一起玩,那些男孩子总是欺负他,但他从来不还手。”
“你看,他从小就是个胆小鬼。”顾欣欣说。
“你别打断奶奶啊。”李卫卫抗议道。
顾欣欣嘟了嘟嘴,耸耸肩,好像剥夺了她什么乐趣,又无所谓。
“但是有一次,”奶奶接着说,“那是在他七岁那年,一个孩子说他爸妈一年到头不在家,他是个没爹妈的可怜鬼。这句话可把他惹恼了,他把那孩子骑在身上狠狠揍了一顿,揍得对方哭着跑回家。”
“这才像话。”顾欣欣说。
“但那天晚上,他躲在被窝里哭,我就问他怎么了?他把打架的事告诉了我,我说你打赢了,不觉得高兴吗?他说但是那孩子哭了,当他看到他哭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做错了,‘我心里很难受,他说,‘奶奶,我就是受不了别人哭,眼泪这东西让我觉得太糟糕了。他就是这样的孩子。”
“眼泪这东西让他受不了,”顾欣欣兀自笑起来,“我就觉得他小时候特别好玩,我喜欢他那样子,如果那时候我就出生了,我不会让别人欺负他的。”
奶奶也笑了,李卫卫没说话,喝了一口桔子汁。这时,顾欣欣带着的手机响了,她讲了几句,对奶奶说:“是爸爸,他叫我们回去了,我们要去农家乐吃烧烤。”
“去吧。”奶奶说。
“那我们走了。”顾欣欣说,拍了一下李卫卫的肩膀,他们便离开了小木屋。
这时,太阳升得老高,山上空气清新,山风吹过树梢,传来“唰唰”的声音。他们绕回来时的小路,顾欣欣在前面走,李卫卫低着头,手伸在口袋里。他又摸到了那颗子弹,手心出了汗,觉得温度仿佛将原先他以为是血迹的红色痕迹融化掉。突然,顾欣欣停下脚步,李卫卫没注意,差点撞上去。
“怎么了?”他问。
“有动静,”顾欣欣说,“你听。”
李卫卫听着,果然,一旁的树丛中有什么东西在动,他朝那里望过去。突然,一只硕大的松鼠冷不丁窜了出来,紧跟着,是另外四只小松鼠,接二连三,仿佛被一根线串着,跑过眼前。
“噜噜,”顾欣欣惊呼道,“是噜噜和它一家。”
松鼠们迈着细碎的步伐,横跨小路,带起路上的树叶,踩得“簌簌”直响。那只带头的松树全身褐色,尾巴像一条拂尘,犹如一阵风,一眨眼跑到路对面的一棵树上,三步并作两步,爬上树干,跳到另一棵树上,枝叶一摇晃,便失去了踪影。
顾欣欣跑过去,抬起头,望着它们消失的地方。
“是它们!真是它们!”她跳起来。
李卫卫还没回过神,他不确定刚才真的看清了它们,太快了,只记得毛茸茸的几个球,这就是松鼠,是噜噜和它的一家。但顾欣欣怎么就断定是它们呢,松鼠不都长得一样吗?这样想着,他放下子弹,把手伸出了口袋。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