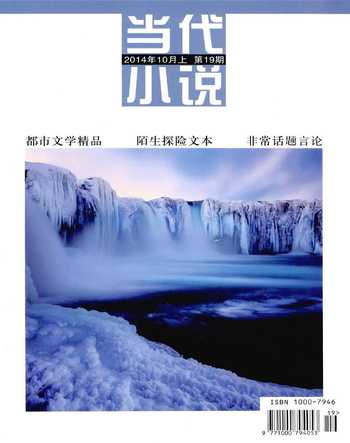我们要去的地方
许仙
我妈常对我说,别去没人的地方。我妈的意思,没人的地方会有坏东西,像毒蛇、恶狼、魔鬼和坏蛋什么的,这些坏东西都会要了你的命。我从小就听我妈的话,能不出门就呆在家里。我妈说家是最安全的地方。但这回我非出远门不可。昨天一大早,我妈背了大半竹箩东西——那是她从山上采下来的土物,一点点野茶、蕨菜、地衣、火梢笋什么的,晒干之后,一样样盛放在竹箩里;等到有大半竹箩了,再加上我家三只老母鸡下的那些蛋,她就背去城里换钱。每隔个把月我妈会去一趟城里。去的那天,我妈天不亮就出门,回到家天早就黑了;她撇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候得我头颈发酸、眼睛发痛,我妈才磨叽磨叽地回到家。但我就盼着我妈去城里;每次她都会带好吃的回来,不是肉馒头,就是洋糖糕,叫人幸福得要死。但这回我盼了又盼,天都不知黑到哪儿去了,我妈还没有回来。来的却是老村长石头爷,把门敲得■■响,那副破锣似的嗓门吼得我心别别跳,还以为有坏东西找上门来了。石头爷阴沉着一张疙瘩老脸,脸上都是乌花般深浅不一的寿斑;他说:“你妈在城里被汽车撞了,医院打电话来催钱,叫你赶紧送去。”我问:“那我妈呢?她咋不回来呀?”“说你傻,你还真的傻呀!你妈躺在医院里怎么回来?”石头爷又问:“家里的钱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我知道我妈把钱藏在我们睡的床上,像枕头底下、垫被底下、席子底下……我妈说这样夜里她才睡得踏实。我们把整张床翻了个底朝天,七零八落的,找出来一大把碎钞;石头爷扑扑地往自己的手指头上吐了不少唾沫,唾沫蜡黄蜡黄的,他也不嫌自己的手臭,就点起钱来。“你干吗吐痰在手上?我妈点钱时,用大拇指抹一下嘴唇就好了。”石头爷横了我一眼,“我喜欢,不可以吗?”他点完钱就骂娘道:“这才一百三十四块八毛,顶个鸡巴毛用!”他把手里的钱往床上一甩,好像这些钱是发了霉烂透了的土物,是垃圾;就又使劲地逼问我:“还有钱呢?还有钱呢?”好像是我把钱藏在了其他地方,不肯拿出来给他。“都有这么多钱了,还不够多吗?”“那是个大手术,没三五千块钱下不来。”我坚定地摇摇头。我家的钱都是我妈管的,我妈的钱都藏在床上了。石头爷懊恼了半天,最后瘪着嘴巴道:“我现在去筹钱,你先准备准备,明儿个一早送去。”我慌了,我说我准备啥呀?“准备吃的呀,你路上吃的,还有给你妈也带点去。”他这么说,我就懂了。石头爷一走,我忙和麦粉,加水,加盐花,加葱花;葱花是我从围墙上的破盆里掐来的,就像我妈每次出门前的那个晚上一样,我妈和面粉,我帮忙加水、加盐花、加葱花,然后看我妈在热锅上摊麦饼,但这回都是我独自完成的,我妈知道了肯定夸我聪明。我先摊了四只麦饼,怕不够,又重新和麦粉,加水,加盐花,加葱花,再摊了四只麦饼;我边摊饼边等石头爷,等等他不来,又去煮了三只鸡蛋。这是家里三只老母鸡今天上午下的蛋,我想带去给我妈吃。我妈说鸡蛋很补的。每次我生病,她才煮鸡蛋给我吃;只要我妈吃了鸡蛋,身体就好了。石头爷气喘吁吁地来了,他说他敲开全村人家的门,一家不落,终于筹到了这两千块钱。“只有这么多了。”石头爷感叹道,又往手指头上吐唾沫,当着我的面把钱点了一遍,就大声地对我说:“这是两千块钱。你记住了,是两千块钱。”我瞧着厚厚一刀红艳艳的钞票,眼睛都花了,我说这么多钱哪。石头爷没吭声,也没把钱给我,而是考问我钱该放在哪儿?我说口袋里呀。石头爷就呲牙咧嘴,生气道:“说你傻,你还真的傻呀!钱放在口袋里,让人一摸就摸掉了。”他突然问我:“你的短裤呢?”我顿时红了脸,双手捂住裤裆,心怦怦直跳;我的短裤自然着肉穿在身上。我说:“石头爷,你干吗?”“小兔崽子,去拿条干净的短裤来。”石头爷那副破锣又■■响了。吓得我赶紧进屋去找,我不知道石头爷要干吗?但石头爷要了我的短裤,又要针线和一块布;我问什么布?他就问我有手帕吗?我说有,就把我的红手帕给了他。石头爷在灯下把红手帕缝在我的短裤里面,缝成一只口袋,把那刀钱塞了进去,再缝住口子。他叫我去把这条短裤穿上。我进屋,把短裤套在外面,但只能拉到膝盖上;我蹦蹦跳跳地出了里屋,我说穿不上去。石头爷猛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生疼生疼的。他说:“谁让你穿外面了,着肉穿懂吗?快去。”我又回屋里换上有钱的短裤。石头爷等我出来,就伸手按我的小肚子,按得我咯咯笑;他按到短裤里面的钱,又按了按,确认之后,那只老手就往下一滑,一把摸到我尿尿的地方。吓得我往后一缩,生气地瞪着他。他就贼秃兮兮地笑道:“你这个孩子,连声谢谢都不会说吗?这有钱的短裤你就穿着睡觉,明天一早,你妈平常啥时候出门的,你就啥时候出门;去城里,找到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四楼,四一八病房,把这些钱给你妈。”石头爷说完,又把一张字条交给我,说忘了就看看这张字条,上面都写着呢。我接过字条,上面的字跟蚯蚓似的,曲里拐弯的,谁看得懂呀。石头爷要走,我慌了;我问:“就我一个人去呀,我没有去过城里,哪知道医院是朝南还是朝北的。”石头爷头一横道:“你都十六岁了,还不能一个人去吗?小萍和小英像你这个年纪,早在外面打工了。”是啊,村里人都出去打工了,就剩下老头老太和一大帮孩子;要不是我妈拦着,我也早就去打工了。出去打工多好呀,你瞧着他们回来过年,一个个穿红戴绿的,说起外面的事情神采飞扬;惟独我像个傻子,他们说些啥我听都听不懂。但我妈就是不许,她说女孩子出去打工,没有一个不被糟蹋的;我妈说:“你别看她们人五人六的,笑在脸上,泪在心里。”
石头爷走了,我熄了灯,胆战心惊地躺在床上。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过过夜,即使在家里。黑夜把我脑袋割走了,我的耳朵在外面飞来飞去,耳朵里除了风声还有各种可怕的声音;我的眼睛就更野了,它一路奔跑,我觉得它都跑去城里了,但它什么也看不到;信不信由你,反正我的脑袋被黑夜割走了,我的鼻子甚至闻到山中野花盛开的气味。我默默地念着妈妈,妈妈,妈妈……好像这样念着,妈妈就在家里;虽然看不到她,但我知道她就在家里。我不是一个人在家里,而是和我妈在一起。她还亲了我的脸呢。每次我妈去城里,临出门时,都会走到床前,悄悄地亲我一下;她以为我在睡梦中,不知道,其实我每次都醒着,我只是假装睡着了而已。我妈爱我,我也爱我妈。每次她回家,我就会抱抱她,抱着她蹦叽蹦叽的,趁她不留神时,亲她一下脸、亲她一下头发、亲她一下手背什么的,反正每次都不固定,哪儿方便我就亲哪儿;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是有意亲她的,那多不好意思呀。我躺在黑暗中,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感觉我妈亲我了;我依旧默念妈妈,忽然我妈又亲了我一下。我突然清醒过来,我妈这是在提醒我,该到我出门的时候了。
我也不管天什么时候会亮,当即就起来,也不用穿戴,因为我睡下去时压根儿什么都没脱,除了鞋子;我洗了把脸,用我读书时用过的旧书包装了摊饼和熟鸡蛋,就出门去。但我被外面的黑暗吓住了,天地都被黑暗糊住了,让人都不知道往哪儿伸腿。我又回到屋里,想找个可以照明的东西,我记得家里有一把手电筒,但被我妈出门时带走了。好在我聪明,找了一根竹竿,用薄刀切去了一大截,剩下我一肩高的样子,虽然摸上去刺啦啦的,但我没时间也没心思去削它,就把它当成瞎子的拐杖,笃笃地敲着摸索着路面,慢慢地朝村外走去。毕竟暮春了,尽管凌晨还有些凉,但春雷早已响过,山里的毒蛇都被雷敲醒了,它们会在没人的时候出来,肆无忌惮地爬在路上;你不小心踩到它,那你就苦了,走不了几步,就会死倒在路上。所以我用竹竿在地上笃笃地敲,把声音敲得很响,识相的就赶紧走开。
我们村在山上,村里人家比较集中,东坡几家西坡几家的,家与家之间的路七高八低、七拐八弯,反而难走;但我手里有竹竿,事情就好办多了。村里静悄悄的,连狗都还在睡觉呢,我却不得不出门了。在家里呼呼大睡的人,哪里知道出门人的辛苦;光是这无边无际的黑暗,就叫人寒毛凛凛的。我妈常对我说,别去没人的地方;可我现在望出去,哪儿不是没人的地方呀。好在我聪明,出门带了竹竿,有什么坏东西,我就一竿打死它。出了村就是盘山公路,倒是比村里的路平坦,我的眼睛也好像明亮了许多,居然在黑暗中能看清楚两边的山,和沿着山溪盘旋而下的公路;我全神贯注地盯着路面。我妈说:“是蛇一身冷,是狼一身腥。”我时刻准备着与它们搏斗。我走到第二道弯坡时,脚底下踩到一样东西,一滑,人就跌倒在路上;我的右手捏着竹竿,左手撑地时居然按住了那东西。“呀哟,我的妈呀!”感觉细溜溜的,“蛇!”吓得我用力向路边的山溪里掷去。我瘫坐在地上,整个人颤抖了好长一会儿,知觉才渐渐回来;我摸摸左手,没有蛇咬过的齿印,也没有痛的感觉。不是蛇,而是一根枯树枝。捏上去有些硬。虽然湿漉漉的,但那是昨夜的露水。我清醒了过来,从地上爬起来,手腕有些痛,刚才不觉得,现在却很明显。我揉着手腕继续往山下走,把竹竿敲得很响。天还是那么黑,好像永远不会亮出来似的。
我在黑暗中胆战心惊地翻过两座山,一座叫羊山,另一座叫印壁山;山里老是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或是一声凄厉的惨叫,很突然的,像是什么鸟落入狼嘴时发出的最后的呼唤;或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蛇群从枯叶上游行;或是冷不丁地传来石落水中的声音,像是有个坏蛋沿着山溪涉水而行,偷偷地跟踪我……我强忍着眼泪,真的,我都忍不住想哭了,我的妈呀,什么时候才天亮呀?什么时候才有人呀?眼泪在我的眼眶里直打转,但我不能哭,我一哭就会暴露目标,坏蛋就知道我害怕了,就会趁黑来袭击我。谢天谢地,我从印壁山下来时,黑漆漆的糊状天空一点点被稀释了,渐渐灰白出来;一个不留神,我都能看出山头上飘移的雾了,东方也渐渐露出朵朵白云,越来越白,白到一定程度就镀上了丝丝淡红。我终于看到了山脚下的水库,白花花的一片,我记得我妈说过,下了水库就真正到了山下;坝下有条大马路,沿着大马路走,就能一直走到城里。
我一口气冲到水库大坝上,我早就看到他了,他是个人,我终于见到人了,我终于到了有人的地方;我太激动了,冲到那人跟前,弓着身体,双手撑在自己的膝盖上;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呜呜地哭。我早就想哭了。但不知为什么,我见到他才终于哭出来。那人傻呆呆地盯着我,看我的眼泪噼里啪啦地砸在白花花的大坝上,砸出一朵朵水花来。我哭了一阵子,抹了抹眼泪,抬头看他;这个清瘦的年轻人穿着一件灰不溜秋的春衣,哆哆嗦嗦的,好像很冷的样子;剃的小平头跟光头也差不到哪儿去,一对细长的眼睛,眯着,闷声不响地盯着我。他上下左右地打量着我,眼睛里倏地闪过一丝贼亮的光。我说:“大哥,谢谢你。”他看看四周,又盯着我来的路上看,好像盼着山上会下来什么似的,又好像盼着山上不要下来什么似的。我蹲下身去,把书包搁在膝盖上,从包里取出两只摊饼,一只给他,一只给我自己。走了这么长夜路,我见到他的那一刻,突然感到饿了,才意识到出门时压根儿没吃东西。他不解地盯着我,确切地说是盯着我递给他的饼。我说:“大哥,吃吗?吃了就不觉得冷了。”他突然生气起来,一脸懊恼地瞪着我问:“你干吗给我吃?”我固执地把饼塞到他手上,我说:“我要谢谢大哥呀。我妈说别去没人的地方,可我一路下来都没有人,到这儿才见到你呀。”他眨巴眨巴细长的眼睛,似乎不明白我的话,需要细细琢磨;随后就问我:“你妈有没有告诉过你,有人的地方更危险?”我摇摇头,反问道:“有人的地方怎么会危险呢?我刚才远远地看到大哥,高兴都来不及呢。”“为什么?”“见到大哥我就安全啦。”我饿坏了,顾不上多说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他举着饼,反复地审视着,好像不认识似的。他问:“你就为这个,给我饼吃?”我笑道:“是呀。你以为呢?”他瘪了一下嘴问:“你就不怕我是个坏人吗?”“大哥不是坏人。”“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坏人?”“我知道。大哥是在这儿等人吧?”“是的,我在等人。我在等贵人。但想不到等来你这么个小丫头。”“我怎么啦?”我三下五除二,一口气吃掉了饼。但他没有吭声,也没有吃饼,大概嫌它不好吃吧;我从书包里摸出来一只鸡蛋,递给他道:“给,吃个鸡蛋吧。”这回他毫不客气地接了过去,蹲下身来,在大坝的水泥地上敲破了蛋壳,小心地剥着,咬一口饼又咬一口鸡蛋,吃了起来。他嘴里边嚼边问我:“你知道世上最坏的东西是什么吗?”我猜是毒蛇、恶狼、魔鬼……但我每猜一样,他就摇一下头,最后定睛盯着我道:“是人。人是这世上最坏的东西。小姑娘,你妈错了;记住大哥的话,没人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有人的地方就有危险,人越多危险就越大。”我笑了,我说:“大哥真会开玩笑,有人的地方才安全呢,我见到大哥就……”我的话似乎激怒了他,他瞪大了眼睛,好像眼乌珠都要瞪出来了,冲我大吼道:“我是劳改犯!我就是坏人!”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书包,哗啦哗啦一阵乱翻,包里只有麦饼和鸡蛋,他拿走了仅剩的两只鸡蛋,便把书包扔给地上。他手里各抓着一只鸡蛋,相互一碰,鸡蛋碎了,只顾自己剥来吃。
我眼睛噙着泪,我说那是留给我妈吃的。但他连头都没别一下,边吃边问我是哪个学校的?书包里怎么没有书?我没有理他,我只感到难过,真的难过极了。他把我留给我妈的鸡蛋都吃了。他吃完了鸡蛋,又舔手指头,一只一只地舔过来。这个动作很像我妈。我妈盛粥盛菜时,大拇指总是浸到粥里或菜里,碗端到饭桌上后,就会舔一下手指头。另外,她抓过吃的东西,也会习惯地舔一下手指头。他拍了拍胸口,像是噎住了,边呛边从大坝上沿着一条窄窄的台阶走下去,一直走到水库底下,不知是去喝水还是洗手;他背对着我,我没有看清楚。我突然明白了,刚才他这么凶是装出来的,是装出来吓唬我的,好让我把他当做坏蛋,来推翻我妈的话。但他要推翻我妈的话做什么呢?他又不是坏蛋。他从水库底下上来,见我还站在大坝上,有些吃惊道:“你怎么还在这儿?是不是又逃学了?”我摇摇头道:“我早就不读书了,我去城里。”“你去城里?”“是的。”“去打工?”“不是,去看我妈。”“你妈在城里打工?”“不是,我妈昨天去城里卖东西,被汽车撞了,在医院里,我去看她。”“噢,是这样呀;那你带钱了吗?”“带了。昨晚石头爷接到电话,就帮我们借遍了整个村子,终于借到了两千块钱;石头爷说一个大手术三五千块下不来,但我们村穷,只能借到这么多了。”他眼睛一亮,反手在屁股后面不知摸什么东西,朝我走来,他说:“那你可要把钱藏好了,城里小偷很多的。”我拍拍肚子道:“没问题,石头爷把钱缝在我短裤里了。”他亮出藏在屁股后面的手,手里多了一把刀;那是一把与众不同的刀,他轻轻地打开,将刀片与锄形刀架别在手指间。我左右张了张,没有看到坏蛋;我说:“大哥,这儿没有坏蛋。”他咬着牙,犹豫了一下,将架刀的手朝我伸过来。我说:“大哥,是不是你妈告诉过你,出门要带点防身的东西?我妈也是这么说的,你瞧……”我拿起竹竿朝他晃了晃,我说:“我只能带了这个。女人不适合带刀,不小心会弄伤自己的。”“是呀,我妈就是这么说的。但这是把刮脸刀,不是用来防身的,而是用来刮胡子的。”他说着缩回了手,在自己脸上上下做着刮脸的动作。我明白了,“大哥是个剃头佬。”他很有意思地瞧着我,笑道:“差不多。但我经常刮破别人的脸。”他收起刮脸刀,重新插回屁股后面;笑微微地拉住我的手问:“小姑娘,你多大了?”“十六。”“叫什么名字?”“紫薇。”“嗯,很好听的名字。”他抚摸着我的手背,一摸一摸的,摸得我心都颤得不行。他说:“你的手好白好软呵。”我脸红红的,心别别乱跳,忙低下头去。他又问:“紫薇,你怕大哥吗?”我摇摇头。他用手指轻轻地托住我的下巴,慢慢地抬起我的头来,直到我的眼睛与他的眼睛对视着,他的目光款款的、温温的,瞧得人非常暖和。他轻轻地问:“为什么不怕大哥?”我笑了,我说:“见到大哥,我就像见到哥哥……”“你有哥哥吗?”我摇摇头,我没有哥哥。“那我做你的哥哥好不好?”“嗯。”“让哥哥抱抱……”他说着就把我拉入怀里,他的怀里有股很好闻的烟味,不,不仅仅是烟味;总之,是很好闻的男人气味。
他一只手搂着我的腰,另一只手撩开挂在我的脸上长发,他的手在我脸上轻轻地划过,然后托在我的后脑勺上;我的脸不由自主地接近他的脸,近得几乎要贴在一起了;他移了一下头,冰凉的嘴唇就印在我的额头上。我一个激灵,“啊唷,我的妈呀!”我浑身颤抖起来,双手拼命地箍住他的腰。他的嘴唇在移动。他的嘴唇在我的脸上移动。他的嘴唇从我额头上缓缓地下滑,吻了我的眼睛,先吻左眼,又吻右眼;吻了我的鼻梁;突然,他吻住了我的嘴巴,火辣辣的舌头往我嘴里一探,我浑身瘫了软了,我都不知道自己了。
他收回了舌头,问:“紫薇,喜欢吗?”
我喜欢。但我没有说,突然踮起脚来,将嘴印在他的嘴上。我也像他那样,把自己火辣辣的舌头伸进他的嘴里,他尝了我的味道,我也要尝尝他的味道。他的味道真好。原来,一个人的嘴与另一个人的嘴贴在一起,竟有这么好的味道。我要了又要,不知要了多久;我睁开眼睛,发觉自己已躺在他怀里,他呢,面朝着水库坐在大坝上。他扶我直起上半身,指着水库道:“你看,水库多漂亮呀。”我就坐在他腿上,转过身去,看到太阳出来了,红彤彤地照在水面上,几朵白云飘在水中,那碧绿碧绿的水呀,就像碧玉一样美丽。我呆呆地望着水库,有几只白鹭忽高忽低地在水面上飞行,我好像在仙境里一样;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的景色,就像在做梦。他轻轻地说:“你还没有说呢?”“说什么?”我满脑袋浆糊,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一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我也是。”“感觉你很亲切,就像上辈子在一起过的。”“我也是。”“除了我也是,你还会说别的吗?”“说什么?”“我爱你呀。”我愣住了,“我……我……爱你。”“我也是。”“你怎么也说我也是了?”“学你呀。你知道吗?两个人相爱了,就要交换爱的信物。”“什么信物?”“短裤。”“短裤?”“是呀,短裤就是爱的信物。”“那多脏呀?”“怎么会呢?你知道相爱的人为什么要交换短裤吗?”我摇摇头,有些为难道:“可我没有带别的短裤呀。”“你错了,要的就是我们着肉穿的短裤。你知道为什么不是交换别的,比如手绢、衬衫什么的,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别人看得见摸得着,不够隐私;惟有短裤是着肉穿的,别人看不见摸不着,最能代表爱了。如果我们交换短裤,你的穿在我身上,我的穿在你身上,即使我们不在一起,也能感觉到和对方在一起。你懂吗?”我想我懂了。我妈曾经说过,谁扒了我的短裤,谁就是我的男人。大哥说的,就是我妈的意思。可是,我四周张张,水库四周空荡荡的,“我们到哪儿去换短裤呀?”“这有何难,换一下很快的,就在这大坝上,我朝东,你朝西,我不看你,你也不要看我,我们换了就赶紧穿上,不会有人看到的,你说好不好?”我想也只有这样了。我点点头。于是,我们就站起身来,他朝东,我朝西,我转过头去,“你不要看我。”“嗯,我们一二三,换。”我弯下腰去,先脱了鞋子,然后赤脚踩在鞋子上,迅速脱裤,先脱长裤,再脱短裤;当我脱光裤子,露出玉色的双腿时,一阵风流氓兮兮地刮过,吓得我直哆嗦,赶紧用手捂住那儿。说好不回头看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扭过头去,见他老老实实地朝东,没有偷看我;但我看到了他的屁股,原来男人的屁股也这么白呀!不过,让我觉得好笑的是,他屁股上——是左屁股还是右屁股,我一时也搞不清左右了——有一块胎记,就像有人剥了块熟的地瓜皮,故意贴在那儿,我忍不住想笑出来,但我忍住了,伸手要过他手上的短裤,又把我的短裤塞到他手上。我迅速穿上他的短裤,再穿上我的长裤和鞋子。我们交换了爱的信物,他就是我的男人了;但我还是羞得不敢看他,低着头,忍住了笑。他忽然问我笑什么?我说我没有笑。他说:“你看你,现在还在笑呢?你到底笑什么?你偷看我了?”我终于忍不住笑了。我说:“大哥,你的屁股花……”“好呀,你偷看我!”他突然挠我的痒痒,胳肢我;双手在我的胳肢窝里挠啊挠,我天生就怕痒,哪里经得住他的疯狂,笑得蹲在地上,笑得肚脐眼都翻出来了,笑得哭了……他终于停止了恶作剧,将我从地上缓缓地抱起身来;我们拥抱在一起,他粗鲁地将嘴压在我的嘴上,疯狂地吻我。我喜欢他的粗鲁,粗鲁得就像村里人酿的大麦烧,醉人。我们吻了长长远远,我觉得自己像一团雪都融化在他的嘴上了。我们艰难地分开身来,因为他说他该走了。我慌了,我说:“我家住在翻过两座山的山上面,一座山叫印壁山,一座叫羊山,过了羊山就到我们山上了;我们村叫纪念村,也不知道纪念什么,但就叫纪念村;大哥你要来找我呵,到了村里你问一下紫薇家在哪儿,就能找到我了。”他说他知道,他说他去过我们那个村,他会去找我的,很快,明天或后天,但现在他该走了。他依依不舍地走了,边走边回头,朝我挥挥手。我突然想起事来,大声道:“大哥,你等一下!”他刹住匆忙的脚步,回头吃惊地望着我。我说:“大哥,你不是在等人吗?”他笑了,他说:“是的,我等到了。”他又朝我摆了摆手,匆匆地走了。“难道他等的人是我?”我晕晕乎乎地站在大坝上,望着他向我来的路上大步流星而去,离开大坝,翻上那边的盘山公路,不见了。
我好像全身的力气都被他吸走了,双腿软软的,跌跌冲冲地爬下大坝,朝大坝下面的大马路走去。但我走着走着,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却又不知道不对劲在哪儿;我一路走一路想着这个事儿,突然我震住了,“啊哟,我的妈呀!”我被脑海里冒出来的东西击倒了,我吓得瘫倒在路上;但我又奋力爬起身来,踩着软屁屁的脚步,像跑在棉花堆上一样,艰难地往回跑。我从水库大坝的台阶上摔了下来,不知是跑得太急一脚踩空了,还是两阶并作一阶跑上去时,脚是上去了,身体却没有上去,人就滚落到大坝底下,脸上不知哪儿磕破了,痛,一抹,手上都红了;但我顾不得痛,也顾不得流血,冲上大坝往回跑去。我边跑边喊:“大哥,等等我;大哥,你等等我呀。”“大哥,我的短裤里有钱,刚才忘了拿了,那是我妈看病的钱呀。”“大哥,你在哪儿?大哥,你回来……”我喊着喊着,眼泪和着血从脸上挂下来了。我跑过大坝,跑到盘山公路上,可是,大哥在哪儿,盘山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再也跑不动了;我坐在路上,呜呜地哭,这可怎么办呢?那些钱要给我妈看病,没有钱,我妈可怎么办呢?我哭了很久,我边哭边喊大哥,又喊我妈,我怎么这么糊涂呀,给大哥短裤时,竟忘了钱……我妈没钱看病,她会死在医院里的;想到我妈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缓缓地爬起身来,也懒得擦一下哭脏的脸,我慢慢地走下盘山公路,来到水库大坝,望着那碧玉一般的湖水,我彻底绝望了。刚刚还幸福得像飘在云端上,现在却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又哭了,我蹲在大坝上,我不想死,我才十六岁,我才刚刚与大哥交换了信物,我才刚刚知道爱是怎么回事,我不想死,大哥,我的短裤穿在你的身上,你感觉到短裤里的钱了吗?你感觉到了就赶紧回来吧……我蹲在大坝上,边哭边胡思乱想,我望着贴着水面飞翔的白鹭,想着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大哥才回来;如果大哥不回来,我还是得死,我害了我妈,我爱我妈,我害了她我就得去死……呜呜,呜呜,我把脸埋在双臂中间,伤心地哭泣。
一只手轻轻地按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抚着我的头发,“紫薇,别哭了。”我仰起头来,只见他站在我的身后,深情地望着我。我猛地直起身来,扑进他怀里,哇哇大哭。他款款地抱住我,说:“对不起,紫薇。我走出去很远,才发现短裤上的钱;就赶紧跑回来了,你一定急坏了吧。”我不知怎么的就举起双手,胡乱地敲打他的胸口,依旧呜呜地哭个不停。他突然“咦”了一声,好像很吃惊的样子,我被他吓住了,问怎么啦?“你的脸怎么啦?血出污拉的。”我这才想起刚才在台阶上摔了一跤。他急忙下到水库里,用衣袖浸湿了水,然后爬上来,用湿衣袖细细地替我把脸擦干净。“痛不痛?”他问。我开心地摇摇头,傻呆呆地望着他;不知为什么,他那张普普通通的脸我怎么看都看不够。他说:“我先把钱给你吧,免得等会儿又忘了。”他解裤带时,我问:“大哥,去城里是走那条路吗?”我指着大坝下那条蜿蜒曲折的大马路。他停下手来,有些吃惊道:“你没去过城里?”“没。”“那你知道你妈住在什么医院吗?”“我知道,石头爷都写在字条上。”可是我摸遍身上的口袋,连书包都翻了个底朝天,就是没有那张字条。我急了,我的字条呢?没有字条我怎么去找我妈呀。他说:“你别急,石头爷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妈住在什么医院?”“说了。他说了‘医院,好像还有‘人民,还有……‘第一……”“那就行了,肯定是第一人民医院。”“不会是人民第一医院吗?”“不会。城里只有第一人民医院,没有人民第一医院。但第一人民医院挺远的,你知道怎么走吗?”“我知道,我走着去呀。”“走?那要走到什么时候?你知道第一人民医院在什么区什么街道上吗?乘什么车子?”“我不知道。”“紫薇,要不要哥陪你去;下面有公交车,我们坐车去。”“真的吗?”我激动地拉住他的手说:“大哥,你真好。”他说:“那钱先放在我这儿吧,到了医院我再给你;到时候你别忘了问我要呵。”“嗯,谢谢大哥。”
我们手挽手下了大坝,他带我到“青山水库”站头,等公交车。我们站在站牌下等车时,他问我:“紫薇,你就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问什么?”“比如我的名字?多大年纪?家住哪儿?有没有结婚?”“对呵,我还不知你的名字呢?大哥。”我突然醒悟过来,要不是他提醒,我还没有想到问呢。他说:“我叫贾义夫,今年二十二岁,家住在牛头山的贾家村,还没有结婚。紫薇,你知道牛头山在哪儿吗?”我摇摇头,我还真不知道。“牛头山就是水库大坝上去,沿盘山公路上去不远,有一条向西的岔路,进去头一座山就是牛头山,很好找的。”“大哥,我知道了。”我们正说着,公交车来了,像一头发疯的怪物,也不知从哪儿窜出来的,轰地停到站牌下;车上满满当当的,都堵到车门口了,却没有一个人下来;他拉着我奋力向车上挤,却怎么也挤不上去。开车的家伙一脸凶相,朝我们大吼道:“付了钱,到后门上。”他问我有零钱吗?我说有,我从裤袋里掏出昨夜从床上找到的那把碎钱,他从中捡了四枚硬币,塞进铁箱子里;然后带我去后门上车。
后门口也塞满了人,但他恶狠狠地往上挤,倒是给他挤出一点点地方来;他转过身来,一只手抓住横杠上的拉环,另一只手箍住我的腰,让我安全地躲进他的怀里。公交车轰地启动了,七晃八摇,一路颠颠颠地向前直奔。我先是双手抓着他两侧的衣裳,但人摇晃得不行,站都站不稳;后来我就索性抱住他,头紧紧地靠在他的胸口。他低着头,下巴轻轻地压着我的脑袋。“紫薇,你爹在外面打工吗?”“我没有爹。不,我应该有爹的,但我不知道我爹是谁?我从没见过我爹,我妈也从没说过我爹是谁?他到哪儿去了?或许早就死了;或许我是个孤儿,是我妈从外面捡来的。村里人只要一说我是捡来的,我妈就骂山门,骂得可凶了。如果我有爹,如果我有哥哥或弟弟就好了,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城里看我妈了。”“嗨嗨,你不是有我嘛。”他见我泪眼汪汪的,就赶紧安慰我。“是啊,现在有了大哥,真好。”我仰起头来,朝他微微地笑,心里甜甜的。
有义夫哥的呵护,我简直爱死公交车的颠簸了;每当它颠簸一下,他就亲一下我的头底心。他以为我不知道,就像我偷偷亲我妈一样;其实我心里最清楚了,就像喝了野蜂蜜一样甜。我第一次进城,什么都不懂;但义夫哥熟门熟路的,到了一个地方下车,又上车;又到一个地方下车,朝前走了没多远就看到第一人民医院,好大好大的一个地方,好多好多的人进进出出,义夫哥带我绕过一座高大的门诊大楼,沿着一条笔笔直的林荫大道,在人群中穿来插去,快步向不远处的一座大楼走去。那就是我们要找的住院部。走在两边大树华冠遮天的林荫大道上,义夫哥问我:“你妈叫什么名字?”“金银花。”他在住院部的值班室问到我妈住的病房。他说在四楼,四一八病房。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对对对,石头爷跟我说过的。我们乘电梯来到四楼,我还是第一次乘这个叫电梯的东西,真是神奇,人站进去,它就自个儿呼呼地上去了。
我们找到四一八病房,病房好大,有六张雪白的床,床上都躺着人;义夫哥一张张地看着床架前的挂牌,就知道我妈是第四床。他指着床上的人对我说:“这是你妈。”可我看到的是一个头上缠满了白带子、身体裹在白被子里的人;天花板上挂着袋子,有水通过细线一滴一滴地流进她的手臂里;床头柜上还有一只铁盒子,亮着绿灯,有几根线消失在被子里;这人的脸像只挤压的熟桃子,胖乎乎的,一点也看不出那就是我妈。她闭着双眼,一动不动;我看看病房里或站或坐的几个年轻人,又看看义夫哥,小声地问:“你确定吗?”他笑道:“紫薇,你不至于连你妈都认不出来了吧?”他撩起床架前的挂牌说:“上面写着你妈的名字,错不了。”我看了看,确实是我妈的名字。我呆呆地望着这个陌生的人。义夫哥朝我眨眨眼,小声地对我说:“这儿不方便,我去厕所把钱取出来给你。”我好像“嗯”了一声。但我不能确定“嗯”了没有,我的心思全在这个陌生人身上了。
我站在我妈病床前不知所措,十分茫然地等着义夫哥回来;突然,我听到楼下的尖叫声,“他抢了我的钱包,抓住他!抓小偷……”我好奇地移到窗口,低头朝下张,只见一个衣着鲜亮的中老年妇女倒在住院大楼门口的地上,一只手按着另一只手,另一只手上在流血;奇怪的是,我看到了义夫哥的身影,他的手里多了一只皮包,头也不回地往人民医院大门口走去。那些从门诊大楼来住院大楼和从住院大楼去门诊大楼的行人挤满了这条林荫大道;他们都听到被抢妇女的叫喊声,他们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们目不斜视、脚步缓慢地走在林荫道上,任由义夫哥在人群中曲里拐弯地穿行而去,消失在门诊大楼与人民医院大门口之间的拐角。我呆呆地趴在病房窗口,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想通了,我知道那些走在林荫道上的人,都是病人。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