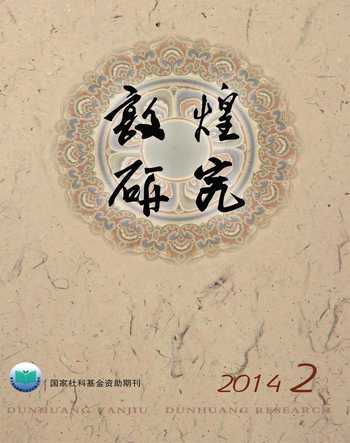库木吐喇第45窟造像内容考证
苗利辉
内容摘要:库木吐喇第45窟是龟兹地区回鹘时期的典型洞窟,该窟体现出华严思想对十方三世佛和涅槃观念的融摄。它是中原汉化佛教回流的结果,反映出宋元时期,西域与中原、回鹘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关键词:龟兹;华严十方三世佛;涅槃;汉化佛教
中图分类号:K87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2-0034-06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Contents of Cave 45 at the Kumutula Grottoes
MIAO Lihui
(Qiuci Research Institute, Baicheng, Xinjiang 842313)
Abstract: Cave 45 of the Kumutula Grottoes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Uighur period in ancient Kucha. It embodies the integration of Buddhist ideas on Buddhas of ten directions and three times as well as on the concept of nirvana in the theory of Huayan sect. As a result of the reflux of the Sinicized Buddhist in the Central Plains, it reflects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blending between the Western Regions, Uighur and Han Chinese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Keywords: Kucha; Buddhas of ten directions and three times in Huayan sect; Nirvana; Sinicized Buddhism
库木吐喇石窟是古龟兹国境内一处重要的石窟群,位于今天新疆库车县西约25公里的三道桥乡库木吐喇村。洞窟分布在渭干河出却勒塔格山口东岸崖壁上。现存的石窟群可分为南北两区,分别称为沟口区和窟群区,两区相距约3公里,现已编号洞窟114个。库木吐喇石窟的壁画风格分为龟兹风、汉风和回鹘风,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回鹘风洞窟,它们见证了漠北回鹘人西迁进入龟兹地区后社会文化、宗教的变迁,为我们了解当时龟兹地区历史、宗教情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库木吐喇第45窟是保存较好的回鹘风洞窟,其壁画风格和内容均具有较大的代表性。笔者考证其内容,分析其思想,试图抛砖引玉,推动学界对龟兹佛教文化及回鹘佛教思想的研究。
一 第45窟概况
第45窟位于库木吐喇窟群区大沟的南侧崖壁上,坐南面北,窟口方向348°,附近没有相邻洞窟。西南侧约60米为第44窟,隔沟与第46窟附1窟相望,两窟相距约80米。
该窟为中心柱窟。现存前室、主室和甬道(图1)。前室平面呈矩形,宽725、残存进深320、高480厘米,平顶,壁面草泥层多已脱落,前壁无存。
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宽386、进深436、高456厘米。纵券顶。主室正壁中部开莲瓣形龛。龛内原有塑像,现已毁。龛上壁面绘树冠、华盖、宝珠、飞天和菩萨。正壁下方两侧开左、右甬道。甬道口绘团花纹。两侧壁中绘一禅定头戴披帛的坐佛像,左右侧各绘小坐佛五排,现东壁残存27身、西壁残存23身,均漫漶,坐佛下绘纹饰。前壁下部壁画大多脱落,仅门道外左侧壁上残存部分壁画。门道上方半圆壁面被德国探险队剥去。窟顶中脊壁画以团花图案为饰,部分被攫。左右券腹各绘小坐佛四排,每排8身,以上下错落的形式排列。右侧券腹壁画有两处被攫走。左右侧壁与券顶交接处原置木像台,上有影塑之身光和头光,每壁3身。影塑左右侧有安置小塑像的痕迹,排列形式为—佛二菩萨。塑像均无存。地面中部有一低台。
左右甬道纵券顶,左、右甬道里端与后室相通,后室平面横长方形,横券顶。左、右甬道内外侧壁和后甬道正壁,皆绘佛与菩萨相间的立像。甬道通顶绘莲花、朵云图案。左甬道内外侧壁的榜题均毁。右甬道外侧壁外起榜题为:“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右甬道内侧壁的榜题里端已毁,外端为“南无释迦牟尼佛”。后甬道正壁的榜题残损。左右端壁与后甬道正壁相连。后甬道前壁壁画被德国探险队攫去。
库木吐喇第45窟属回鹘风洞窟,其开凿年代大约在公元10世纪后期[1],洞窟壁画保存基本完整,为我们了解龟兹地区这一时期回鹘人的历史、宗教和艺术特点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二 第45窟研究概况,拟研究问题
最早提到库木吐喇第45窟的是德国的勒柯克和瓦尔德施密特。勒柯克在其所著的《新疆佛教艺术》中对切割自库木吐喇第45窟(他称之为阿布沙罗斯窟)的主室前壁、券顶、左右甬道侧壁和后甬道前壁的壁画进行了介绍,并对这些图像进行了识别,他识别出了前室正壁的弥勒说法图、券顶的坐佛和后甬道前壁的涅槃图,但对甬道侧壁壁画的判定是有些是错误的[2]582。实际上这些壁画中有个别是属于库木吐喇石窟第38窟的(勒柯克将其命名为涅槃窟),这种错误瓦尔德施密特给予了纠正[2]572。德国学者认为这个石窟的绘画年代应该为公元8-9世纪,而且其发展尚未达到顶峰。此外,他们还认为该窟在色彩的使用上,运用了红色、红褐色以及黄色之间的色彩变幻的情况[2]582。中国学者最早对库木吐喇第45窟进行介绍的是阎文儒先生,他在其所著的《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主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库木吐拉》一文中,对第45窟侧甬道的壁画及榜题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认为它的开凿年代在唐到回鹘人统治龟兹时期[3]。随后对第45窟研究的是刘增琪先生,他在对第45窟洞窟形制、洞窟壁画题材及其壁画艺术特点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该窟为龟兹地区吐蕃控制时期开凿的,是来自中原的画家绘制的[4]。后来北京大学的马世长先生在其《库木吐喇的汉风洞窟》一文中以及《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中的《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叙》,也对库木吐喇第45窟的壁画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5]。此外,新疆博物馆的贾应逸先生在认真核对库木吐喇第45窟现存壁画保存状况的基础上,指出勒柯克将部分38窟壁画划入该窟的错误[6],在对该窟形制、题材及艺术分析的基础上,并认为该窟是回鹘中期的洞窟,其时代为公元9世纪及其以后绘制的,风格为典型的回鹘风格,此外,她认为主室两侧壁的壁画为密宗的大日如来[7]。
综观以往对第45窟的研究,可以说对该窟的研究主要是从考古学及艺术学两个方向展开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文献学、图像志、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但可以看出上述研究并不系统,也不全面,研究中也未将个整个石窟的形制、壁画作为整体加以考虑,尤其对于这一石窟最本质方面——它所反映的佛教思想没有加以考虑,从而使得对这一石窟的研究未能深入。笔者以为,站在过去诸领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学、图像学和文献学的方法,把石窟形制、造像和壁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进而揭示出该窟所反映的佛教思想,对于我们了解当时龟兹地区佛教及中西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三 壁画反映的佛教思想
1. 主室正壁、券顶的壁画内容
第45窟的主尊现已无存,不过可以根据本窟内的造像组合作一推测。该窟主室正壁开一龛,龛上绘华盖,华盖上点缀摩尼宝珠,华盖上方和两侧均绘菩提树冠,菩提外侧上方各绘一身飞天,下方各绘一身跪姿菩萨,飞天和菩萨均站于云朵上(图2)。此种情景与唐代实叉难陀翻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一·世主妙严品》中关于卢舍那佛在摩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讲法时的记载吻合:
一时,佛在摩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上妙宝轮及众宝华、清净摩尼以为严饰;诸色相海,无边显现;摩尼为幢,常放光明,恒出妙音;众宝罗网,妙香华缨,周匝垂布;摩尼宝王,变现自在,雨无尽宝及众妙华分散于地;宝树行列,枝叶光茂。佛神力故,令此道场一切庄严于中影现。其菩提树高显殊特;金刚为身,琉璃为干;众杂妙宝以为枝条;宝叶扶疏,垂荫如云;宝华杂色,分枝布影,复以摩尼而为其果,含辉发焰,与华间列。其树周圆咸放光明,于光明中雨摩尼宝。摩尼宝内,有诸菩萨,其众如云,俱时出现。又以如来威神力故,其菩提树恒出妙音,说种种法,无有尽极……
尔时,世尊处于此座,于一切法成最正觉,智入三世悉皆平等。其身充满一切世间,其音普顺十方国土。譬如虚空具含众像,于诸境界无所分别;又如虚空普遍一切,于诸国土平等随入。身恒遍坐一切道场,菩萨众中威光赫奕,如日轮出,照明世界。三世所行,众福大海,悉已清净,而恒示生诸佛国土。无边色相,圆满光明,遍周法界,等无差别。演一切法,如布大云。一一毛端,悉能容受一切世界而无障碍,各现无量神通之力,教化调伏一切众生;身遍十方而无来往,智入诸相,了法空寂。三世诸佛所有神变,于光明中靡不咸睹。一切佛土不思议劫所有庄严,悉令显现。[8]
这些描绘又和第45窟主室券顶绘制十方诸佛(均面向主尊)、诸佛度化众生的因缘故事和券腹下方绘制三世佛这些图像相吻合,说明该窟主室主要部位绘制的应是华严经变,描绘的是卢舍那佛在摩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讲法的情景,那么主尊应是卢舍那佛。该窟正壁龛台前的低台上原来可能放置卢舍那佛造像组合。与第45窟形制、绘制题材接近的还有库木吐喇窟群区第38窟。该窟本窟为中心柱纵券顶窟,现保存少量的前室,主室及左右后三甬道保存较好(图3)。该窟主室正壁前也有像台,像台上原有一身卢舍那佛塑像{1},现已毁,但浮塑的项背光遗迹尚存,背光由内向外绘小坐佛,坐佛的项背光外沿绘火焰纹,再外绘一圈三角形的组合纹样,最外沿一周贴塑小千佛,惜已无存(图4)。背光上方绘菩提树冠,树冠左侧绘一身天人,天人脚下有一身形体较小的飞天。左右侧壁下部均有通壁像台,像台上方各开两个莲瓣龛。该窟两侧券腹绘一佛二菩萨,佛的头光上方均有菩提树冠和华盖。左右甬道外侧壁各绘立佛四身,立佛间均绘一身形体较小的菩萨,内侧壁绘千佛。顶部绘飞天。后甬道正壁中部开龛,龛外左侧绘立姿一佛一菩萨,其间绘有其他人物。右侧也绘立姿一佛一菩萨。前壁绘涅槃图,顶部绘飞天。两个窟除主室侧壁及甬道内侧壁壁画内容差别较大外,形制和壁画题材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其反映的思想应该大致不差,可以互相佐证。第38窟的主尊可以确定为卢舍那佛,那么第45窟的主尊推定为卢舍那佛应该大致不差。库木吐喇石窟的窟群区第9、13窟中也塑或绘卢舍那佛。第9窟绘于右甬道外侧壁外端(图5),第13窟的主尊为卢舍那佛。上述三个洞窟均为龟兹地区回鹘时期修建的。另外,目前出土的回鹘文文书中,也发现有上述《华严经》本的残卷{2}。上述文献和石窟图像的材料均说明,这一时期,华严思想在龟兹地区还是比较流行的。那么第45窟出现卢舍那佛的造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2. 主室侧壁的壁画内容
关于主室侧壁正中的带披帛坐佛像(图6),有学者认为是大日如来像[1]343笔者认为此像应为卢舍那佛像。首先大日如来是密宗主尊,关于其造像特点,《大日经义释》中记载:
观作宝莲华台宝王宫殿,于中敷座,座上置白莲华台。以阿字门转作大日如来身,如阎浮檀紫摩金色。如菩萨形,首戴髮髻犹如冠形,通身放种种色光,被绡縠衣,此是首陀会天成最正觉之标帜也。[9]
可以看出,大日如来造像为菩萨形,身披纱或丝绸之衣。而本窟侧壁正中的造像身着袈裟,为佛装,因而肯定不是大日如来。至于此头戴披帛的坐佛,应属北传华严系统的“装饰佛”,其代表的是华严的卢舍那佛。“阿富汗华严义学的主尊为‘宝冠如来及其他以当时王者衣饰为主的所谓 ‘装饰佛,伴随装饰佛出现的背景通常石窟窟顶是‘十方佛。”[10]本窟的侧壁正中坐佛两侧各有五列坐佛,表现得应是十方佛。尽管这十方佛没有绘制于石窟顶部,但其表达的内涵应该是相同的。
3. 主室前壁上方圆拱壁壁画内容
该壁画已被德国探险队剥走。下面根据他们发表的照片[2]661对其进行描述和辨识。
画面正中为绘一倚坐(或交脚坐?)佛像,头部上方绘树冠,两侧各绘三身闻法菩萨。菩萨头上方亦绘树冠(图7)。
此画面与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下生经》相吻合:
尔时去鸡头城不远,有道树名曰龙华,高一由旬,广五百步。时弥勒菩萨坐彼树下,成无上道果……是时魔王将欲界无数人天,至弥勒佛所恭敬礼拜。弥勒圣尊与诸人天渐渐说法微妙之论。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净不净想,出要为妙。尔时弥勒见诸人民已发心欢喜,诸佛世尊常所说法苦集尽道,与诸天人广分别其义。尔时座上八万四千天子,诸尘垢尽,得法眼净。[11]
尽管经中没有提到弥勒的坐姿仪轨,但根据敦煌、云冈和龙门等地已明确的弥勒造像特征来看,倚坐或交脚坐,手作说法印是弥勒佛的特征[12]。因而,我们可以判断第45窟前壁圆拱壁上绘的是弥勒佛龙华说法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第45窟主室正壁、券顶及侧壁是依据《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一·世主妙严品》绘制的华严经变,而主室前壁依据《佛说观弥勒菩萨下生经》所绘制的弥勒龙华说法图,属三世佛系列,一方面延续了龟兹地区三世佛的信仰传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一时期龟兹地区的弥勒上生和下生信仰的并存,同时它也是此时期龟兹地区华严思想对三世佛思想融摄的具体反映。
4. 左右和后甬道的壁画内容
后甬道前壁原绘涅槃变,画面简单,释迦牟尼位于画面下方,右胁而卧,身后绘五身天人立于娑罗树下(图8)。涅槃是龟兹地区流行题材。该涅槃图画面构成、构成元素与龟兹本土的其他涅槃图非常相似,位置亦位于后甬道内,应该是龟兹地区涅槃信仰与艺术传统的继续。但左右后甬道的其它壁面均绘一佛一菩萨,其中依据榜题可以辨识的有右甬道外侧壁的“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和右甬道内侧壁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为大乘佛教西方净土三圣,代表了西方净土信仰,在此与涅槃图共同出现,反映了此窟涅槃图反映的应是大乘涅槃观,即常、乐、我、净,并与净土等大乘信仰的融合。“南无释迦牟尼佛”由于没有其它可以辨识的佛名与菩萨名参考,其可能反映的大乘信仰已无法断定。涅槃与净土能够结合的渊源在于净土思想所反映的大乘法身观乃是大乘涅槃的本质,净土的性质即常、乐、我、净乃是涅槃的特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由炳灵寺石窟发端的大乘涅槃思想与净土的结合,后来逐渐传入敦煌,为敦煌北凉三窟所继承,发展到北朝的中心柱窟,隋以后又发展出以经变表现两者结合的造像组合[10]65-102,147-148,162-164。库木吐喇第45窟左右后甬道出现的造像情况应该是这种思想影响的表现。
库木吐喇第45窟还反映出龟兹地区华严思想统摄或代替涅槃思想的特点,这点我们可以从左右后甬道中的立佛及菩萨皆面向主室正壁主尊的情况看出。这也是中原汉传佛教唐以后的重大变化。涅槃思想为华严思想代替,肇始于北齐高僧僧稠开凿的小南海石窟中洞和大住窟中。这两窟造像结构相同,其中大住窟为三壁三龛,每龛各一坐佛,各有榜题。东壁为“弥勒佛”,西壁为“阿弥陀佛”。正壁佛像有“卢舍那佛”题刻[13]236,反映出华严思想对涅槃思想的融摄。这种思想后来为唐初高僧杜顺发展,创造出以卢舍那佛统摄涅槃的禅法及石窟造像,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在敦煌莫高窟盛唐的第205窟中看到[10]176。
小 结
1. 库木土喇第45窟是龟兹地区回鹘时期的典型洞窟,该洞窟的主尊为卢舍那佛,主室两侧壁亦绘出卢舍那佛。该窟主室券顶前壁则绘出十方三世佛,左右后甬道和后甬道前壁外,绘出立佛立菩萨,其中有榜题的可见阿弥陀佛等,体现出华严思想对十方三世佛观念的融摄,后甬道前壁绘涅槃图则体现出华严思想对涅槃思想的融汇。
2.库木吐喇第45窟开凿于公元10世纪,所反映的上述佛教思想特点,是中原汉化佛教西传的结果,反映出宋元时期西域与中原、回鹘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参考文献:
[1]贾应逸.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335-339.
[2]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著.管平,巫新华译.新疆佛教艺术[M].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548-550,661-662.
[3] 阎文儒.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主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库木吐拉[J].现代佛学,1962(4):27-29.
[4]刘增祺.库木吐拉45窟壁画浅析[J].新疆社会科学,1988(1):101.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库车县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210,268.
[6]贾应逸.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窃取库木吐喇石窟壁画的位置核对[C]//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38-239.
[7]贾应逸.库木吐喇回鹘窟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C]//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13.
[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0册[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1-2.
[9]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3册[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313.
[10]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4.
[1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421-422.
[12]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 十六国北朝卷[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15-29.
[13]赖鹏举.丝路佛教的图像与禅法[M].圆光佛学研究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