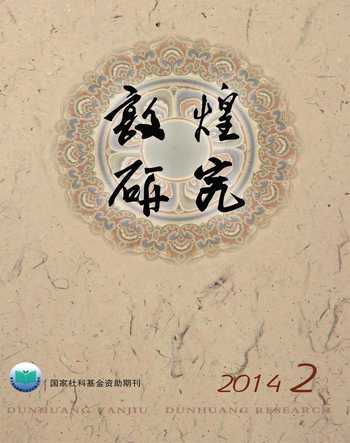唐代佛幡图案与工艺研究
杨建军 崔岩
内容摘要:幡是佛教供养佛、菩萨的供养具。现在所见佛幡实物多来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出土发现和日本寺院的传世品,此外敦煌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绢画中描绘了佛幡的形制、颜色和功用等。依据这些具体的实物与图像,参考文字记载,可以对唐代佛幡的来源、形制、图案和工艺进行探讨,以认识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综合特点。
关键词:唐代;佛幡;敦煌壁画;藏经洞;图案;工艺
中图分类号:J18.4;K87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2-0001-15
A Study on the Patterns and Techniques of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t Banners
YANG Jianjun1 CUI Yan2
(1.School of Fine Art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2.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China Institute of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2208)
Abstract: A Buddhist banner is not only an offering to Buddha and Bodhisattvas, but also an ornament in Buddhist rites. Through its use and dissemination, i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relatively fixed form and usage. Now most Buddhist banners surviving today are either from the Library Cave at Dunhuang or monastic heirlooms in Japan. In addition, the murals of the Dunhuang caves and the silk paintings from the Library Cave inform the shape, color and function of Buddhist banners. Based on these specific objects, images and written recor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origin, shape, pattern and techniques of Buddhist banners, and thus demonstrate their art and technological features.
Keywords: Tang dynasty; Buddhist banner; Dunhuang mural; Library Cave; Pattern; Technique
引 言
幡,又作旛,梵语波哆迦(Patākā)[1]、驮缚若(dhvaja)[1]1238、计都(ketu)[2]、脱阇(Dhraja)[3],一般译云幡、幢、旗,为旌旗的总称 [1]347。形状无大分别,或有依外形作区别者,谓圆桶状者为幢,长片状者为幡,皆为军旗之意。《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9云:“梵云驮嚩(二合)若,此翻为幢;梵云计都,此翻为旗。其相稍异:幢但以种种杂彩摽帜庄严,计都相亦大同……如兵家画作龟龙鸟兽等种种类形,以为三军节度。”[4] 意谓天竺诸王以军旗之幢统领军旅以向敌军。而佛陀则以智慧之幢,降伏一切烦恼之魔军,以幢象征摧破之义,故被视为庄严具,用于赞叹佛菩萨及庄严道场,及表示佛菩萨之威德,亦用于祈福或其它佛教仪式中。在寺院中,幡是供养佛、菩萨及殿堂法会的重要用具,于佛教传播与仪式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形制和用法,或以材料种类分,或以颜色分,或以用途分等,逐渐演变成种种不同的类别{1},佛经及古代典籍中屡屡提及。
如《长阿含经》卷4《游行经》所载:“以佛舍利置于床上,使末罗童子举床四角,擎持幡盖,烧香散华,伎乐供养。”[5]从此处可得知幡为供养佛舍利的供具。
又如《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所载:“欲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应先造立彼佛形像,敷清净座而安处之。散种种花,烧种种香,以种种幢幡庄严其处。”“有诸众生,为种种患之所困厄……时彼病人亲属知识,若能为彼归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请诸众僧转读此经,然七层之灯,悬五色续命神幡。”“造五色彩幡,长四十九拃手,应放杂类众生至四十九,可得过度危厄之难,不为诸横恶鬼所持。”[6]如经中所述,幡为庄严道场的器具,也可作为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祈求度过危厄的法器。
《华严经》亦谓造立此幡,能得福德,避苦难,往生诸佛净土,供养幡可得菩提及其功德。
另有成书于北朝年间的《洛阳伽蓝记》,著者杨衒之依据惠生行记、宋云家纪、道荣传记载了北魏神龟年间宋云、惠生向西域求经的史实[7]。他们从鄯善赴于阗途中遇捍么城{2},在城南寺中看到:“后人于像边造丈六像者,及诸宫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幅上隶书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幅,观其年号,是姚秦时幡。”[7]266这里所载幡上所记年号分别对应公元495年、501年和513年。而中国历史上的姚秦时期为公元384年至417年,期间有法显西行,法国人沙畹(E.Chavannes)《宋云行纪笺注》(Voyage de Song Yun dans LUdyana et le Gandhara. 518-522)认为宋云所见姚秦时期的幡为法显所建[7]270-271。同卷中还记载:“惠生初发京师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从于阗至乾陀,所有佛事处悉皆流布,至此顿尽,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拟奉尸毗王塔。”[7]329可见,4世纪末5世纪初,幡已是佛事中重要的供养具。至6世纪初宋云和惠生西行时,佛幡作为皇家与公侯大臣的主要献纳品而伴随西行求法者沿途供养之用。
以上记载涉及到幡的用法,强调其为染织品所制,具有五彩的特点,也可看出早期佛幡有题记年号的传统,这为我们研究和确定它的年代起到了重要作用。幡的形制大小不一,关于图案或使用何种工艺制作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下面通过对唐代佛幡的来源、形制、图案和工艺的探讨,来认识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综合特点。
一 唐代佛幡的来源
我们对唐代佛幡的认识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实物、绘画作品及文字记载。这三方面相互补充,从平面到立体彼此印证,可提供一个较全面的研究框架。
1. 实物
现存唐代佛幡,最主要的来源是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这些幡随着其它藏经洞的珍宝在20世纪初陆续被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攫走,现保存在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包括印度事务部)、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国外的大型博物馆中。例如英国的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收集了230件幡(含残件),其中约有179件丝质幡、42件麻布幡和9件纸幡[8];法国的吉美博物馆也保存了至少10件相当完好的幡[9]。这些幡大多为使用品,丝质幡较精致,麻布幡相对简陋,有的因时间久远而已残损不全。据敦煌文书记载,当地寺院会将不能使用的残幡妥当保存,或将残幡裁开用于经帙、幡头缘、幡足等,而将供奉给寺院的较完整和精美的纺织品用于经帙、佛幡的幡头和幡身、帷幔或用作桌帘。现存幡的面貌各异,绝少重复,但是出于使用或节俭的原因,当地的僧人会使用同一面料制作大小不同的系列幡,所以出现了现存不同博物馆的幡头是一模一样的现象。
1965年,敦煌莫高窟第130窟主室南壁的岩孔内和第122窟、第123窟窟前两处,发现六十余件天宝十三载(754)的丝织品,保存较好的大部分是各类染缬绢、各色纹绮缀联而成的长条彩幡,这些幡现藏敦煌研究院。
另在邻邦日本的各地新老寺院中都有保存的佛幡,从飞鸟时代(592—710)到奈良时代(710—794)保存下来的大大小小的幡有五六百件,多数保存在正仓院,属于8世纪中叶,相当于中国盛唐时期。还有一部分为法隆寺现存的藏品,以及法隆寺1876年献纳给日本皇室而后转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佛幡,其年代属于7世纪下半叶。这些佛幡大都属于日本皇室的供养物,材质珍贵,制作工艺十分精美。
2. 绘画作品
能够体现唐代佛幡图案与工艺特点的绘画作品主要是敦煌莫高窟壁画与藏经洞出土的绢画。
莫高窟壁画是敦煌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千余年中形成了历代的风格特点,发展至隋唐时期盛行各类大型经变图,即根据佛经绘制的壁画。据统计,莫高窟有经变33种[10],而在唐代最为流行的是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经变、弥勒经变、维摩诘经变、如意轮观音经变、不空索观音经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法华经变、报恩经变、天请问经变、华严经变、涅槃经变等十余种。在这些内容丰富的壁画中,依据经文内容的表述或社会生活的习俗,绘制出了佛幡。
初唐第332窟南壁涅槃经变举棺场景中(图1),用以引导的彩幡悬挂于龙首与莲花首长杖上,由幡头、幡身、两幡手、三幡足构成。幡身为绿、白、青、黑褐四色反复连缀而成,中有五瓣花纹。
初唐第220窟北壁药师经变中,绘三件多坪彩幡随风舞动,每坪均有幡手,一些幡身中绘有非常清晰的小圆圈纹和花卉纹。
初唐第323窟南壁石佛浮江故事图中绘道士设蘸坛迎请石佛场景,坛侧设六长杆,每杆悬挂一彩幡,有幡头,幡身四坪,为青、赤、黑、褐,无幡手,幡足为燕尾形。
盛唐第172窟东壁北侧文殊变中天人眷属执两彩幡,有幡头,无幡手,幡身九坪,分别为绿、黑、赤、青四色,两幡足,无图案。
盛唐第148窟东壁药师经变中彩幡(图2),幡身八坪,分别为白、黑、青三色反复,幡身中有褐色五瓣花卉纹,呈散点排列。其中五坪两侧有幡手,幡手为两叉燕尾形,两幡足。
晚唐第9窟东壁北侧文殊变天人眷属执两彩幡,幡悬挂于莲花首长杖上,两幡手,幡身十八坪,分别为绿、黑、青、赤四色循环,坪间有橙红色缘,两幡足,无图案。
另外五代第61窟西壁五台山化现图、宋第76窟东壁八塔变、西夏第153窟南壁文殊变等壁画中均有各色佛幡的表现。这些壁画不仅提供了佛幡的形制、色彩、图案等方面的信息,也展示了使用的场所和方法。
1900年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绢画中有几幅引路菩萨图,其中两幅藏于大英博物馆。其一绘于唐代,画面中菩萨回首顾盼,右手执香炉、左手执莲花,上悬幡,有幡头,幡身四坪,浅黄色地上呈白色大团花纹,两幡手,两幡足(图3)。菩萨身后为一贵妇,虔诚尾随菩萨往生净土。另一幅绘于五代,构图略同,引路菩萨左手持香炉,右手持长杆悬幡,幡头有对称图案,缘为红色,幡身为白地浅黄色散点花纹,两幡手与两幡足为黑地,上有亮黄色菱格纹。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引路菩萨图中,菩萨手持彩幡,幡头缘为红色,幡身四坪,分别为白、红二色,白色幡身中有四瓣小花纹,两幡手青黛色,两幡足为燕尾形,均为绿色。同藏于法国的绢画华严经十地品变相图和绢画行道天王像中均有对彩幡的描绘,前者绘制于唐末五代初,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身后眷属天众持彩幡,后者表现毗沙门天王乘云出行的场景,天王右手持戟,上系五色彩幡,仅为赤、黄、青、黑、白五色彩条。
3. 文字记载
除了实物与绘画作品之外,唐代佛幡的资料还散见于各类文献中,如佛经、历史古籍、敦煌文书以及探险笔记等。
如敦煌文书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记载某寺有幡380件,其中196件为绢质,83件为麻质,5件为印花色织物[9]22。其中多次提到敦煌使用夹缬的情况,如夹缬伞子、夹缬带、夹缬幡等,说明了夹缬工艺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另外,敦煌文书中常见银泥幡的记载,如S.3565(2)《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浔阳郡夫人等供养具疏》提及“银泥幡”,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提及“小银泥幡子伍口”,P.3587《年代不明(10世纪)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提及“官施银泥幡柒口。又大银泥幡壹口”,并提到了幡的尺寸[11]。这些数据可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佛幡的形制、尺寸和制作工艺等情况。
日本对于完整系统的数据保存历来重视,文献通常可直接与实物对应,或帮助确定文物年代,或辅助解释工艺方法。例如正仓院所藏的一些文献中提到的“押蜡缬”一词,对于了解当时蜡缬工艺使用模具进行防染的应用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二 幡的形制
从以上提及的实物、绘画作品及文字记载等来看,一具完整的幡一般由三角形幡头、矩形幡身、幡头下部及幡身左右垂饰的垂手、长条状的幡足构成(图4){1}。制作幡的材质有丝、麻、银、铜、玉、木、纸等,依据使用场所的不同而有区别,如堂幡多用锦幡、绫幡、刺绣幡,用于请雨法之庭仪的庭幡多用玉幡{1}、丝幡{2}、青幡,施饿鬼幡主用纸幡。为使染织面料所制的幡保持平整,在其各部分的连接处夹缝常有细竿,悬挂时不致翻转扭结。
在常见的丝质幡中,幡身主要有两种变化:第一种幡身的坪通常较长,为一整块面料裁成的矩形,幡身缘和坪界较宽;第二种幡身的坪接近正方形,由三块或四块不同的面料连缀拼接,幡身缘和坪界狭窄。幡足通常是与幡身大致等宽的整块面料,将这块上下相连的面料中间裁为二至四条,边缘用细小的针脚缝边,形成幡足,末端往往连有木制彩绘悬板。关于悬板的形象与作用在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中曾有记述:“长条的底端绕在一窄条竹篾上,然后用胶粘在一块扁平的彩绘木板上。木板可以将幢幡拉直,防止它被风卷起,上面通常画有植物图案。利用这块木板还可以很方便地将幢幡卷起来,便于运输或存放。我本人就曾这样做过。这无疑说明,幢幡这样卷起来后保存得极好。”[8]133另有一类幡足为燕尾形,末端没有悬板,在敦煌莫高窟壁画及藏经洞出土绢画中可以见到,如前文提到的大英博物馆藏唐代绢画《引路菩萨图》中菩萨手持幡即属此类。
现存日本的佛幡形制有不同的变化。藏于正仓院的佛幡上有关于年代和事件的题签,其中一部分与天平胜宝四年(752)东大寺大佛开眼会有关,一部分曾用于天平胜宝九岁(757)圣武天皇一周忌斋会,大多为8世纪中叶所制。后者所用佛幡有几百件,称为道场幡,悬挂于法会举行的大堂上;另有十几件大型幡,称作灌顶幡{3},长约17至18米。缝于道场幡的白绫题签上有朱书和墨书的题记:“平成攻御宇后太上天皇周忌御斋道场幡 天平胜宝九岁岁次丁酉夏五月二日己酉右(或左)番东大寺。”灌顶幡上也有同样日期的白绫题签。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佛幡只题写着它们被捐献的干支纪年{4},而无事件的记录,大多属于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初。两组佛幡藏品从形制上看有显著的差别,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佛幡幡头顶角为锐角,有的有幡头面,有的仅有三角形幡头缘外框;幡身的坪通常较长,缘和坪界宽阔,有的有双缘和双坪界;垂手有的用染织品制成,有的用镀金雕镂小铜板代替;幡足由独立的染织条带组成,下端通常为径直裁切。第二种类型的佛幡幡头为等边三角形;幡身的坪通常为正方形,缘和坪界狭窄,并且相互独立;幡的垂手由染织品和流苏构成,没有铜板装饰;幡足由连在一起的一条条染织品构成,有的幡足末端有装饰物。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佛幡多属于第一类型,时间较早,据日本学者研究原应为法隆寺的藏品[12],而正仓院的佛幡多属于第二种类型,时间稍晚。这种差异可能体现了幡的形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
幡有大幡、小幡之分,其大小、寸法均有一定之规准。敦煌文书P.2613记载了陆尺、玖尺、壹丈贰尺、壹拾玖尺、肆拾三尺、肆拾玖尺等六种尺寸的幡,按唐尺约为现今30厘米来计算,小幡的尺寸不超过2米,大幡的尺寸在13至15米之间[13]。现存较完整的幡中,高度为1.3至2米的数量最多。大幡多保存不全,仅残存幡足或幡带,依计算其整体高度也应与敦煌文书所载一致。
三 唐代佛幡的图案
唐代佛幡多为彩色幡,通常为不同织物的拼缝组合。现存实物中有一些由于使用、保存和修复的得当,至今图案清晰,色彩明丽。根据佛幡所呈现色彩和图案造型的特点,可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1. 彩幡
前面引文中多次提到五色幡,《佛学大辞典》解释道:“止观辅行曰:‘五色旛者总举五色。绣画间色亦应无在。字应作旛。旛者旌旗之总名也。经中多作此幡。幡帑字耳。今佛法供具。相状似彼。故云旛耳。凡造旛法。切不得安佛菩萨像。旛是供具。供于所供。如何复以形像为之。”[14]可见这种五色幡为供具,其色彩应限于五种{1},无刺绣或彩绘工艺的附加,无间色,且幡身无佛像或菩萨像。大英博物馆所藏彩幡(MAS.860){2}应是按这种规制所作的(图5),幡头由两块织锦拼缝而成,一块为蓝地黄色飞鹰图案,一块为粉红地粉绿花卉纹,均不完整。幡头缘为绿色绮和紫色绢,垂手为黄、红色绢拼缝,幡身由青、白和红色绢上下相连构成,幡足为整块青色绢切成三条,下有梯形彩绘悬板。这是藏经洞出土的最为完好的彩幡之一,色彩的组合遵照佛教五色进行配置,仅用正绿代替黑色{3},幡头的织锦一方面可显示出彩幡的高档,另一方面也取图案中的黄色调来共同形成五彩幡。1965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发现的残幡,有几件幡身由色彩单纯的各色暗纹绮缝缀而成,也同为五色幡。
制作彩幡的织物通常为单色平纹或斜纹的绢或绮{4},图案是通过织造时经纬线交织而呈现肌理与光泽变化的暗纹,有折线纹、菱格纹、龟背纹、散点小花纹等。大英博物馆藏唐代绿色菱格纹绮幡足残片(MAS.947)和唐代灰绿色菱纹绮幡足残片(1919.0101.0.132){5},所用织物均为单色暗花菱格纹绮,正仓院也保存有一块类似的菱格纹黄绫残幡片,说明这类图案的丝织品在唐代十分流行。
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发现的彩幡残片中,还有在彩绢底上用绞缬、蜡缬等工艺表现的菱形格、花鸟纹、灵芝纹、云头纹等图案,图案精致小巧,均呈散点分布,但仍以表现单纯的色调为主。
2. 绘像幡
现存唐代佛幡中有一部分是在幡头和幡身上直接以墨、颜料或银粉绘制佛、菩萨、天王和金刚力士像,它们有着供养、发愿的用途,同时是很珍贵的绘画作品。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八件棉质和麻布幡头,其上均彩绘佛像,制作年代跨越唐代、五代至宋初。所绘佛陀披红色袈裟,结跏趺坐于红色莲座上,有头光和身光,莲座两侧各有花叶伸出,适合于幡头的三角形轮廓(图6)。幡身绘佛像的例子不多,但是绘制的手法比幡头精细。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因的收藏中有一类唐代佛传故事幡,可辨别的故事包括乘象入胎至菩提树下成正觉等多个场景。由于幡身的限制,佛传故事以上下排列的构图展开,一件幡只能表现其中的一部分场景和情节,所以使用时应为组合成套悬挂的。佛传故事画在莫高窟壁画中从北凉时期一直延续至宋代,尤其在早期壁画中更为流行,如规模最大的北周第290窟人字披顶的佛传故事画,以顺序式的横卷描绘了释迦牟尼从诞生到出家之间的80个画面,内容最为丰富。后因隋唐时新兴的经变画占据石窟的主要壁面而退至次要地位。而此处可见的佛传故事幡绘制手法熟练精美,构图上以竖幅为主,与五代第61窟的屏风佛传故事画风格类似,说明佛传故事题材绘画的延续。再加上同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众多7至10世纪的绢画、麻布画和纸画,这种现象似乎表明古代绘画从早期的石窟壁画发展至晚唐、五代时,已逐渐转移到可移动、可悬挂或展开的纺织品上的一种趋势。
佛像之外,菩萨像是绘像幡中最重要的主题,有观世音、文殊、普贤、地藏诸菩萨以及供养菩萨像等,有的在人物造型、服装饰物等方面带有鲜明的印度风格,有的经画工加工融合而传承了中国古代中原地区传统绘画的脉络。绘像幡中还有数量不多的天王和金刚力士像,其形象和色彩与同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壁画相类似。这些造型鲜明、设色明艳的绘像幡表现出受到印度、西亚、中亚以及中国中原地区影响的多元化绘画风格。
3. 几何抽象纹
几何纹包括前节中所涉及的单色织物表现的几何暗纹,还有多色织物以不同色彩丝线的交织变化以及以其它工艺手段所表现的几何纹样。
例如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藏的唐代青地小花纹锦幡头缘(L.S.659){1}和唐代菱格花卉纹锦幡头缘(L.S.633),两者均属于幡的残片。前者在青地上显红色小圆花纹;后者图案为深褐色地上斜向交叉浅棕色菱格纹,菱格中间为浅棕色四瓣花,另有草绿、浅蓝、橙色横条相间穿过花心中央。图案虽然简单,但是色彩明暗搭配,冷暖协调,所以十分耐看。
再如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发现的多色花鸟纹缬染幡,幡身其中的五段以绞缬法在绿色或紫色地上显白色菱形纹(图7),图案排列整齐规则,色彩边缘有淡淡的晕染效果。模拟色彩渐变效果的制作方法有晕染和晕锦{2},在中国新疆阿斯塔那墓葬曾出土过一件晕提花锦裙,锦用黄、白、绿、粉红、褐色五色经线织成,然后再于斜纹晕色彩条纹上,以金黄色细纬线织出小团花。正如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小花晕纹锦悬袢残片(L.S.602)(图8),图案以黄、红、棕、浅绿、墨绿等各色彩条组成,每条条纹上装饰着四瓣和六瓣的小花纹,颜色亮丽。又如日本正仓院所藏的晕锦幡缘残片,这件经锦幡缘曾用于天平胜宝九岁(757)圣武天皇一周忌斋会,它主要表现蓝、绿、褐、白、黄、红等几道彩条交替变化,其中散布着细小的白色圆点和绿色花叶,色彩绚丽缤纷,好似光芒四射。
日本法隆寺所藏佛幡中几何纹所占数量最多,主要包括菱形纹、格子纹、龟背纹和山形纹等,材质多为绫和经锦。因其制作年代较早,这类以直线、折线为主要造型元素的图案更多体现了织造工艺发展初期的特点。如原藏法隆寺,现藏正仓院的菱形联珠纹白绫幡足,是将联珠纹中填饰大小相接的菱形格形成四方连续,其余空间再饰以相套叠的菱形纹,可见简单的几何纹通过相互组合、重复变化也可产生复杂丰富的效果。再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棋格地散花纹锦幡头(图9),在绿地上显红、白色棋格纹,地纹上散点排列黄色小团花纹,经纬组织复杂,为8世纪下半叶所制。棋格纹图案简洁,配色对比鲜明,显得生动活泼。
几何抽象纹中还有一些有趣而费解的纹样,因时间的久远,使得它们的形象和含义非常神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藏有一批称为広东小幡和広东大幡的佛幡,“広东”这个词在日本用于指代一类特殊的上古染织品。幡面显示这是一种被称为伊卡特{1}的扎经织物(图10),是先将经线捆扎入染再进行织造而形成图案的工艺。这类纹样参差错列,色彩斑斓,与中国新疆传统的艾德莱斯绸风格相似。抽象的图案究竟表示花卉、山峦、云气或是水波?这可供我们联想和进一步的研究。
4. 圆形适合纹样
唐代佛幡图案中最有代表性的圆形适合纹样是联珠纹、团花和宝相花。
联珠纹源自波斯萨珊王朝的装饰艺术,特征是在圆轮的边缘饰以圆点串成联珠,构成几何形骨架,圆环中间装饰着禽兽纹或人物纹。相似的纹样可以在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20彩塑菩萨服饰上见到,另在中国新疆出土的年代相当于北朝晚期至隋代的染织品中也有表现,所以这种纹样很可能早在6世纪下半叶就已传入中国。在日本大阪府下野中寺金铜弥勒菩萨半跏像服饰纹样可以看到相类似的联珠纹,塑像的铭文显示为丙寅年,也就是天智天皇五年(666)。从这些考古发现或传世文物中,可以看到联珠纹从波斯经中亚传入中国内陆,进而影响日本装饰图案艺术的历程。
现藏大英博物馆的红地联珠对羊纹锦幡头残片(MAS.862)(图11),图案为红地上显绿、白、棕三色花,联珠纹圆环中央棕榈叶上站立着一对山羊,身上以四瓣小花纹为装饰,环外填饰对鸟图案。据学者的研究,这件织锦中山羊的造型与收藏于比利时辉伊大教堂中带有粟特文题记“赞丹尼奇”的织锦完全一致[15]。这件织锦中联珠纹的造型带有早期的特点,相比之下,朵花团窠{1}对鹿纹夹缬绢残幡(MAS.874)和朵花团窠对雁夹缬绢幡(MAS.876-877)(图12)两件作品中的联珠纹造型已显示着后期的变化,联珠不再是单纯的串珠,而是以朵花连接而成的团窠。主题图案一是白地蓝花的花树对鹿,一是彩色的团花双鸟,完整的联珠团窠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花纹清晰准确,形象气势丰满,应为盛唐时期的作品。
中国盛唐时期最为典型和具有本土化创造的装饰图案是团花与宝相花。团花指外轮廓为圆形的装饰纹样,小型的团花纹在中国新疆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联珠小团花纹锦中可以看到,团花八瓣,结构简单,后来又发展出形体更大、结构更复杂的团花纹。
宝相花并不是指某一种或某一类的花,而是将多种自然形态的花朵进行艺术处理,例如牡丹、莲花、菊花的花苞、花托、叶片等,使之综合成为富有装饰性的图案。敦煌藏经洞出土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的持红莲菩萨幡(EO.1399)幡头(图13)中绘制了非常华丽的宝相花图案,与敦煌莫高窟盛唐时期壁画中的图案风格相似。造型上花叶重重套叠,用色以退晕法为主,即以一种色相的不同深浅变化来形成色彩的层次,从而体现富丽华贵的效果。日本圣武天皇一周忌斋会(757)所用的道场幡中,约四百件四坪或五坪形制的锦制道场幡中有近九成的织锦面料装饰着宝相花纹,其代表为现藏正仓院的赤地宝相花纹锦幡头(图14)。织锦图案中的宝相花层层套叠,花叶相连,加之以六种色彩的丝线织成,色彩对比强烈,效果华美丰富。正仓院中另藏有一件紫地宝相花纹锦幡头,同样突出了宝相花多向对称放射的骨架形式与冷暖对比的配色特点,四角装饰的莲花带有写实的意味,整体色泽沉稳,制作时间略晚于前者。
5. 动物纹
动物纹在唐代佛幡图案中很少单独使用,常配合联珠纹、卷草纹或花卉纹共同表现。这些图案包括鸟、鸳鸯、羊、鹿、狮子等,有的成对出现,有的单体伫立,形式丰富多样,在前文介绍联珠纹时已有所论述。
赤地鸳鸯纹唐草{1}锦幡足饰(图15)和浅绿地鹿宝相花纹锦幡足饰是藏于日本正仓院的两片纬锦织物,它们作为幡足下端的装饰用于长约十余米的幡中,同属圣武天皇一周忌斋会(757)的用品。两幡足饰外轮廓均裁剪为花头形,内饰图案不完整,但是可以看出前者在蜿蜒翻转的唐草环绕中,有两只相对立于莲花上的鸳鸯,共衔一绶带花朵;后者将一只写实的鹿置于团窠的环形花饰中,旁侧还有宝相花装饰。尤其是前者以红、绿、浅绿、青、紫、黄、白等各色丝线织就,色彩搭配鲜明艳丽,充满着盛唐时期的勃勃生机。
日本正仓院中还藏有一批以非团窠动物形式为主题图案的佛幡,其中动物纹仅作为辅助纹饰出现,如茶地唐花狮子纹锦幡和紫地山羊纹锦幡头,均以深地浅花显色,色调单纯统一,而更注重图案构图和造型的表现。此类织物图案组成的完整道场幡中,幡身四坪均以两块不同底色而相似图案的三角形织锦拼制而成。
6. 花鸟纹
进入8世纪后期,唐代中晚期的佛幡图案中出现了写实的花鸟纹,艺术风格趋向自由,同时期的服饰面料中也广泛应用,流行延续至五代。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现藏大英博物馆的墨绘鸟衔花枝纹幡(MAS.887)是一个完整的例子。在长约43.1厘米、宽约14.3厘米的幡身部分,以墨绘制了两组鸟衔花枝的纹样,运笔自由,动物的形态生动活泼。另一件蓝地朵花鸟衔璎珞纹锦幡头悬袢残片(MAS.921)同样表现了这个主题,但是工艺不同。它是以深蓝色经线作地、以白、橙、绿、浅绿、黄色经线显花的经锦,残片两侧各有一排六瓣小团花纹,花间有两两相对的鸟共衔一花枝,鸟胸前垂饰璎珞连缀成一结形带穗装饰。相比起绘制的自由,织锦表现的图案更加规则整齐。
同样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的唐代佛幡中有一组非常有代表性的绘制花鸟纹幡,即银泥练鹊衔枝纹绢幡(EO.3584){2}、银泥迦陵频伽纹绢幡(EO.3585)和银泥花鸟祥云纹绢幡(EO.3586)。这三件佛幡图案主题一致,用料、色彩和形制都基本相同。在黄色绢面上以现已变色发黑的银泥分别绘制了练鹊衔着长长的花枝飞翔、人首鸟身的迦陵频伽弹奏乐器和祥云衬托的绶带鸟衔折枝花的图案,绘制轻松,构图自由,仿佛是一幅幅绘画。另有一件绢地银绘对鸟花卉幡身(EO.1164)(图16)以同样的工艺制成,幡上图案为左右对称式。幡身上方绘一对飞鸟共衔一环,环下低垂弯曲的花枝,残缺的幡身下方可看到还有一对飞鸟在花枝两侧飞舞。此幡为残片,绘制精致,图案的组织也是匠心独具,显得工整大方。
日本正仓院所藏白地花鸟纹锦幡残片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绿地花鸟纹锦幡足饰的图案更像是花鸟画。前者以白色经线为地,以白、绿两色纬线显花,描绘了百花竞放、百鸟争鸣、蜂飞蝶舞的场景。后者的图案更具平面性和装饰感,锦面以碧绿的水波为地纹,水中有成对的鸳鸯,并散点分布着六瓣大小团花纹。这种图案的流行体现出新的审美趋向,一种清新、自然的装饰风格正在形成。
四 唐代佛幡的工艺
唐代佛幡主要以丝、麻、棉等染织品制成,几乎每件都使用了不同的织物品种和制作工艺。通常幡头和幡身使用的材料不一样,特别是幡头缘常镶以结实而精美的织锦,这可能是出于幡头负重的角度进行考虑和制作的。如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锦缘彩绢幡(MAS.861),悬袢为蓝色绢制;幡头为两面,正面为蓝绿色地唐草纬锦和方格花纹锦拼缝,反面由两块褐色暗花绮拼合制成;幡头缘也为不同面料,左边为蓝地花卉纹纬锦,右边是绿色素绢;幡手为蓝色素绢;幡身为三坪,分别为蓝色绢、白色菱格纹绮和红色素绫;幡足为蓝色绢裁切而成。佛幡的多种用料反映了唐代染织品的丰富性,另外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幡大多为实用品,长期使用磨损后再以不同面料进行修补。
将唐代佛幡染织品所用工艺综合起来,可以分为织、染、绘、绣等四大类。
1. 织
唐代丝质佛幡采用的织物品种很丰富,包括绢、、绮、绫、罗、锦、妆花织物、缂丝等。其中最为丰富多彩的是织锦,按织造技术可分为经锦和纬锦两大类。经锦以两色或多色经线与单色纬线织造而成,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如前文提到的持红莲菩萨幡(EO.1399),其幡头缘的三瓣朵花纹锦便是一种经锦织物。纬锦织物恰好相反,经线为同一颜色,纬线可为两色或多色,即经线为地、纬线显花,可以织造出比经锦色彩更丰富和图案更复杂的面料。这种工艺在中国唐代大量发展并流行,为表现宝相花、团窠动物纹等复杂的图案提供了技术上的前提和条件。如吉美博物馆藏吉字葡萄卷草团窠凤纹锦(EO.1201),图案组织、主题与日本正仓院的紫地卷草团窠立凤纹锦非常相像,应同为唐代流行的纬锦织物。
日本法隆寺所藏年代较久远的约170件佛幡中,绫是运用较多的,但最主要的面料是,锦仅用于其中的10件,包括広东大幡、広东小幡及蜀江锦幡,而且仅限于佛幡上的小面积部位,如幡头、幡手或幡缘。公元746年编纂的法隆寺资财帐所纪录的染织佛幡共167具,其中有“秘锦灌顶幡”的称谓,日本的学者松本包夫认为它可能与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広东大幡一样,同属于伊卡特织物的范畴[12]210。相比之下,日本正仓院所藏的佛幡展现出染织工艺的多样化,使用的面料包括经锦、纬锦、缀织、绫、罗、染缬、刺绣等,表现的图案种类也大大丰富了。
缂丝又称为刻丝、克丝,《鸡肋编》所记缂丝的织法是“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16]这种织造方法又称通经回纬,即纬线不贯穿整幅面料,只在需要的一段织入,所以可以表现形象自由而色彩丰富的图案。中国新疆吐鲁番和青海都兰等地都曾出土过小面积的唐代缂丝,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幡和经帙上也有局部的表现,或作为佛幡悬袢和幡头缘,或用于经帙系带。如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绢地彩绘幡头(MAS.905a)(图17),幡头为彩绘花卉纹,幡头缘为红地团窠立鸟纹缂丝织物,据学者研究,此图案应属于唐代流行的陵阳公样{1}。
2. 染
唐代印染的方法很多,最为著名的是夹缬、蜡缬、绞缬这三种,在唐代佛幡中可以看到这几类染色工艺的体现。
夹缬在盛唐时期非常流行,它是用两块雕镂相同的花版夹紧织物入染的方法,可以染多种颜色,染成的图案具有对称的特点。夹缬所做织物可以作为服饰面料,也可以做成大型的室内装饰屏风,如日本正仓院所藏绀地花树双鸟纹夹缬屏风、鹿草木夹缬屏风等。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幡中有大量以夹缬工艺制作的幡头、幡身等,如花卉纹夹缬绢幡(L.S.293)、浅黄地簇六球路朵花纹夹缬绢幡(1919.0101.0.127)、方胜朵花夹缬绮残幡(L.S.556)、绿地蛱蝶团花飞鸟夹缬绢幡(L.S.552)、朵花团窠对鹿纹夹缬绢残幡(MAS.875)、黄地团窠盘鹤纹夹缬绢幡(L.S.621)、朵花团窠对雁夹缬绢幡(MAS.876-877)、文殊菩萨骑狮像幡(EO.1398)夹缬幡头、花卉纹夹缬绢幡(MG.26460){2}、绿地红花夹缬绢幡头(EO.1192/A)、花卉纹夹缬绢幡头(EO.1192/C1)、花卉纹夹缬缘绢面幡头(EO.1192/C2)等。藏于日本正仓院和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两件夹缬罗幡(图18)是以夹缬技法制作的花卉纹佛幡,图案以牡丹花为主,组织自由灵活,打破了夹缬工艺擅长表现的对称图案构图,呈散点排列的格局,是夹缬工艺发展变化的极好范例。
晕染是在夹缬基础上的变化,将面料夹在木版之间,然后涂上染料,表现色彩从浓到浅渐变的效果。日本法隆寺藏有许多用绞缬和蜡缬技法制作的佛幡,而没有用夹缬和晕染的,正仓院所藏8世纪的染织品中可以找到大量用这四种染色方法制作的面料,展现出新旧技术的多样化。
古代蜡缬技法以蜡绘和模具印蜡为主{1},手法灵活。唐代蜡缬佛幡的代表为1965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第130窟主室南壁岩孔内的多色彩幡(图19),幡身第三段用蜡染技法表现出流云、飞鸟、浮禽、花鸟等图案。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件绛地灵芝花鸟纹蜡缬绢残幡,现存幡身两段,一段为绛色绢地蜡染灵芝花草飞鸟图案,印染精致。另有同年在莫高窟第122窟前发现的湖蓝地云头花鸟纹蜡缬绢,据同时发现的纪年遗物确定此绢的制作时代为唐开元、天宝时期。湖蓝色绢面上,以蜡染的方法显出浮游的水禽、舒展的花朵和翱翔的飞鸟。从仅存的回环图案中可以看到表现的随意性,应为手绘。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蜡缬制品可以看出,它既可做成有主题性的观赏装饰品,如成批量、成系列的蜡缬屏风,也大量用于皇室实用品中,做成乐器袋、武器袋、袈裟箱袋、几褥、花蔓以及屏风的边缘等。
绞缬即今日所谓的扎染,依据技法的不同可分为缝绞法、夹板法、打结法、绑扎法等四大类,因制作简便,易于普及推广。与夹缬、蜡缬不同的是,绞缬无法制作出精细、具体和复杂的图案,但是图案的简洁与色彩的渐变可令人感到自然的趣味,所以在宫廷和民间均十分流行。如前文提到的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发现的多色花鸟纹缬染幡即是以绑扎法制作的例子,另有藏经洞出土现分别藏于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两件蓝地白点纹夹缬绢(L.S.555,MAS.932)(图20),两片残片原本可能为一件幡上悬袢的部分,蓝地上显白花的图案是将面料折叠后再用夹板法制作出来的,花纹简单,自然清新。
3. 彩绘
彩绘的自由度较大,可表现丰富的内容。
前文提到的绘像幡即是彩绘工艺的具体表现之一,有些幡身上的彩绘与绘画相通,运笔用色极为精到,与同时期的壁画、绢画如出一辙。
另有用墨或单色颜料在幡手、幡足上进行绘制图案的例子,内容为当时流行的飞鸟、花卉、祥云、卷草等主题。绘制的内容需安排在长条状的幡手或幡足上,所以通常采用竖向散点排列或“之”字形波状布局。如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云鸟花卉纹手绘幡带(MAS.884)、墨绘折枝花幡手(EO.1197)、黄地墨绘蔓草纹幡手(EO.1198)、黄地墨绘折枝幡头缘和幡足(EO.1204)、墨绘折枝云幡足(EO.1205/ter)等。
除以墨、颜料作为绘制材料外,还有以银绘制的技术,在唐代称为银泥,常用于佛幡的绘制。如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浅蓝色绢银绘幡带残片(1919.0101.0.123)、伞盖纹银泥绢幡头(Hir.24Oct04/9.1a){1}、红绫地银泥幡身(L.S.379.a-b)、银泥练鹊衔枝纹绢幡(EO.3548)、银泥迦陵频伽纹绢幡(EO.3585)、银泥花鸟祥云纹绢幡(EO.3586)等。
彩绘亦可用于麻布和棉布,如前文提到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八件棉质和麻布彩绘佛像幡头。另在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有同样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八件相同材质和面料的红地彩绘团雁纹麻幡头(MG.24643-24648;MG.26718-26719),红地布面上绘有两只首尾相接回旋飞翔的雁纹(图21)。《佛学大辞典》解释曰:“信旛,为信号之旛也。《祖庭事苑》三曰:‘今晋朝。唯白虎示信。用鸟取其飞腾轻疾也。一曰鸿雁燕乙。有去来之信是也。”[14]1410除了雁纹图案在唐代流行的政治原因之外{2},带有这种图案的佛幡在法会仪式当中是否起着特定的信号或引导的作用呢?
4. 刺绣
唐代刺绣应用广泛,针法有新的发展。除用于服饰品的装点之外,刺绣还用于绣像和绣经,以皇家为表率,规模极盛。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敕宫中彩绣释迦佛像,法琳法师描绘曰:
爰敕上宫,式摹遗景,奉造释迦绣像一帧,并菩萨、圣僧、金刚、狮子。备摛仙藻,殚诸神变。六文杂沓,五色相宣。写满月于双针,托修杨于素手。妍逾蜀锦,丽越燕缇。纷纶含七曜之光,布濩列九华之彩。日轮吐焰,蔼袁宏之丝;莲目凝辉,发秦姬之缕。隋侯百里之珠,惭斯百福;子羽千金之壁,愧彼千轮。华盖陆离,看疑涌出;云衣摇曳,望似飞来。何但思极回肠,抑亦巧穷元妙。以今岁在庚寅,月居太簇,三元启候之节,四始交泰之辰,乃降纶言,于胜光伽蓝,设斋庆像。[17]
精美如斯的刺绣佛像在敦煌藏经洞也曾发现,即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刺绣灵鹫山释迦牟尼佛说法图(MAS.1129)。整幅刺绣作品长241厘米,宽159.5厘米,描绘了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说法的场景,构图严谨,色彩丰富,是巨型刺绣作品中的杰作。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还藏有长200厘米、宽105厘米的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刺绣,针法细腻,色彩浓烈,应为7世纪初制作的代表唐朝绣像风貌的作品。敦煌藏经洞所出唯一一件刺绣佛经作品为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佛说斋法清净经》(Pelliot chinois 4500){3},长90.5厘米,宽27.8厘米,全经文字完整,是敦煌遗物中的孤例。
刺绣用于唐代佛幡的例子有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白色暗花绫地彩绣花卉纹幡头残片(L.S.590)和夹缬花卉刺绣鸟纹幡头(EO.1191/E),均以劈针绣表现。前者为白色暗花绫地上以褐、绿、米色、蓝、橙红色丝线刺绣的对称花卉纹,是适合于三角形幡头的适合纹样;后者幡头的其中一面为褐色地上彩绣展翅鸟纹,以蓝、浅蓝、墨绿、黄、白色绣线表现。日本正仓院也藏有一件刺绣用于幡头的实例:花蝶纹刺绣幡头(图22),它是以绿色罗为地,用米色、土黄、褐、土红、浅绿等不同色彩的绣线描绘出一幅牡丹盛开、蝴蝶飞舞的场景,图案对称,色彩渐变生动自然。
因刺绣费时费工,所以全以刺绣工艺制作实用佛幡的例子并不多,但在日本正仓院藏有一件孔雀纹绣片,可能是幡身的残存。绣片残长81厘米,幅宽30.7厘米,幡身在紫色绫地上绣出孔雀伫立、花树葱茏的复杂图案,主纹全以平绣针法表现,树干与枝条处运用了锁绣法,线条平整优雅,富有平和的光泽。幡身缘为黄绿相间的晕染包裹。因针法的细致,这件绣片两面均呈现相同的图案,在当时这是非常复杂的工艺。残片的尺寸和两面可观的特点,使得这件刺绣残片可能为幡身的可能性很大。
以上列举的唐代刺绣佛幡同时反映了针法的发展和进步,除了运用战国以来传统的辫绣以外,还采用了平绣、劈针绣、打籽绣等不同的针法,表现深浅不一的色彩,使得图案更加富丽,具有浓郁的装饰效果。
结 论
本文对唐代佛幡的来源、形制、图案和工艺进行了依次的梳理,试图呈现出唐代佛幡的真实面貌。从佛经、古籍、敦煌文书的文字记载,到敦煌壁画、藏经洞绢画中佛幡的形象数据,再结合现存的佛幡实物——主要是1900年出土于敦煌藏经洞、1965年出土于敦煌莫高窟诸窟以及现存日本正仓院、法隆寺、国立博物馆等机构中的佛幡。从中可以看出唐代佛幡与当时染织工艺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在文化交流密切顺畅的历史背景之下,体现出多种文化艺术融合的状况。
参考文献:
[1]梵语杂名[C]//大正藏:第54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1238.
[2]一切经音义[C]//大正藏:第54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546.
[3]翻译名义集[C]//大正藏:第54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5:1168.
[4]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C]//大正藏:第39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673.
[5]长阿含经[C]//大正藏:第1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27.
[6]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C]//大正藏:第14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406-407.
[7]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
[8]奥雷尔·斯坦因.发现藏经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3.
[9]劳合·费日.吉美博物馆藏敦煌纺织品概述[C]//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22.
[10]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81.
[11]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68.
[12]松本包夫.正仓院裂と飞鸟天平の染织[M].东京:紫红社,1984:172-174.
[13]王乐.法藏敦煌纺织品的形制[C]//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49.
[14]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409.
[15]Dorothy G.Shepherd & W.Henning,Zandaniji Identified? In Aus der Welt der islamichen Kunst.Festscherift Ernst Kuhnel, Berlin, 1959, pp.15-40.[C]//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128.
[16]庄绰.鸡肋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33.
[17]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