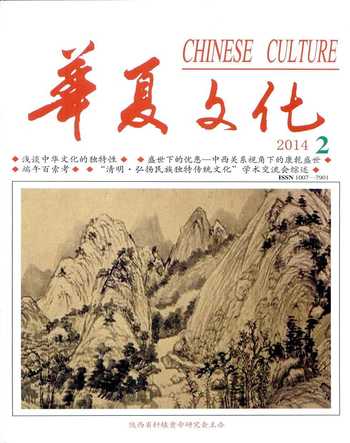庄子之“明”
程旺
“莫若以明”和“以明”在《齐物论》中共出现三次,都是作为总结性的话语,对理解整个《齐物论》的思想宗旨也有很大的关系。历代学者的解释也不尽同,但主流的诠释是把“明”解释为《老子》所谓“知常日明”(五十五章)或“照之以天”、“照之以本然之明”。如宋吕惠卿说:“明者,复命知常之谓。今儒墨之是非不离乎智识而未尝以明,故不足为是非之正。若释智回光,以明观之,则物所谓彼是者果无定体。无定体,则无非彼、无非是矣”。又说:“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相为用而已。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则以明之谓也”。“所以为是不用而寄诸万物之自功,此之谓以明。”(《庄子义》)明焦竑说:“盖行乎是非无穷之涂,而其无是无非者自若,非照之以天者不能,所谓莫若以明。”(《焦氏笔乘》)清宣颖说:“两家欲以己之是非正彼之是非而愈生是非,无益也!莫若以道原无隐,言原无隐者,同相忘于本明之地,则一总不用是非,大家俱可省事矣!”(《南华经解》)清王先谦说:“莫若以明者,言莫若即以本然之明照之。”“惟本明之照,可以应无穷。此言有彼此而是非生,非以明不能见道。”(《庄子集解》)这些解释都认为,“莫若以明”的意思是要人们抛弃一般世俗人运用智力去分别是非、彼此的那种认识活动,而要从物本来就没有确定不移的是非、彼此之分的所谓“常”去加以认识。这种认识活动(“明”)与一般世俗的认识活动(“智”)不同,是一种非“智力”的认识活动,所以叫做“照之以天”的“本然之明”。持这一见解的学者较多。
此外,另有一种比较“另类”的诠释,今人楼宇烈先生认为上面诸种诠释未能充分揭示出《齐物论》的思想主旨,他指出《齐物论》认为“可不可,然不然”,“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万物之间无所谓彼此、是非之分,而“道通为一”。因此,如果斤斤计较于彼此、是非的分别,必将陷于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无穷无尽的是非之“环”,白白浪费精神、智虑,而一无结果。《齐物论》认为,是非是越分别越混乱,它是永远辨别不清楚的。《齐物论》称那些斤斤计较于是非、彼此分别的争论为“荣华之言”、“滑疑之耀”,是为圣人所鄙弃的。要求人们“忘年忘义,振于无竞,故寓诸无竞”,超脱无穷无尽的是非之“环”,使“彼是莫得其偶”。因此,对一切问题,都回答一个“吾恶乎知之”!取消一切认识,取消一切回答。由此,楼先生提出“莫若以明”之“以”字当训为“已”,有“止”、“去”、“弃”等意义。而“莫若以明”或“以明”中之“明”字,当如下文所谓“劳神明为一”中“明”的意思,即指智慧、认识活动而言。因此,“以明”即“已明”,亦即“止明”、“去明”、“弃明”、“不用明”的意思。“莫若以明”就如同说“不如不用智慧(认识活动)”(详参楼宇烈《“莫若以明”释》,载《中国哲学》第七辑。近来劳悦强先生撰文《以明乎已明乎——释《庄子》的“明”义》,载《诸子学刊》第三辑,从“明”字的详细分疏人手,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
这两类诠释的分歧焦点并不在于“以”字的训诂,而在于对“明”理解不同,前一种将“明”理解为本然之明,而后一种将“明”理解为是非之明。由此造成分歧也就在所难免。问题是这两种诠释在《齐物论》都能找到内在的支持,似乎都能自圆其说。但两者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其实,这两种诠释都各有所得、各有所见,但又不免各有所偏。让我们回到文本中逐步进行分析。
从文本语境来看,《齐物论》对“莫若以明”和“以明”定位并不相同,不能等同视之。试比较原文:(1)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2)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3)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可以看出,“莫若以明”都是承接是非之争而来,“以明”则上接“寓诸庸”,即知常知明、照之于天之义。“则”、“故曰”和“此之谓”也有所不同,前两者主要是通过引出后文所造成的后果来说明前文,“此之谓”则是引出前文对后文的修饰说明。也就是说,“莫若以明”即会造成“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之是非无穷争论的一种后果,“以明”则是通过寓之于“本然之明”而照之于天,从而达到超越是非之争的“环中”。
从“以明”看,前述第一类解释以本然之明、照之于天,庶几近之;而楼宇烈先生所谓“不如不用智慧”,也不能不说有见于“莫若以明”之患。但前面两类诠释都未将“莫若以明”和“以明”区分开来,而是将两者作同样的解释,故不免有所偏执。其他解释如郭象注从“反覆相明”或“反覆相喻”的思想方法来解释,成玄英疏继承这种解释,都未将两者区分开来,而且郭注成疏泯同是非、取消是非而不是超越是非,似不合“以明”之旨。从前后联系的角度看,能对“莫若以明”和“以明”做出自觉区分的,应属王船山,其《庄子解》在注解第二处“莫若以明”时曾敏锐地指出:“两‘莫若以明,与后‘此之谓以明,读《庄》者多混看。”他认为应将两者分别观之。“莫若以明”就是因其成心,“浮明而以之”,自以为明,而“谓人之莫若也”;“莫若以明”即后文所谓“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实则“愈明愈隐矣”。其后所言“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这句话适可与“此之谓以明”相对照。船山明确说:“莫若以明者,间间闲闲之知,争小大于一曲之慧者也。滑疑之耀,寓庸而无是非,无成亏,此则一知之所知而为真知。而后可谓之‘以明一。从船山的分疏可以看出,对于“莫若以明”和“以明”的分歧,关键应结合前后文“是非”悖论的叙述,从“照之于天”的本然之明的“以明”来超越是非,否则若“随其成心而师之”,就会陷入“莫若”之妄,成为“劳神明为一”的“朝三暮四”之“一曲之慧”,“本然之明”由此堕入“间间闲闲之知”,而对这种“世俗之智”,庄子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黜聪明”。
综上,庄子不仅提出以“照之于天”之本然之明来超越是非、齐同物论,同时亦揭示出“莫若以明”之类的囿于成心而自以为是的偏曲之“明”;既彰显出其“齐物论”的高明,又显示出其对世俗之智的警惕。
我们认清《齐物论》之“莫若以明”的真实含义及其与“以明”之不同,方能得庄子“齐物论”之真谛。“以明”作为“照之于天”的“本然之明”,是以一种价值的态度,强调的是事物、是非的存在在价值意义上的齐一性,并不否认事物在实在意义上的差异性,以不齐齐之,才是真正达至“齐物论”;相反,从“莫若以明”出发去“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从事物、是非的实在意义上取消分别,实则是对“齐物论”做出一种事实性的判断,不可能真正做到“齐一”。由此而观,理解“齐物论”应首先区分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不同(关于这一点,可参李景林《庄子“齐物”新解》,载《孔子研究》1991年3期)。
(作者:北京市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邮编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