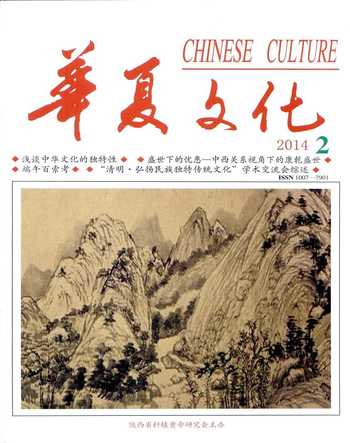唐代女性家庭角色及其地位
许若潇
要对传统女性的地位得出较实际的认识,必须立足于原始的历史情境。如果我们以现代女权主义兴起后的价值为标准,不但会和过去的历史环境脱节,更无法对女性地位变化的情况作精细入微的观察——因为若按照现代的标准,无论宋代前后,女性地位都可以用“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之类的话一言以蔽之。唐代作为中国古代较具特色的一个时期,其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更多的女性有机会突破传统的性别角色,表现更为活跃。因此,唐代妇女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段塔丽先生在《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一书中对女性地位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发表论文《唐代女性的家庭角色及其地位》,分别从“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说明。本文主要从另外的三个视角即“唐人的妒妇心态”、“唐人的妻女观”、“唐人造像活动的主力军”,与多种文献资料相结合,来研究唐代女性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
一、唐人的妒妇心态
所谓“妒妇”,牛志平先生指出:“盖专指妒忌丈夫纳妾嫖妓的妇女,这是封建制度下产生的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牛志平:《唐代妒妇述论》,载《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那么,为什么研究唐人的妒妇心态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女性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状况呢?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开放型的封建社会,在这样一种相对较为开明的社会风气下,就为唐代为人妻的心态和性格带来了相对自由解放的一面。从而造就了唐代部分“为人妻”女性雄健强悍的性格和其妒性的发达。而唐代这一妒妇心态得以存在并得到认可,本身就说明了唐代妇女的家庭地位曾一度相对提高。
关于唐人的妒妇心态,在《太平广记》中有大量记载,比如太宗朝时,“唐管国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赐二侍子,瓌拜谢,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云,饮之立死……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柳氏)饮尽而卧,然实非鸩也,……帝谓瓌日,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他日,杜正伦讥弄瓌,瓌曰,妇当怕者三,初娶之时,端居若菩萨,岂有人不怕菩萨耶。既长生男女,如养儿大虫,岂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皱,如鸠盘荼鬼,岂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妇,亦何怪焉,闻者欢喜”(见《太平广记》卷248“任瓌”条,《朝野佥载》卷3);到了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释氏,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时韦庶人颇袭武后之风,中宗渐畏之。内宴玄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日: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见《太平广记》卷249“裴谈”条)。上述材料均引自笔记小说,荒诞离奇似乎不可尽信,但其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当时唐代妒妇的社会生活和家庭心态。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唐代的妒妇多出现在上层统治阶级当中,上自皇室,下自士大夫之家,妇人妒忌之事屡见不鲜,而在平民百姓家中则很少见到,唐人的笔记小说中也鲜有记载,这应当与普通百姓所处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条件息息相关。寻常百姓家的男子,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可能都没办法保证,哪里还有多余的钱财和心思来纳妾嫖妓呢,自然唐代的下层妇女也就不存在妒忌的对象了。较为可悲的一点是妒妇原本为传统夫权社会的受害者,而她们反过来迫害的对象却是比自己——无论是在身份地位上还是人格上,都更为弱小的婢妾。这就不得不令人联想到长期以来女性地位的低下应当与其自身的某些做法和观念有着很大的关系。不过总的来说,唐代妇女妒性的发达和男子惧内之风的盛行,说明唐代妇女地位曾一度相对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几例让我们从中体会到唐代妒妇心态的同时又夹杂着些许令人忍俊不禁的意味。但仔细想想,笑话背后则蕴藏着惧内男子的无奈和自嘲。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家庭中畏惧妻子的存在。但他们无法在外面承认这一点,因为若妻子比丈夫强悍,那么身为一家之长的丈夫便无法治家,这样的话又如何做得了好官?因此:
“在唐代,表面上看起来是以夫权为主的儒家意识形态的复活,而且整个统治阶级都承认这一点,并极力推崇和发扬,但事实上,这种推崇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见得会被社会大众所接受”(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842页)。也就是说,在唐代社会,以夫权为主的儒家意识形态并不见得符合实际的生活状况,在大多数上层统治阶级的家庭中,女性比男性往往表现得更为强悍。还有要注意的一点,本文所论述的唐代妒妇心态是在唐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但是特定的社会条件与具体的嫉妒心态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行为准则有时候并不会被社会条件轻易改变,所以在此希望读者不要被这种观点所束缚,努力从旧史料中发掘新问题,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分析这个问题。
二、唐人的妻女观
陈弱水先生曾经指出:“传统妇女生活的一个主要困境是,妇女必须离开本生的家,一个在正常情况下有自然之爱的家,到另一个家庭度过她生命的绝大部分一如果她不早死的话。”换句话说,为了完成“为人妻”的义务,女子必须放弃“为人女”的角色和情感,在妇女的现实生活中,“为人女”与“为人妻”的角色不一定有重大冲突,但冲突存在的可能性并不低,特别是在婚姻初期。由于“女”和“妻”的角色之间多多少少存在些紧张对立,那么研究唐人的妻女观似乎可以作为衡量妇女地位的指标之一。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能容许已为人妻的妇女多方面保持与本家的纽带,那么婚后的妇女就容易从本家得到支持,这对她在夫家的处境应会有所帮助,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女儿的角色在家庭中有相当的重要性。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强调已婚妇女必须尽量减少与本家的联系,那么至少在青年中年时期,妇女的家庭处境只能取决于她与夫家的关系(特别是丈夫与婆婆),而没法得到其他的奥援。接下来,我们将从唐人在处理“为人女”和“为人妻”的角色冲突上所采取的立场来探讨唐代社会对于妇女多方面保持与本家的纽带所持的态度,进而得出唐代妇女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状况。那么,在唐人的眼里,他们是如何看待“为人女”和“为人妻”的角色冲突问题的呢?当这两种角色存在冲突甚至不可兼得的时候,唐人到底会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取舍呢?
中国正统的儒家礼教并不重点强调已婚妇女与本家之间的关系,对于这项关系,隋唐五代时期也没有特别强调过,更别说形成普遍化、权威化的理论系统了。但这并不是说,当时人对这个看法完全是混乱的,从时人的言辞中,可以看到某些原则性陈述背后所蕴藏的大家共同承认的观点。
首先,在判别标准方面,陈弱水先生的观点是:
“对于这个问题,唐人有两个大家共同承认的基本判别标准,即儒家经典和人情”(陈弱水:《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页)。即是说当一个人在讨论具体的规范性问题时,无论其抱持什么看法,当他要声称自己观点正确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方面他可以说他的看法合于经典,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顺乎人情。当然,最完美的办法是,经典和人情都站在自己这边。唐初著名学者颜师古在一篇讨论丧服的文章中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个事实:“原夫服纪之制,异统同归,或本恩情,或申教义,所以慎终追远,敦风厉俗”(《全唐文》卷147,颜师古《嫂叔舅服议》)。这里的恩情即是人情,其实这种伦常观也非隋唐所独有的思想。需指出的是,在唐代有关规范的论辩中,经典和人情只能是论辩的根据,并不一定是经典或人情本身所代表的立场。人情是什么?个人当然有不同的体会,而关于经典的解释,也常常是百家争鸣,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只是各取所需罢了。下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用以详细说明当时的唐人或是出于经典或是出于人情到底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为人妻”和“为人女”的角色冲突问题的?
如《新唐书·列女传》载有唐初一位叫夏侯碎金的女子的故事:“刘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长云为盐城丞,丧明。时刘已生二女矣,求与刘绝,归侍父疾。又事后母以孝称。五年父亡,毁不胜丧,被发徒跣,身负土作冢,庐其左,寒不绵、日一食者三年。诏赐物二十段、粟十石,表异门间。后其女居母丧,亦如母行,官又赐粟帛,表其门”。夏侯碎金的故事并不算特别,在任何时代,奇行异事并不少,更何况夏侯碎金的所作所为也并未偏离一般人情的范围。这个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夏侯氏的父亲死后,夏侯氏因为至孝的品德,得到朝廷的褒扬,并诏赐物二十段、粟十石。我们不知道朝廷诏书的具体内容,但可以确定的是,朝廷当时并未考虑或者说故意忽视夏侯氏对夫家和对本家的责任间可能有的冲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大胆的想象,在决定褒扬夏侯氏的官员心中,“孝”——对亲生父母的“孝”——根乎天性,符合人之常情,这就体现了人情的倾向;同时视“孝”为至高德行也是我国中古文化中很重要的态度,这对唐代官员处理夏侯氏对夫家和对本家的责任冲突时起了很大的影响,从而体现了经典的倾向。这样看来,唐代官员的做法似乎既合于经典,也顺乎人情。在经典和人情都站在了自己这一边之后,唐代的官员便依据此标准对夏侯氏进行了褒扬。由此可见,在这些官员眼里,夏侯氏对亲生父母的“孝”要高过她贞顺于夫的责任,高过她侍奉舅姑的责任(假设夏侯氏离婚时,舅姑尚有在者),即唐代妇女“为人女”角色的扮演要高过其“为人妻”角色的扮演。
此外,《白居易集》中有一个“判”从孝的观点强调妇女与本家的联系。案情是:某人之妻给在田里劳作的丈夫送饭,路途上遇到自己的父亲,父亲告诉女儿他很饿,女儿就把饭给父亲吃,于是丈夫挨了饿,一怒之下就要出妻,妻子不服,告进官里。这个案子直接触及到做女儿与做妻子的责任冲突问题,是典型的道德两难。白居易的判决是,妻子的举动本乎天性使然,丈夫的要求无理,离婚无效。白居易说:“象彼坤仪,妻惟守顺;根乎天性,父则本恩”(《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六)。从这则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承认作为妻子,应同时尽为人女和为人妻的责任,但若不幸必须要做出选择的话,只好以父亲为先,因为父亲只有一个,这种爱是根于天性的。这篇判决所透露出来的看法,表现了白居易对妇女处境给予极大的同情,与其本人对妇女命运的一贯关心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以上两则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为人女”和“为人妻”两种角色发生冲突时,许多唐人是将“为人女”的角色放在第一位的,唐代社会对于已婚妇女多方面保持其与本家的纽带也是持肯定和鼓励态度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妇女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是相对比较高的。
三、唐人造像活动的主力军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张迎晓先生已经做了较为深入和细致的分析,并据此撰写文章《唐代妇女佛教造像活动研究》,指出:“造像活动作为唐代女性所参与诸种社会活动中的一项,其能有机会参与其中,便是女性对自己性别角色的一种突破,是扩展自己生存空间所作出的一种努力”。那么,她们参与各种组织形式的造像活动折射出她们在家庭中怎样一种生活状态?又体现出她们在家庭中怎么的一种经济地位呢?
我们知道,佛教造像是一种需要一定财力支持才可以开展的宗教活动。因此,唐代贵族宫廷女子参加造像活动颇多,她们富裕的经济地位和雄厚的财力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后盾。但并不表示,普通家庭的女性很少参与,相反,根据张迎晓先生对造像参与者身份的统计分析,普通家庭的女性才是造像活动的主力军,她们或单独或与拥有共同心愿的女性——通过造像表现对父母公婆的孝顺、对家人健康平安的祈福、对自身尤其是有孕期间的自我保护,相合作来参与这项活动。那么,她们之所以有如此经济实力来完成这项需要相当经济消耗的活动与其在家庭中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密不可分。如大中年间傅二娘在岳林寺造塔所留下的铭刻中对各捐助人的舍钱数目有明确记载:“傅五百文,马六娘一千文……傅二娘又舍二百五十千文、……舍二百文,大佛殿又四千丈人斋堂……”(《唐岳林寺塔名》,见《两浙金石志》卷三)。从女性在造像活动中所捐钱财数目可以看出,唐代女性有一定的私有钱财来任其自由支配。可见,唐代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是相当高的。关于唐代妇女财产权问题,已有不少学者探讨过,总体来讲她们财产主要来源于嫁妆和对家庭财产的继承。段塔丽先生在《唐代女性的家庭地位》一文中指出,特别是出嫁女,其财产不仅包括嫁妆,同时若遇父母身亡,家中无子嗣继立门户,即所谓“户绝”情况下,其可继承除父母治丧所需费用以外的全部遗产。
可以看出,不管是室女的财产继承权还是已婚妇女的财产支配权,其所拥有的数额都是相当可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可见唐代女性的家庭地位应是相当高的。
四、结语
纵观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自两汉以来,“男尊女卑”便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意识,儒家所倡导的“三从四德”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样也被封建时代的妇女视为自身完美人,格的体现。然而在唐代,由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以及社会风气的高度开放,促使广大妇女不断向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相抗争。本文主要关注于唐人“为人女”和“为人妻”的角色和地位,通过对“唐人的妒妇心态”、“唐人的妻女观”、以及“唐人造像活动的主力军”三个方面的论述,来窥视唐代女性在家庭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基地班本科,邮编710069)